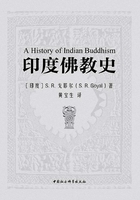
四 出现新的综合
新的综合的需求
非吠陀意识形态的影响给吠陀社会提出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甚至威胁到它依靠的基础。非吠陀意识形态一方面在雅利安人面前提出男女乱交  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诱导他们接受出世的或沙门的观点。其中后者成为佛教和其他这类意识形态的源头。这似乎显得奇怪,却又是事实,思想家们响应这两种与楼陀罗-湿婆崇拜相联系的、显得相当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两种观点的奇怪对照更多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的。因为甚至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的怛特罗宗教被发现同时与出世法和最粗俗的性仪式相联系。在卡朱罗霍和其他地方的湿婆寺庙中发现的爱欲形象是湿婆教中这种结合的最好证明。往世书中有许多故事,讲述湿婆常常裸体出外乞食,吸引仙人们的妻子与他相爱[130]。在吠陀时代的许多部落中,有一种性宽松的气氛,这是有案可查的。虽然这些部落的身份常常不能确定,但可以想象他们与上面讨论的楼陀罗和林伽崇拜有关。他们的影响在吠陀社会引起混乱。《梨俱吠陀》第十卷中阎摩和阎蜜的对话记录下阎摩的精神焦虑。他的妹妹阎蜜想要与他发生乱伦关系,借口他们受到时间和传统的认可,而阎摩感到这种关系违背伐楼那的法规。这里,我们可以回想印度河流域文明中流行兄妹婚姻[131]。很可能阎蜜的借口来自这个事实:在印度河流域的一些部落中,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阎摩的观点是依据吠陀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这是一对青年男女生活在两种道德观的边界线上的绝好例子。《摩诃婆罗多》记载有好几个具有吠陀时代特征的故事,讲述吠陀雅利安人必须保护他们的社会,避免受到那些相信男女乱交的人的影响。按照一个故事,长暗仙人
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诱导他们接受出世的或沙门的观点。其中后者成为佛教和其他这类意识形态的源头。这似乎显得奇怪,却又是事实,思想家们响应这两种与楼陀罗-湿婆崇拜相联系的、显得相当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两种观点的奇怪对照更多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的。因为甚至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的怛特罗宗教被发现同时与出世法和最粗俗的性仪式相联系。在卡朱罗霍和其他地方的湿婆寺庙中发现的爱欲形象是湿婆教中这种结合的最好证明。往世书中有许多故事,讲述湿婆常常裸体出外乞食,吸引仙人们的妻子与他相爱[130]。在吠陀时代的许多部落中,有一种性宽松的气氛,这是有案可查的。虽然这些部落的身份常常不能确定,但可以想象他们与上面讨论的楼陀罗和林伽崇拜有关。他们的影响在吠陀社会引起混乱。《梨俱吠陀》第十卷中阎摩和阎蜜的对话记录下阎摩的精神焦虑。他的妹妹阎蜜想要与他发生乱伦关系,借口他们受到时间和传统的认可,而阎摩感到这种关系违背伐楼那的法规。这里,我们可以回想印度河流域文明中流行兄妹婚姻[131]。很可能阎蜜的借口来自这个事实:在印度河流域的一些部落中,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阎摩的观点是依据吠陀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这是一对青年男女生活在两种道德观的边界线上的绝好例子。《摩诃婆罗多》记载有好几个具有吠陀时代特征的故事,讲述吠陀雅利安人必须保护他们的社会,避免受到那些相信男女乱交的人的影响。按照一个故事,长暗仙人 开始追随性自由的生活(godharma,“牛法”),而其他仙人因为他的这种罪孽,而将他驱逐出净修林[132]。在这同一部史诗中,有一处,般度提到有这样的时代,妇女不受缚于一个丈夫,与她们喜欢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133]。然后,乌达罗迦之子白幢引进婚姻制度。从吠陀雅利安人的道德观念中,不可能推断出这类男女乱交的性关系,同时有迹象表明许多非雅利安部落依随这种习惯,因此可以合理地证明男女乱交不是吠陀社会的特点,或者宁可说那是吠陀社会面对的一种危险。
开始追随性自由的生活(godharma,“牛法”),而其他仙人因为他的这种罪孽,而将他驱逐出净修林[132]。在这同一部史诗中,有一处,般度提到有这样的时代,妇女不受缚于一个丈夫,与她们喜欢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133]。然后,乌达罗迦之子白幢引进婚姻制度。从吠陀雅利安人的道德观念中,不可能推断出这类男女乱交的性关系,同时有迹象表明许多非雅利安部落依随这种习惯,因此可以合理地证明男女乱交不是吠陀社会的特点,或者宁可说那是吠陀社会面对的一种危险。
在雅利安人中,家庭生活  的重要性是至高的。他们的宗教是入世的,家庭的圆满依靠男性后代的繁衍。因此,一些雅利安人受到牟尼的出世理想吸引时,成为一个是否应该斥责弃世哲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的古代文献充满对牟尼、耶底和弃世者的赞扬;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章节段落严厉斥责他们。这种矛盾的态度见于《梨俱吠陀》自身,一方面将牟尼视为吠陀传统的异己者;另一方面又视为因陀罗的朋友。同样,对于耶底,既视为婆利古族的朋友,又视为因陀罗的敌人。但是,直到中期吠陀时代结束,主要的倾向是强烈斥责所有这些群体。《摩诃婆罗多》谴责弃世者是“罪人”
的重要性是至高的。他们的宗教是入世的,家庭的圆满依靠男性后代的繁衍。因此,一些雅利安人受到牟尼的出世理想吸引时,成为一个是否应该斥责弃世哲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的古代文献充满对牟尼、耶底和弃世者的赞扬;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章节段落严厉斥责他们。这种矛盾的态度见于《梨俱吠陀》自身,一方面将牟尼视为吠陀传统的异己者;另一方面又视为因陀罗的朋友。同样,对于耶底,既视为婆利古族的朋友,又视为因陀罗的敌人。但是,直到中期吠陀时代结束,主要的倾向是强烈斥责所有这些群体。《摩诃婆罗多》谴责弃世者是“罪人” [134]。按照一个故事[135],悔罪的遮罗特迦鲁贪求苦行的力量,而他的祖先说服他结婚,因为不结婚就不能生儿子,也就没有儿子举行祭祀让祖先的灵魂获得解脱。同样,说到古尼伽尔伽的女儿一生实施苦行,仍然不能升入天国。唯有在她抛弃处女性,嫁给舍楞伽伐那后,才得以升入天国[136]。在有个章节中,因陀罗这位入世宗教意识形态的大神向一些想要采取隐居生活的婆罗门儿子解释弃世无益[137]。在坚战表示想要过弃世生活时,他的弟弟们和德罗波蒂成功地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强调弃世无益,而必须过家庭生活。所有这些例子表明那些雅利安人的困境,他们受到弃世生活的吸引,同时又发现难以抛弃将这个世界视为值得向往的传统。
[134]。按照一个故事[135],悔罪的遮罗特迦鲁贪求苦行的力量,而他的祖先说服他结婚,因为不结婚就不能生儿子,也就没有儿子举行祭祀让祖先的灵魂获得解脱。同样,说到古尼伽尔伽的女儿一生实施苦行,仍然不能升入天国。唯有在她抛弃处女性,嫁给舍楞伽伐那后,才得以升入天国[136]。在有个章节中,因陀罗这位入世宗教意识形态的大神向一些想要采取隐居生活的婆罗门儿子解释弃世无益[137]。在坚战表示想要过弃世生活时,他的弟弟们和德罗波蒂成功地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强调弃世无益,而必须过家庭生活。所有这些例子表明那些雅利安人的困境,他们受到弃世生活的吸引,同时又发现难以抛弃将这个世界视为值得向往的传统。
奥义书作为吠陀主义和沙门主义之间的纽带
奥义书时代的思想家试图综合吠陀的入世理想和沙门思潮的出世理想。奥义书一方面体现吠陀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另一方面体现向沙门苦行主义的“半转折”①。奥义书的学说主要代表中期吠陀宗教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当我们突然在多处遇见相信生死轮回和强调苦行主义的基本价值,也就很明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沙门的影响②。例如,在《歌者奥义书》第二章中提到正法的三个部分:祭祀、诵习吠陀和布施,分别等同于苦行、梵行者和向老师供奉礼物。其中前两者令人想起沙门主义。在第四章中,说到一个知道梵的人不再关心世俗事物,人类生活充满欲望、罪孽和病痛,因此死亡并不更坏。进而,提到一种神的道路(Devapatha)或梵的道路(Brahmapatha),追随这种道路的人不再返回人类旋涡中。按照G.C.般代,这明显是提到再生学说③,在这里与罪孽和无知相联系。在第七章中,那罗陀宣称希望通过知道自我而摆脱痛苦。这里,“希望知道梵” 与生活的烦恼相联系。在《大森林奥义书》中,耶若伏吉耶在准备脱离家居生活时,宣称追求永生
与生活的烦恼相联系。在《大森林奥义书》中,耶若伏吉耶在准备脱离家居生活时,宣称追求永生  不同于追求财富(vitta)。精神生活最终导致一切二重性结束。精神与身体一起死亡,仅仅“伟大的存在”
不同于追求财富(vitta)。精神生活最终导致一切二重性结束。精神与身体一起死亡,仅仅“伟大的存在” 保持。这显然预示唯识论佛教徒
保持。这显然预示唯识论佛教徒  所理解的涅槃学说④。
所理解的涅槃学说④。
Pande,G.C., ,第4页。
,第4页。
关于沙门主义  的古老,参阅RHAI,1,第95页以下。也参阅Jain,Bhagchandra,The Antiquity of
的古老,参阅RHAI,1,第95页以下。也参阅Jain,Bhagchandra,The Antiquity of  Cult,World Buddhism,No.1,第3—6页。
Cult,World Buddhism,No.1,第3—6页。
Pande,G.C., ,第7页。
,第7页。
Pande,G.C., ,第10页。
,第10页。
最有意义的沙门学说是与业报(karman)规律一致的再生学说或生死轮回  学说。这种学说的起源及其迅速流行和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是印度思想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查特吉(S.K.Chatterji)将生死轮回观念追溯到“原始南方土著居民”[138]。而阿伯代(V.M.Apte)质疑这种理论,即雅利安人的生死轮回学说源自“土著人的泛灵论”[139]。业报学说意谓一个人做出的任何行为会留下某种潜能,具有决定他在将来按照这种行为的好坏获得快乐或痛苦的力量。一旦它与再生学说结合,它意谓他们在今生不能获得这种行为的果报,必定会在下一生获得。所做的行为会消失,而它的道德效力储存在潜能中,在将来获得果报[140]。一些学者在梵书的死后学思考中看到与业报一致的再生学说的起源。这已经被正确地受到质疑。在《梨俱吠陀》中,绝对没有生死轮回的踪迹。在《梨俱吠陀》中,注意的焦点是世俗生活,死亡者的世界被认为是幽暗朦胧的。《梨俱吠陀》(10.163)暗示在死后,一个人可能消失在水中或植物中,意识与宇宙合一,并非获得再生。一种道德规律
学说。这种学说的起源及其迅速流行和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是印度思想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查特吉(S.K.Chatterji)将生死轮回观念追溯到“原始南方土著居民”[138]。而阿伯代(V.M.Apte)质疑这种理论,即雅利安人的生死轮回学说源自“土著人的泛灵论”[139]。业报学说意谓一个人做出的任何行为会留下某种潜能,具有决定他在将来按照这种行为的好坏获得快乐或痛苦的力量。一旦它与再生学说结合,它意谓他们在今生不能获得这种行为的果报,必定会在下一生获得。所做的行为会消失,而它的道德效力储存在潜能中,在将来获得果报[140]。一些学者在梵书的死后学思考中看到与业报一致的再生学说的起源。这已经被正确地受到质疑。在《梨俱吠陀》中,绝对没有生死轮回的踪迹。在《梨俱吠陀》中,注意的焦点是世俗生活,死亡者的世界被认为是幽暗朦胧的。《梨俱吠陀》(10.163)暗示在死后,一个人可能消失在水中或植物中,意识与宇宙合一,并非获得再生。一种道德规律  在宇宙中发挥作用得到确认,而它被认为依靠诸神的意志实施,人的意志承认它和寻求跟随它。至于梵书,确实,正如基思(Keith)已经指出[141],其中发现有在死后世界中“再死”
在宇宙中发挥作用得到确认,而它被认为依靠诸神的意志实施,人的意志承认它和寻求跟随它。至于梵书,确实,正如基思(Keith)已经指出[141],其中发现有在死后世界中“再死” 的观念。但是,这里的“再死”似乎是指第二次出生在天国。在《爱多雷耶梵书》(7.13.6)中,一个人在他的儿子身体中复活。正如恰格罗伐尔提(Chakravarti)已经指出,梵书对待死后生活的通常态度不表现为相信生死轮回学说。在梵书中,祭祀者在死后再生在天神中间,享受一种按照世俗生活方式想象的不朽存在[142]。另一方面,正如G.C.般代所指出,生死轮回学说以相信一种不朽的意识本原(
的观念。但是,这里的“再死”似乎是指第二次出生在天国。在《爱多雷耶梵书》(7.13.6)中,一个人在他的儿子身体中复活。正如恰格罗伐尔提(Chakravarti)已经指出,梵书对待死后生活的通常态度不表现为相信生死轮回学说。在梵书中,祭祀者在死后再生在天神中间,享受一种按照世俗生活方式想象的不朽存在[142]。另一方面,正如G.C.般代所指出,生死轮回学说以相信一种不朽的意识本原( ,“自我”)为前提,确认业报(karman)规律和一种追求解脱(mukti)的强烈渴望。业报和再生学说已被称为原始观念,或原始的吠陀观念,或吠陀思想派别中逐渐发展的观念。然而,按照G.C.般代,这些观念似乎表明以牟尼和沙门为代表的前存在的非吠陀意识形态源泉已经流入吠陀思想。到了后期吠陀时代,吠陀思想家已经准备接受这些观念,这样,我们在奥义书中突然发现提到它们。尽管如此,在提到它们时,这些观念对于他们显然是新鲜的[143]。例如,在《大森林奥义书》中,在遮那迦王宫的集会中,阿尔多跋伽询问耶若伏吉耶:人死后会发生什么?耶若伏吉耶将阿尔多跋伽拉到一旁,回答他这个问题,教导他业报学说。这暗示在那时,与业报学说一致的再生学说在婆罗门圈内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甚至秘密的学说。另一方面,正如巴沙姆(Basham)所指出,在巴利语经文中,生死轮回获得认可。“除了唯物主义派别完全否认任何形式的死后再生,无论对于生死轮回的事实,或对于摆脱生死轮回而获得解脱的追求,都不存在不同观点。一个派别与另一个派别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再生过程的机制和个人摆脱生死轮回后获得的最终平静状态的性质。就我们的知识而言,我们在佛教经文中没有发现哪里有一位导师试图说服听众相信生死轮回的事实。这肯定暗示在佛陀时代,这个学说在印度的所有文明地区几乎已被普遍接受。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怎么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清楚。而暗示它源自土著的非雅利安人的信仰,这至多是个猜想,文本证据本身更暗示它起始于上层阶级的小圈子内,无论是刹帝利或婆罗门。”[144]
,“自我”)为前提,确认业报(karman)规律和一种追求解脱(mukti)的强烈渴望。业报和再生学说已被称为原始观念,或原始的吠陀观念,或吠陀思想派别中逐渐发展的观念。然而,按照G.C.般代,这些观念似乎表明以牟尼和沙门为代表的前存在的非吠陀意识形态源泉已经流入吠陀思想。到了后期吠陀时代,吠陀思想家已经准备接受这些观念,这样,我们在奥义书中突然发现提到它们。尽管如此,在提到它们时,这些观念对于他们显然是新鲜的[143]。例如,在《大森林奥义书》中,在遮那迦王宫的集会中,阿尔多跋伽询问耶若伏吉耶:人死后会发生什么?耶若伏吉耶将阿尔多跋伽拉到一旁,回答他这个问题,教导他业报学说。这暗示在那时,与业报学说一致的再生学说在婆罗门圈内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甚至秘密的学说。另一方面,正如巴沙姆(Basham)所指出,在巴利语经文中,生死轮回获得认可。“除了唯物主义派别完全否认任何形式的死后再生,无论对于生死轮回的事实,或对于摆脱生死轮回而获得解脱的追求,都不存在不同观点。一个派别与另一个派别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再生过程的机制和个人摆脱生死轮回后获得的最终平静状态的性质。就我们的知识而言,我们在佛教经文中没有发现哪里有一位导师试图说服听众相信生死轮回的事实。这肯定暗示在佛陀时代,这个学说在印度的所有文明地区几乎已被普遍接受。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怎么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清楚。而暗示它源自土著的非雅利安人的信仰,这至多是个猜想,文本证据本身更暗示它起始于上层阶级的小圈子内,无论是刹帝利或婆罗门。”[144]
无论如何,接受生死轮回和业报学说在吠陀社会引起一次真正的革命。早期吠陀宗教是肯定生活的,而后期吠陀的态度是更多地否定生活的或出世的。这种变化的出现主要通过生活概念的变化,其中含有生死轮回和业报学说。如果一种行为的道德性质对将来起到唯一的和不可变更的决定作用,那么,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祭司和祭祀就不再必不可少。甚至诸神也受缚于这个规律,变成只是出生在某个位置的灵魂。耶若伏吉耶解释这种业报学说,说“一个人怎样行动,怎样指引自己,他就变成那样。因善业而成为善人,因恶业而成为恶人。欲望是生死轮回之源。如果没有欲望,甚至业也不能束缚他”。只是一种典型的佛教学说,也得到《薄伽梵歌》中“无欲望的” 行动学说的支持。
行动学说的支持。
从耶若伏吉耶与遮那迦的谈话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很了解牟尼和沙门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他在解释什么导致解脱时,说到一种熟睡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中,旃陀罗不知道旃陀罗,包格沙不知道包格沙,沙门不知道沙门,苦行者不知道苦行者。他在别处说到牟尼和出家人全都通过“无欲望” 追求灵魂摆脱生死轮回。婆罗门通过诵习吠陀、祭祀和慷慨布施追求它。牟尼和出家人通过苦行和禁食。对牟尼和沙门以及再生和业报的这些描述表明耶若伏吉耶熟悉沙门学说和受到他们影响,虽然他与有神论的关联明显不同于他接受的沙门主义哲学[145]。
追求灵魂摆脱生死轮回。婆罗门通过诵习吠陀、祭祀和慷慨布施追求它。牟尼和出家人通过苦行和禁食。对牟尼和沙门以及再生和业报的这些描述表明耶若伏吉耶熟悉沙门学说和受到他们影响,虽然他与有神论的关联明显不同于他接受的沙门主义哲学[145]。
熟悉生死轮回学说在诗体奥义书中变得更为明显。在《伽陀奥义书》第二章中直接提到牟尼,描述人受束缚和解脱的过程。“一旦摒弃心中的所有欲望,凡人就达到永恒,就在这里获得梵。”按照G.C.般代,这暗示生命解脱和阿罗汉性的可能性。
沙门主义的最大影响见于《剃发奥义书》。这个书名就暗示沙门的影响。它贬斥祭祀是“破船”,宣称那些追随仪式主义道路和忙于慈善活动的人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这部奥义书也提到“比丘行” ,也提到耶底,他们摒弃内在罪恶,遵奉真理、苦行、梵行和正知
,也提到耶底,他们摒弃内在罪恶,遵奉真理、苦行、梵行和正知  。《自在奥义书》讨论吠陀传统的行动、仪式主义和道德与沙门的弃世哲学之间的矛盾。如同《薄伽梵歌》,它得出结论:只要怀着献身精神行动,感到神的遍在,行动就不会束缚行动者(nakarma lipyate nare)。确实,不应该抛弃行动,一个人应该始终从事行动。
。《自在奥义书》讨论吠陀传统的行动、仪式主义和道德与沙门的弃世哲学之间的矛盾。如同《薄伽梵歌》,它得出结论:只要怀着献身精神行动,感到神的遍在,行动就不会束缚行动者(nakarma lipyate nare)。确实,不应该抛弃行动,一个人应该始终从事行动。
然而,应该注意到,虽然奥义书一般了解与一个人的行动一致
的再生学说和弃世,但不能认为这些文本在整体上倡导出世的意识
形态。按照G.C.般代,“在奥义书中流行的学说是展现神圣的存
在和能力。早期的许多天神无疑融入一个与自我同一的伟大存在,
而结果是一种唯灵主义的宇宙观。……其中,每个限定的对象只是
无限的梵的有限展现。创造和展现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
的。确实,在另一方面也能引述偶然提到否定二重性或断定名称和
形式不真实的说法。但是……现实主义的解释似乎是正确的解
释”[146]。这样,似乎应该认为虽然奥义书提供日益增长的沙门意识
形态的证据,而它们仍然主要强调肯定的、行动的和健壮的生活
观,寻求在我们所见事物背后更高的真实[147]。
生活阶段作为一种新的综合设计
这样,在奥义书时代,苦行倾向对吠陀社会的影响不一定意味弃世生活阶段早已制度化。个人生活四个阶段的设计被认为是古代印度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词在文字上意味“隐居地”或“栖息地”,而在技术上意味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四个生活阶段的设计是社会-宗教性的。它确认四个阶段,即梵行期(
一词在文字上意味“隐居地”或“栖息地”,而在技术上意味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四个生活阶段的设计是社会-宗教性的。它确认四个阶段,即梵行期( ,“学习吠陀的学生阶段”)、家居期(
,“学习吠陀的学生阶段”)、家居期( ,家主的阶段)、林居期(
,家主的阶段)、林居期( ,隐居林中的阶段)和弃世期(
,隐居林中的阶段)和弃世期( ,摒弃一切世俗考虑的阶段)[148]。一些早期学者包括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比勒
,摒弃一切世俗考虑的阶段)[148]。一些早期学者包括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比勒  和雅各比(Jacobi)相信苦行主义产生于吠陀社会本身。雅各比已经暗示婆罗门苦行者提供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复制的共同原型。为支持这种观点,也指出耆那教和佛教为苦行者规定的戒律与《乔答摩法经》和《包达延那法经》中所见的那些戒律相似。但是,S.K.达多和G.C.般代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弱点[149]。般代指出,首先,上述相似性主要属于一般性质的戒律。例如,弃世者的头四种誓愿可以说是属于苦行主义的一般常识,换言之,如果存在借用,与其说是这些特殊规定,不如说是苦行的理想。其次,“阶段”
和雅各比(Jacobi)相信苦行主义产生于吠陀社会本身。雅各比已经暗示婆罗门苦行者提供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复制的共同原型。为支持这种观点,也指出耆那教和佛教为苦行者规定的戒律与《乔答摩法经》和《包达延那法经》中所见的那些戒律相似。但是,S.K.达多和G.C.般代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弱点[149]。般代指出,首先,上述相似性主要属于一般性质的戒律。例如,弃世者的头四种誓愿可以说是属于苦行主义的一般常识,换言之,如果存在借用,与其说是这些特殊规定,不如说是苦行的理想。其次,“阶段” 一词没有出现在本集和梵书中。按照迦奈(Kane),在吠陀文献中,也没有与“林居”
一词没有出现在本集和梵书中。按照迦奈(Kane),在吠陀文献中,也没有与“林居”  相应的表达[150]。
相应的表达[150]。 这个词并不非常古老。它最早见于《白骡奥义书》(6.21)中使用的
这个词并不非常古老。它最早见于《白骡奥义书》(6.21)中使用的 
 一词。但按照般代,这种用法似乎表示行乞生活仍在四阶段范围之外[151]。按照迦奈,或许最早提到四阶段的是《爱多雷耶梵书》(33.1),其中说到“污垢有什么用?鹿皮有什么用?苦行有什么用?婆罗门啊,盼望一个儿子吧!他是一个受到高度赞美的世界”。但是,在这里发现提到四阶段,显得十分冒险。迦奈承认甚至在《歌者奥义书》(2.23.1)中更为清晰的表述中,仍然缺乏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的明确区别。以上讨论的一些奥义书中的表述无疑表明熟悉行乞生活,尽管认为它们表示四阶段的设计是值得怀疑的。至于那些法经
一词。但按照般代,这种用法似乎表示行乞生活仍在四阶段范围之外[151]。按照迦奈,或许最早提到四阶段的是《爱多雷耶梵书》(33.1),其中说到“污垢有什么用?鹿皮有什么用?苦行有什么用?婆罗门啊,盼望一个儿子吧!他是一个受到高度赞美的世界”。但是,在这里发现提到四阶段,显得十分冒险。迦奈承认甚至在《歌者奥义书》(2.23.1)中更为清晰的表述中,仍然缺乏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的明确区别。以上讨论的一些奥义书中的表述无疑表明熟悉行乞生活,尽管认为它们表示四阶段的设计是值得怀疑的。至于那些法经  ,它们的年代不确定,甚至它们之中被设想为最古老的《乔答摩法经》和《包达延那法经》就目前的形式而言,也是一种汇编性质的著作。按照霍普金斯(Hopkins),这些法经不可能早于公元前七世纪和晚于公元前二世纪。因此,似乎不可能安全地设想在这些著作中接受的理论前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婆罗门圈内已经完全确立的教条。而在公元前六世纪,耆那教已经是一个古老而受尊敬的派别。也应该记住婆罗门社会本身是与第四生活阶段对立的。整个祭祀传统以及它的物质价值是反苦行主义的。上面引用的《爱多雷耶梵书》中的段落,正是对吠陀社会怀抱的价值的出色描述。确实,在一些早期奥义书中,可以见到向苦行理想的“半转折”。但是,甚至在这些奥义书中,仍然主要强调肯定的、行动的和健壮的生活观[152]。“这也许不无意义,即最强烈谴责祭祀和倡导‘第四生活阶段’的奥义书是《剃发奥义书》。”[153]事实是四阶段的理论在法经时代尚未成为最终确立的理论。依据他们在这方面使用的名称不规则,这一点是明显的。《阿波斯坦跋法经》使用
,它们的年代不确定,甚至它们之中被设想为最古老的《乔答摩法经》和《包达延那法经》就目前的形式而言,也是一种汇编性质的著作。按照霍普金斯(Hopkins),这些法经不可能早于公元前七世纪和晚于公元前二世纪。因此,似乎不可能安全地设想在这些著作中接受的理论前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婆罗门圈内已经完全确立的教条。而在公元前六世纪,耆那教已经是一个古老而受尊敬的派别。也应该记住婆罗门社会本身是与第四生活阶段对立的。整个祭祀传统以及它的物质价值是反苦行主义的。上面引用的《爱多雷耶梵书》中的段落,正是对吠陀社会怀抱的价值的出色描述。确实,在一些早期奥义书中,可以见到向苦行理想的“半转折”。但是,甚至在这些奥义书中,仍然主要强调肯定的、行动的和健壮的生活观[152]。“这也许不无意义,即最强烈谴责祭祀和倡导‘第四生活阶段’的奥义书是《剃发奥义书》。”[153]事实是四阶段的理论在法经时代尚未成为最终确立的理论。依据他们在这方面使用的名称不规则,这一点是明显的。《阿波斯坦跋法经》使用 (“家居者”)、
(“家居者”)、 (“老师的家”)、mauna(“沉默者”)和
(“老师的家”)、mauna(“沉默者”)和 (“林居者”)。《乔答摩法经》使用
(“林居者”)。《乔答摩法经》使用 (“梵行者”)、
(“梵行者”)、 (“家居者”)、
(“家居者”)、 (“比丘”)和
(“比丘”)和 (“隐居者”)。《婆私湿吒法经》和《包达延那法经》使用
(“隐居者”)。《婆私湿吒法经》和《包达延那法经》使用 (“梵行者”)、
(“梵行者”)、 (“家居者”)、
(“家居者”)、 (“林居者”)和
(“林居者”)和 (“出家者”)[154]。按照般代,在吠陀传统中最初确认的是前两者。后来,可能随着沉思
(“出家者”)[154]。按照般代,在吠陀传统中最初确认的是前两者。后来,可能随着沉思  时代的开启,隐居林中的实践流行,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一种真正的制度[155]。在严格的吠陀圈外,始终有游荡的苦行者群体,有时称为牟尼。到了奥义书时期结束时,婆罗门的价值经历了变化,吠陀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倾向接受生死轮回学说遗传的悲观主义世界观,第四阶段即弃世期被确立为制度。换言之,苦行理想似乎已经传给耆那教和佛教,而不源自婆罗门,而是源自前已存在的牟尼-沙门派别。进而,也应该承认吠陀社会以弃世生活阶段的形式接受的苦行理想发生在奥义书之后的时期,虽然甚至在奥义书自身中已经认同苦行的倾向。
时代的开启,隐居林中的实践流行,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一种真正的制度[155]。在严格的吠陀圈外,始终有游荡的苦行者群体,有时称为牟尼。到了奥义书时期结束时,婆罗门的价值经历了变化,吠陀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倾向接受生死轮回学说遗传的悲观主义世界观,第四阶段即弃世期被确立为制度。换言之,苦行理想似乎已经传给耆那教和佛教,而不源自婆罗门,而是源自前已存在的牟尼-沙门派别。进而,也应该承认吠陀社会以弃世生活阶段的形式接受的苦行理想发生在奥义书之后的时期,虽然甚至在奥义书自身中已经认同苦行的倾向。
人生目的和种姓制度作为新的综合设计
各种雅利安人(属于吠陀和非吠陀两者)和非雅利安的(属于印度河流域和非印度河流域两者)文化潮流的互相接触不仅产生它们的混合,也产生它们的复合——不仅是各种意识形态的结合,也是某种全新的事物。这不仅出现作为个人生活理想格式的生活阶段理论,也导致产生作为人类生活目标的人生目的  [156]理论和作为社会组织理想格式的瓦尔那
[156]理论和作为社会组织理想格式的瓦尔那  [157]体系。所有这三种制度旨在达到入世和出世两种对立意识形态主张的综合。这种综合,尤其是生活阶段和人生目的学说的出现,更多发生在后期吠陀或奥义书时代,或者更晚。但是,后来转化为种姓体系的瓦尔那体系,在中期吠陀时代已经开始得到巩固。
[157]体系。所有这三种制度旨在达到入世和出世两种对立意识形态主张的综合。这种综合,尤其是生活阶段和人生目的学说的出现,更多发生在后期吠陀或奥义书时代,或者更晚。但是,后来转化为种姓体系的瓦尔那体系,在中期吠陀时代已经开始得到巩固。
雅利安和非雅利安种族的文化融合的主要障碍不仅在于他们的语言、精神和文化构成不同,也在于他们的体貌不同。在现代,日本人发现由于他们的种族体貌,比欧洲人更难与美国人混合。黑皮肤的非雅利安人的威胁是现代美国人意识中的所谓“黄祸”的翻版。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生活在一起,各自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仍然长期觉察不到他们之间的杂交。在其他国家,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关系通常变成奴隶制形式。而在印度,在调整关系中,采取瓦尔那体系(它逐步转化为种姓体系)的形式,使两者成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这样,瓦尔那体系成为一种调整形式,部落涌入造成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由此得以解决。
但是,瓦尔那体系的出现并不能完全解决“边缘人”的问题。因为瓦尔那体系从一开始,至少在实践中,就依据出身,而不是依据一个人的品质和性向。因此,它只是产生人的附加类别。人们发现很难越过一个人世袭的群体界限。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吠陀时代,一个人的种姓取决于职业,而不是出身,这是不正确的。众友仙人是刹帝利,想要获得婆罗门地位,而尽管他的伟大精神成就,受到他的对手们钦佩,但仍然不能实现他的雄心。《爱多雷耶梵书》的作者摩希陀娑·爱多雷耶是一个首陀罗妇女伊多拉的儿子[158]。他的父亲也有与其他高级种姓妻子生育的儿子,然而鄙视他,不让他使用自己的姓氏。在奥义书时代,一个首陀罗遮那悉如底通过馈赠大量礼物,说服雷格瓦传授给他真正的知识,但他并不能取得高于首陀罗的地位。同样,在《摩诃婆罗多》中,迦尔纳作为车夫的儿子,即使难敌让他担任盎伽国国王,他也没有被接受为刹帝利。德罗波蒂借口他是低级种姓,而拒绝他参加她的选婿大典。在《罗摩衍那》中,一个首陀罗商菩迦企图成为苦行者,而被这部史诗的主人公罗摩冷酷地杀死。像迦婆舍·埃卢舍、摩希陀娑·爱多雷耶、众友仙人、迦尔纳、遮那悉如底和商菩迦这些人的烦恼不难想象。在这方面,回想在这同样的社会中,诸如持斧罗摩和德罗纳,他们一生从事刹帝利武士的活动,但所有人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是婆罗门,是有趣的。然而,设想只有婆罗门对种姓体系存在这样的矛盾态度,是不正确的。刹帝利也纠缠于种姓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佛陀和大雄一方面斥责四个等级[159]的种姓体系,另一方面从不疲倦地主张刹帝利的最高地位。这种心理活动,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可以阐明印度古代宗教史的许多社会方面的问题,包括佛教的社会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