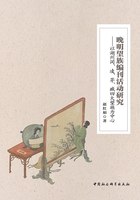
第一节 茅氏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
明中叶前湖州市镇经济还是较为落后的。虽然北宋景德间湖州一地即有施渚、大钱、东林、乌墩、东迁、巡莫、新市、梅溪、水口等十六镇,但当时这些镇的规模很小,仅设监镇,管理火禁和酒税。其中巡莫,即琏市,又名练市,在湖州城东八十里,茅氏世居之地花林即隶属该镇,不少茅氏族人定居镇上。嘉靖以来,该镇经济繁荣,民风豪奢,“惟以资财气力相雄长”[1]。湖州菱湖成化时尚称“市”[2],万历时却已成为“万家烟火”、丝业甲一邑的“东南巨都”[3]。湖州双林从元代到明初尚为“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的“村落”[4],成化时人口倍增,嘉靖万历间则已工各居肆,百业俱备,“庐井千区,于郡城东南称巨镇”[5],并“生齿日繁,氓隶杂处。凫沙寥岸变作桑田,花坞板桥翻为机杼……百货狼藉,走万里之估客”[6]。湖州历史悠久的乌镇与南浔,至晚明亦有新发展。乌镇嘉靖时“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7],万历时“本镇居民近万”[8];南浔在嘉靖万历间也是“市廛云屯栉比”[9],乃商贾辐辏之所。
可见,到了晚明,湖州市镇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经济繁荣。茅坤就曾这样说:“至于市镇,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练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10]晚明湖州区区一个市镇,其富足程度竟可敌中原地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府,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蚕丝业的发达,双林、菱湖、练市、乌镇、南浔都是当时江南丝织业巨镇,而茅氏的经济活动与这些市镇关系十分密切。
茅氏是在晚明蚕丝业繁荣背景下,因经营专业化桑园而发家致富,并在此基础上投资丝织业、酒楼业、刻书业等其他商业活动而成豪富的望族典型。据湖州练市人所撰《沈氏农书》,当时雇工1名,种地4亩,种田8亩,其收益要比出租土地增加银10两[11]。这使得以出租土地为特征的封建地主开始向以雇工为特征的经营地主转变,并意味着晚明江南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明中叶以来,湖州成为江南丝织业中心,湖丝基本垄断了国内生丝市场,对桑叶需求猛增,种桑因此比种田更有利可图。茅氏世居练市花林,原以治筏为生,大致于嘉靖间茅坤之父茅迁开始,拥有雇工,并调整产业结构,由种田转到更有经济效益的栽桑,进行规模化生产。唐顺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五《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曰:“湖俗以桑为业,而处士治生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茅迁善于经营,“其治生,操纵出入,心算盈缩,无所爽”[12]。若干年后,积财“数千金而羡”[13],“家大饶”,以致有实力“岁入粟千余,悉分赈人”,“割田百亩赡宗人”[14]。去世时,有家财万金、田产1600亩[15]。
茅迁第三子艮最能承继父业,于稼穑最精[16]。他雇用更多人工,在唐家村扩种桑树数十万株[17],面积数百亩[18],而且事必躬亲,精耕细作,薙草化土,辇粪饶土,种田收入要比普通农民增加一倍,种桑收入比普通桑农增加十倍甚至百倍,家财累积至数万金。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亡弟双泉墓志铭》曰:
君起田家子,少即知田。年十余岁,随府君督农陇亩间,辄能身操畚锸,为诸田者先。其所按壤分播、薙草化土之法,一乡人所共首推之者。已而树桑,桑且数十万树,而君并能深耕易耨,辇粪菑以饶之。桑所患者蛀与蛾,君又一一别为劖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应德尝铭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郁维桑兮。生也游于斯,死以为葬兮。”盖善府君之治桑而没,且歌于其墓也,而不知于中君之力为多。故其桑也,亦一乡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乡之所入;而君之桑,则又什且百乡之所入。故君既以田与桑佐府君,起家累数千金而羡;而其继也,君又能以田与桑自为起家,累数万金而羡。[19]
由于桑园规模大,种植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因此茅艮巨富。其生前分授夔、龙、皋三子田产家财,各“殆且万也”。卒后还有“存田八百亩,别属三兄弟之奴者五百五十金,米谷二千五百有奇,他所贮僮仆什器称是,大较犹及五千金而羡”[20]。茅艮还善于总结生产经验,著有《农桑谱》六卷,为茅氏家族及姻亲的农桑经营提供了宝贵经验。
茅迁次子坤,虽以科第显,但受家风影响,中年落职后,亦重视治生。特别是其妻姚氏,善操内秉,“督诸僮奴臧获十余辈,力田里,勤纺织”[21]。不数年,“家大饶于桑麻”[22]。茅坤曾写信给练市瑶庄的外甥顾儆韦,向他介绍种桑的经济效益:“大略地之所出,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斤,岁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斤;最下者,岁所入亦不下一二金。故上地之值,每亩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犹三四金。”[23]也就是说,每亩桑地产值上者十金,最下者三四金,除去雇工工资及其他成本,每亩可得净利上者五六金,最下者也有一二金。凭着种桑,茅氏及其姻亲均成为里中巨富。明末张履祥曰:“归安茅氏,农事为远近最。”[24]又曰:“(茅氏)治生有法,桑田畜养所出,恒有余饶,后人守之,世益其富”,“鹿门之甥为顾侍御,为富大略慕效茅氏”。[25]除了外甥顾氏,茅坤外祖父李氏一家亦以农桑丝织成为里中巨富: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珪,农业起家;而外大母施孺人,复佐以机杼,家故颇饶。已而,伯舅氏观稼公深,稍稍世其业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渊,……躬督诸僮奴以耕于林墟之西,星而出,星而入,虽风雨寒暑无间也。……又习见母(舅母邵氏)躬督诸婢妾以织于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虽风雨寒暑无间也。……故田之所入,数以倍他人;织之所鬻,他贩者来,数争操厚价以购之。虽里中转相效,弗能也。故并观稼公累赀而富,遂以甲于里邑中,为名族。[26]
茅迁长子乾除继承田产、经营农桑外,还很有商业头脑,曾外出经商。茅坤《伯兄少溪公墓志铭》曰:“间操赀出游燕,累数千金而归。”又,祝世禄《南宁判少溪茅公暨配郭安人墓表》曰:“时藏名于贾,则贾起万金。”[27]由于家业丰厚,茅乾平日生活豪奢,逍遥于裘马声伎之场,混迹于纨绔子弟之群;遇到美女,就挥金买归,一生妻妾众多。茅坤《伯兄少溪公墓志铭》曰:“两孺人兮早亡,窟左右兮卧明珰。”又,《亡嫂郭孺人行状》曰:“少操赀贾游四方,一来归,辄买一姬”,“一日从商舶中载而来归者三人,内外且大骇”,“故予兄所后先帷侍者十二人,燕、赵、瓯、越,杂沓以进”。
茅氏通过蚕桑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又被投入店铺业、丝织业、刻书业,甚至高利贷等商业活动中,以获取更大收益。如茅坤就在附近双林镇经营店铺[28],形成极其繁华的市廛“赛双林”。《双林镇志》卷二十二曰:“(茅坤)家素饶,既显,筑花园于镇北,广田宅,起市廛,人称曰赛双林,年九十犹往来花林而自督租。”又《双林镇志》卷四《街市》“赛双林”条曰:“在成化桥北,明茅鹿门宪副所构市廛,旗亭百队,环货喧阗,故名。渔唱曰:‘旗亭百队列方塘,环货喧阗作市场。却笑白华风雅客,苦将钟鼎媲翁张。’”“旗亭”即酒楼,“旗亭百队”可见街市之繁华,其店面房租、日常营业等收入也必定可观。
当时湖州双林等地能产生高额利润的还有丝织业。《双林镇志》卷十六《沈泊村乐府》曰:“商人积丝不解织,放与农家预定值。盘盘龙凤腾向梭,九月辛勤织一匹。”注曰:“庄家有赊丝与机户,即取其绢,以牟重利者。”据此可知,豪富之家利用资金收购蚕丝,分包给机户加工成丝织品,出售后就能赚取大利。而茅氏巨富,又有商业意识和眼光,参与当时繁荣的丝织业是自然而然的事[29]。也就是说,赛双林不仅是店铺房产投资,而且应是茅氏丝织品加工、销售场所。双林河塘可以通往嘉兴、杭州、吴淞等地,茅坤沿河塘开辟市场,首先在销售方面占据了地理优势。
茅氏家族的编刊活动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们在练市列肆刻书,形成“书街”[30]。所刻之书还发往南京等地销售,茅坤《与唐凝庵礼部书》曰:“族子遣家童,囊近刻韩、柳以下八大家诸书,过售金陵。”《唐宋八大家文抄》后来“盛行于世,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31],由此可以想象该书编刊带来的商业利润。
茅氏资产剧增与高利贷收益、门第势力等也关系密切。茅坤就曾言,妻子姚氏除致力蚕桑纺织,“间操子母钱,以筹时赢”[32]。同里吴梦旸甚至将茅坤的发家致富直接归于姚氏高利贷,其《茅公鹿门传》曰:
公之罢大名归,橐如洗也。兄若弟皆息处士公业而雄于赀。公配姚孺人戏谓公云:“公业儒,乃不得为富家翁。”公大笑。姚孺人固有心计,善操内秉,逐十一之息,锱铢无爽。居数岁,赀遂于里中豪埒。[33]
茅坤先官后商,凭借门第影响和家族经济实力,很容易成为商业战场中的强者。施樑《何淑人六秩文》中谈到凌仲郁在双林“有别业数十间,当市之孔道,度直可千金。鹿门茅先生心欲之,而未敢言。公揣知其意,立简原券畀先生,无难色”[34]。凌仲郁属湖州凌氏双林支,与晟舍凌氏同宗,乃名医凌汉章之后,且亦以医术名,与不少显宦有往来,故产业颇丰,然而他却主动将繁华地段的房产以原价相让,可见茅氏家族的强大势力。
因善于治生,商业经营多样,茅氏资产雄厚,成为江南豪富望族典型。这从其园第数量之多、建筑之豪华可见一斑。茅坤在花林构筑了拥书数万卷号称明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白华楼”;在繁华市镇双林营构了别业,茅家巷也因此得名[35];在郡城拥有横塘别业,它原为赵孟頫故宅,甚有名气。其子茅国缙财力雄厚,万历间曾购得号称湖州城东第一家的沈氏西楼[36],复筑双鹤堂、翠云楼。《练溪文献·园第》引沈象先《寓黎废言》曰:“东栅旧宅美轮美奂,号城东第一家。万历初始易主。”又引旧志曰:“庄丽甲一镇”,“旧传前后左右共五千零四十八间”。规模之大,简直难以想象,远超当时号称东南巨富的亲家董份在南浔所筑之百间楼。其孙茅元仪在南京著名景点赏心亭旁拥有私邸,“该博”即为此宅中堂名。又湖州花林西南有其侄茅一相所筑豪园——华林园。茅国缙《苕朔和鸣稿引》曰:“康伯辞官拂衣,处华林园,自号园公。”园中有连塍街、文霞阁、竹径、沧浪亭、几桥、竹邬、荷薰汇、澄襟塘、红薇亭、蕉戺、柿偃、啸堂、曲水轩、瘗鹤处、晖照滩诸胜,茅国缙皆有题咏。
因家业富饶,以赀入太学或以赀为郎的,在茅氏家族成员中时有见之,茅乾、茅艮等皆是。也因家业丰厚,其后世子孙茅翁积、茅维、茅元仪等风流放宕,一掷千金。这一切都让时人将该家族与“好利”挂起钩来。如茅坤虽进士出身,曾任兵备副使,但有人就当众呼其为茅翁,“讥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则好利之尤者也”[37]。朱彝尊甚至认为,茅坤之所以拿到了“唐宋八大家”的冠名权,就是因其有钱而能抢先刊刻《唐宋八大家文抄》,“茅氏饶于赀,遂开雕行世”[38]。
凭着经济实力,茅氏家族创造了良好的隐读、著述与刊刻条件。章嘉祯《题华林园诗》写罢官后的茅一相在华林园以著述自娱,曰:“缥缃娱曛旭,含毫晷恒移。”陈尚古《簪云楼杂说》更是记载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茅坤子茅镳[39],偶向众友吹嘘家中有奇书,然“实无此书。暮归,即鸠工匠及内外誊写者百余人”,“或以口语,或以手授,随笔随刊”,“天将曙,而百回已竣,序目评阅俱备”,“题曰《祈禹传》”[40]。因茅镳此人无法考证,故笔者只能目之为传说。然而这个传说背后所隐含的茅氏编刊活动的雄厚实力是真实的,那就是:拥有人员数量庞大的编刊队伍,可以编撰、誊写、刻板、印刷、装订一条龙服务,只要有需要,可随时出书,甚至像《祈禹传》这样篇幅百回的巨著,亦可一夕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