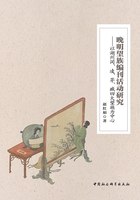
第三节 四大望族的社会交游
四大望族与太仓王氏家族均有交游。太仓王氏乃江南著名望族,族中人才辈出,其中著名者有文坛盟主王世贞。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晟舍镇志·流寓》曰:“(王世贞)解组后,与闵一鹤为至友,放棹来湖,勾留数月,杯酒论文无虚日,有忘归之乐云。”闵一鹤字声甫,号芝山,乃闵珪玄孙。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应闵一鹤之请,为闵氏聚芳亭作跋[50]。隆庆三年(1569)秋八月,王世贞又为闵氏所藏《甲申十同年图》作跋[51]。
凌、王两家因刻书、作序等原因,相互间往来更为频繁。凌约言有书信集《凤笙阁简抄》,其子凌迪知付梓时,请王世贞为序。王氏赞曰:“余友人济南李攀龙、歙县汪道昆、吴都俞允文皆以尺牍名,今并凌公四矣。凌氏尤精二氏学,俱见集中。”凌约言卒后,王世贞为之题墓,评其诗曰:“晚乃多病,不数为诗,其传者三百余章,皆有唐人风致。论诗十法,凿乎其言之也。”[52]其弟王世懋亦作有《比部藻泉公诔》。凌迪知、稚隆兄弟,在其父凌约言《史记评抄》的基础上广搜群籍,集其大成,共同刊刻了《史记评林》一书,王世贞为之宣扬曰:“发简而了如指掌,又林然若列怀宝于肆者也。”[53]凌迪知所著《古今万姓统谱》、其长子湛初所著《赫蹄书》、次子润初所著《叹逝录》,均请王世贞为序[54]。其中《赫蹄书序》略曰:“按班史《赵后传》,箧有裹药二枚、赫蹄书。应劭译曰:‘薄小纸也。’元(玄)旻之为书,大者数百千言矣,称‘赫蹄’,示抑也。”[55]凌迪知、湛初父子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信往来频繁。《国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二收王世贞与凌迪知书信三通、与湛初书信两通,卷四十一收王世懋与凌迪知书信三通,卷五十二收凌湛初与王世贞尺牍两通,这些尺牍不少涉及凌氏刻书求序之事。湛初卒后,王世贞还为之撰《凌玄旻墓志铭》。湛初仅活了二十五岁,他能与太仓王氏交游,并得王世贞为序,显然是源于凌、王两家世交之谊。
凌迪知二弟述知与王世贞亦有交游。述知字雅明,号次泉,有隐逸之思。他在盘渚漾旁建盟鸥馆,馆外有水云居、乐鱼矶,淡翠浅绿,一望无际。王世贞曾作盟鸥馆排律寄之[56]。凌迪知三弟稚隆,原名遇知,与王氏交往更为密切。王氏《弇州续稿》收与稚隆相关书信三通[57],《国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二收与稚隆书信二通。王氏对凌稚隆的史才评价很高,尝云:“我高皇帝德逾汉高万万,文献即小未称,亦不下武宣叔季,有能整齐其业,以上接班、马,舍以栋,奚择哉!”[58]凌稚隆编刊《史记纂》《汉书评林》《史记评林》《春秋左传注评测义》皆由王氏作序。这些序对凌稚隆编刊活动均褒奖有加,如《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序》略曰:“以栋少习《春秋》,于左氏尤精诣,尽采诸家之合者荟蕞之,发杜预之所不合者而针砭之,诸评骘左氏而媺者皆胪列之,左氏之所错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谥或封号,咸置之编首,一开卷而可得。”[59]
凌氏一族在编刊活动中,常请王世贞等名人出谋划策,借以提高书籍质量和知名度。朱国祯《缮部绎泉公(凌迪知)行状》曰:“长子湛初、次子润初颖甚,先生益发舒,与元美、子与两家[60],时议论校刻秦汉诸书,义例纲领,一经裁定,井井可观。于是凌氏书布天下,干麾所指多及其庐。”太仓王氏对凌氏编刊事业确实贡献不小,凌氏《唐诗选》等书的刊刻也与王世贞有关。先是李攀龙选古今诗于历下,王世贞携之吴中,馆客某抄录之而付凌述知,凌氏择其唐诗而授诸梓,名曰《唐诗选》,时在万历三年。后世贞晤凌迪知,见到该墨刻本,谓馆客有抄漏,并告知徐中行别有校本,较此本稍全。于是凌氏昆仲凌瑞森、凌南荣据徐中行本再刻,题为《唐诗广选》,由凌濛初为序[61]。此乃朱墨刊本,估计当时非常畅销,以致后来凌弘宪又去掉凌濛初序,再次将它改头换面而刊行[62]。王世懋是凌氏刻本中常见的评点者,凌瀛初曾得王世懋《世说新语》批点本而附之梓[63]。
尽管王世贞万历十八年(1590)卒时凌濛初才十一岁,但王世贞兄弟对凌濛初成年后的文化事业影响颇大。凌濛初的戏曲理论著作《谭曲杂札》对王世贞的文学主张有许多深刻评价。在编刊方面,凌濛初也很能利用王世贞的名气来抢抓商机。如王世贞曾据刘义庆《世说新语》和何良俊《语林》删编成《世说新语补》。由于王氏久负盛名,所以此书由张文柱刊刻出版后,非常畅销,以致《世说新语》原书反而湮没不闻。凌濛初刻本则“遵古本分为六卷,附以弇州所续,另为一帙,名曰《鼓吹》”[64],这就不仅巧妙地利用了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的流行效应,而且还新增了一个卖点,那就是,可以对外宣传此书恢复了宋本《世说新语》的原貌。
王世贞与茅坤及其伯子翁积、仲子国缙俱有交往。其《茅章丘传小序》曰:“吴兴有茅鹿门先生者,其居官所至,负才术,顾厄于才,不尽究,归而以文学收远近声。其伯子翁积能嗣茅先生为文,而以不胜任侠夭,父子余俱识之。……且以寿鹿门先生,曰:‘先生有子,先生所未竟者,荐卿尽之矣。’”[65]茅章丘,即国缙,字荐卿,曾任章丘县令。茅坤与王世贞虽多有交往,然同为文坛领袖,亦未免争名相轧。这种争名较胜甚至延及其子孙后人。茅元仪有诗文评《艺活甲编》五卷,《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十七曰:“此编皆评诗论文之语。当嘉靖中,元仪祖坤与王世贞争名相轧。坤作《史记抄》,世贞未见其书,即先断其必不解。又世贞题《归有光集》,诋坤《八家文抄》右永叔而左昌黎。元仪修先世之憾,故此书大旨主于排斥世贞。然世贞摹拟之弊,虽可议者多,而元仪评论古人,又往往大言无当,所见实粗。其任意雌黄,亦皆不为定论也。”
关于臧懋循与王世贞,虽然没有找到他们交游的诗文,然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两人是老朋友。因为朱氏说,臧懋循虽然与明代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宴游,但诗歌“不堕七子之习”,是一位“磊落之士”。臧懋循与王世贞在戏曲观念上也是对立的,一主张本色,一主张绮丽。如在明代《琵琶记》和《拜月亭》(亦名《幽闺记》)高下的争论中,臧懋循就赞同何良俊《拜月亭》胜于《琵琶记》之说,认为《琵琶记》【梁州序】【念奴娇序】二曲是刻意求工,不类高明口吻,是后人窜入;而讥笑王氏以修饰词章为美,对这些赝曲“津津称诩不置”,“是恶知所谓《幽闺》者哉”[66]。如此看来,两位当是诤友。
四大望族与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屠隆也多有交游。屠隆(1543—1605),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他曾为凌迪知所刊《国朝名公翰藻》作序,曰:“吴兴凌君稚哲人伦之□□古,藏书为当今邺侯家,诸所□□业遍方内,又博搜我朝学士大夫尺牍,汇为一编,名之曰《国朝名公翰藻》。”《国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九收屠隆《与凌稚哲》尺牍三通。
屠隆与茅坤父子交往密切,曾曰:“吴兴鹿门先生,执海内文章牛耳,意不可一世,独奖借余。余生也晚,犹及因先生仲子荐卿、季子孝若而一再望见先生眉宇。”[67]茅坤卒后,屠氏前往吊之,茅国缙、茅维兄弟“遂以状属焉”[68]。屠隆还曾为茅坤侄一夔撰墓志铭。万历丙申(1596)夏五月,屠隆于杭州南屏禅舍为茅维《十赉堂初集(甲集)》作叙。万历三十八年(1610),茅元仪刊刻屠隆《鸿苞集》四十八卷。
屠氏与臧懋循交好,章嘉祯谈到臧懋循之交游时,即曰懋循“于甬东善屠长卿”[69]。臧、屠两人不仅共好词曲,而且同好男风。万历十二年(1584),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隆因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而被劾,削籍归鄞。次年五月,臧懋循也同样因好男风而被国子监祭酒黄仪庭弹劾,罢官回湖。此时两人的共同朋友汤显祖正在南京任职,因写诗送别臧懋循,并寄屠隆[70]。
闵、凌、茅三大家族与明代竟陵派领袖谭元春、钟惺亦有或多或少之关系。闵宗德万历间官湖广时,与谭元春、刘侗、黄正色等三楚名士论文讲艺[71]。凌义渠与谭元春的相识与闵宗德类似。凌义康《明大廷尉忠介公行状》曰:“(凌义渠)生平好延揽文士,干旌孑指,先及名宿,在吴则识徐丈方广及徐波、杨彝诸子,使楚则识谭元春、易暹道、刘敷仁诸子。”万历三十七年(1609)秋冬之间,凌濛初与钟惺、朱无瑕、潘之恒等人在秦淮河畔结社吟诗[72]。天启四年(1624),凌濛初因选官淹留京城,在重阳日,与谭元春等共集妓女郝月娟邸中,饮酒赋诗[73]。茅维亦参加了这次雅集。茅维侄子茅元仪有《怀谭友夏》诗,作于天启八年(1628)。诗歌回忆了以前的聚首共饮、梦中的往还,并感叹“几次诗成未寄君”。钟惺与谭元春论文重性灵,反对摹古,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茅元仪诗歌创作颇受其影响。朱彝尊就认为其诗歌“下笔未能醇雅”,是因为“竟陵之派方盛,又与友夏衿契,宜其染素为缁也”[74]。钟、谭又是著名评选家,曾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隋以前诗为《古诗归》,流布天下。闵振业与闵振声不仅合刻有三色本《唐诗归》三十六卷、《古诗归》十五卷,还合刻了题为“钟惺伯敬”评选的《东坡文选》二十卷。凌濛初则不仅喜欢以钟惺的观点评论诗歌,而且两次刻《诗经》均采用钟惺的评点本,可见受钟惺的影响之大。
凌、茅、臧三氏与吴郡王穉登均有交往。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常州府武进县人,后移居苏州。《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等有传。王氏不仅以其诗文、戏曲名扬江南,而且也以他的高风亮节闻名吴郡。他喜爱湖州山水清远,曾前后两次游玩,并集两次游玩诗作为《清苕集》,自序曰:
吴兴物产丰饶,山溪清远,僧庐道院,园墅林亭,隐见于峭蒨青葱间,似武陵桃源,非复人境。……万历丙申之岁,谢使君在杭为郡司里,余始一至。后八年为今岁癸卯,陈使君惠甫为郡将,余乃再至。……丙申之岁,余方神王,时当冰雪凝寒,犹能蜡屐,从事道场、苍弁游,得十二焉。今年秋暑如炮烙,余又困河鱼之疾,养疴白雀方丈。……既归园庐,命童子检前后二游诗若干篇,丙申六之,癸卯四之,授友人范东生窜定,且就劂焉,名《清苕集》[75]。
集中有《臧晋叔见访不值》诗,赞扬臧懋循,并告知对方将赴顾渚山会面。集中与茅维交游的诗歌更是在在可见,如《客居慈感寺茅孝若见过》《茅孝若斋头》《答茅孝若》《茅孝若虎丘看月贻书问余白雀寺却寄》等。
当然要说交往的密切,那还是凌氏,其一门三代与王氏均有往来,并因此影响到凌氏的编刊活动。关于凌家与王穉登的过从,笔者曾据《光绪凌谱》中所收朱国祯《善部绎泉公行状》一文,认为始于凌濛初之父迪知。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因为当时所据仅此行状,所以“凌迪知在常州同知任上,因逮捕犯人与王穉登相识”的话就讲得不正确[76]。笔者此说有学者引用,为避免再以讹传讹,现据新的材料澄清如下。
据缪荃孙手抄本《王百穀先生集外诗文》[77],凌迪知去世后,王穉登曾作《祭凌常州文》。该文详细记录了两人因偶发事件而相识的经过:
公昔量移毗陵日,武进有鸷令,疑不肖匿亡人,破柱取之,不得,将甘心于我。是时,不肖就逮至毗陵,公与郡将李公元树犹未识不肖,相与下记,援而出之虎口,令耽耽,莫敢若何。不肖齿发之余,皆二公赐也。
可知,当时武进县令怀疑王氏藏匿犯人,于是将其逮至常州府。后来在凌迪知和李元树的帮助下,才脱离牢狱之灾。由此可见,逮逃犯和逮藏匿逃犯的均是武进县令,与凌迪知无关。凌氏所做的是,援助藏匿犯人的王氏,“出之虎口”。所用的方法,朱国祯《善部绎泉公行状》有记载:
某孝廉捕急,匿友王穉登所,王身当之。吏捕将诣县。先生素不识王,遇诸途,戒迟一昔。召县令饮,示王扇诗,令亦称善。先生因曰:“假士如平原君匿魏齐,谬曰:‘在,固不出也!’将如何?”令嘿,未有以应。明日见王悟,遂得解。
凌迪知招县令来饮酒,宴饮中展示王氏诗扇,宣扬王氏的诗歌和书法才华,旨在赢得县令对王的赏识。然后以平原君藏匿魏齐的典故,说明王氏这样做乃讲朋友之义气。由于上司凌迪知的巧妙说情,原本铁面无私对王氏藏匿行为颇为气愤的县令,最后妥善处理了此事。两文均言事前凌、王并不相识,可知凌氏之解救王氏主要是慕王之名。
在这个事件中,一起参与说情的还有李元树,但李是楚人,距离遥远,王氏后来与他联系较少,而湖州“去吴门一衣带水”,故此后岁时节日两家就时相往来,成了知己。《祭凌常州文》曰:
岁时,尝得拜公,床下奏起居,为公祝鲠祝噎。公见不肖至,辄色喜,曰:“有心哉,王生。”烹鱼沽酒留客,剪西窗烛,娓娓谈苍弁、清苕之胜;或出所著书,商略品骘;又或述司空郎与倅天雄贰守常州时事,漏不下二十五声,不听客寝。
祭文还谈到,凌迪知七十岁生日时,王因病不能亲自前往凌家祝寿,但仍不忘撰写贺文。凌迪知目王氏为“南州孺子”,王氏对凌迪知也十分敬重与感恩。王氏《竹箭编》卷上有《凌使君且适园》《答凌使君》两诗,《谋野集》卷一又有尺牍《与凌使君》。其中《凌使君且适园》一诗,既夸赞凌迪知为官政绩,也写到其归隐后的著述情怀。
凌迪知卒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王穉登游湖州,涵初、濛初、浚初三兄弟前往拜见。王氏《清苕集》卷下《凌玄渤、玄房、玄静携酒问病》赞美凌氏三兄弟曰:“公子气翩翩,才华总少年。凤元非一薛,荆可比三田。”[78]在凌氏三兄弟的盛情邀请下,王氏扶病重游且适园,写下了情真意切的怀念之作:“水木清华池,重来迹已陈。楼空惟鸟毛,松老半龙鳞。把酒怀知己,看花无主人。西州门下路,但到即沾巾。”[79]有了这层世交关系,凌湛初之《申椒馆敝帚集》由王穉登校阅,也就容易理解。也由于这层世交关系,凌濛初刊行自己学术著作《后汉书纂》时,为抬高身价、打造影响,就请了王穉登这位名人兼父执作序。凭借与王氏的交往和了解,凌濛初曾对《吴骚集》的一个注语进行了纠正[80],认为其所收《月云高》曲并非王氏所撰。王穉登善书法,行草篆隶皆精,钱谦益云:“穉登妙于书及篆隶”,“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踵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81]凌濛初之侄凌毓柟所刻《楚辞》十七卷,首有《屈原贾生列传》一篇,即请王穉登书写。
凌氏与苏州文氏家族关系密切,其交游首先源于凌震与文征明。文征明是明代吴中书画大家,凌震在京候选时,因文采出众,为其所敬重。陈良谟《简藻泉比部公(凌约言)》曰:“先尊昔年需次京师甚久,芳誉藉藉播缙绅间。即如刑部诸郎署,每夜必轮一人直宿省中,凡当直者,必邀练溪先生同往。酌酒论文,赓诗联句,月无虚夕。不但浙中乡友,虽异省东西南北之人亦无不尔。至于出游西山诸名胜,必固请谐行,曰:‘坐中若无凌君,自觉无兴趣耳。’翰林如陈石亭、文衡山二公,尤敬慕焉。”[82]与文征明的西山之游,有凌震自己《同陈石亭、文衡山、马积石三太史及袁邦正太学同游西山道中》一诗为证[83]。文征明亟称凌震“明淑博雅”[84],曾数次为凌震挥毫泼墨。凌湛初《与文子悱书》曰:“先王父练溪公与先太史雅相友善,太史尝为作《练溪图》,自言十年来未有此笔。又匹纸写苏、黄、米、蔡四家字。”[85]凌震一日访文征明,文氏正吃饭,接到名帖后,“亟吐哺出迓,仓卒致伤一足,至老不良能行”[86]。凌震后选为黔阳训导,文氏有《送凌震训导黔阳》诗,曰:“短棹沅湘路不迷,黔阳更在武陵西。平生事业经千里,晚岁文章到五溪。荏苒雪泥鸿雁迹,阴深云木鹧鸪啼。莫言游宦伤行役,剩有江山入品题。”凌震卒后,刘麟为之作墓志铭,文征明为之篆盖[87]。
以凌震与文征明的交往为开端,凌、文二氏在此后数代均有往来。文征明长子曰彭,字寿承;文彭之子曰元发,字子悱。凌约言曾有科举提拔之恩于文彭,凌湛初《与文子悱书》曰:“家大夫观铨政时,值尊公以贡计谐,既而得阅贡卷,首拔公于吴。”家大夫,即凌约言。凌约言曾以东宫恩诏,进阶朝列大夫。凌湛初为凌迪知之子,凌约言之孙,从辈分上看,是文元发的晚辈。但两人因年龄相仿,所以言谈较为亲近。《与文子悱书》曰:“尚书公络世谊[88],足下盖不佞长公辈也。亟欲伸孔、李之义,冀不陨前好,而块处霅上,无从执鞭珥笔,以充锥刀之用。何间梦入吴王城,与足下散发对膑,出梨花春,相与倾百斛哉!”信中凌湛初高度赞扬了文氏一门三代的艺术才华:
不佞生晚,不及挹先太史清扬。然先太史声称,自羁角时,窃啧啧艳之矣。先太史为明宗英,书画与希哲、启南一时擅美天下。尊公寿承公,惠徼先太史芬芳,行楷篆隶,号当代独步,而草书悟入孙、钱佳境,其菁名馺沓宇宙间,业五十余祀。休承、德承,又皆赤帙艺府。迨及足下,不特克继先太史、尊公书钵,而倚马才高,行将移龙舟,馔夺兽袍。嗟乎!即唐宋以来,谁见三叶嶙峋如此!难矣,难矣!
“休承”乃文征明仲子文嘉之字。文嘉,号文水,能诗,工书,尤擅画。其画得父真传,是吴门画派代表画家。曾为湖州府乌程县训导,与凌氏交往密切。凌约言卒后,文嘉为之作诔[89]。文嘉与凌约言次子凌述知亦交好。述知盟鸥馆建成后,请其作记。《盟鸥馆记》曰:“盟鸥馆者,光禄次泉凌君新筑也。光禄一日过吴诣予,请记之。”凌迪知所刊《国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中收有不少凌氏与文嘉、文元发的尺牍。凌湛初刻《申椒馆敝帚集》,文嘉为之序,并参与校订工作。
凌氏与琼州唐氏家族亦世代交好。琼州唐氏是名门望族,自宋淳祐间唐震以台阁大臣身份贬琼州刺史而落籍琼山以来,名人辈出,代不乏人。其中明代就出了6名进士,他们是:唐舟、唐亮、唐绢、唐鼐、唐胄、唐穆。其中唐舟和唐亮、唐胄和唐穆均是父子进士。唐舟(1368—1449),字汝济,永乐甲申(1404)进士,官至浙江巡按。为官30余年,所至多有政绩。为人光明磊落,曾自题门联曰:“雪霜自染中年鬓,天地应知暮夜心。”其子唐亮,永乐戊戌(1418)进士,官至给事中。唐胄(1471—1539),字平侯,号西洲。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山东巡抚。嘉靖时,因议礼而被削籍归乡。其子唐穆,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
这两对父子进士及其后人均与凌氏关系密切。凌晏如丧偶后,娶御史唐舟之爱女为继配。唐舟《琼山唐氏姻书》曰:“余昔以事谪戍居庸,携家憩安定寓舍。时吴兴凌氏安然,室家未庆,执柯者屡请求之。余次且未允者再。适男亮扈从来,具道其共事黄门,素知其贤,且簪缨世裔。余感其言,慨然许以爱女妻之,聘仪绝无较焉。”可知,凌晏如与唐亮交好,其娶唐氏,即得力于此。唐舟十分看重此次缔姻,以为姻缘天赐,因赋诗两首以赠其婿。其一曰:“种玉蓝田岂偶然,检书月下系前缘。琼台毓秀尤贞淑,湖郡抡才亦俊贤。万里奇逢佳伉俪,百年亲爱永纯全。冰翁乐道姻缘事,留与儿孙世代传。”其二曰:“素位安行付自然,穷通用舍总天缘。家山淹滞嗟予老,馆阁修裁羡汝贤。圣代恩威覃四表,男儿忠孝贵双全。得时须展经纶志,要使香名远近传。”唐夫人仅生一子,即凌氏迁晟舍之始祖凌敷。凌约言《简内台唐尧封》曰:“先是,曾祖讳晏如,以都台丧偶,而令高祖讳舟者,时为御史,因娶其女,遂为唐夫人。唐夫人举一子,讳敷,弟之祖也。”嘉靖时,凌敷之子凌震与唐舟之孙唐胄曾一会于京师,再会于黔阳。凌约言《简内台唐尧封》曰:
嘉靖初,令祖西洲公与先君会于京师,款接极欢。嗣以督府过黔阳,再申前睠,且曰:“吾两家亲远,非仕宦不能相通,幸各勉旃。”其情抑何厚也。
西洲公即唐胄,乃唐夫人之侄[90],凌震称之为表叔。凌震在京师候选时,两人相识。后凌震选为黔阳训导,唐胄按察广西时,路过黔阳,两人再次相会。凌震作有《送唐西洲表叔按察桂岭十五韵》,诗曰:
惟昔联姻好,于兹盖百年。祖孙情未远,中表世仍延。叔父声名起,儒林藉甚传。曾将书过岭,忽又雁回燕。瞻望音尘隔,倾依岁月迁。歘从京国见,复漫别离筵。士论新收价,人区旧有缘。官程虽夙夜,王事要劳贤。桂郡征骖解,霜台属史虔。清风常洒匕,周道亦乎平。更喜乡山近,兼应土俗便。桄榔春叶暗,荜拨夏笛鲜。内外俱勋业,安攘间后先。望之辞魏阙,长孺卧淮壖。请借埋轮手,归来早秉铨。[91]
凌震卒后,其墓志铭由唐胄书丹,当时唐氏官衔是通议大夫、户部右侍郎。唐胄之子唐穆、唐穆之子唐尧封,与凌约言父子亦多有往来。凌约言《简内台唐尧封》曰:“尊翁礼部公亦两承翰寄,惜无由一面,以尽所怀。今儿辈得遇兄于南都,且辱缱绻。非天假之缘,其会合能至是哉!”礼部公即唐穆。据此,凌氏与唐氏的交往,由永乐间一直延续到了嘉靖万历间,几乎贯穿整个明代。
值得一说的是,晟舍凌氏万历间曾三修宗谱,这使得其与各地凌氏往来频繁,并有可能影响到其刻书业。这三次修谱依次是:万历己卯(1579)凌迪知修、万历戊申(1608)凌嗣音继修、万历乙卯(1615)凌嗣音从弟嗣功纂续。凌迪知等修谱以元代凌时中为一世、凌懋翁为二世。凌懋翁生活于元末,预感到一场社会动乱即将发生,为避免全族毁灭,于是让其十六子“以寿为行”迁徙各地。其中寿四迁居湖州归安练溪,晟舍凌氏即为寿四后裔;寿一则迁居湖州归安双林。据《顺治凌谱》所载诸序,这三次修谱的访查工作很细,联络到了元末这十六支凌氏的诸多后裔。对晟舍凌氏刻书业有影响的主要是同处湖州的双林凌氏。寿一迁双林后,其玄孙名云,字汉章,号卧岩,郡廪生,以孝感异人授针术,为太医院吏目。云有孙曰瑄,号双湖;双湖长子曰仲郁,号藻湖;仲郁第四子曰士麟,号振湖,均为针灸名医,且以号名世。弘治间,秦王两脚麻木无力,恭请汉章为其医治。治愈后,秦王有《送汉章公还乡四律》。嘉靖间,宗藩定襄王曾延请双湖治其小儿,不仅亲自写信相求,而且请总督胡宗宪以礼致聘,又请凌氏同乡显宦董份写信劝行。天启间,河南周藩朱勤美曾请振湖治其痿疾。振湖回乡,周藩制序赠别,有《赠振湖君文》。这些藩王均好文能诗,且府中藏书丰富。而汉章曾与晟舍刻书家凌森美、练市凌斗光等重修宗谱。又万历间福建巡抚沈秱的外祖父是双林支凌昊,字钦伯,别号味清,乃汉章之侄[92]。生前曾感慨子孙业医而无以儒显者,希望能“弃术业儒”。凌迪知修谱时,奉双林寿一支为大宗,沈秱及其表弟凌濂将双林支材料贡献于凌迪知,并希望双林支子弟能籍进士凌迪知以兴族[93]。
可见,凌氏各族支间因修谱,多有往来。他们与名人的交游,特别是与藩府有交往的双林凌氏,很可能是晟舍凌氏获取刻书底本的一个桥梁。如凌氏御医双湖公像[94],由丰坊撰,这不由地让人想起凌濛初《圣门传诗嫡冢》。此书在《孔门两弟子言诗翼》基础上,添加了毛传、郑笺,以丰坊诗传冠各篇之首,互考其异同,并在末尾附录丰坊所作《申公诗说》。是书编成后,凌濛初非常满意,自以为对圣门传诗的渊源探究,比千百年来率意而为的要高明很多,甚至可以解决千百年来《诗经》的疑案。又凌濛初自言其所刊《西厢记》用的是“周宪王元本”[95],然学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郑振铎就认为所谓周宪王本是“子虚公子”一流,不过是凌氏“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96]。笔者认为,从上述凌氏族人与周藩的往来看,凌濛初有可能得到这种本子。
凭借交游关系而得到善本或名家批点本,从而对自己家族编刊活动起重要作用的典型人物,是官居高位而又雅好书籍的闵梦得。闵齐伋曾刊戴君恩《读风臆评》,其底本即来自闵梦得为官四川时所得。龚惟敬《绘孟跋》云:“初,先生(戴君恩)令巴,有《读风臆评》四卷”,“已而乌程闵遇五太学得于其尊兄方伯昭余先生,复加朱黛,为刻于吴中,海内人士竟相传诵”。闵齐伋《书戴忠甫读风臆评后》亦曰:“戊午之后,我仲兄翁次氏承乏监试蜀闱,遂得与先生朝夕焉。而读其所以读《风》者,火齐不夜,枕中可得而秘与?是宜广其读,以与《三百篇》同不朽矣。”如果没有闵梦得与戴氏的官场交游,闵齐伋就不可能得到戴氏《读风臆评》,也就不可能产生风行海内的《读风臆评》闵齐伋套印本。闵梦得在南京为官时,与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孙鑛交游,因得其所评《春秋左传》《文选》,交由自己两位兄弟刊行。闵齐伋万历四十四年(1616)所刊《春秋左传凡例》第七则云:“大司马孙月峰先生研几索隐,句字不漏,其所指摘处,更无不透入渊微,岂唯后学之指南,即起盲史而面证之,当亦有心契者。家翁次兄为水部留都时,遂得手受于先生,不敢自秘,用以公之同好。”又,闵齐华天启二年所刊《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之《凡例》云:“大司马孙月峰先生博览群书,老而不倦,兹评则其林居时所手裁也。仲兄翁次,宦游南都,先生手授焉。”可见,齐伋所刊孙氏评点本《春秋左传》、齐华所刊《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也都是闵梦得交游官场所得。另外,闵氏所撰所刊诸书,也会通过仕宦的闵梦得传播到政界各官员手中。如叶秉敬序闵元衢著作曰:“往予与闵昭余公同在冬官时,得康侯手书,并得《(欧余)漫录》诸刻而读焉,予辄赏心而不能自已。兹复得《草堂赓咏》与其《咫园吟》而反复讽诵,若有一阵清风,不知何自而来。”总之,正如董捷所言,“梦得的官场交际,对于提高其家族刻书的质量并扩大影响,是有相当帮助的”[97]。
而从四大望族所编刊的书籍序跋来看,凌稚隆、茅维、闵元衢、凌濛初、凌启康等的交游都很广泛。如凌稚隆,除前面提到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外,还有以下11人。
1—2.金学曾与张之象。凌稚隆编刊的《史记评林》,有他本人识语,曰:“乃伯兄稚哲、友人金子鲁来自国门,获所录诸名家批评总总焉,私窃艳之。而云间张玄超持所纂发微者,造余庐而印证也。”其中金子鲁,名学曾,钱塘人。善草书。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福建巡抚。金氏与凌稚隆伯兄凌迪知亦有交游,《国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三收有金氏《与凌稚哲(迪知)》尺牍两通。
张玄超,名之象,别号碧山外史,上海人。出身簪缨之家,祖萱为湖广参政,父鸣谦为顺天通判。张之象自幼颖异,曾游学南京,与前辈何良俊、黄姬水等赋诗染翰,才情蕴藉,为时贤所推许,与文征明、董宜阳、彭孔嘉等为莫逆交。后由太学生入赀为郎,授浙江布政司经历。为人耿直,罢官家居后,闭户著书,冬夏不辍,诗文均有声名。曾协修万历《上海县志》,品叙详雅,为世所重。其撰述不下千卷,有《韵学统宗》《诗学指南》《彤管新编》《古诗类苑》《唐诗类苑》《唐雅》《回文类聚》等。张氏亦好刻书,“其室经籍纷披,客来无坐处”[98],与凌稚隆可谓志同道合。
3.范应期(1527—1594),字伯祯,号屏麓,湖州府乌程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状元,官至国子监祭酒,著有《玉拙堂集》。范应期曾为凌稚隆《五车韵瑞》作叙,曰:“自经史以及诗歌,凡名儒、硕卿、骚人、处士绮思玮句,莫不依韵而甄裁之,使采拾者如入邓林,泛瑶海,金波 羽,无非异光,驱使古人,俨然南面而门内外坐之,真洋洋大观也。”亦曾为凌氏《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作序,曰:“余友凌以栋氏,笃古耆修,下帏发愤,业已校评班、马二史,梓行海内,播诵艺林颇久。顷复潜心左氏,搜集群书,阅五载而成。”凌稚隆卒后,范应期为之作像赞及《鸿胪寺磊泉公传》,该传就是对凌稚隆一生编刊活动的记载:从《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到《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再到《五车韵瑞》《文林绮绣》[99],最后辑《三才统志》,未竟而卒。
羽,无非异光,驱使古人,俨然南面而门内外坐之,真洋洋大观也。”亦曾为凌氏《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作序,曰:“余友凌以栋氏,笃古耆修,下帏发愤,业已校评班、马二史,梓行海内,播诵艺林颇久。顷复潜心左氏,搜集群书,阅五载而成。”凌稚隆卒后,范应期为之作像赞及《鸿胪寺磊泉公传》,该传就是对凌稚隆一生编刊活动的记载:从《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到《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再到《五车韵瑞》《文林绮绣》[99],最后辑《三才统志》,未竟而卒。
4—5.王宗沐与蔡汝佐。王宗沐(1524—1592),字新甫、敬所,号撄宁子,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与李攀龙、王世贞辈相友善,有《敬所文集》等。凌稚隆刊行《汉书评林》时,曾通过友人蔡大节问序于王宗沐[100],王氏因“述其大者,以复凌君,使刻焉”[101]。《国朝名公翰藻》收有王宗沐与凌稚隆尺牍一札,乃回复凌氏刻《汉书评林》求序之事,曰:“高贤家学,文藻丕振,《汉史》重刻,不自措手,而以付拙工,海内览之,其谓公何?翰音下逮,适抱疴山中,方欲与赤松为侣,而归使又迫使蹇浅,益艰于报命。尚祈蔡君归时,或能勉卒请教也。”[102]此“蔡君”即王氏《刻汉书评林叙》所言替凌氏求序的蔡大节。王宗沐尺牍又曰:“冲寰每会,辄道及大雅。”按:明代万历间新安蔡汝佐,字元勋,号冲寰,善画,尤工诗意图,亦能刻版画,当时传奇图像多为其所画。凌刻本戏曲插图多出自新安版画家,因此号冲寰的蔡汝佐有可能即王氏尺牍所言之“冲寰”。而从王序与尺牍上下文来看,这个“冲寰”应是替凌氏来求序的“蔡君”“蔡生大节”,但目前还未找到蔡汝佐又字大节的文献依据。
6.何洛文,字启图,河南信阳人。何景明孙。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曾为凌稚隆所刊《汉书评林》作序,曰:“先是吴兴凌子稚隆镂《史记评林》,海内学士读而赏者半,病者半。凌子意不自持,间以问余”,“余为之说”,而“凌子爽然释,坚然信,归复镂《汉书评林》,而以余言弁其端。”可见,两人有交游。
7.陈文烛(1525—?),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北沔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1565),官至南京大理寺卿。有《二酉园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四卷、《续集》二十三卷。陈氏序凌稚隆《汉书评林》曰:“吴兴凌以栋博学善藏书,承其先大夫季默与其兄工部郎稚哲之训,作《史记评林》,复取《汉书》者而汇次之。”工部郎稚哲,即凌迪知,亦与陈氏有交游,《国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三就收有陈氏《与凌稚哲(迪知)》尺牍两通。
8.茅坤,同郡归安人,与凌稚隆关系密切。《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五有《与凌太学书》,“凌太学”即凌稚隆。茅氏曾先后为凌稚隆所刊《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作序。茅氏对《史记评林》溢美有加,曰:“兹编也,殆亦渡海之筏也。而后之读其书,想见其至,当必有如古人所称‘湘灵鼓瑟于秋江之上,曲终而人不见’者。”[103]茅氏《刻汉书评林序》曰:“凌太学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诸家读《史记》者之评,属序而梓之,已盛行于世矣。世之缙绅先生嘉其梓之工,与其所采诸家者之评,或稍稍概于心也,复促之《汉书》为一编。工既竣,复来属予序之。”[104]作为唐宋派领袖,茅氏之序跋,对凌氏书籍的传播行世当有促进作用。
9.徐中行(1517—1578),字子舆,一作子与,号龙湾,浙江长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明“后七子”之一,与长兴县丞吴承恩友善,著有《天目先生集》等。徐、凌二氏是世交,徐中行与凌约言多有尺牍往来,是凌稚隆父执。其《史记评林序》不仅指出了凌氏的史学传统,而且盛赞凌稚隆之史才:“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默(凌约言)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凌迪知)所录,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马之后。观乎所裒次,其才可概见已。使金匮石室,其自成一家言,何如哉!”
10.王兆云,字元桢,湖北麻城人。万历二十九年前后在世,著有《词林人物考》《碣石剩谈》等。王氏在给凌稚隆万历十一年刊《汉书纂》所作序中,自称“楚黄友弟”,盛赞友人凌氏“闳材兼总,其于编摩家,盖能博约互为用”,并勾勒了凌氏一生编刊事迹。先是“《史(记)评林》成,艺苑大匠便之”;又因“虑博士子弟未便也,复辑《史(记)纂》”;“乃者《汉书评林》成,以栋复辑《汉书纂》,亦如《史(记)纂》也者”;《汉书纂》杀青后,又“大搜古今竹素类缀之,命曰《三才志统》,即《汉书》不过其畸支耳”。
11.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小草斋主人,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任湖州推官,天启元年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为闽派诗人代表,有《小草斋集》。凌稚隆刊《五车韵瑞》请其作序,而谢氏笔记《五杂组》对晚明湖州刻书特点、凌氏刻书的射利特征均有论述。
书籍刊刻出版时,请当时名公巨卿作序,以提高书籍的知名度,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能请到什么人,请到多少人,还得看家族与出版者本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之高下及其交游的广泛程度。如编刊家闵齐华崇祯庚午以岁贡为常熟训导,成为钱谦益的父母官。钱氏与陈必谦曾为之撰《虞司训去思碑记》,曰:“推租却贽,诸生凛凛受绳,感佩无 。葺宫墙,复书院,赙僚友,俸薪不给,佐以橐资。”[105]有这样的交游作基础,闵齐华所纂《文选瀹注》(即《孙月峰先生评文选》)由钱谦益作序就顺理成章[106]。又如崇祯四年(1631),凌濛初出游福建,请到了何万化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作序,并于是年刊行。何万化,字宗元,上海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时任福建提学副使。其《圣门传诗嫡冢序》曰:
。葺宫墙,复书院,赙僚友,俸薪不给,佐以橐资。”[105]有这样的交游作基础,闵齐华所纂《文选瀹注》(即《孙月峰先生评文选》)由钱谦益作序就顺理成章[106]。又如崇祯四年(1631),凌濛初出游福建,请到了何万化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作序,并于是年刊行。何万化,字宗元,上海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时任福建提学副使。其《圣门传诗嫡冢序》曰:
西吴凌子初成,穷经嗜古,尝以合子夏序为《孔门两弟子言诗翼》,已深玩笃好。更合《鲁诗》毛传、郑笺诠正,以己意名曰《圣门传诗嫡冢》。寅长潘昭度先生,其戚也,居闽,尝出示余索序。予始而愕,继而喜,渐觉其义味之有沁于予心也。
可见,凌濛初之所以能请到何氏作序,凭借的是其在福建任职的亲戚潘曾纮的关系。在为四大望族所刊书籍作序跋的当时政治文化名流中,像闵齐华与钱谦益、凌濛初与何元化、凌稚隆与王世贞、陈文烛、王兆云等的交游,均有一定文献资料为证,但更多的是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然而不管情形如何,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这些序跋作者与四大望族间一定有某种社交关系。
据笔者初步统计,现存的四大望族出版物之序跋与凡例,共涉及四大望族编刊成员与155人次的交游,参见本书所附《四大望族出版物之序跋凡例所涉与名人交游关系表》。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四大望族出版物中名人序跋涉及的该名人与四大望族成员的交游;二是四大望族出版物中编刊者本人或亲属序跋及凡例所揭示的望族成员与名人的交游,以及望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助。另外,还有个别情况是,刊本已佚,但通过散见于名人别集中的四大望族出版物序跋,或编刊者与名人往来尺牍中的信息,我们知道该名人曾为某个刊本作过序跋。
《四大望族出版物之序跋凡例所涉与名人交游关系表》不能反映的一种情况是,某刊本的名人序跋文字虽未反映与编刊者交游关系,但基本上能确知其序跋是为本刊本所作。如辽图[107]藏套色本《东坡志林》五卷扉页右上角有“闵”印、左下角有“遇五氏”印,据此可判定该书为闵齐伋刊,而该书有沈绪蕃《东坡志林小引》,沈氏为湖州人,给凌汝亨、闵于忱等人刊本作过序,是闵齐伋同时代人,因此可确定沈氏该小引当为闵齐伋刊本《东坡志林》所作。又如闵振业、闵振声刊《东坡文选》有钟惺万历四十八年序,而钟惺又与闵氏家族闵宗德有交集,所以钟氏序也很可能是为闵氏刊本而作。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尽管如此,《四大望族出版物之序跋凡例所涉与名人交游关系表》已足以见出四大望族编刊活动背后所存在的社交关系网络的庞大,而这个庞大的社交关系网络既是四大望族提高编刊活动知名度、立足出版市场的重要支撑,也体现了四大望族编刊活动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某些刊本的旧序旧跋由刊刻者聘请当时名人或书法家书写,这也反映了望族编刊者的社会交游关系。其中松陵盛文明[108]、乌程冯年是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人。如凌濛初刊《苏长公表启》之钱槚序、凌弘宪刊《楞严经证疏》之乐纯跋、凌弘宪刊《会稽三赋》之陶望龄序均为盛文明所书;茅一桢刊《花间集》之欧阳炯序、茅一桂刊《唐宋八大家文抄》之顾尔行题辞、茅一相刊《欣赏续编》之顾元庆《大石山房十友谱序》均为冯年所书。
另外,从一些刊本的校订评阅者,亦可考察四大望族的社会关系,如凌湛初《申椒馆敝帚集》由王穉登校,凌濛初刊《圣门传诗嫡冢》由潘湛校订,茅献征刊《吴兴掌故集》由“延州布衣吴梦旸阅”,茅一桂辑《史汉合编》署“同郡陆弘祚校”等。又如凌濛初撰刊《孔门两弟子言诗翼》,其校阅者有沈汝法、潘湛、凌瀛初、凌义渠等;茅震东刊《新镌武经七书》,其参阅者有余姚王承锦 父、乌程闵昭明伯弢、归安潘荣铨子仪、归安施元熊尚父等。
父、乌程闵昭明伯弢、归安潘荣铨子仪、归安施元熊尚父等。
[1] 以上据《闵谱》之《坊表志》。
[2] 见《闵谱》之《荐绅纪》。
[3] 晟舍黄、闵二氏有血缘关系。南宋时,闵将仕之子闵德源曾入赘晟舍黄氏。德源生衍(从黄姓),衍第五子逊(从黄姓),过继给闵天福,归宗复闵姓,是为闵珪高祖。
[4] 民间有闵氏尚书四个半之说,另半个,或以为是工部尚书严震直,他是闵珪的外大父。
[5]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盛事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页),言闵珪、闵如霖为“叔侄尚书”,然据《闵谱》,闵珪为八世,闵如霖为十世,乃叔祖从孙关系。
[6] 见《闵谱》之《著述录》。
[7] 入清后还有闵广《国华录》、闵文山《诵芬录》等。
[8] 以上均引自《闵谱》之《著述录》。
[9] 进士闵宗德也是闵如霖曾孙。
[10]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有明清时期部分江南名镇进士与举人数量统计,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晟舍与这些名镇相比,也不逊色。
[11] 据《练溪文献·墓域》,凌贤、凌晏如父子的墓在练溪永亭村藏字圩,东西异域,康熙间被盗掘发,遂湮。
[12] 若据《嘉庆凌谱》统计,从元代凌时中到明末,凌氏登仕版者有近100人,但这里包括由凌懋翁十六子播迁的其他支凌氏,而不纯是晟舍支系。
[13] 《晟舍镇志》卷五《人物》。
[14] 《晟舍镇志》卷五《人物》。
[15] 据《顺治凌谱》之《明都察院安然公第五子怡云公晟舍支世系》统计,晟舍凌氏从凌敷(1424—1511)到顺治间,有男性300余人。
[16] 另有清初举人3人,他们是:茅张琛(武举),字子昭,茅允昌子;茅启光,字升扶,茅栻子;茅煐。贡生9人,他们是:茅允庆,顺治乙酉岁贡,字子建,瑞征子;茅棻,顺治壬辰岁贡,字芳茹,任教谕;茅元铭,顺治辛丑岁贡,字鼎叔,任陕西朝邑知县,坤孙;茅曙光,康熙间贡生;茅乐,康熙间贡生,允隆子,字吉人;茅栻,康熙丙戌贡生;茅应奎,康熙庚子贡生;茅锡兰,康熙间贡生;茅星来,康熙间贡生,曾勋孙。封荫者2人,他们是:茅允修、茅丕承父子,以茅煐赠知县。又据《归安县志》卷三十二,清初茅氏有两名武举进士,他们是:茅兆吉,顺治九年壬辰进士(顺治八年辛卯举人);茅世膺,顺治十二年乙未进士(顺治十一年甲午举人)。
[17] 明代茅氏有两名庠生收入《练溪文献·列传》,他们是:茅遇,字于巷,号介川;茅霞杲,兆河子,字扶光。
[18] 臧氏明清两代有十七人建有专祠。
[19] 臧应奎时代,湖州有一批理学名人,湛若水《礼部精膳清吏司主事贤征臧公墓志铭》曰:“余求志于圣人之学者,于天下仅数百人,得其门者几人。其在湖州,自吾贤征之外,有若评事韦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枢、陈忠甫良谟。其在广之顺德,则有仪制主事张景川澯。澯与应奎以诤礼跪门,同死于杖。商臣以言礼刑,落职清江丞;枢亦以论大狱,褫职编管。良谟虽不死,亦病且去。”
[20] 《臧谱》卷五《敕赠文林郎臧铁崖公暨元配周孺人合葬墓志铭》。
[21] 《臧谱》卷五《敕赠文林郎臧铁崖公暨元配周孺人合葬墓志铭》。
[22] 《臧谱》卷二《明故两京工科都给事中升河南布政司左参政澹庵臧公乡贤录》。
[23] 《臧谱》卷三凌义渠《臧孝廉传》。
[24] [日]佐藤仁史:《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25] 除允仁岳父未知外,其他三人岳父依次是:举人闵道鸣、布政司经历闵允庆、进士邵武知府闵世翔。其中闵允庆之子一栻、闵世翔之子元衢均为编刊家。闵洪学是世翔之子,凌义渠是洽初之子,也就是凌义渠之母与闵洪学是亲兄妹。
[26] 其岳父名字依次是:闵大纲、闵世文、闵振胄、闵晋德、闵完生、闵宗圣。
[27] 其女婿名字可考的是:楷——闵寅生、琛——闵皋、启康——闵廓正、义渠——闵南仲、义康——闵昶、义远——闵士瑛、汝亨——闵允锡、汝樑——闵元赏、翘椿——闵象泰、森生——闵完孟、森发——闵中琛。
[28] 两诗均见同治《晟舍镇志·杂记》。
[29] 冯梦桢:《快雪堂集》卷二十八《乙巳十月出行记》,《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64册,第419页。
[30] 臧懋中、臧懋德分别是臧懋循从兄、兄。
[31] 《臧谱》卷四沈圣岐《广西按察使佥事静涵臧公暨元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铭》。
[32] 闵声女适臧焘。
[33] 《臧谱》卷四《闵洪学孙孺人奠章》。
[34] 见《臧谱》卷四《奠章》。
[35] 世基早卒,无子,“闵以庚申随父任,殁于晋署”。见《臧谱》卷五臧尔炳《腾字号圹碑记》。
[36] 臧焯如与凌洽初连襟,闵元衢、元京是他们妻兄或妻弟。
[37] 《臧谱》卷一臧基鲁《闵母行实》。按:臧焯如继娶之妻亦闵氏。
[38] 上海图书馆藏《兵垣四编》臧懋循跋曰:“因手辑诸编,而附以《边海图论》,汇为六卷,存之箧中,以俟知兵者识兵机之有在。”又闵声跋曰:“曾于先渭阳晋叔氏手受诸编。”又闵暎张跋曰:“兹汇而梓之以传者,则张从父襄子氏也。……而张不敏,得共刊阅,书成辄志数语。”又天启元年陈继儒跋曰:“臧晋叔酷好此书,高卧山中,批阅点定,悠然有隆中抱膝之思焉。闵襄子得之,因付剞劂氏。”
[39] 闵暎张乃闵暎璧之弟。
[40] 董说娶闵洪得女;董樵娶闵光德之子闵启女;董牧娶闵元衢子闵三台女;董耒娶闵齐华之子闵广生女,闵维申女亦嫁董耒;董舫娶闵洪觉之子闵晖吉女。
[41] 闵元衢子三台娶董斯张女,闵声继子晃娶董说女。
[42] 闵世魁曾语朱国祯曰:“子,闵婿也;汝子,又我婿也。”见《闵谱》之朱国祯《万历戊申谱序》。
[43] 另外,刻书家闵昭明之母乃马腰沈氏。
[44] 闵文齐弟闵梦得、闵齐华、闵齐伋均是闵氏编刊活动家。
[45] 闵齐伋刊《唐孙职方集·跋》:“家有写本,为吾亡友潘昭度所遗,存箧中久矣。”
[46] 这种联姻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闵若孩对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竹溪沈涵曰:“子为我姑所出,且族婿也。”见《臧谱》之沈涵《康熙己丑续修藏谱序》。
[47] 《臧谱》卷五《明故敕封安人臧母吴氏墓志铭》。
[48] 见《臧谱》卷一。
[49] 见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50] 见同治《晟舍镇志》卷七《艺文》之王世贞《聚芳亭跋》。
[51] 见同治《晟舍镇志》卷八《艺文》之王世贞《甲申十同年图书后》。《甲申十同年图》所绘乃明天顺八年(1464)十位进士。此十人均为当时朝廷重臣: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吏部左侍郎焦芳、户部右侍郎陈清、礼部右侍郎谢铎和工部右侍郎张达。其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任职,王轼则在南京任职。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适逢王轼来朝,十人在闵珪宅中聚会,其后特请画工绘制群像,并各自题诗纪念。在六十七年之后,闵一鹤、一琴持此图示王世贞,王氏因为之跋。
[52] 见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四《南京刑部郎进朝列大夫藻泉凌君墓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
[53] 见同治《晟舍镇志》卷六《著述》“《史记评抄》”条。
[54] 其中《叹逝录序》,为润初卒后,凌湛初托俞氏请王世贞所作。凌湛初《上王观察元美》:“曩俞君之以《叹逝》序请也,谓先生当噤吟哦也,而先生乃许我也。”(《国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606页。)又王世贞《与凌玄旻》曰:“昨从匆匆中叙《叹逝》,乃足下加灾于木矣。今复欲序《薄蹄书》,何足下之偏嗜也。”(《国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110页。)按:《薄蹄书》,《晟舍镇志》卷六《著述》作“《赫蹄书》”。
[55] 《晟舍镇志》卷六《著述》。
[56] 《国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二王世贞《与凌以栋》,《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110页。
[57] 参看冯保善《凌濛初家世述略》,《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
[58] 见《顺治凌谱》卷六范应期《鸿胪寺磊泉公传》。
[59] 见《晟舍镇志》卷六《著述》。
[60] “子与”即长兴徐中行,与王世贞同属明代后七子成员。徐氏与凌迪知之父凌约言有交游,《国朝名公翰藻》卷三十四收徐中行《与凌藻泉(约言)》尺牍两通,卷三十八收凌约言《简龙湾徐比部(徐中行)》《简龙湾》尺牍两通。
[61] 见凌瑞森、凌南荣(楷)刻朱墨本《唐诗广选》之凌濛初序。
[6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4辑影印北图分馆藏本《李于鳞唐诗广选》乃凌瑞森、凌南荣刊本,却题为李攀龙、凌弘宪辑,盖受到《四库提要》著录的影响。
[63] 见凌刻六卷本《世说新语》之凌濛初跋。
[64] 沈荃:《重刻世说新语鼓吹序》,转引自潘建国《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65] 见《练溪文献·艺文志》。
[66] 见臧懋循《元曲选序》,《臧懋循集》,第114页。
[67]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备兵大名道鹿门茅公行状》,《茅坤集》,第1349页。
[68]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备兵大名道鹿门茅公行状》,《茅坤集》,第1349页。
[69] 章嘉祯:《南京国子监博士臧顾渚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章嘉祯《墓志铭》),《臧懋循集》,第179页。
[70] 见汤显祖《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汤显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04页。
[71] 《晟舍镇志》卷五《人物》“闵宗德”条。
[72] 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六《朱无瑕传》:“己酉(万历三十七年),与泰玉结吟社者凡五,所集皆天下名流,粤之韩、楚之钟、吴之蒋若陈若俞、越之吴若凌、闽之二林。”其中“楚之钟”即钟惺;“越之吴若凌”中的“凌”即凌濛初。
[73] 见茅维《十赉堂丙集》卷五《甲子重九集葛震甫、于鳦先、王开美、周安期、谭友夏、程应止、张葆生、沈定之、沈不倾、凌初成、侄厚之郝姬月娟邸中,限赋八韵,分得深字》。
[74]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9页。
[75] 王穉登:《清苕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5册,第106页。
[76] 赵红娟:《淩濛初交游新探》,《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另外,赵红娟所著《拍案惊奇——凌濛初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9页)中亦有同样错误,一并改正。
[77] 湖州书商顾某曾从海宁访得一批古籍,缪氏手抄本《王百穀先生集外诗文》是其中之一,笔者曾有幸一阅,并抄录了书中《祭凌常州文》。
[78] 王穉登:《清苕集》卷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5册,第118页。
[79] 王穉登:《清苕集》卷下《重游且适园怀故凌使君稚哲》,第118页。
[80] 凌濛初:《南音三籁》卷下收有无名氏小令《月云高·闺怨》,凌氏按语云:“《吴骚》注以王百穀,非也。百穀与余交,生平未尝为曲。”见《凌濛初全集》第四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8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82页。
[82] 《嘉庆凌谱》卷三《荣赠录》。
[83] 《嘉庆凌谱》卷三《艺文录》。
[84] 《顺治凌谱》之《明故练溪先生元配王夫人合葬墓志铭》。
[85] 《嘉庆凌谱》卷三《艺文录》。
[86] 《嘉庆凌谱》卷三陈良谟《简藻泉比部公》。
[87] 《嘉庆凌谱》卷五《碑志》之刘麟《学博练溪公墓志》。
[88] 尚书公指凌约言。以曾孙凌义渠殉难,凌约言被追赠为太子太保、刑部尚书。
[89] 见《嘉庆凌谱》卷五《碑志》。
[90] 《嘉庆凌谱》卷五《学博练溪公墓志》:“夫人,广东琼台宦族,今户部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按:唐胄,字平侯。
[91] 见《嘉庆凌谱》之《艺文录》。
[92] 汉章孙仲郁第三子曰士麒,娶沈秱长男沈规甫之次女。
[93] 见万历八年沈秱《双林凌氏族谱序》。
[94] 即双林支凌瑄,太医院御医,卒于隆庆二年。
[95] 凌濛初刊《西厢记·凡例十则》。
[96] 参见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收入《郑振铎全集》第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574页。
[97] 董文,第92页。
[98]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shanghai/node54197/node54199/node63622/userobject1ai52020.html.
[99] 《文林绮绣》由凌迪知编刊,凌稚隆大概亦参与其中,故范氏及之。
[100] 王宗沐《刻汉书评林叙》:“因友人蔡生大节而问序于余。”见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刻本《汉书评林》。
[101] 王宗沐:《刻汉书评林叙》,见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刻本《汉书评林》。
[102] 见《国朝名公翰藻》卷二十四王宗沐《与凌以栋》,《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3册,第746页。
[103]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十四《史记评林序》,《茅坤集》,第478页。
[104]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十四《史记评林序》,《茅坤集》,第494页。
[105] 见《晟舍镇志》卷五。
[106] 序中,钱谦益频以“先生”称闵齐华,而自称“虞乡老民”。
[107] 辽宁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分别简称辽图、国图、上图、南图、浙图;其他××省、××市、××单位,是指该省、该市、该单位图书馆;各大学在无歧义的情况下用简称。
[108] 号盛山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