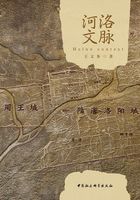
第五节 郭泰机《答傅咸》诗的成就
郭泰机(239—294),西晋诗人。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西郊涧水东岸)人。出身寒门,有才气,能诗。《文选》存其《答傅咸》诗:
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人不取诸身,世事焉所希?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31]
傅咸有《赠郭泰机诗》残篇,今存序,从傅咸诗序文可知,郭诗是请求傅咸给予援引擢拔的干谒诗。干谒诗是古代文人为推荐自己而写,类似自荐信。文人为求进身,给权贵或者名人写诗,希望得到援引,自汉代开始到唐代蔚然成风。相比前代,《答傅咸》第一次以织机下的寒女及其才华自喻,倾诉自己出身寒门而怀才不遇之怨愤,也是古代诗歌史上现存的第一首反省自己的省谒诗,并首开在交际中用女性作比喻的先河。
一 诗歌史上特有的寒女形象
《答傅咸》是一首省谒诗[32]。祈求他人荐举是无奈和心酸的,在唐代为公荐贤的风气形成之前也是不太光彩的,经常会遭到拒绝,或者嘴上答应而实际不予推荐,或者存在虽举荐也不成功的尴尬。所以求人举荐往往委婉道出,或借助写景,如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开头描述洞庭湖壮丽景象和磅礴气势,为后文感叹欲渡无舟做铺垫,曲折表达希望援引之意。钱起的《赠阙下裴舍人》开头描画一幅秾丽的宫苑春景图,烘托裴舍人特殊身份,传达恭维和求援之意。或托物言志,如卢照邻《赠益府群官》和李白《上李邕》,或以鸟自喻,如吴均《赠柳秘书》,或以骏马自喻,如杜挚《赠毌丘俭》和李群玉《骢马》等,而郭泰机诗采用借女言志的比兴手法。
古代女性题材诗歌中,有现实描写女性,有以女性作比兴的,用于比兴的女性多是神女和美女。楚辞以神女比喻诗人的高洁品行,张衡《四愁诗》以美人难寻,诉说追求理想的艰辛;《同声歌》借高贵大方的新娘子献身夫君,比况能臣对君王的忠贞;曹植用思妇表达君臣隔阂的痛苦,用弃妇比喻自己被家庭伦理、政治所弃的悲愤,所用的喻体都是美人佳人。其他如阮籍《咏怀诗》,傅玄《吴楚歌》《拟四愁诗》《明月篇》,石崇《楚妃叹》《王昭君辞》,陆机《拟兰若生春阳》《拟西北有高楼》《塘上行》《婕妤怨》均采用美人做比喻笔法,而郭泰机以现实中位卑才高的寒女做喻体。
唐宋,写贫寒多为反映现实,表达对寒女的同情。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白居易《缭绫》“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红线毯》 “红线毯,择蚕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一丈毯,千两丝”,宋代寇准妾蒨桃的“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贫寒女性的写照。但郭泰机诗所关注的不是寒女辛劳,而是寒女才技不能发挥,善于织纫却不得跻身于织女行列,她急切盼望能亲操机杼,为他人制作寒衣。寒女形象是一个积极入世者,以寒女比喻进身无路的寒士,写寒女美,比喻寒士品行高;写寒女巧,比喻寒士才华过人;写寒女无缘操持机杼,比喻寒士不能进身仕途;写寒女对衣工的怨恨,比喻寒士对选举制度及其执行者的不满。
郭诗强调寒女的才艺不被重视,塑造了一个才华出众却不得志的寒女形象。出身贫寒、地位卑微就是寒女和诗人见弃当朝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共同命运。郭诗以寒女自况后,到唐代时,才较多地出现以贫女自喻。如秦韬玉《贫女》突出贫女和寒士共享的人格美,《贵公子行》中书生的潦倒与贫女的怨诉互相辉映,借咏贫女为寒士鸣不平,邵谒《寒女行》和白居易《议婚》以贫女自伤,来为寒士写照。
二 现存的第一首省谒诗
《答傅咸》不仅是一首干谒诗,而且是一首省谒诗。省谒诗是诗人对干谒活动的一种反省,有抒写干谒成功后感激之情的,而更多是抒发失败后的失落和悲愤。诗题中的傅咸,字长虞,傅玄之子,是西晋名诗人之一,出身世族,先后任冀州大中正、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官职。傅咸和作者素称相知,曾有《赠郭泰机诗》,其诗小序云:“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复非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傅诗现仅存“素丝岂不洁,寒女难为容”及“贫寒手犹拙,机杼安能工”的残句。序言表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而“戏以答其诗”,表达了冷嘲世道,以此声援之意。
傅诗的“素丝岂不洁,寒女难为容”一开始并非比兴,而是借写技艺高超的贫女织出美丽衣服却不是给自己装扮,揭露“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不公平。而“贫寒手犹拙,机杼安能工”的反诘,表现不满世俗成见,肯定寒女才华弥足珍贵。可见郭泰机之前曾经有诗赠傅咸,即傅序“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傅咸回赠诗后他以此诗再答傅咸,所以此诗是干谒系列诗中的一首,也是一首省谒诗。
三 以女性喻体用于交际,突破怨而不怒传统
诗歌用于交际可追溯至《诗经》。《左传》众多赋诗活动中大量使用爱情诗,使赋诗显得风流文雅。春秋赋诗中以爱情喻国家亲善,到《楚辞》中“香草美人”寄托君臣关系,可见春秋赋诗在女性做比喻方面有开创之功。但所赋之诗选取《诗经》已经有的篇目,不是创作,所以与后世文人雅集唱和有区别。自己作诗用于人际交往,典型的是赠答、唱和诗。最早的赠答诗,据文献记载可上溯到西汉苏武、李陵的送别诗。东汉《客示桓麟诗》与桓麟《答客诗》,以及秦嘉与其妻徐淑、贾充与李氏的夫妇赠答,但这些诗多写现实而无比兴,更无借女言志。而用于交际的诗歌首推这首《答傅咸》。
秦汉魏晋诗人多借女性抒发怀才不遇或忠君爱国情感,但均为自我抒怀,而郭泰机是写给傅咸的,向傅咸倾诉抱负难伸的怨愤和渴望用世之情。是朋友间的互相交流,将女性作为象征符号用于文人的交际,将难言的求援之词托于男女兴寄,并且突破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西晋讲究门第,庶族士人仕进艰难。郭泰机以“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比况自己受门第所限入仕无门,而“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况复已朝食,易由知我饥”两句,更体现出空怀才学、无处施用的悲愤,揭露了晋代士庶对立,洋溢一股不平之气,表现出与一般的干谒诗有很大不同。因此,不但引起寒族士人的共鸣,也赢得了一些世族人士的理解和同情。钟嵘《诗品》称“泰机寒女之制,孤寂宜怨”,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把它收入选本,其主要原因应该在于此。[33]
[1]梁中效:《三曹与洛阳述论》,《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2](汉)司马迁:《高祖本纪》,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5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73页。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85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6页。
[6]李希:《郭象哲学与中古的自然审美》,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年,第135页。
[7]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
[8]陈士部:《郭象玄学与文学的自觉》,《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9]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古代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下同。
[10](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以下所引原文均出自此版本。
[11](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第176页。
[12](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88页。
[13](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页。
[14](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15](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16](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17](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页。
[18]成润淑:《〈洛阳伽蓝记〉 的小说艺术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4期。
[19](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
[20](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21](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页。
[22](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下同。
[23](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
[24](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99页。
[25](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26](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
[27](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28](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页。
[29]顾农:《〈洛阳伽蓝记〉 里的文学史料》,《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30]席格:《〈洛阳伽蓝记〉 的美学史价值》,《中州学刊》2017年第12期。
[3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