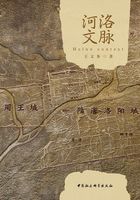
第二节 郭象《庄子注》的文学价值
郭象(252? —312),字子玄,洛阳人。西晋玄学家,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少有才理,慕道好学,好老庄,善清谈。郭象的《庄子注》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庄子》的标准注解,同时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集魏晋玄学之大成,与孕育于洛阳的老庄思想一脉相承,对其后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郭象哲学对自然审美的影响,反映在魏晋文人的创作实践中。东晋、刘宋之际的田园诗、山水诗、禅宗美学与郭象哲学都受到了河洛同一文化脉络的影响。郭象玄学作为一股与主流相异的哲学思潮,给中国美学发展历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 郭象哲学对陶渊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之教,同时也受当时玄学的影响,将生命体验融入诗中。其生命境界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生活经历的积淀,另一方面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底蕴,调和了儒道两家文化。陶渊明生活的东晋年间,正是郭象玄学盛行之时。其“本真”的生命追求与郭象“独化”哲学密不可分。郭象认为各个物类的殊异是因定分所决定,其存在地位是等同的。他肯定每一物的独立存在性,认为生命中最大的负累是羡欲,主张人人都要安分守己。陶渊明的生活平淡而自足,羡欲与他的世界太过遥远。郭象“独化”哲学中“性分”说具有本体论色彩,“性”是一物区别于另一物内在的规定性。“性”的说法产生了万物平等的观念,这种天性授予的本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郭象认为人们只要充分发展自我之“性”,就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庄子注》开篇:“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专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人都有自身特有的“性”,只要将其充分展开,便能获得人生最大的自由乐趣,达到无上的审美之境。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就是随着自然天性而回归田园。有人归隐是为韬光养晦,有人是为躲避尘世喧嚣,而陶渊明是为鸟鱼林草之乐,因此“性分所至”而人生追求相异。
陶渊明深感官场不符合自然之性,为生计又不得不为。在田园生活中,他怡然自乐,找到了精神栖息的场所,他的自然之性自由舒展,实现了精神的自由超越。为了满足自然之性的发展,就必须越名教而任自然,陶渊明在郭象那找到了二者的平衡点,从而完成了归于田园从最初的不得已到心安理得的心理转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成为他出世思想的最好注解,这和郭象哲学的“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庄子·大宗师注》)之说殊途同归。陶渊明的守拙是要返回自然的本性上,是修行于世俗的表现,他既实现了内在的自由,又做到了返回外在的自然。他躬耕的目的不仅仅是收成,还有自己的修养真性情,当然,更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二 魏晋南北朝山水诗深受郭象哲学影响
玄学又被称为“玄远之学”,它凭借对本体的追问,为人的生命自由寻找最终归依。讲究本末体用,虽貌似虚无缥缈,但确为魏晋士人生存境况和心理需求的真实反映。魏晋文人对不自由的社会现实的挣脱和人身自由的渴求,通过“名教”和“自然”、“本末”和“体用”、“有”和“无”的思辨表达了人生的矛盾和痛苦,具有强
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文化内涵。玄学的定位乃本末有无之辨的本体之学。可以说,玄学是魏晋精神的集中体现,是魏晋人超越内心、追求审美理想、实现自由的理论体现。唯有把握住了玄学,才能把握魏晋美学的精神实质。郭象追求自由,但又肯定外在之物是对个性的束缚。在魏晋的历史环境中,复苏的人性对抹杀人独立价值的传统规范的反对,的确是采取了一种荒诞而颓废的形式,并体现为自我意识的扩张,否定外在的束缚,认为只有与大道逍遥和绝对自由才值得尊敬。郭象把这种绝对的逍遥和绝对的精神拉入了现实生活,注入了人间的温情。郭象说的逍遥游,与庄子不同,实指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郭象把庄子的“游心”拉入了世俗生活,他所说的游心不是老庄对天地之道的追求,而是在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对自由存在的体认。
郭象的“逍遥游”把庄子的“逍遥游”改造成世俗化但不庸俗化的人生哲学,并使得这种“逍遥游”流行于六朝文人间。东晋以来,游赏山水之风逐渐兴盛,和郭象玄学流行有直接关系。依庄子之说,方内的人饱受礼法束缚,痛苦而不能自拔,而方外的人缥缈无为,弃绝俗物,享受着真正的无限自由。郭象一反此说,认为方内人只要通过自身修行便可自如兼得。郭象改造了庄子,摆脱吸风饮露的神人,将虚构的超现实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郭象身居庙堂而心同于山林,士人的逍遥可以在出世和入世中自由获得,这是郭象对“逍遥游”的现实复归。
郭象的逍遥是万物在具体生命形态中,在现实的生活中实现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这显然比庄子的超拔要实际容易得多。一方面,郭象将“名教”与“自然”、“游外”与“弘内”相融合,使出世入世均可以效仿;另一方面,山水自然作为入世之人修行的途径和场所开始备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山水游赏极盛一时,为山水诗的出现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自然中感悟天地间生机勃勃的生命流荡,并自由舒展情性,从而得到审美满足,对这种存在方式,是郭象首先以明确的哲学语言加以肯定的。其深远意义在于肯定了万物生机与个体生机相感应的双向关系,从而山水游赏成为中国文人的重要审美方式。面对纷纷扰扰的尘世,山水自然是洗涤心灵的最佳空间,大自然的自然而然是无心状态的最好写照。我们从中也可看出,东晋山水游赏之风以及后来山水诗的兴起,其精神内蕴与郭象玄学密切关联。
郭象作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了魏晋时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其思想深深渗透于后来的美学著作和文学创作。郭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表面上看是一种人生哲学,其实它开创了一股新的审美思潮,改变中国美学的发展趋向。以境界为审美本体的中国传统美学,在思考和建构人生意义上建立起来,它有落实于人生的特点。郭象提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为审美生存提供了宝贵资源,深刻影响了六朝文人的文学创作。郭象重视个体价值和自然生命的原发精神,以哲学思辨表达了对人生意义和生死命运等问题的思考。
汉代重经世致用而轻视人的情感,人们在实践和观念上都与自然隔着一层,自然之美只是政治伦理观念的外在体现。魏晋玄学将士大夫从烦琐的经学束缚下摆脱出来,带来了个性解放和个性主义高扬。郭象哲学的掺入,以万物为各自独立的生命实体,又带来了自然的解脱,山水自然由此以独立审美对象的姿态出现,自然山水变得风情万种,成了文人可亲近的朋友。于是,中国诗歌创作一改将自然万物作为背景和道德比附的表现方式,首开山水即道和山水即天理的咏物之风,真正把自然感性引入审美殿堂。魏晋文人在思辨的道路上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之美。[6]
三 郭象玄学促进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玄学作为一种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社会思潮,对当时的社会心理,以及文化形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具体语境中与特定历史发展状态相联系,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轨迹:由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到元康年间的“崇有论”,再到永嘉年间郭象的“独化论”。郭象消除“贵无”派和“崇有”派的对峙,论证自然与名教统一,综合各派主张,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郭象《庄子·齐物论注》)的命题。使有与无、言与意、现象与本体、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对立在理论形态上得以解决,使魏晋玄学本体论达到顶峰。“极大地提高了哲学的抽象思辨性,它影响各种精神领域,自然也有助于提高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思想水平。”[7]对玄学与文学的关系,钟嵘、刘勰做过精到的论述,“永嘉时,贵黄老,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循务之志,崇盛玄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玄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微妙复杂,玄风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自然会波及诗歌风格,但抽象思辨的玄学却往往妨碍探究文论。专注于玄理思辨的正始文人,极少有文学理论的探讨。到了西晋,探讨文学理论的风气才开始兴起。“贵无”的玄风无益于文学的生长,抽象僵硬的理论很难切实对文学的研究,这由正始玄学的品格所注定。郭象以注《庄子》为依托,整合众家之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以全新品格对文学理论探讨,促使文艺自觉,从而在郭象《庄子注》同时或稍后出现了《文赋》和《文心雕龙》。
文学自觉和文学理论的自足与完善,对文学审美本质和文学思维规律的探讨需要感性审美主体的确立。汉末建安时期,儒学式微,名教松动,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建安风骨”“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的文论主张提出,个体意识张扬,重情感、以悲情为美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但正始文人对无的形而上的思辨,对圣人之情的一味效仿,窒息了弥漫着美学精神的社会风气。郭象玄学贬抑圣人之情,提出“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庄子·胠箧注》),主张“人各自正则无羡於大圣而趣之”(《庄子·德充符注》),并基于“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庄子·齐物论注》)的思想,提倡适性逍遥和率性自然。郭象的观念中,自然与名教相统一,主体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神人与圣人、常人相统一。把感性的审美的主体从思辨的形而上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把人生从儒教工具理性约束里解放出来。通过对思辨哲学理性与政治工具理性的双重批判,捍卫了主体的独立地位,从而完成对审美主体的理论建构。这对文学自觉,对探讨文学审美创造和审美价值有着极其深远的启发意义。
陆机的《文赋》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专论,分析创作主体的“感物”“缘情”和“托言”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道家思想为指导。陆机仕晋来到洛阳,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到郭象玄学影响,虽无具体史料佐证,但其诗学思想和对“感物” “缘情”心理特点的描述,与郭象玄学对诗化审美主体论述内在一致。郭象“适性逍遥”“率性自然”主张和对主体性的肯定,为陆机等人构筑文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是文艺真正走向独立自觉的基本前提。刘勰强调的“性灵”是能感物吟志的感性主体,与郭象“适性逍遥”“率性自然”和陆机“感物”“缘情”说一脉相承。文学本质论的建立和完善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无、本末、体用和言意是玄学论辩的核心问题,这些范畴已由老庄的宇宙生成论被移置到世界本体论,并由言意为中介与文学本体论联系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学观念的转化。在有无、本末等问题上,郭象作出了综合性的独特阐释。刘勰之所以能将“心”与“道”统一于理论体系中,所借助的正是自然范畴。由此,他在《原道》开篇就将“文之德”推崇到“与天地并生”的高度。刘勰“自然之道”与郭象万物“块然自生”的“齐物论”思想,以及他的“天地之心”与郭象“极两仪之至会”的“圣人之心”(《庄子·逍遥游注》)蕴涵一致。以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理论解读刘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篇》)等文论名句,就会豁然开朗。
文学自觉在于文学主体审美意识的独立,在于文论自觉地对文学内在规律的考察与探讨。总之,只有在郭象玄学的理论语境中,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两部文论著作的问世才有可能;正是郭象玄学为中国文学从两汉文学的逐渐自觉,到魏晋文学创作与文论的全面觉醒,提供了丰厚的理论依据和明晰的审美判断尺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