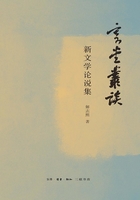
疑义相与析:“毛戴”到底是什么意思?
拙文《“毛戴”的影射问题》是对陈建华先生的《章秋柳:都市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的一点商榷。文章寄给《上海文化》时,我曾经提请编者,“方便时,刊布前请贵刊知会陈建华先生,请他哂正——或许我误解了他也未可知”(2007年10月11日晚致编者函)。过了一个多月,未见陈建华先生的回应,我便接受编者的建议先发表了拙文。
今天终于接到了编者转来的陈建华先生的答辩文章《“毛戴”即“模特”?——答解志熙君“说文解字之疑义”》。陈先生在答辩中承认我的批评——说他的文章“显然无疑地将‘毛戴’和‘毛泽东’关联了起来,力图引导读者相信茅盾确在借此讽喻毛泽东”——“这样的一种理解也无不可”。这使我如释重负,总算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尽管陈先生强调自己的观点“更多的是怀疑”,所以下笔不免“踌躇”,但其实他在明知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并不迟疑地将影射的“怀疑”引向了毛泽东,而又运用着很不可靠的“情色的讽喻”的阐释方法——从“她的光滑的皮肤始终近于所谓‘毛戴’”这样一句描写女性体肤的话里,抓住一个比较“费解”的词“毛戴”,居然大胆地假设这是在影射毛泽东,这正是陈先生的“情色的讽喻”的阐释方法之表现,而也正是我那篇小文所要质疑的问题。对此,陈先生现在的答辩并不足以解除我过去的疑虑。现在的我仍然认为他的这种解读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曲解和显然过度的阐释。
至于说“毛戴”即model,乃是我在文末顺手提出的一个替代性的解释。其实我对model并无专门研究。拜读了陈先生对model翻译史的梳理,我很受教益,并愿意坦率地承认,拙文说“‘毛戴’肯定是指模特而非影射毛泽东”,虽然后面的“非”未必非,但前一个“肯定”显然武断,对我的武断给陈先生的伤害,我深感抱歉。而说来可笑的是,我的武断倒也在无形中受了陈先生的“情色的讽喻”阐释思路的启发,并且陈先生说“毛戴”一词“令人费解”,也使我误以为他已经翻检过中文辞书、确证“毛戴”在中文中无解,于是我对“毛戴”的解释也便只从外来语词的音译角度考虑,以至于武断地做出了那样想当然的误断。
有错就应该纠正,不论是我的还是陈先生的。说“毛戴”即model,毕竟是我的武断,陈先生不能替我负责任,而我确乎有责任按陈先生的要求给出几个例证。然而,现在却已经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这并不是我要推脱责任、掩饰错误,而是我发现“毛戴”这个词另有其解。
其实,陈先生和我都忽视了“毛戴”这个词古已有之,意即“寒毛竖立”,一般用来形容人的恐惧震惊,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盗侠》:“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睹者无不毛戴。”并且我们也都忽视了茅盾不止一次用过这个词,如《三人行》:“惠简直狂笑了,笑声是那样磔磔地令人毛戴。”这古今两例“毛戴”都是令人惊恐之极而不禁寒毛竖立之意。此外,这个词也用以形容人的愤怒,如鲁迅《中国地质略论》:“其他幻形旅人,变相侦探,更不知其几许……然吾知之,恒为毛戴血涌,吾不知何祥也。”以上的解释及词例,都不是我的发明,而采自《汉语大词典》第6卷第1006页。应该说,这个词不大常用,但茅盾既然在别处用过,则他在《追求》中写章秋柳“她的光滑的皮肤始终近于所谓‘毛戴’”,大概也不出“寒毛竖立”之意。至于章秋柳之“毛戴”到底是出于惊恐还是愤怒,从上下文看似乎都可以成立,或者兼而有之吧。
倘若此解成立,则无论章秋柳像不像model,她的“毛戴”都与毛泽东无关。当然,如果真能证明章秋柳的“毛戴”与毛泽东有关系,那也“没有关系”,我关心的只是词义解释的准确与否,反对的乃是没有根据的影射索隐。
很感谢陈先生的反批评以及他提前示知的雅量,使我能够及早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也很高兴在彼此质疑中逐渐弄清“毛戴”的意思。所谓“疑义相与析”,毕竟不算浪费。而检讨起来,我的自以为是的武断和陈先生的没有根据的曲解,似乎都证明现代文学研究确实需要一点“古典化”的治学态度——比如在阅读现代文学作品过程中,碰到不大常见、不好理解的词如“毛戴”之类,也不妨像古典文学研究者那样去翻检一下辞书,如果实在查不出、弄不懂则不妨存疑,而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解释。倘如此,则我和陈先生都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了。我之所以提倡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正是有感于说文解字之难,自觉功夫不够,常犯轻率的错误,所以我非常愿意接受陈先生的教言:为学之道长而宽,还是以脚踏实地、多下些功夫为好。
2008年3月4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