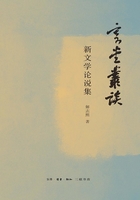
四
的确,《狂人日记》以“吃人”来盖棺论定旧文化、旧礼教、旧家庭以至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出语惊人的刻深,但不免有过甚其词、简单归罪之嫌。这反而会启人疑窦,不禁要生“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的疑问。就此而言,《狂人日记》倒是求深反浅、弄巧成拙了。
仿佛意识到《狂人日记》的偏颇,鲁迅后来又写了另一篇小说《弟兄》。《弟兄》和《狂人日记》都以一对兄弟的关系作为主题的载体,但两者所表达的文化态度显然有别。与《狂人日记》的“吃人”“救人”的象征寓意不同,《弟兄》在平实的写实中揭示出耐人寻味的文化—道德困境。《弟兄》中的兄长张沛君在弟弟病后,下意识地生出自私之念,确是深刻的心理真实,但从作品的整体描写来看,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和恪守传统礼教的真诚,也同样是不容置疑的真实。看得出来,鲁迅创作《弟兄》的旨趣,已不再是为了揭露旧礼教的虚伪,而旨在具体地展示新旧文化冲突时代的人们面对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或行为模式而难以协调的苦闷:一方面是传统的孝悌友于之教,它旨在维护大家庭的整体利益与和谐;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的个人利益观念——一个靠工薪养家糊口的机关职员是不能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的。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张沛君是无法长期避免矛盾的,因为他是一个既不很新又不全旧的“中间人物”,所以他既不能彻底抑制自己的个人主义意念,又不能也不愿舍弃家族主义的礼教人情,如此一来人生选择的困惑和价值分裂的苦恼也就在所难免,只在早晚间耳;而弟弟突如其来的病,则恰如其时地触发了张沛君的心理危机。虽然弟弟的病只是虚惊一场,却实实在在地惊醒了张沛君先生兄弟友于的好梦,令他对自己的“心病”有了真切的自觉。应该说,这样的心病或者说文化情结在那个时代并非罕见,倒是典型的文化症候,至少鲁迅本人就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尽管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控诉礼教吃人并对传统大家庭内的兄弟关系做了严酷的揭露,但实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极重兄弟手足之情、笃守孝悌友于之教的。鲁迅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当他和自己的二弟周作人都转型成为倡导“人的文学”的新文化人之后,原本“兄弟怡怡”的哥俩却因为彼此的个性和利害难以调和而无可挽回地失和了。兄弟失和无疑是鲁迅终身的隐痛,而写于兄弟失和之后的小说《弟兄》显然凝聚着鲁迅个人的生活体验。但鲁迅并没有因为兄弟失和,就简单地把《弟兄》这篇小说写成对旧伦理的控诉状和新道德的宣言书,更没有借机宣泄自己的憾恨或分辨兄弟间的是非,而是用既略带微讽又不无同情的笔触,感同身受地揭示出身为兄长的张沛君在人生选择上的两难和道德操守上的困惑。张沛君的这些矛盾的反应都是富有人性的真实的——倘若兄弟俩只追求各自的利益,兄弟友于之情也就未必存在了。就此而言,鲁迅写《弟兄》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鲁迅在《狂人日记》和《灯下漫笔》等小说杂文中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吃人”的偏颇指控,并不代表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真实认知,他的严厉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文化—社会改革策略的考虑:由于旧文化、旧传统的力量在新文化初期仍很强大而且顽固,所以革新者为了打开新路,一开始不能不有意识地对旧文化、旧社会采取严厉的甚至全然否定的激烈态度;至于这种态度对旧文化、旧社会是否公正,并且是否完全表达了他们对旧文化、旧社会的真实感受,他们是无暇顾及、即使顾及也在所不惜的。此中隐衷,鲁迅曾向他深为信任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吐露过。据内山完造回忆,当他在《活中国的姿态》的漫谈中说了一些中国的优点的时候,鲁迅坦诚地对他说:“老板,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板哪,我反对。”(10)由此可见,鲁迅对旧文化的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其实并未反映他对旧文化的真实感受,他之所以采取断然否定的严厉态度,乃是为了推动中国变革而不得不然的矫枉过正之举。对此,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里有一段话极富洞见:“他(鲁迅)对当时争论的问题所采取的极端态度,和他的积极鼓吹进步、科学与开明风气,都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并不构成他的整个人格,也不能代表他的天才;除非我们把他对他所厌恨的事物之好奇,和一份秘密的渴望与爱慕之情也算进。”(11)这话发人深省。事实上,鲁迅在私下的言谈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民族性倒是不无肯定的。即如当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被译成中文并改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即将在中国出版的时候,鲁迅在1936年3月4日致译者尤炳圻的私信里,这样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和国民性——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12)
令人惊讶的是,鲁迅在这封私信里充分肯定了中国的历史和国民性“其实是伟大的”,这无疑是发自衷心的也合乎历史实际的肯认。并且,鲁迅在30年代也曾公开肯认——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
可惜的是,如此肯定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话,鲁迅确乎言说不多,他说的更多而且影响更大的,则是诸如《狂人日记》等“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14)的小说与杂文。
诚然,鲁迅的激烈言说在现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消极影响也无须讳言:当鲁迅借狂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历史真实之后,后起者竞相效仿此种“深刻的片面”之论,终于蜕变为批判论者装饰其“深刻”的修辞皮毛,却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蒙冤至今;而鲁迅所一再鼓吹的个人主义新人学——所谓“惟有此我,本属自由”(15)“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16)的个人,带着“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17)的革命勇气,成为从事“辟人荒”创世胜业的“新人类”云云,但如此这般的个人主义“新人学”其实是缺乏道德灵魂的,而必定会趋于“朕归于我”“我即真理”之极端,张狂到纵情任性甚至丧心病狂之境,催生出周作人之类“赤精的利己主义”者(18),和专革他人之命、践踏他人自由的革命—自由投机主义者。诸如此类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是的革命—自由投机主义者,在现当代中国是层出不穷的。由此反省一下,作为新文化“人权宣言”的《狂人日记》及相关杂文,是不是有些自迷于“人的自觉”却“人而不仁”呢?!
事实上,周氏兄弟大力倡导的“任个人”的“新人学”也确实产生了流弊。到了抗战时期,作为五四过来人的朱自清先生检讨五四,对新文化运动蛮横地贬斥仁义道德、热狂地放任个人的“新人学”观念之偏颇有非常痛切的反省——
五四运动以来,攻击礼教成为一般的努力,儒家也被波及。礼教果然渐渐失势,个人主义抬头。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个人主义似乎不大相同。结果只发展了任性和玩世两种情形,而缺少严肃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健全的。近些年抗战的力量虽然压倒了个人主义,但是现在式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间,任性和玩世两种影响还多少潜伏着。时代和国家所需要的严肃,这些影响非根绝不可。还有,这二十年来,行为的标准很纷歧;取巧的人或用新标准,或用旧标准,但实际的标准只是“自私”一个。自私也是于时代和国家有害的。(19)
应该说,朱自清对五四新人学流弊的反省是切中要害、极富历史感和思想深度的。可叹的是,五四和周氏兄弟的崇拜者们至今仍对五四所标榜的新人学之偏颇缺乏反省,于是新时期以来再次高涨的新人学思潮也就仍然故我地沿着“任个人”的惯性向下滑行了。
当然,好的个人主义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但个人主义却并不必然都是好的,那种只知“任个人”的“立人”之道,只会助长任性、玩世、自私、狂妄的个人,只能离“人国”愈来愈远。健全的个人必须且首先要把别人也当作人来尊重。就此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仁学思想,确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遗产。
2019年4月22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附记:2019年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拟于第5期推出“世纪回旋:百年五四的文学省思”一组圆桌笔谈,以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的纪念,编者殷勤征稿于予,固辞不获,于是勉强写了这篇《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不料字数却超出了定数,刊物发表时有所删节,此处是全文,文字略有订正。
(1) 记者(傅斯年):《〈新青年〉杂志》,《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出刊。
(2) 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1982年3月2日出刊。
(3) 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1日出刊。
(4)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师大月刊》第30期,1936年10月30日出刊。
(5)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
(6)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出刊。
(7)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出刊。
(8) 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转引自《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40—241页。
(9) 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转引自《三松堂自序》,第238页。
(10) 内山完造:《鲁迅先生》,《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11) 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12) 鲁迅:致尤炳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82—683页。
(13)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14)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7页。
(15)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页。
(16)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17) 鲁迅:《忽然想到(五至六)》,《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页。
(18) 冯雪峰:《厌恶》,《乡风与市风》,作家书屋,1948年,第129页。顺便说一下,近年钱理群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之说颇为流行,但人们多不知钱说是从冯雪峰所谓“赤精的利己主义”变化而来。
(19) 朱自清:《生活方法论——评冯友兰〈新世训〉》,《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