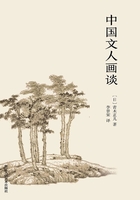
隶家三绝
第一章 文人画即为隶家画
若是谈论文人画,笔者或许可以勉力为之。此言听上去或许信心满满,其实笔者一向无甚自信。不过笔者在绘画史一途本来就是外行,既然所谓文人画本来就不是职业行家的绘画,那么非职业的绘画交给非职业的人去论述品评也无可厚非——笔者姑且以此聊以自许,或者更应该说是聊以自慰。所谓外行,本来其做法与构思就是极为大胆的,虽不免有“无知者无畏”之嫌,自由的风格却是它的优点。让我们将那些艰深的理论交给专家,带着外行人的轻松愉快开始隶家绘画的叙述。
首先,文人画就是隶家绘画这句话,出自元朝初期,两位玄人也就是非职业的画家之间的交谈。其中一人是赵孟 ,字子昂,另一人为钱选,字舜举。两人居住在浙江湖州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某天赵子昂问钱舜举:“如何是士夫画?”钱舜举答:“隶家画也。”这是《唐六如画谱》所载元王绎画论中所引用的有名故事,原文的“隶家”二字稍微有些问题,需要对其略加解说考证。明初在宁献王《太和正音谱》的“杂剧十二科”条中,引用赵子昂对于戏剧的评价,其中相对于“行家”,可见“戾家”之语。“行家”即为专家,广为众人所知,它的反义词“戾家”与之相反,是门外汉之意,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外行”。因为明代何良俊也在《四友斋丛说》的画论中提到:
,字子昂,另一人为钱选,字舜举。两人居住在浙江湖州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某天赵子昂问钱舜举:“如何是士夫画?”钱舜举答:“隶家画也。”这是《唐六如画谱》所载元王绎画论中所引用的有名故事,原文的“隶家”二字稍微有些问题,需要对其略加解说考证。明初在宁献王《太和正音谱》的“杂剧十二科”条中,引用赵子昂对于戏剧的评价,其中相对于“行家”,可见“戾家”之语。“行家”即为专家,广为众人所知,它的反义词“戾家”与之相反,是门外汉之意,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外行”。因为明代何良俊也在《四友斋丛说》的画论中提到:
我朝善画者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以沈石田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其次也。
将“行家”与“利家”作为相对概念列举出来,所以这里的“利家”应也是“外行”之意无疑。而近代以来在发音上“戾”“利”和“隶”都是相通的。(元代《中原音韵》中,三个字都是齐微之韵的去声,在当今的北京话中也都是这样的去声)“利家”“戾家”也就是“隶家”。且沈石田以下皆是士夫画家,都是非职业画家这一点是无法隐藏的明显事实,这是证明“利家”通“隶家”门外汉之意的最有力证明。另外,明代高濂在其《尊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这一赏鉴收藏书帖的条目中,对狡猾的书画商人用尽各种手段赝造古画欺骗外行人的行为进行叙述时,使用了“以愚隶家”之辞,这本书中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用例。据此所谓“隶家”的含义可以得到解释。另外,明末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董其昌对于上述问答之语重新撰写为:“赵文敏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据《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所载董其昌文)董其昌大概领会错了“隶家”的意思,把它当成了“隶书家”,所以将这段对话改成了前述的样子。证据就是,董其昌在他的《画禅室随笔》卷二中也发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乃为士气。”并且“隶体”一词在董其昌的观念中,因其指相对于楷书而言的隶书书体,与楷书相比更为古拙,于绘画而言就相当于与画工画不同,不拘泥于形似与技巧等的稚拙画风,这种画风的绘画有“士气”(士大夫的品格),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画。这样看来董其昌也把非职业性这点作为“隶”。虽然曲解了“隶家”的意思,着落点还是在“士夫画”即为“非职业绘画”这一点上。但是因为董其昌的名望,他的观点包括这一曲解都被迅速推行开来,因此后来全盘接受他的学说而形成的观点通行全国。例如清代王学浩的《山南论画》中,举清初王翚在回答别人“如何是士夫画?”的提问时,答曰:“只一‘写’字尽之。”的例子,并解说“此语最为中肯。字要写,不要描,画亦如之。一入描画,便为俗工矣”。盖王翚的“写”之说也不过是董其昌“隶体”之说换骨脱胎而来而已。还有清代钱杜《松壶画忆》上卷中说:“子昂尝谓钱舜举曰:‘如何为士夫画? ’舜举曰:‘隶法耳。’隶者有异于描,故书画皆曰写,本无二也。”这是借王学浩的解说来解释董其昌的“隶体”之说。这些观点陷入诡辩,都是因为过于笃信董其昌之说以至于徒劳无功。一句“士夫画就是非职业的绘画”不是非常简单明了吗?而“士夫画”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文人画”。
试着以这一观点通览古来著名的画家,非专业画家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试着来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所记录的画家,先是秦代以前身份不明的画家:西汉六人,毛延寿以下是元帝时为后宫丽人作像的职业画工;但在东汉六人中,已经有了如张衡、蔡邕这样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最优秀的文人存在,也有赵岐这样能为《孟子》作注直到如今都为人所尊敬的鸿儒。三国八人中仅吴曹不兴一人为专门画家,其他七人都是如魏杨修、桓范这样知名的文人,或者魏徐邈、蜀诸葛亮(孔明)及其子瞻这种了不起的文武官员以及魏少帝、吴王赵夫人等这样高贵的人。晋代二十三人中,虽然专门画家为数不少,但是大半以上还是素人。其中有嵇康、荀勖、王廙、王羲之、王献之、温峤、戴逵、王濛这样著名的文人,范宣这样学德高深的隐士(戴逵的老师),戴勃(戴逵之子)、江思远这样隐逸的学者,而顾恺之特别以画闻名,又是善诗赋的文人。南朝刘宋二十八人虽大半都是专门画家,其中还是有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这样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诗人和文人,王微这样博学能艺的名士,宗炳、戴颙(戴逵之子)这样飘然物外的高人,以及谢稚、谢约、刘胤祖与其弟绍祖这样官职在身的文人。之后专门画家数量渐渐增加,然而被作为画家列入《历代名画记》中的几乎都是在正史中留有姓名的名人高士,比如梁陶弘景、陈顾野王之类为数不少,他们都是非专业的画家。他们之后,点亮唐代绘画史的人中,阎立本与其弟阎立德,以及李思训与其子李昭道都官居高位,王维则是屈指可数的诗人,郑虔也是诗人,曹霸是将军,韩滉是大官,毕宏、杨炎、张璪、刘商等都有相当的官职。另外还有卢鸿一、张志和之类有名的善于绘画的隐者,顾况、杜牧等有名的诗人也被列入画家之中,当时的状况大抵如此。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指出了这一现状,“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之后宋代景况亦与之相同,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是承续《历代名画记》所作,在列叙北宋画家之时,做出了第一列仁宗皇帝一人,继而“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艺臻乎至极者”十三人,其次“高尚其事,以画自娱者”二人,最后“业于绘事,驰名当代者”一百四十六人的分类。作为它的后继编纂的南宋邓椿的《画继》也效仿此风,“圣艺”一人(徽宗);“侯王贵戚”十三人;“轩冕才贤”十七人;“岩穴上士”六人;“缙绅韦布”四十五人;“道人衲子”二十二人;“世胄妇女”十九人。先列出这些非职业画家,最后才列记了画院的画工等以画为业的七十六人,以此应可窥得其大势。元明以后也是同样,士大夫秀于此道者不胜枚举。
文人画的渊源虽然极其古远,然而在唐代以前,尚无仅因绘画者是文人士大夫,就将文人画作为一种画风的意识。然而北宋中叶以后,相对于职业的专门画家所代表的画风,也就是所谓的“院体”,产生了鼓吹在士大夫等游艺者之间所产生的这一新画风的倾向,所谓文人画的意识渐渐显著起来。这种风潮大约从北宋神宗、哲宗年间王诜(晋卿)、文同(与可)、苏轼(东坡)、米芾(元章)、李公麟(龙眠)等文人开始,到元初钱选(舜举)、赵孟 (子昂)等益发显著,又被元末四大家即黄公望(子久)、倪瓒(元镇)、王蒙(叔明)、吴镇(仲圭)等继承,经明代沈周(石田)、文徵明(衡山)等最终到明末董其昌(玄宰)等人达到顶峰,呈现出一大派系的景象。对此,董其昌又将画派分南宗、北宗之别,将南宗作为“文人之画”,在他的《画禅室随笔》卷二中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这与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对于绘画“南北宗”系统的论述主旨是相同的,将南宗画派视为“文人之画”。将绘画分为南北两派是董其昌的独断之言,本来就很难像他说的一样将两派绘画分别清楚,不过他进行这种划分的初衷是将宋代文人如李公麟、米芾等的作品同画院画工李唐、刘松年等人的绘画区别开来,并上溯至唐代,将王维与李思训作为南北画派各自的起点,下及“元四家”和明代沈、文等,将他们列入南宗,而承袭画院画风的则是北宗,也就是相对于院体画,将非院体画视为南宗画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画”。董其昌南北分宗一说是否正确妥当暂且不论,把王维写成文人画始祖,将其局限于南宗绘画之内未免失之狭隘。如若对王维如此拥戴,对于顾恺之也应如此,也许还可以往前追溯到东汉张衡方更显出历史性意义。而且,也没有必要把王维局限在南宗画范围内,明代唐寅(伯虎)的画风也出自院体,却能与沈周及文徵明等比肩作为文人画的代表而无人提出异议。董其昌的“南北宗”理论作为见多识广的大收藏家的学说当然能给我们很多教益,然而也不足以将它作为金科玉律。
(子昂)等益发显著,又被元末四大家即黄公望(子久)、倪瓒(元镇)、王蒙(叔明)、吴镇(仲圭)等继承,经明代沈周(石田)、文徵明(衡山)等最终到明末董其昌(玄宰)等人达到顶峰,呈现出一大派系的景象。对此,董其昌又将画派分南宗、北宗之别,将南宗作为“文人之画”,在他的《画禅室随笔》卷二中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这与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对于绘画“南北宗”系统的论述主旨是相同的,将南宗画派视为“文人之画”。将绘画分为南北两派是董其昌的独断之言,本来就很难像他说的一样将两派绘画分别清楚,不过他进行这种划分的初衷是将宋代文人如李公麟、米芾等的作品同画院画工李唐、刘松年等人的绘画区别开来,并上溯至唐代,将王维与李思训作为南北画派各自的起点,下及“元四家”和明代沈、文等,将他们列入南宗,而承袭画院画风的则是北宗,也就是相对于院体画,将非院体画视为南宗画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画”。董其昌南北分宗一说是否正确妥当暂且不论,把王维写成文人画始祖,将其局限于南宗绘画之内未免失之狭隘。如若对王维如此拥戴,对于顾恺之也应如此,也许还可以往前追溯到东汉张衡方更显出历史性意义。而且,也没有必要把王维局限在南宗画范围内,明代唐寅(伯虎)的画风也出自院体,却能与沈周及文徵明等比肩作为文人画的代表而无人提出异议。董其昌的“南北宗”理论作为见多识广的大收藏家的学说当然能给我们很多教益,然而也不足以将它作为金科玉律。
笔者还是更愿意尊奉钱舜举对于赵子昂“如何是士夫画”这一疑问所回答的“隶家画也”这一充满禅意的答案。当然,也不是说既然是非专业绘画就完全无视技巧,在上述问答之中,赵子昂注意到了钱舜举定义里的这一点,因而对话再次回到之前的问答。赵子昂问钱舜举:“如何是士夫画?”钱舜举回答:“隶家画也。”因此赵子昂说:“然。观之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盖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其谬甚矣。”当时所谓的士夫画,因为并非专职画家所画而无视画法,过于放纵,难免颦蹩。这种错误的想法在后世也仍然持续着,明末沈颢的《画麈》中就曾讽刺这种风气:“今见画之简洁高逸,曰士大夫画也,以为无实诣也,实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维、李成、范宽、米氏父子、苏子瞻、晁无咎、李伯时辈,皆士大夫也,无实诣乎?行家乎?”这与赵子昂想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钱舜举的定义固然可以视为对于院体画发出的挑战,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很大问题,过于无视实技、放纵狂乱,不能不说是文人画走火入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