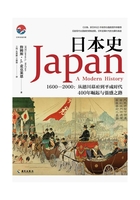
第二章 城市、商业和生活方式
大约就在德川家康成为日本幕府将军的同时,三井家族决定弃武从商。几代以来,三井屋的首领一直在为近江的佐佐木大名尽忠,到16世纪中叶,三井高安,因其荣誉封号“越后阁下”而闻名,在琵琶湖附近的一个城堡安顿了下来。16世纪60年代晚期,织田信长在发动战争巩固其在日本中部的控制权时,消灭了佐佐木家族,三井高安迅速撤退到伊势的小商业中心松坂。在那里,三井高安的儿子及家族的继任首领三井高俊,目睹了德川家族崛起为新的军事领袖。据此后很久官方编撰的一部家族史介绍,三井高俊不久敏锐地断定,日本将出现一个长期和平的时代,他进一步断言,三井家族当店主比当武士的前途更为光辉灿烂。在凑齐了必需的资金之后,他开了一家酒屋,命名为“越后殿酒屋”。
三井高俊幸运地选对了时机,因为酒屋的生意为这位年轻人赚足了成亲和养家糊口的钱。更幸运的是他娶了同行商人的女儿为妻,她12岁就嫁给了三井高俊,最后一共为他生了12个孩子,而且还有时间为家族生意的成功献策献力。除了照看酿酒的生意谋取更多的收入,妻子还劝说丈夫用部分积蓄兼营典当和借贷的生意。结果从这个生意中赚取的利润很快超过了越后殿酒屋的收益,三井家族开始成为伊势国主要的商人家族之一。
1633年三井高俊去世后,遗孀派其长子带上足够的资金到江户开了一家分店。两年后她又派幼子三井高利前去协助。之后不久,三井高利就从兄长手中接管了江户的业务。三井高利是个机敏的商人,他也充当稻米买卖的中间人,并且把三井各项事业的利润积攒为一大笔钱。1673年,他最终决定在江户开设一家吴服店,并命名为“越后屋”。一开始,这只是个雇用了六七名店员的小生意,由店员把精美丝绸的货样送到富裕武士的家里让他们挑选,根据顾客的不同财力商议价格,也接受赊账订货。

越后屋的招牌及店内情景
1673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吴服店后,三井高利在日本桥重开了一家越后屋。直到今天,作为越后屋直接传承的三越百货商店依然屹立在那里。三井高利对吴服店的布料零售进行了一番改革,他在店里挂出一块著名的布告牌,宣布“只收现金,谢绝还价”。这块布告牌至今仍保留在三井博物馆。也就是说,三井高利开始销售的各种纺织品,不仅富裕的武士,连普通商人和手工业者家庭都能买得起;同时他希望顾客直接到他的店里付现金选购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明码标价的商品。随着销售额急遽上升,三井高利通过在下雨天把装饰着商店商标的精美油纸伞借给顾客使用,以及接近剧作家和诗人,让他们在作品中进一步宣扬三井商店的公众形象等做法,扩大了越后屋的声誉。到1700年,越后屋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商店,在京都和大阪也都开设了分店。
三井夫妇不是典型的商人,但没有多少人能和他们的成功相提并论,也没有多少家族史会给予家族的女性像三井高俊的妻子曾获得的那么多的嘉许。三井高俊只不过是近世早期选择弃武从商的成千个武士之一,对一位母亲和妻子来说,分担经营家族生意的责任也并非不同寻常,即便丈夫和父亲仍是正式的一家之长。在近世早期,许多家庭和三井家族一起经历了席卷日本的三次伟大变革。当德川家康接受天皇任命成为幕府将军时,日本还是一个以农村和自给自足性很强的农户为主的国家。在一个世纪之内,它就转变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无数农民子女,还有前武士的后裔,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搬迁到新兴城市里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在城市里,他们为了养活自己而努力奋斗,甚至希望获得成功,由此创造出一种商品经济,其中纺织品大商店如越后屋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相应的,由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集聚了各种动力,使各种各样的新商品流向市场,全国大量的家庭得以享受稳定提高的生活水平——更优质的住房、食品和服装。
◎城市革命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许多城堡小镇的出现点燃了日本城市革命之火。在那期间,各地大名为了巩固日益扩大的领地,开始仿照伏见城堡的样式营造巨大的城壕和塔式堡垒,作为军事和行政根据地。通常,地方藩主会把他们的新根据地建在战略要地,从那里他们可以控制向他们缴纳税收和粮食必需品的周围农村。当大名要求他们的武士在巨大的石头堡垒周围建造住宅,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移居到新兴小镇,为武士阶层提供各种日常用品和服务时,新的街市几乎立即开始以城堡为中心萌芽发展。
日本戏剧性地突然成为一个耀眼的城市国家。如今日本的大城市中,几乎有一半在1580年至1610年之间就作为城堡小镇开始存在,从日本北部的仙台、福岛,到中部的金泽、甲府、静冈、名古屋,再到南部和西部的广岛、冈山、高知和熊本。城堡小镇的面积和它们的数量一样让人印象深刻。一般情况下,聚居在新町的人口会占到藩内全部人口的10%左右。全国大约共计有140个城堡小镇,每个小镇的人口至少为5 000,其中的大镇金泽和名古屋人口多达10万。
城堡小镇的布局紧紧围绕着大名及其武士家臣的需要。大名一般都把城堡造在军事防御要地,例如鹿儿岛的城堡就是沿海岸而建,或者如金泽和广岛把城堡造在两河之间的高地。大名一家居住在城堡中心,由高耸的围墙和纵横交错的城壕以及运河安全地拱卫着。大名把他的主要家臣安置在毗邻城堡的地方。那里代表着很高的声望和安全性,同时也是个很方便的地方,因为那些高级武士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花费在城堡围墙之内的行政事务所里。接下来的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居住带,他们在大多数城堡小镇占到人口的一半左右。足轻和其他低级武士家庭离得更远,住在处于外围的兵营风格的住宅内。最后,多数大名还指示佛教宗派把寺院建造在城市四周的战略通道,万一敌人来犯,大名可以派兵在宽阔的佛殿里把守,墓地的空旷也使敌人只有冒着风险才能穿越过去。
京都、大阪、江户——幕府直辖的三个全国性城市,盘踞在地方城堡小镇网络的顶端。近世早期,大名、上层武士和其他有产者已开始珍藏手工业者制造的奢侈手工艺品,这在有着几百年文化成就和皇室贵族所在地的城市——京都的形象中增添了商业的维度。一份1685年的人口登记文件反映了京都居民的多样性和富裕程度。除了内科、儿科医师,牙医、诗人、作家以及茶道、插花和能剧表演的大师们之外,文件还罗列了数百家著名商店,其店主因为制作和销售精美的丝绸、瓷器、折扇、书写纸以及家用佛教祭坛的支架而享誉国内。截至登记完毕的那天,京都的总人口大大超过了30万,其中许多人靠在日本各地制造和出售高质量的手工艺品谋生。
附近的大阪有着历史上有名的、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往事。早在六七世纪,一个位于宏伟的大阪湾海岸的据点,就已经成为从大陆经由濑户内海到日本的使团和商队的终点站。645年大化改新之后,新的君主制国家暂时定都在那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一个兴旺的港口和市场区在从京都流向大海的淀川两岸稍微向内的地方发展起来。16世纪,净土真宗的支派本愿寺派的高级僧侣在该地建造了他们的要塞寺庙石山本愿寺后,一个更大的商人町形成了。16世纪70年代当织田信长攻破这个要塞寺庙时,那里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丰臣秀吉于1584年建造了壮观的大阪城堡后,商人町得以复兴;但是在1614年和1615年的残酷战争中,它几乎再度湮没。
德川家族察觉到大阪地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于是重建大阪城堡作为他们在日本西部的防御基地。到17世纪末,大阪周围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剧增到大约365 000人,几乎淹没了大约1 000名驻扎在城堡的武士。大阪经历了从军事堡垒到商业活动据点的蜕变,开始成为全国许多日常用品的制造中心。到1700年为止,大阪的手工业者已经因为把油菜籽榨成灯油,把原棉制成成品布,把干沙丁鱼捣烂做农田的肥料而著称。住友家族和其他冶铜业业主已经成为城市中最大的雇主之一;城市里共有17家精炼厂,约有10 000个家庭靠冶铜业维持生计。
作为众多制造业的所在地,大阪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主要的航运和集散中心,以及因靠近内陆海而发展起来的转运港口。到了18世纪头10年,住在城里的船匠就有2 000多名,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批发商、销售商、临时工和运输商。稍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城市官员写道,大阪“位于全国主要航线的交汇处,货物云集,交通繁忙,因此人们通常称它为 ‘国家的厨房’,即全日本的食品仓库。的确,街道两旁富人和富商家的房屋相沿成行,港口总是停泊着来自许多地方的船只。所有的一切,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稻米,甚至是海外的商品,都运到大阪出售。人们什么都不缺”。①
将军的直参,即旗本和御家人,是江户城市成长的核心。大约20 000个直参家庭中的大多数都雇用了随从、贴身男仆、家庭佣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移民来到幕府都城。17世纪30年代德川家光把参觐交代制度化以后,定居在江户的大名家庭成员及其众多的随从,为城市100万的人口又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使武士的总数达50万人。像罗马一样,江户也是建造在七座小山之上。精英大名把他们的庄园建造在蜿蜒通向城堡以南的青翠的山坡上。幕府把亲信旗本及其家庭安置在城堡以西的麹町。这个决定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为那个地区面向袭击城堡的天然通道——武藏平原。起伏不平的山顶对多数武士来说也是个理想的位置,因为他们可以找到阳光明媚的地方,把住宅和花园建造在那里。

繁华热闹的江户日本桥
在整个17世纪,建筑工、手艺人和各种货物的经销商川流不息地涌入江户,迎合新兴的幕府统治者的需要。商业城市江户的心脏地带是日本桥,大致为江户湾海滨到江户城堡主要入口之间的中点。以此为中心,工匠町和商人町向外扩展,分布在山谷之中,山谷迤逦穿越了布满大名庄园和武士府邸的向阳山坡。截至18世纪20年代,居住在江户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武士一样多,总人口远远超过了100万。江户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有了江户的领先,日本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近世早期之初,京都是日本唯一一个拥有10万多居民的城市。到1700年为止,江户、大阪、名古屋和金泽的人口也都超过了10万,而且5%~7%的日本人都生活在类似的大都市里。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数据是2%,并且只有14个城市和日本的一样大,只有荷兰以及英格兰、威尔士拥有比日本还大的城市聚居区。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城市建设时期,日本城市非同寻常的百年成长,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城市和商业
“三都”——江户、大阪、京都显而易见的充沛活力,诱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伟大商业革命。虽然大名和将军的原意是把地方的城堡小镇以及江户、大阪作为防御性的据点,但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大量移入,把这些地方转变成了消费和制造的脉动处,最终它们的商业意义超越了原来的军事目的。相应的,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手工艺品产量和贸易额,有赖于一个全国性的高度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可靠的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服务业等基础设施的创立。日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步入了近世早期,但是到了19世纪,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立足于城市的商品经济,而且都受到了这一结果的影响。
具有讽刺性的是,太平盛世中获得的超乎寻常的商业发展,起源于16世纪战争的严酷考验。甚至在普遍的毁灭和混乱之中,军队也需要供给,农民也希望通过改进工具、培育新品系的种子和使用更丰裕的肥料来提高农作物产量。与此同时,革新的工程技术使大型的灌溉、防洪以及垦荒工程得到发展,耕地的数量在1550年到165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国家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人口的加速增长。结果1550年后的一个半世纪,日本的人口总数从一千万或一千两百万跃升至三千一百万;同时也使许多年轻人有可能脱离土地,到城里当商人或手工业者,寻找自己的出路。
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食物、服装和建材的永无止境的消费需求,刺激了区域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全国市场体系的发展。很清楚,没有一个领地能生产出本地居民所消耗的所有不同的商品和食物,只有穷一国之力才能满足江户和大阪的男人、妇女、儿童的近乎不知餍足的胃口。响应城市市场的召唤,不同地区的生产商开始因某些特产而著称:九州岛南部的樟脑和香菇,土佐藩的木材和木炭,富山的药物,以及甲府的葡萄。这些仅仅是那些能在三大都市卖出好价钱的商品中的很小一部分。
大名的政策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商品交换的扩大。地方大名需要大笔现金以修缮城堡,开展藩内的灌溉和垦荒工程,定期向幕府纳税,负担每年往返江户的开支,支付维持庄园所需的费用,供养在城里定居的亲戚和家臣的扈从。由于大名收入的绝大部分得自用稻米支付的农业税,因此他们必须把征收上来的稻米转换成现金来偿付面临的各种账单。17世纪20年代,日本中西部的大名就开始把年贡米载运到大阪,再由那里的稻米买卖中间人安排销售到各市中心。一开始大概每年有100万石的稻米从大阪的仓库流出,到18世纪20年代这个数字就增长了不止4倍。人民的主食——数额如此之大的谷物在大阪的流进流出,有助于城市转化为日本的经济中心,用那时的说法就是“国家的厨房”。
为了保证收入,许多大名最后制定了政策,谋求促进经济作物和土特产的发展,以在诸如江户、大阪之类的消费中心出售。他们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实施这种计划。前田大名付给京都一位著名陶工丰厚的津贴,让他在多雪的加贺藩留住一年,在村庄的陶窑里培训当地的手艺人。在更往北的米泽藩,藩主上杉屋从国家的其他地方延聘专家,开办了靛青种植园用来制造很受日本人喜爱的一种染料,并向当地农民传授织造棉布的新技术。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米泽藩的官吏再次邀请外面的专家过来。这次是指导农民植桑造林,桑树柔嫩的叶子可以用来喂蚕。米泽藩藩主还出资成立了12个培育桑树树苗的苗圃,并且出版手册向农户教授养蚕和在市场上买卖桑蚕的秘诀。
各地大名采用了多种方法希望能从藩政资助的事业中牟利。在某些情况下,官员只授权给某些商人或村庄,让他们参与到新举措中来,然后每年向他们收取专营费。另外有些时候,地方藩主会征收新税,例如向种植的每一棵桑树或者运出领地的每一包陶瓷制品抽取固定的税金。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官吏则强迫生产商把他们的产品卖给指定的批发商,然后由后者用船把货物运给大阪的经销商,最后再把一部分收益交到领地的金库。除了增加藩内的收入之外,大多数藩主也希望成功的经济干预能够有利于普通人民,使他们感受到藩主统治的仁慈。正如19世纪早期一本养蚕手册所解释的那样,“丝绸业带给社会的直接效益是,使河岸、山区、海边的空地都种上了桑树,通过纺丝织绸走向繁荣。更不必说地方产品外销到其他地区后,人民会富裕,藩国会兴旺发达。”①
幕府通过统一度量衡,建立国家的货币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商品流通。由于国家的绝大多数矿山已经为幕府所控制,幕府开始在几个城市铸造货币。其中江户的银币铸造处即“银座”极为著名,以致这个词最后被用作铸币处所在地的地名。将军铸造的钱币很快成为国家的通货,而大名大多发行在各藩内流通的交易用的纸币。商人要根据幕府发行的金币、银币和铜钱,计算跨越各藩界的商品以及在江户、大阪和其他中心市场达成交易的付款额。

画家歌川广重所绘《江户名胜百景》之“月光下的街道”
幕府支持了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发展。因为陆路交通在多山的日本很困难,多数商人宁愿把自己的货物委托给远洋航行的驳船和货船。为了帮助水运业,幕府委托江户一位富裕的木材商川村瑞贤制定减少海上航船现存危险的措施。川村瑞贤立即着手把危险的水域制成图,建立信标和灯塔,提供从江户到北太平洋沿海各港口的救生和救援设备。随后他又把同样的措施推行到穿越马关海峡,经濑户内海直到大阪的沿日本海的整条海岸线。17世纪70年代,所谓的“东西环形线”已经把日本最偏远的地区和主要消费中心连接了起来。
幕府也实行了改进道路的系统规划,重点是从江户的商业中心日本桥向外辐射的五条干道。东海道是其中交通最繁忙的干道,它沿太平洋连接江户和京都,长达近482.8公里,支线则延伸到大阪。东海道分级的路基上先铺上一层厚厚的碎砾石,再用沙子压实,平均宽度约为6.1米。里程碑安放在种着松树的土墩上,告诉行人他们从日本桥过来已经行进了多远,或者还有几里路待走。石制路标避免了行人在十字路口走错方向。53个驿站沿东海道排成一列,疲惫的行人可以在那里换便鞋,吃小吃,喝茶,或者在客栈吃顿晚餐并住上一宿。
由于大批量货物大多走海路,东海道上熙熙攘攘的大名队伍只能遇到一些腿部裹着稻草,由马夫牵着的驮马,马夫看上去通常不像他们的马那样卑下。此外,还有许多递送急件的信使,在路上来回疾行。17世纪一开始,幕府就派遣官方信使每月三次往返于江户和大阪之间。1664年,江户、大阪和京都的商人开创了面向私人的速递服务,几乎每天都有“飞脚”携带着小件包裹、商业文书和现金从各个城市起程。起初,飞脚在江户和大阪之间来回一次需要六天,但是到19世纪初,昂贵的特快业务已经把时间缩短为两天。这时信使们已经把通信网络扩展到了长崎、金泽和仙台等城市。
日本几个首要的商人屋创设了其他许多服务于商业,促使经济继续发展的业务。在大阪,鸿池屋和其他富商开始开办相当于银行的钱庄。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十组问屋”组合有时提供大额贷款给大名,让他们填补眼前的预算赤字,支付履行参觐交代义务以及施行藩政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费用。有时金融商还贷款给个别批发商,这些人再把钱借给农户,他们需要资金作为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制造出售给城市顾客的纺织品和手工艺品的本钱。此外,大阪和其他地方的钱庄主还为托运人提供保险,吸收现金存款,发行以房地产作担保的期票,发行信用证及兑换券,以加快不同城市商人之间的交易速度。

江户时期拥挤的歌舞伎剧院
日本的商业革命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如果说开始时城堡小镇和大都市江户、大阪只是大名和武士的城市,那么到了近世早期的最后阶段,它们就已经成为普通人的领地。这一转变在赞美商人町生活的木刻浮世绘中清晰可见。常被誉为日本最出色的浮世绘画家的歌川广重,创作了《江户名胜百景》(又译《名所江户百景》),而且当时他从江户商业中心日本桥的风景入手已经开始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东海道五十三驿站》。一些通俗的旅行指南,如《难波雀》和《插图本江户名所指南》,用类似手法描绘了在大阪和江户人头攒动的商店里,顾客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仔细考虑着如何取舍。
旅行指南也会指点好奇者前往三大都市中活跃的歌舞伎剧院,还有从17世纪末一直到18世纪在大阪非常流行的偶人戏剧院。因为当局禁止武士去剧院,他们认为武士应该欣赏更优雅、更有益的能剧作品,所以为大众化剧院写作的剧作家把创作集中于能激发富裕商人和手工业者想象的题材。其中一种类型的作品被称为“世话物”,或者叫家庭伦理剧,多半叙述一些半虚构的凶杀事件或者其他让人惊叹的丑闻。例如一个妓女和她经商的情人双双自杀,因为后者没钱帮她从妓院赎身。相反,时代剧或者说“时代物”,记述的是历史事件,尤其是12世纪平氏和源氏的英勇奋斗,以及有武士参加的较近期的重新统一的战争。他们的事迹树立了诸如忠诚、英勇等人人都珍视的价值典范。
◎农业商品化和原初工业化
日本的商业革命也改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模式。全国每个地区的农民家庭都转向种植出售给新兴城市人口的茶叶、烟草、水果和蔬菜。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作物在不适合种水稻的隙地长势良好;也有些地方的农民在收割完水稻后种上第二茬作物。例如, 17世纪早期大阪商人发现了一个从油菜籽中榨取灯油的便宜办法,全国的城里人都开始享受可靠的油灯带来的舒适,它的光亮让人安心、着迷,正如它能打消小偷和其他不怀好意者的念头而增强安全感。随着需求的增长,大阪周围村庄里的农民种了很多第二茬的油菜,以至于早春的田野仿佛染上了一层金黄色。
整个德川时期,乡村工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到19世纪初,全国的手工场坊生产出种类繁多的商品:从丝棉织品到草帽、纸张、榻榻米的贴边、木炭、钉子、工具、漆器和陶器,还有各种食品如盐、糖、醋、酱油以及味噌。有些地方,藩地官吏带头在农村开辟事业,例如加贺藩的陶器、瓦器生产。更多情况下,已经因经营商品化农业而积累了一笔储蓄的富有商人和农户,为这类事业提供资本和组织的诀窍。不过,这种立足于农村且适合市场销售的商品生产的蔓延,代表了日本经济的原初工业化。也就是说,新兴的乡村工业折射了一种初生的企业精神:个体怀着从投资中获利的希望,冒险投入资本,创办为远方市场生产产品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原初工业化既不同于每家每户为自己制造日常生活所需的衣服及工具的普通家庭生产,也不同于传统的手工业贸易,即手艺人制作在当地销售的产品,很少考虑扩大业务或者赚多于养家糊口的钱。
乡村的新企业规模差别很大。极端的例子是一个雇用了多达六七百人,酿造酱油或冶铁锻造工具的大工场。生产木炭、糖、盐、茶叶及纺织品的乡村小作坊则普遍雇用5至20名工人。有的甚至可能根本没有集中的作坊。日本的很多地方都有乡村妇女晚上在家织布,织好后交给已经把钱预付给她们买织机和纱线的包买商。
像那些从农忙中抽出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织布的农村妇女一样,有些工人也是不定期工作。还有一些工人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日本西部的长州藩,村庄沿多山的半岛分布,村里的妇女夏天的几个月通常在海边的盐场干活,只有当制盐季节结束后才回到家里,重新开始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日本北部,下雪的冬季整个村子的男人都在遥远的酿酒厂或酱油酿制厂做工,这在当地是件很普通的事情。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工人们都已经开始出卖劳动力换取某种形式的工资。这是原初工业化定义的另一个特征。
丝绸制造业在近世早期日本原初工业化活动中特别突出。丝绸的制造是个复杂的过程。它始于蚕的孵化和饲养,农户把蚕养在房子里的所有平地上。把最后结成的蚕茧煮沸后,工人们抽出又轻又细的蚕丝纤维,把它们捻成长长的几股细丝,接着把细丝缠绕到卷轴上。然后工人把几股细丝按各种式样编在一起,制成不同种类和级别的丝线,这一过程叫作“捻丝”。到这时,染工和织工就可以把丝线织造成成品面料,预备裁剪并缝制成和服或其他式样的衣服了。
近世早期之始,只有少数日本家庭生产数量有限的低档丝绸面料,供自己使用或在当地出售。唯一一个主要的丝绸制造中心位于京都的西阵区,那里的织工为贵族和富裕大名生产高质量的丝绸。从17世纪中叶开始,有经济头脑的商人开始鼓励养蚕,把丝绸制造过程合理化,提高成品面料的质量,并且开始针对全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革新者首先关注丝绸制造过程的最早阶段,即蚕种的孵化。那些蚕种很容易得病,甚至对温度的轻微变化也很敏感。经过几十年的选择育种试验后,农民培育出了更顽强的品种。到18世纪早期,日本北部福岛地区的珍贵蚕种行销全国。与此同时,其他农民发现了培育杂交蚕的方法,这种蚕的纤维的颜色和光泽刚好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1702年印行的第一本关于这些试验者的繁忙和成功的养蚕手册描写了5种蚕,而19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则列举了将近200种。而且,对丝绸生产的不同教本的比较表明,每个蚕茧可用纤维的数量已经增加了大约25%。
最显著的技术进步之一是水力捻丝机的应用。18世纪后半叶,大约在英国成立首家丝厂的6年之后,一位日本轮匠发明了用水力带动捻丝用的多锭丝车的方法。虽然没有多少人采用这项突破性技术,但是这使得他的家乡,位于江户西北上野国一个崎岖不平之地的桐生,成为领先的丝绸制造中心。还有些革新者改进了缫丝方法。起初丝绸制造商依靠的是简易的设备,它要求缫丝工用手把丝线捻在一起,然后卷绕在木头轴子或框架上。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使用齿轮和传动皮带的缫丝设备开始在全国不同地方出现。在一些地方,新缫丝机已经靠水力而不是人力驱动。
缫丝和捻丝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大型纺织工场的发展。18世纪60年代,当地织工掌握了京都西阵著名纺织品生产场坊以前作为家族秘密来保护的精妙染色技术后,桐生和周围街区崛起成为全国的丝绸制造中心。桐生丝绸由于质量精良而誉满全国后,其他熟练织工也搬到那里,另外购买一些织机,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多者一人雇用上百名工人。据1835年的一份文件记载,“来谋生的织户雇用女工纺纱织布,人们从其他藩国涌入小镇,在那里甚至周边小村租赁房屋”。①
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使销往地方和全国市场的产品产量最大化,计酬劳力和基本机器的使用也开始成为棉布制造业的典型特征。日本人从远古时期就种植了大麻及其相关纤维作物,如亚麻和苎麻,为普通民众提供最重要的衣料,直到一些士兵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场上回来,带回了特别适合在大阪地区种植的一种棉株。棉布经久耐用,冬天穿舒适,夏天穿凉爽,因此到19世纪上半叶,很快成为大多数普通日本人的上选衣料。棉布广为流行,以至于大阪周围各藩国的农户把多达70%的田地都种上了棉花,与水稻实行一年一季或两年一季的轮作。
日本中部以种植业为主,而更远地区的一些包买商则购买原棉或棉纱,交给织布能手织成棉布。许多地方的农妇空闲时在家织布,按件领取报酬。但是,随着顾客需求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织布能手开始全天候织布。其中一些人仍然是独立的生产者,但其他一些熟练织工开始雇用计酬的人手,在拥有二三十架甚至更多架织机的作坊干活。和制丝业的情形一样,革新者也采用了一些改进技术的方法:选择育种增加了棉株的种类,新纺纱机能纺出更坚固的棉纱,更高效的织机提高了生产力,织染工艺的发展最后生产出一批批式样、质地和色彩都让人惊叹的棉布。
由于商品化农业和乡村工业遍及农村,许多村庄成长为作为工业、贸易、交通交汇处的农村集镇。桐生的规模在1757年到1855年之间增至原来的三倍,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家庭都从事与丝绸贸易有关的行业。与此相似,1843年在大阪腹地的一个村子, 277户农户中只有14%还在务农,而46%为棉布产业工作。两年后对尾张一个村庄所做的统计表明,该村262户农户中,20%在经营农业,31%从事棉花生产,还有22%的职业与交通业有关。从极小的不起眼的村庄到有几千户居民熙来攘往的城镇的转变,丰富了日本的城市层级。在把农村的穷乡僻壤和日本的港口、驿站、城堡小镇及三大都市相连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形成了新的联结。
◎对外贸易
17世纪30年代幕府颁布所谓的“锁国令”,目的在于确认自己主导日本对外关系的特权,控制对外贸易,铲除它视为“危险的宗教”的基督教。只要这些目标实现,江户政府并不打算终止和外面世界的所有关系。相反,整个近世早期,幕府一直接待朝鲜和琉球群岛的使团。在驻守长崎的幕府官员的全面监视下,和中国以及荷兰商人的贸易有时也很兴旺。此外,幕府允许萨摩、对马、松前诸藩的大名、商人与琉球群岛、朝鲜及日本北部领土进行贸易。
一个获幕府许可并受其管制的半官方商人组织“长崎会所”,组织并管理长崎的贸易。长崎会所成立于1604年,“锁国令”颁布后被授予垄断外贸的权利。长崎会所接受外商订购各种国内商品,购买在出岛卸载的中国和荷兰商船带来的商品。出岛是个位于长崎港的人工岛屿,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常年居住此地,维持常设的荷兰商馆。日本商人特别喜欢进口丝线、纤维、药草、香料、糖和药物。外运船只满载的则是日本商人的出口商品:铜、樟脑、硫黄、剑、陶器和漆器。
17世纪晚期长崎的贸易总额上下起伏不定,但日本人常常买进比卖出多。17世纪30年代和葡萄牙关系的中断,暂时停止了曾经让德川家光及其谋士担忧不已的贵金属的流出。但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为了平衡贸易逆差,金银的重新外流再次使幕府警觉。1715年幕府发布了《海舶互市新令》。新令的条款限定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每年只能有30艘,贸易额为白银22.5吨;荷兰商船为2艘,贸易额为白银11.3吨。
萨摩藩1611年攫取了琉球群岛的宗主权后,幕府允许萨摩藩主继续维持和琉球群岛,以及通过琉球群岛和中国沿海私商建立的早已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直到17世纪80年代幕府限制萨摩藩的白银出口量为止,萨摩和琉球之间的贸易繁盛了几十年之久。但从那以后,贸易量明显减少,不过琉球群岛依然是甘蔗和精制糖的重要来源,萨摩藩从那里进口后再运到大阪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市场出售。
在日本九州岛和朝鲜之间的海面上,宗氏大名统治着对马岛。他们长期盘踞在崎岖的对马岛上。从15世纪以来一直和朝鲜保持着友好关系,定期派遣商团前往朝鲜半岛。经宗义朝的斡旋, 1607年江户和汉城重修和平后,幕府同意恢复两国的贸易关系。贸易协定允许宗氏每年派出20艘满载出售给朝鲜政府商品的船只,也允许日本人派员在釜山设立贸易据点,在那里他们可以和朝鲜商人进行私人买卖。最后,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相当比重,日本人主要用金银购买朝鲜的丝绸和人参,还有数额较小的马口铁、牛角、胡椒、苏木,以及如陶瓷器、水墨画之类的艺术品。然而到19世纪中叶,白银外流的老问题又迫使幕府采取限制措施,削弱对马和朝鲜之间的贸易。

1.俄国2.勘察加3.鄂霍茨克海4.贝加尔湖5.黑龙江6.库页岛7.千岛群岛8.虾夷地9.根室湾10.鸭绿江11.朝鲜12.日本海13.汉城14.釜山15.日本16.中国17.对马18.长崎19.琉球群岛20.台湾21.太平洋22.渡岛半岛
地图2.1日本及其邻居
在北方,日本人也和阿伊努人进行贸易。语言文化独特的阿伊努人的起源已经遗失在时间的迷雾中,不过到9世纪为止,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现在的北海道已经繁荣兴旺。其一是占据了岛屿大部分的擦文人的文化(从8世纪到13世纪北海道原住民的文化。在以河川渔业和农业为主的初期发展阶段,他们日用的陶瓷制品表面有了纹样,好像用木刀或刷子按上的,独特的学者称之为“擦纹”,以“文”通用为“纹”,因此叫“擦文文化”。——译注),其二是居住在北海道东北海岸沿线及附近的千岛群岛和南部库页岛的鄂霍次克人的文化。到13世纪时,一种脱胎于擦文文化传统的范围更广泛的阿伊努文化已经发展起来,当地人包括为躲避日本人统治而逃到北方的前东夷人。因为日本人逐渐把东夷称为“虾夷”(“东夷”意思是“东方的野蛮人”, “虾夷”是对“东夷”的另一种称呼),所以他们也就自然地把阿伊努人的家园叫作“虾夷地”,即“虾夷人的地方”。

阿伊努人风俗画,表现的是他们在一头用栅栏围着的、作为牺牲用的熊前面宴饮的场面
德川家康接受幕府将军的任命时,阿伊努人大概有三四万。虽然他们说不同的方言,显现出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他们生活在世代居住的通常只有十来个家庭的村子里,通过共同猎捕鹿、熊和其他动物,在虾夷地的河流捕鱼,在海边捞海藻和大海的其他恩赐,采集水果蔬菜,在河边园子培植蜀黍、粟和多种可吃的植物来养活自己。阿伊努人还以听丰富的以史诗为主的口头传说为乐,他们也崇拜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认为万物都是“神”。
虾夷地丰富的渔猎场所使得阿伊努人自给有余,有时他们经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把剩余的毛皮和海产品用船运到亚洲大陆。16世纪期间贸易量扩大,于是日本人沿着北海道最西南的大岛半岛海岸成立了一些贸易团体。最后蛎崎武士家族成为大岛日本人的首领,1599年他们改姓松前。五年之后,幕府承认松前家族的头领为半岛南半部一块领地的领主,并确认他有权控制和阿伊努人的贸易。
松前氏武士从他们位于大岛半岛一端的城堡小镇根据地,沿着虾夷地海岸建立了一连串贸易场所。在那儿他们用稻米、清酒、海藻、烟草、衣服、铁器和其他家用器具,交换大马哈鱼、鲑鱼、海藻和一些奇特的东西如熊胆、海中动物的毛皮、打猎用的活猎鹰。许多阿伊努人都怨恨日本武士、商人的入侵,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政治自治权和以往随心所欲自由贸易的特权。阿伊努人的歌谣表达了这种日益增长的认为他们的邻居出卖了他们的感觉。一句歌词写道:“我听到日本人被称为可敬的人们,真正好心的人们,但你们的心肯定十分邪恶!”①这种怨恨于1669年转变为暴动,当时一支由当地头领夏顾夏因指挥的大军袭击了虾夷地的日本人居住区,并且准备向松前藩进军。
震惊的幕府调集武士,并从本州岛北部几个藩国征调火枪手前去镇压,几百个日本殖民者和大概更多的阿伊努人死于双方的对抗之中。夏顾夏因的战争失败后,阿伊努人遭受了更沉重的经济剥削。1717年,日本大陆的商人开始向松前大名缴纳固定年费,作为特许他们经管特定贸易前站的交换。到18世纪末,新贸易区已经拓展到地势较低的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当它们进一步推进到虾夷地时,一些日本商人建立了“商业帝国”,控制北部物产丰富的海上捕渔业。到后来,把鲱鱼粉加工成肥料成为该地区获利最丰的行业。日本商人町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人们充当了肥料制造业的先锋,他们引进大大提高了鲱鱼捕获量的先进捕捞方法,建造加工厂和阿伊努工人居住的木板房(阿伊努人通常工资微薄,生活贫困),把鲱鱼粉肥饼载运到日本几个主要岛屿上种水稻的村庄。
18世纪中叶,幕府开始卷入北部贸易。长崎的日本官员在寻找替代银、铜的出口产品时,欣喜地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鱼翅、干鲍鱼、海带、海参和其他烹饪用海货的需求市场。因为那些在虾夷地经管贸易前站的商人把这些商品装在草袋里,所以这些商品一般被称为“俵物”。1785年幕府在长崎成立了“俵物会所”,向虾夷地和本州岛北部的商人收购海中美味,然后卖给中国商人。
根据估算,经长崎一地和阿伊努、琉球、朝鲜、荷兰及中国进行贸易的总额,在近世早期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在日本经济中占据重要比重。虽然如此,出口的机会还是为许多日本人提供了工作,包括九州岛的陶工,他们的陶器畅销荷兰;大阪的住友家族和其他铜业商人、手工业者,到18世纪初几乎把他们的所有产品都运往长崎。而且,一些进口商品也有助于农业产量的提高。截至1740年,虾夷地的鲱鱼粉肥饼施用于日本西部将近一半的稻田。其他的进口商品丰富了生活,提高了生活水准。富裕阶层珍爱朝鲜的艺术品和中国的华贵丝绸。许多日本人得以享有更健康的生活,因为长崎会所把从亚洲进口的所有药物都交给大阪的一个药剂师协会,由他们测定药物成分,用日语重新命名,包装成大小便于携带的样子,然后出售给全国各地的药商。
◎阶级、身份和生活水平
鱿鱼、鳗鱼、章鱼;沙丁鱼、鲭鱼;大米、大麦;糖、盐、醋、酱油;牛蒡、芜箐、莲藕;橘子、柿子;茶、清酒;精美丝绸、耐穿棉布;鞋类、雨伞;雨具;头饰和各种个人小饰品;建造和维修房子的工具;书籍、木版画;罐、锅、涂漆碗筷。即便对日本中等城市的旅行指南和描绘不同城堡小镇商人町的装饰屏风匆匆一瞥,也能发现17世纪末日本城市市场上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丰富多彩。
经济上隶属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从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中获取的“利益”形成了反差。在一些主要城市,常常能看到上层武士和像鸿池屋那样的富商家庭的仆人,用手戳一戳海鲷验证它是否新鲜,闻一闻茶叶判断它质量是否优良,或者为了讨好他们的主人只选择最上乘的织锦缎。而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是,技艺生疏的工匠、散工和佃农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从豆腐而不是鱼肉中汲取蛋白质,佐餐的是白开水,而且只买得起最便宜的棉织品,经常从商人那里淘取二手服装。
社会地位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整个17世纪,幕府和地方大名政府都在寻求新方法,在构成新儒学社会秩序的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间制造更具深意、更显而易见的区别。有些人提倡实行身份制的统治体系。在其他方面,官吏们相信只要把人民相互隔离,他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向统治秩序挑战。而且,严格划分社会等级的过程,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向人民说教:每个具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人都必须履行合乎他身份的义务。在这一点上,官吏们似乎尤其想要让日本的普通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白,他们必须遵守法律,缴纳赋税,通过少花钱多生产促使社会繁荣。最后,国家统治者通过赋予武士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特权,希望武士们永远对他们感恩戴德,保证作为国家权力的忠诚、坚定的执行者为他们效命。
幕府和大名政权通过多种方法实行身份制的统治。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建造的城堡小镇创建了地理分区,农民散居在乡村,而在新兴的城下町,武士住在和商人、手工业者相隔离而自成一体的区域。此外,由丰臣秀吉首倡,德川氏将军充实的一系列法令,教导人们继承父母的职业,禁止武士的后人和其他阶层通婚,并且给予武士独一无二的携带武器的权利。新政权形成后,幕府和大名授予武士担任决策者和政府重要职官的特权。还有,只有武士可以称姓;农民通常只有自己的名字,商人则习惯上被冠以职业或店名。
从17世纪中期开始,幕府将军和各藩发布了一连串规定消费模式的条令,作为进一步强化身份差异的手段。本着这种精神,1660年,加贺藩前田大名公布了一个法令,规定上层武士可以穿13种丝绸,并对此做了准确细致的说明,限定低级武士只能穿4种品级稍低的丝绸,例如府绸。这个法令还把商人和手工业者合并为一个单一阶层“町人”(即市民),规定他们只能穿普通丝绸和棉布。全国各地普遍颁布了这种法令。与此相似,1683年,幕府的一个法令要求江户的町人只能拿府绸、棉布、麻布当衣料。官吏们也不会放过农民。1649年的《庆安告示》告诫农民只能穿棉布衣服,这个规定在11年后加贺藩通行的禁令以及日本各地大名颁行的类似法令中又被重申。
历史记载对于人民如何遵守规定的叙述互相矛盾。很清楚,不服从是普遍的。加贺藩首府金泽的奏报表明,富有的町人通常无视关于衣着的规定,他们乐于付一小笔罚金,或者满足于向艳羡的邻居炫耀他们最好的衣服。作为代价,他们得耐着性子听完官员关于社会责任的说教。据19世纪初一位生活在江户的敏锐观察者记载,甚至在江户,“将军的公告和法令也被称为 ‘三日法’。没有人畏惧,也没有人注意它们。三日之后它们就无人理睬。人人皆知政府只是在它自己觉得需要时颁布法律,所以难怪下层人民不学习、不遵守法律”。①
虽然有各种冷嘲热讽,但还是有其他证据表明,有关身份的规定和经济实力的制约互相结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各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富人不仅吃新鲜海鲷,也品尝鹤、鹅、雉鸡、野猪、鹿肉等美味。金泽的一些武士成为美食者,以致大名害怕他们会因此丧失尚武精神。结果1663年加贺藩颁布一项法令,开门见山地说“近多有奏报武士设盛筵”,然后限制节日和正式场合的饮食为两个汤、一条鱼、五道蔬菜附加菜(即正菜之外的附加菜)、两长颈瓶清酒、米饭、腌菜、糕点和绿茶。②前田大名接着规定,商人家庭的餐饮应该更有节制,符合他们的身份,即为一个汤、三道附加菜、两圆酒瓶清酒、米饭、腌菜、茶和甜点。
正如我们可以从金泽的规定中猜到的,蒸米饭配汤、附加菜、茶正成为近世早期许多人偏爱的食物。不过,经济状况中等,也就是和同时代人相比不富也不穷的人的日常费用,由于地区、时节和个人自我感觉的不同,还是有很大的差异。1837年,加贺藩一个中等武士日记里的相关记载表明,他每天吃鱼,每餐都有蒸米饭;而日本西部另一个武士的日记则显示,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家经常吃掺杂了大麦的米饭,每顿一道蔬菜或豆腐,还有味噌汤,鱼只是每月稍许几次出现在餐桌上。在此之前好多年的1817年2月,一位沿东海道旅行的学者,在他的旅行日志里准确记录了他每天所吃的食物。19日中午,他在一家可以远眺琵琶湖的小客栈停留,享用了一顿有清汤、牛蒡、海藻炒细胡萝卜丝、白芝麻酱拌三叶草的午餐。傍晚大雪开始飘落时,他到草津驿站的一家旅店投宿,进食晚餐温暖身体。晚餐包括:豆腐干和蔬菜汤;醋熘萝卜、柿子和蔬菜;一小碗和熟鱼片一起上来的什锦蔬菜;烤腌鲭鱼。
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农民们都不得不忍受一连串有关他们饮食的禁令。在17世纪4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幕府禁止农民饮酒喝茶,而且进一步规定农民少吃米饭,多吃小麦、土豆和粟米。这类法令的效果还不清楚,但确实有许多农户靠粗茶淡饭凑合着过活。“产稻区的农民,”18世纪20年代的某位官员写道,“有时吃米饭,但只是和其他可吃之物混在一起的稀饭。许多生活在山区或种植其他谷物的地区的农民,甚至新年的三天节日中也吃不到米饭。即使煮粟米或小麦饭时,他们也要掺入许多芜箐、土豆和豆叶,而且连这样的食物他们一天也只能吃上一顿,其他两顿就喝像水一样的稀粥。”①
正如前文所述,江户和日本城堡小镇的建筑外观上体现了潜藏于身份制统治观念中的主要原则,住宅风格因身份和经济地位而有所不同。富裕的武士雇用技艺娴熟的木匠,使用最好的建筑材料营造宽敞的住宅。典型的武士豪宅坐落在围墙和精巧的大门之内,门的大小和装饰用品与住宅主人在武士阶层内部的地位相符。住宅本身通常包括人们脱鞋进屋的正式入口和接待客人的起居室,还有家里人白天聚在一起聊天及晚上睡觉用的其他几个房间。榻榻米铺在大多数房间的地板上,房间之间用障子和拉阖门相隔,后者是一种在木质框架上糊上厚纸做成的活动门。在最好的房间里,常用画作来装饰拉阖门。起居室的特点是有一张摆放书本和陶瓷器的固定案桌和一个壁龛,即用来安放书画立轴、插花或一些珍贵艺术品的壁橱。等级稍低的武士住在结构相似但较小的房子里,随着武士收入和名望的逐级下降,他们的房间数量和装饰用品也相应减少。
典型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房是前店后屋,店门面朝街道,在店里做生意,家人和雇工则住在后面的房子里。大多数这种商住两用的房子都很简陋,建筑物本身未经装饰,反映出室内也并不舒适。例如在近世早期之始,几乎所有家庭的坐卧都在粗陋的木地板上,只有几只塞满稻草的袋子减轻他们的不适。后来,仿照在富裕武士家中看到的装饰,有条件照做的町人也铺设了榻榻米。在本地法令许可的地方,町人还把房子加高到两层甚至三层。富商发现,如果想建造自己梦想中的住房,有必要玩弄诡计制造遁词。金泽和其他许多城市规定,町人住宅的正面不得超过一层半,这就促使一些町人造的房子,正面测量刚好达到这个高度,而后面屋顶却陡然斜着向上,使房子足足有两层高。在布置这样一个家时,人们往往采取种种手法来逾越例行的规矩;在对付禁止町人使用金银叶子装饰房屋,或者使用金漆镶嵌家用品的讨厌的规定时,一个成功的商人如果不用这样的手法来蒙混过关还能怎么样呢?
许多收入微薄的工匠和散工住在穷街陋巷叫作“长屋”的房子里。房子的前门通常通向泥土地板的逼仄的厨房,厨房里放着做饭用的泥炉、堆柴火的柴橱,墙面的钉子上还挂着罐子和锅,此外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个人或者全家生活在一个长宽大约各为2.7米的房间里,有时甚至还要在房间里干活。在日本潮湿闷热的夏季,长屋里的住户汗流浃背,冬天则靠做饭的火炉取暖。没有活水接到各个单元,所有人共享一口水井、一个厕所和一个垃圾箱。
虽然农舍的面积和设计差别很大,但大都明确分为居住区和工作区两个部分。农民在泥土地面的工作区干农活,有时也在那儿圈养动物。那种房间一般也有做饭的泥炉和饭后洗涮用的槽子。在最贫穷的农民家里,居住区有简陋的泥土地板,上面铺着装了稻草的袋子,并用低矮的分隔物与干活区隔开。收入较高的家庭会多造几间房,房间里放上垫高的木地板,一家人围坐在室内的炉膛边吃饭,冬天则取暖。可以猜想,乡村精英们自得于有若干房间的住宅,也享有许多在富裕商人和武士家里才能发现的舒适。
大体上,近世早期日本的物质福利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可观的改善。虽然缺乏可靠的数据,但有足够的其他证据证明:19世纪早期的商人和工匠家庭穿得更好,吃的食物更多样,住得比他们两百年前的先人更宽敞。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坐在榻榻米而不是木地板上,睡在塞满棉花的寝具上,把被褥存放在内置的壁橱里,把其他物品如备用的衣服、药品、书写用品、化妆品、工商业票据和现金等放在专为收纳这类东西而造的柜子里,房间也变得更加舒适。由于人们普遍能获得甘薯、马铃薯、南瓜、胡萝卜、青豆、西瓜以及其他从西方引进的食物,饮食有了很大改变。18世纪,一些以天妇罗、烤鳗鱼和其他食品为特色的餐馆出现在江户、大阪和其他主要城市,这是城市不断繁荣的另一个标志。19世纪初,江户的一个厨师发明了寿司后,这种食物开始风靡各地。
相似的趋势在农村也很明显。虽然农民在17世纪初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截至近世早期的中间阶段,即便是偏远小村的家庭也能购买不同的食物和衣服,有时还有小件奢侈品。起初,小贩们在乡村穿梭,兜售干鱼、厨房用具、锄头和其他农具。后来,对商品的需求扩大,以至于许多村民开始自己开设长期性的“杂货铺”,当地村民可以在那儿买到他们认为是日常必需品的全部商品:豆酱、豆腐、海藻、面条、仙贝(米饼)、灯油、蜡烛、针线、便鞋、木屐、草鞋、烟草、烟斗、笔、墨以及毛笔等等。正如19世纪早期一位观察者所言:“农村零售业年复一年地增长。清酒、染料、干货、化妆用品、五金器具、漆器,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在农村出售。”①
当然,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兴旺了。没有能力或时运不济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沦于贫困,而那些没有做好准备利用商品化农业和原初工业化提供的时机的农户,则世代居住在劣等的房子里,喝大米粥度日。武士阶层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们从大名那里领取固定年俸,其数额从17世纪初定下来后基本没有提高。由于关于身份的规定禁止他们投身于商品经济之中,大多数武士和其他日本人一样,没有从生活水平的普遍上升中受益。
不过,正如有例外就有规则,这类观察确定了当时存在一个普遍规则: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1600年至1850年之间,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了重大改变和提高。多少事物得到改善还不能确知,但是对住房风格和舒适度、服装、饮食的考察表明,19世纪中叶,大多数日本人家庭的生活条件可以和工业革命前夕的英美两国相比。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出生于近世早期末叶的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和出生于1840年的西欧人(男性39.6岁,女性42.5岁)一样长,略高于1850年出生的美国人(男性37岁,女性39岁)。
坚毅的骑马环球旅行者伊莎贝拉·露西·伯德于1878年骑马从东京到本州岛北部旅行了近2 400公里后,在她的《日本僻径》里善意地比较了二十年前她在美国的经历。19世纪50年代当这位英国妇女游览芝加哥时,旅馆主人先把她安排到一个有四张床、五位妇女和一个生病小孩的房间里。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后,伯德被安排到一个小房间,但她很快就惊慌地发现,狭窄的单人床上铺着一张“肮脏的水牛皮”,招引了“一大群活生物”。后来饭厅的污秽又吓坏了伯德,她没有胃口吃“几乎全生的煮羊腿、硬如吉他琴弦的很老的鸡腿肉”,或者“浸泡在油脂中的烤猪肉”。①相反,当她参观日光时,她住在让她“高兴”的“中等阶层”的乡村住宅里。“关于这幢房子,我不知该写些什么,”她这样写道,“它就像日本的田园风光,无一物不悦目。”赞叹完锃亮的楼梯和“如此美丽洁白,我几乎不敢从上面走过去”的榻榻米,以及一幅悬挂在壁龛中的“画在白色丝绸上的花朵盛开的樱桃树枝”图之后,她吐露说,“我几乎希望房间少几分雅致,因为我不断担心会撒上墨水,会使榻榻米凹陷,或者撕破纸窗户”。至于饮食,伯德对盛在“精美的加贺瓷器”里的鲑鱼、鸡蛋、米饭和茶,更是赞不绝口。
①James L.McClain, “Space, Power, Wealth, and Statu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Osaka, ”in McClain and Wakita Osamu, eds., Osaka: The Merchants' Capital of Early Modern Japa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5-56(modified).
① Tessa Morris-Suzuki,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994), p.29.
①Thomas C.Smith, “Premodern Economic Growth:Japan and the West, ”in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 750 -192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29.
① Tessa Morris-Suzuki, Re-Inventing Japan:Time, Space, N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 998), p.1 3.
① Takeuchi Makoto,“Festivals and Fights: The Law and the People of Edo, ”in James L.McClain, John M.Merriman, and Ugawa Kaoru, eds., Edo and Paris: Urban Life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Modern Er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04-05(modified).
②James L.McClain, Kanazawa: A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ese Castle Tow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 982), p.94.
① Nishiyama Matsunosuke, Edo Culture: Daily Life and Diversions in Urban Japan, 1 600 -1 868, tr.and ed.Gerald Groemer(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 997), p.1 60(modified).
①Smith, “Premodern Economic Growth, ”p.27.
①Susan B.Hanley, Everyday Things in Premodern Japan: The Hidden Legacy of Material Cultu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 997), p.1 88; Isabella Lucy Bird,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1 973, reprint edition), pp.49 -53; and Bird, The Englishwoman in America(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 966, rep.ed.), pp.1 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