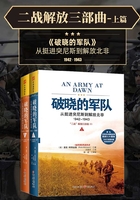
战斗到底
从环绕阿尔及尔的半月形海湾极目远眺,这座城市仿佛葱山翠岭间展开的一幅白色画卷。阿拉伯城区弥漫着恶臭,法国的殖民统治与穆斯林欲说还羞、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丝毫不影响这座城市的魅力,距离反而为它平添一分风韵。林荫大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电影院、商场以及别致的咖啡馆,昂首阔步的公子哥儿徜徉其中,让一个个夜晚顿添生气。在1492年出走西班牙的穆尔人来此地避难前,阿尔及尔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与奥兰一样,这座城市很快靠海盗繁荣昌盛,庇护横行地中海的海盗船队长达3个世纪之久。高达400英尺的巴巴罗萨(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译者注)王宫建于16世纪,如今仍屹立港口上方天际。20世纪20年代,一名西方游客站在王宫前浮想联翩,认为这座古老的建筑里“回荡着基督徒奴隶的呻吟”。
一个多世纪以来,阿尔及尔一直是法属北非帝国的中心,这座白色的城市里“苍蝇乱飞,街上满是乞丐和巴黎上等人”。在法国人的眼里,这座昔日的海盗城如今犹如“一个露着白花花的身子、倚门卖俏的半老徐娘”。但艾森豪威尔及其参谋人员认为,即使没有覆盖整条非洲海岸线,阿尔及尔也是阿尔及利亚的战略要冲。作为“火炬行动”最东端的登陆点,这座城市是随后盟军长驱直入挺进突尼斯的一块跳板。继英美联军登陆之后(打着美军旗号),英军转道东折直取突尼斯。
11月8日一早,罗伯特·墨菲开着一辆大别克,匆匆穿过阿尔及尔最繁华的城区,去履行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项外交使命。在11月7日周六傍晚之前,这位美国外交官一直待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对于即将发生的大事还浑然不觉。现在,用他的话说,“两年的酝酿和筹划”即将接受检验。此前艾森豪威尔和白宫一口否决了他提出的将“火炬行动”推迟的建议,这令他颇为不快。墨菲致电罗斯福:“我深信,如果得不到法军最高指挥部的支持,那么北非登陆必将是一场灾难。”华盛顿的回电也毫不含糊:“总统决定,登陆行动按原计划进行。”墨菲接到指示,“务必确保目前与你接洽的法国军官的沟通和合作”。
他已经尽力。几位可靠的法国起义人员,包括马斯特将军在内都在几天前提醒他盟军在北非可能会有所行动。“你好,罗伯特,富兰克林来了”,一听到伦敦发来这条事先定好的电报,墨菲即刻提醒这些起义人员,盟军的登陆行动即将开始。奥兰市内的兵变显然以失败告终,但在阿尔及尔,虽然克拉克无法兑现在歇尔谢尔会议中作出的提供现代化武器的承诺,数百名法国游击队员仍开始占领一些关键设施,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者后来写道,旨在“消灭这座城市”。起义人员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很快控制了警察局、发电厂、阿尔及尔电台和电话交换台,还把许多法军指挥官关在司令部。许多维希官员乐得被拘禁,一位旁观者指出,“如此他们就不必苦苦寻觅自己的良知了”。至于墨菲一再致电直布罗陀,询问:“吉罗在哪里?”却始终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星期天中午12点45分,墨菲来到比亚尔这块飞地上一座戒备森严的黄色阿拉伯宅邸——橄榄别墅,与身材高大的塞内加尔哨兵擦肩而过。他敲了敲门,一名面色黝黑、留着小胡子的男子阴沉着脸走进客厅。维希政府北非陆军司令阿方索·皮埃尔·朱安将军的一贯装束是一顶巴斯克贝雷帽、一件泥迹斑斑的短斗篷,这次却穿着一身粉红色条纹睡衣。因为1915年右臂重伤,朱安获准以左手行礼。可这一次,他既未向墨菲敬礼,也没有与他握手。
“很荣幸受我国政府委派,前来通知你,美英联军即将登陆北非。”墨菲说。
“什么?你是说,我们在地中海看到的舰队要在这里登陆?”
墨菲忍不住紧张地咧嘴一笑,点了点头。
“可一个星期前你还亲口对我说,美国绝对不会进攻我们。”
“我们受人之邀。”墨菲说。
“谁的邀请?”
“吉罗将军。”
“他来了?”
墨菲暂时不想透露吉罗这会儿正在直布罗陀的一个地下室里生闷气,便对朱安的问题置之不理,立即转移了话题:“他很快就到。”

维希军队和盟军停战后,美国驻阿尔及尔高级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和法国驻北非地面部队司令阿方索·朱安将军合影。墨菲刚刚被授予优质服务勋章,以表彰他在“火炬行动”中的贡献。

1942年11月8日,登陆阿尔及尔
1 Commando 第1突击队
MOORE 穆尔第168步兵团第2营
RYDER 赖德第34师
Terminal Force On H.M.S.Broke and H.M.S.Malcom “布洛克”号和“马尔科姆”号上的“终极行动”部队
To Bone 往波尼方向
To Cherchel and Oran 往歇尔谢尔和奥兰方向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in Taya 艾因塔亚
Airfield 机场
Algies Bay 阿尔及尔湾
Apple Beaches 苹果海滩
Arba 阿尔巴
Beer Beaches 啤酒海滩
Beer Red Beaches 红啤酒海滩
Blida 卜利达
Boufarik 布法里克
CAP SIDI RERRUCH 西迪费鲁西角
Castiglione 卡斯蒂廖内
Charlie Beaches 查理海滩
Cheragas 舍拉加
El Harrach R. 哈拉彻河
El-Biar 比亚尔
Fort I’Empereur 拿破仑堡
Hotel St.Georges 圣乔治饭店
Hussein Dey 侯赛因代
Lambiridi 朗比利迪
Maison Blanche 白屋
Maison Carree 卡利神殿
Mazafran R. 马扎弗兰河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Summer Palace 夏宫
Surcouf 叙尔库夫
Zeralda 齐拉尔达
墨菲介绍了埋伏在非洲海岸的登陆大军,同时还不忘将军队规模夸大了7倍。“从你我这几年的交往来看,”他对朱安说,“你比谁都希望解放法国,但只有和美国合作这件事才有可能成功。”
现在,一出滑稽剧正式上演。朱安将军对盟军的事业深表同情,但碍于顶头上司不久便会来到阿尔及尔,他表示爱莫能助。“他可以立刻撤销我发布的命令,”朱安说,“这样的话,部下只会听命于他,而不是我。”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朱安匆匆派出一辆别克。20分钟后,二战中一个万夫所指的人物粉墨登场,走进了这座官邸。
在这个只剩下平庸之辈的国家,达尔朗上将是个最不起眼的角色。时年61岁的达尔朗出身于法国水兵世家,五短身材、鸡胸驼背,无疑是对德军自诩的高颜值一个莫大讽刺。虽然是美国人叫他金鱼眼,但他却对英国人恨之入骨,想必是因为他的曾祖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葬身直布罗陀。他是法国舰队的掌权人,同时也是贝当元帅的继任者和维希政府三军总司令。作为一名亲纳粹分子,达尔朗为第三帝国提供托管地叙利亚的机场,并允许其借道突尼斯为隆美尔提供补给。丘吉尔给他的评价是“一个足智多谋却眼光狭窄的坏蛋”。
不知是上天刻意安排还是机缘巧合,此刻达尔朗正在阿尔及尔陪伴儿子阿兰。阿兰患脊髓灰质炎躺在马约医院,即将不久于人世。过去的两年间,这位上将在背地里曾不止一次暗示,如果条件允许,他愿意支持盟军。在艾森豪威尔从伦敦动身赴直布罗陀前,丘吉尔还对他说:“如果能见达尔朗一面就好了,虽然我恨他,但若能争取他的舰队加入盟军阵营,哪怕要我跪在地上爬一英里,我都愿意。”罗斯福总统的想法与丘吉尔惊人相似,10月17日他给墨菲也下达了类似的指示,命令他与这位对“火炬行动”极为有利的维希海军上将接洽。
但达尔朗态度暧昧,似乎不愿多谈。获悉盟军即将发动登陆战,他满脸通红地说道:“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极其愚蠢,但也深信美国人还是更聪明一些。但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显然要和英国人一样铸成大错。”
达尔朗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整整15分钟。墨菲放慢脚步,走到达尔朗身边,焦急地说道:“眼下时机已到!”上将一挥手,回绝了他的请求。“我向贝当发过誓,”他不肯就范,“我不能违背诺言。”但他答应会致电维希政府,请求进一步指示。刚一走出室外,两人就发现原来的塞内加尔卫兵换成了40名戴着白臂章、端着普法战争时代长筒步枪的起义人员。“这么说,我们被俘了?”达尔朗问。
他说的没错。墨菲的同事肯尼斯·潘德受命火速前往法军上将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拿到达尔朗写给维希政府的密电。潘德私下拆开信件,仔细阅读之后认为达尔朗对盟军事业的诚意不够,当即将其丢弃。回到别墅之后,潘德含糊不清地对达尔朗说:“该做的都做了。”
维希政府没有发来片言只语,盟军也不见任何动静。就在僵持之际,墨菲误以为自己看错了日期,准备提前一天仓促发动起义。时间在嘀嗒声中一分一秒地流逝。天已破晓,达尔朗停下脚步,长舒了一口气,给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建议:“吉罗不是你们的人,政治上他还很幼稚。他不过是个优秀的师长,仅此而已。”
事实上起义已经失败。“这不就是一次民防演习么?”一名摸不着头脑的维希政府官员问道。维希政府军冷静沉着,一连夺回了几个坚固的支撑点(军事上指对巩固防御阵地起支撑作用的扼守要点。——译者注)。在陆军司令部,起义人员和政府军同唱《马赛曲》,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分子缴械投降,列队走出大楼。获悉阿尔及尔和奥兰事变,身在维希的贝当立即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事关法国的安危和荣誉。有敌来犯,我们应当自卫。”
一支政府军巡逻队开着3辆坦克封锁了橄榄别墅的各个大门,击退了起义人员,把墨菲和潘德锁进门房。朱安手下的一名副官挥着一柄特大左轮手枪,指着美国人喊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潘德恍若进入了《潘赞斯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的场景之中。一名塞内加尔卫兵给每个美国人发了一支吉丹雪茄,要被执行枪决的人都会受到如此礼遇。
★★★
盟军又策划正面突袭阿尔及尔港,但可悲的是,与“预备役行动”一样,这次行动也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这次任务“终极行动”仍由英方策划指挥,由美国人助阵,意在完好无损地拿下这座港口,主力是两艘古董级驱逐舰——“布洛克”号和“马尔科姆”号,由皇家海军H.L.圣·J.范考特上尉指挥。为抵挡火力,工兵在每艘驱逐舰甲板四周焊上厚达0.5英寸、高3英尺的铁板。船艏舱内被填满水泥,船艏装上重型装甲板。就在墨菲对于盟军登陆时间疑神疑鬼之际,这两艘战舰已经抵达阿尔及尔湾的11寻(测量水深用的长度单位,约1.829米。——译者注)等深线处,继而向西驶向栅栏揿(战时布置在港口的水底铁丝网。——译者注),阻塞海港入口。
“布洛克”号和“马尔科姆”号两艘战舰上的686名士兵均来自第135步兵团第3营,两年前离开明尼苏达州与姐妹团一起加入第34师。该团在葛底斯堡的一场苦战换来一句“战斗到底”的座右铭。第3营自称“歌唱的第3营”,因为军营歌谣是这个营的保留节目,比如《一艘驶离孟买的运兵船》这首黄色英国小调。这支部队沿袭了明尼苏达特色,士兵名字清一色的埃里克森、卡尔森和安德森。营长埃德温·T.斯文森中校担任过斯蒂尔沃特明尼苏达州立感化院典狱长助理。
斯文森中校机智、慷慨,有一张职业拳击手般棱角分明的脸,据说他能滔滔不绝地骂上几个小时都不重复一个脏字。斯文森曾对一名英国人夸下海口,说随便叫出第3营的一个军士长,都能把他给揍趴下。范考特上尉则告诉斯文森,盟军突击队要拿下把守这座俯瞰港口的法军炮台。几门法军大炮炮口离地过高,下方有一片盲区无法命中目标。“终极行动”在阿尔及尔东西两翼展开的第一梯队登陆的目的是引蛇出洞,很可能将守军引出港口。后来证明范考特的话与事实截然相反。
阿尔及尔港灯光闪烁,盟军驱逐舰冲向伸出半月形防波堤的栅栏揿。星条旗在桅杆上猎猎作响,市内陡然一片漆黑,探照灯光柱交替掠过水面。斯文森一度以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轰炸机指明入港方向。很快探照灯发现并且盯上了这两艘驱逐舰,灯柱晃得驾驶台上的人睁不开眼睛。“布洛克”号和身后1海里的“马尔科姆”号一边开炮,一边转向右舷避开防波堤,在烟幕的掩护下掉头。驱逐舰试图第二次冲破栅栏揿也失败了,法军的探照灯仍然完好无损,斯文森手下的士兵发射了几颗照明弹打算照亮入口,但照明弹的光束却无法穿透驱逐舰释放的烟幕。
这时“马尔科姆”号进入了法军大炮的射程。从凌晨4点06分开始,炮弹接二连三地击中船体,锅炉被打穿,舰速只剩下4节,裹着白烟的“马尔科姆”号一时成了活靶子。有几颗炮弹击中烟囱,弹片散花般落在甲板上,300名步兵哆哆嗦嗦地趴在不堪一击的防狙击盾牌后面。堆着成箱榴弹的中舱燃起大火,舰身严重右倾,风雨甲板离水面不到6英寸,士兵拼命将着火的榴弹箱扔出船舷外。“马尔科姆”号终于重新发动,左右摇晃向海上开去。船员花了几个小时冲洗甲板上的血迹和脑浆,用床垫套当作裹尸布包着尸体丢进海中。
在第四次进港的途中,“布洛克”号舰长A.F.C.莱亚德发现了标明进港航道的两盏昏暗的绿色浮标灯,于是他下令提速到20节,不费吹灰之力就冲破了用铁链绑在一起的木栅栏揿。莱亚德将战舰停靠在路易·比亚尔码头,期间舰上的火炮也将码头方向的狙击火力压制住。
“马尔科姆”号颠簸得厉害,斯文森中校和“歌唱的第3营”费了好大力气才爬上甲板,冲过跳板上了码头。斯文森指示手下:“你们要像屁股后面追着个老虎的狒狒一样冲上码头,找到隐蔽的地方后,给我狠狠地打。”其实没有必要狠狠地打。天刚破晓,盟军就控制了阿尔及尔的电厂、莫雷的油库以及航母基地码头以南的几座仓库。航拍照片上与海防炮台类似的圆形目标其实是厕所。礼拜天弥撒的祈祷钟声响彻城市上空,码头和米舍莱街两侧漂亮的白色宅邸异乎寻常的宁静。士兵开玩笑说,阿尔及尔的味道就像沙龙,这是因为汽油短缺,汽车只能用酒精作燃料。斯文森竖着耳朵听第168步兵团的脚步,盼这支来自艾奥瓦西南的姐妹团下山来接应从该市以西登陆的战友。
确实有声音传来——恰恰相反,“嗖嗖嗖”的声音来自北面一英里的诺尔码头上一座炮台发射的炮弹。法国水兵拆了一段老城墙,海滨全部暴露在这座炮台的火力之下。第三发炮弹一下削掉“布洛克”号的艏尖舱,码头岸壁顿时腾起一阵烟尘。经范考特上尉许可,莱亚德砍断舰上的缆绳,将驱逐舰移泊到一艘停泊在敦刻尔克码头的法国货轮下风。上午9点20分,阿尔及尔港暂时恢复平静,突然间法国炮兵又在左上方开火。前6发打偏,后5发全部命中海图室和军官舱。还有一发从医务室呼啸而过,一名医生当即死亡,另一名军医的右臂被打断,他趁吗啡的劲还没过,传授了美国助手一些紧急截肢技术。
范考特拉响撤退号,但斯文森的部下仍分散在码头各处,处在法军狙击手的火力下。直到“布洛克”号再次断缆、拖着一股尾巴似的浓烟迂回离泊时,只有60名士兵爬上船。上等兵哈洛德·卡勒姆的胳膊和腹部早已中弹,等他爬到码头边,驱逐舰已开走。他只好躺在太阳下,嚼着磺胺片,喝着水壶里的水,目送“布洛克”号驶出视线。“众目睽睽之下驱逐舰在港内沉没,对军中士气大为不利。”范考特3天后如此解释道,但他却对被丢在岸上的250名士兵的士气只字不提。“布洛克”号船身被炸开22个洞,舰上的人员跳上救援船后不久便沉没。
虽然损失了这艘驱逐舰,斯文森仍未气馁。他估计共有4个法军步兵连包围路易·比亚尔码头,敌军虽然人数众多,但还不至于势不可挡。他不敢动用迫击炮和机枪,怕伤到从门口和十字路口向外张望的平民。但皇家海军炮手却连连轰炸诺尔码头上方的一座要塞,斯文森仍然心存幻想,以为第168步兵团会按计划尽快赶来增援。他用草垛和包装箱构筑了一道工事,外围可将法军挡在手榴弹射程外,内围可掩护伤员和重武器。
没过多久,码头上到处回荡着清晰的装甲履带声。几辆雷诺轻型坦克的机枪和一门37mm口径大炮对准斯文森的防御工事发起猛攻。他连忙集中仅有的几枚反坦克手榴弹,命令炮兵伏击闯过来的坦克。可惜每一发手榴弹都未命中目标。炮弹爆炸引燃了草垛,火势逐渐蔓延到仓库。又赶来的两辆雷诺坦克织成一条交叉火力带,把美军逼到海边。火苗舔舐着成摞的弹药箱,引爆一轮轮迫击炮弹。美军步兵即将弹尽粮绝,斯文森指示士兵装上刺刀,转念又觉得不妥,“终极行动”已经造成盟军24人死亡、55人受伤。在码头上耗尽这些士兵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中午12点30分,斯文森举旗投降。
担架员连忙转移伤员,滚滚的烈焰就快烧到他们的绷带。斯文森和他的手下集合完毕,塞内加尔士兵就开始搜刮他们的手表、戒指和钱夹。这时,一名法国军官走了过来,命他们退还赃物,还拔枪吓唬这群抢劫者。在美国人列队上山去俘虏营的路上,一名顽固的狙击手最后一枪命中阿尔文·朗宁下士,这个来自明尼苏达米兰的高大金发农家小伙当场死亡。与破败的奥兰港不同,这里的法国守军粉碎了盟军的突袭行动,得意忘形之际忘记破坏港口。对于参加“终极行动”的美军来说,这个意外的收获兴许可以聊以自慰吧。
11月8日,3.3万名盟军士兵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地登上阿尔及尔东西两翼的海滩。有几艘超载的登陆艇进水沉没;许多人因艇艏跳板放得过早,或舵手缺乏经验致艇身打横而落水;有些攀登网太短,士兵们要从6英尺高处跳入等在下面的小艇中。尽管上级命令要保持绝对安静,但喧闹声还是大得“恨不得让远在柏林的德国人都听见”,一位军官事后写道。东萨里和皇家西肯特郡团最终等来了配给的酒,当士兵们喊着口号下艇冲向巴巴里海滩,至少有两名借口“尝尝味道”的军官却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地爬上床酣然大睡。
事后证明,夜间登陆阿尔及尔滩头的难度相较奥兰突袭有过之而无不及。登陆艇仿佛追逐萤火虫的孩子,在一盏盏信号灯间漫无目的地徘徊了几个小时。许多身强体壮的士兵都晕船晕得不想动,甚至不去理会自己将因临阵退缩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要去哪里?”这些大声的询问,只能招来断断续续的回应或一顿臭骂。一位戴着白臂章、黑暗中更显眼的英国登陆指挥官,嗔怪地对一艘接一艘的登陆艇说:“对不起,你们登错了滩!”有6艘登陆艇偏离航线2海里,进入马林岛法军炮台的射程,其中4艘被击沉。由于操作失误,阿尔及尔舰队的104艘登陆艇中,第一波只有4艘成功登陆。6艘艇返回去接第二波,却发现母船不见踪影——一股2.5节的西向海流在4个小时内将舰队向下游推移了11海里。
法国守军以一敌五,不久就败下阵来。阿尔及尔湾东部的开普马迪府附近,一队士兵误在一片沙洲上下艇,他们蹚着没顶的海水,拽着缆索像袋鼠一样跳上海滩。英美突击队在马迪府发现了一座他们正在寻找的海防炮台,便立即向弹药仓扔了几枚手榴弹。几声闷响过后便是一阵尖叫和熟悉的骂声:“你们干吗不去打德国鬼子?”英国海军的炮没打中目标,反而伤到了平民和盟军。一名法国农夫抱着他12岁儿子的尸体,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滨海大道上。一户户衣着考究、准备赶早弥撒的法国人家遇到盟军士兵时都别过脸去。在艾因泰耶市广场,一群落海的士兵正围着一大堆篝火取暖,一群穿着睡衣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冷冷地望着这个奇怪的礼拜天早上隆起的海面,这时一个精明的酒店老板打开了店门。
盟军登陆的最西端,英军第11旅将7 000名士兵送上卡斯蒂廖内,惊奇地发现一位同情盟军的法国军官不肯给部下发放弹药。1830年,在西迪费鲁希,一支法国军队宣称阿尔及利亚属于拿破仑二世之后,驻军几分钟内即宣告投降。一位炮兵少校走出海滩附近的掩体,说:“先生们来迟了。”
第34师第168团本来要挥师向东,赶往阿尔及尔港增援斯文森被困的“终极行动”大军,但他们不仅来得太迟,还迷了路。第168团4 000名美军稀稀落落分散在35英里的海岸沿线。军官们驾驶征用的汽车一遍遍驶过狭窄的乡村小道寻找自己的部下。登错滩头的士兵中就有艾奥瓦州维利斯卡的娃娃上尉——罗伯特·穆尔,他如今是该团第2营的副营长。午夜前穆尔带着2个连从“凯伦”号下来,分乘9艘登陆艇到离船几百码的集结区,但他等了几个小时也没等来一艘登陆艇,随后便命艇长调头驶往陆地。
闯过离岸1海里处一片汹涌的浪区后,一名海军军官请穆尔放心,他没有走错航道。冲滩并将装备拖上海滩后,士兵们却懊恼地见到了第11旅的士兵。穆尔当即断定,他们非但没有登陆白啤酒海滩,反而顺风转向航行8海里,到了白苹果。穆尔派了一个班去纵深侦察。这个班一去不返,他只好集合余下的200人,出发去找该营余部。
第34师两年的训练这时候才见分晓。艾奥瓦州国民警卫队业余橄榄球场演习和小镇广场训练似乎与阿尔及利亚沿海的短叶松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该师师史中记载,第34师提前10个月仓促调到英国,各团分散到北爱尔兰各地,训练设施不足、人事变动过于频繁,各部队挪作劳工或司令部警卫,表明抵达非洲的各部多半“仓促上阵”。和该师其他团一样,第168团也拥有傲人的历史,仅一战中就立下5次战功。可惜辉煌的过去既不能占领阿尔及尔,也给不了士兵作战经验,更不能告诉罗伯特·穆尔他如今身在何处。
穆尔带2个连沿海滨的山坡穿过1英里的葡萄园和松树林后,才发现走错了路。他立即下令停止前进,按原路返回,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中尉没听到命令,仍带领一小支先头部队继续前行。将近中午时分,200名法国殖民军乘坐12辆卡车在穆尔一行人面前驶过。穆尔和手下士兵瞪大眼睛一声不吭地看着车队走远,未发一枪一弹。
登陆几个小时后,穆尔又累又渴,这时阿尔及尔以西的朗比利迪方向传来炮火声。公路一侧土丘上一挺法军机枪将G连2名士兵击毙,另外2人受伤。穆尔立即命令3个排将这个阵地包围,经过一阵激烈交火后,7名敌军投降。就在几个孩子挤在家门口,伸手向美军士兵讨香烟的工夫,法军狙击手的子弹钻进石墙、掀起人行道上一块块草皮。几名阿拉伯人身穿邋遢的长袍、脚趿发黑的拖鞋,仿佛法军狙击手和他们的美国目标根本不存在一样,慢吞吞地穿过广场。
穆尔混在一群行人中快步穿过一段没有遮蔽物的十字路口,准备再次组织部下从侧翼突袭。现在他的手下是该团3个营的余部,还有几十名掉队的士兵。一栋楼上的一挺机枪打死一名中尉,伤了一名上尉。穆尔爬上一座高出这栋楼的小山,匍匐着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他陡然一翻身,惊得目瞪口呆。紧挨他的一名列兵中了一枪。穆尔解开帽带,脱下头盔。狙击子弹在帽顶开了一条黑疤似的深槽,只要再低一英寸,这一枪就会要了这个娃娃上尉的小命。
穆尔第一次体会到恐惧是什么感觉。哪怕一次莫名的冲突也能置人死地。“或许和狙击手交手才是真正的战斗。”几个月后,他因在朗比利迪的英勇表现荣获银星勋章时说,“我现在才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喜歌剧(指前古典主义时期在意大利首先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歌剧形式。——译者注)战争”。此外,优秀的士兵应该像在安蒂特姆河和默兹—阿尔贡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穆尔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子弹在钢盔上擦出一道裂痕,我刚要坐起来,突然意识到那样会变成敌人的靶子。除此之外我吓得半死,还好安然无恙。”
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与非洲北端数千名美军士兵一样,穆尔得到了几个重要教训,包括战斗时要低头;出发前多花些时间研究地图。另外几项涉及战争和领导的教训则是:混乱是战场的固有属性;随机应变是必备技能;速度、伪装和火力能赢得小战斗,也能赢得大会战;每一刻都有危险、人人都会死。
穆尔戴上钢盔,叫来一名军医助手照顾负伤的列兵。生者仍在等待上级的命令,远处是阿尔及尔若隐若现的白色屋顶。没有受伤但流着血的罗伯特·穆尔继续迎敌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