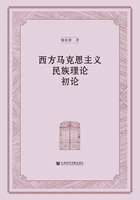
绪论
一 研究缘由及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里的“边缘”内容,很多内容都渗透或依附于其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理论中。也许正是鉴于这一情况,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较少。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在当代还产生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另译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很有影响的民族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解读、反思和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某些方面深化了对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的认识。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偏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系统梳理,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有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首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或趋势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源于对“成熟的”欧洲民族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和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设中出现的民族问题的思考。正是因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观察总体上是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为着眼点的。因此,他们更多的是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他们以生产方式的历史推进为依据,侧重于经济与政治的互动,相对而言,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研究较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统治和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丧失。因此,从文化、政治、哲学,甚至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意识形态层面,解读民族问题,构建民族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为重要的方面。乔治·卢卡奇(Georgy Lukacs)从德国的哲学文化思想发展史来论证法西斯及其种族主义产生的非理性主义根源,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则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反犹主义问题。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则孕育和开启了从“文化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模式”研究民族问题的可行性路径。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新左派”都沿袭了对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的这一文化意识形态阐释路径,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对其进行了不断拓展、丰富和发展。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另译作威廉·赖希或莱奇)从大众心理的非理性视角和精神分析学视域系统研究了法西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产生及其特点以及苏联民族主义的“倒退”。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从心理学、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维度来解读民族问题,阐释民族理论。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英国“新左派”,他们开创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霍尔更是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直接影响,从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媒体与意识形态相互接洽的复杂话语中,批判撒切尔构建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霸权,挖掘文化对种族、散居族裔身份构建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但是,这其中也存在严重问题,就是它们的解读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和阶级斗争理论越来越远。
另外,因为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具体民族问题讨论较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新问题,进行了新解读、新探索。霍布斯鲍姆研究了当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哈贝马斯讨论了后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策略,霍尔反思了现代化和后殖民时代的少数族裔身份构建问题,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讨论了民族身份的承认和民族共同体构建问题。而对当今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及其超越是他们关注的共同点。这些探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野,呈现了新材料、新信息和新问题。
其次,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前,虽然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带来了较大冲击,但它“尚不能动摇国家的存在,由于‘民族’仍为维护和巩固国家所需要,所以与民族国家仍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主体相适应,民族建设仍将是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1]。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面临着任务艰巨的民族建设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遇到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研究,特别是重点研究了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种族歧视问题、散居族裔问题和当代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们也做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批判、研究和探索可以给正在进行现代民族建设的中国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族问题的揭示和分析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也是广义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构成。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需要吸收尽可能多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养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份遗产和资源需要我们好好珍惜和发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梳理将对我们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提供一份难得的理论借鉴。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争议较大的概念,在此,首先需要对它进行明确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奠基人之一的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在1930年重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提出的,他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去指称以他和卢卡奇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55年,法国学者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也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去指称从卢卡奇开始的“拒绝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2],并论证了这一革命哲学与列宁主义的冲突。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逐渐被人使用。1976年,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扩大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使之成为不仅包括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包括新实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者的理论取向与前者相反,它反对人道主义,而拥护科学传统。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同安德森的做法,并一直延续至今。
从国内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崇温先生最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他对这一概念论述较多,而且影响也较大。不过,也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持以下几种意见。
首先,徐崇温先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思想史概念,一个意识形态概念”[3]。它是一战后西方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与列宁主义对立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它在哲学方面批判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张借助于现代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去“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在实践上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徐崇温先生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不加分析地混合在一起,是一种折中主义,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针对徐崇温先生的看法,王雨辰具体分析了柯尔施、梅洛-庞蒂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认识差异。他指出: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所指称的理论思潮,“并不是什么反列宁主义的,而是在探寻适合西方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一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4]。柯尔施眼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历史条件下的体现。而梅洛-庞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者”,其理论不是为了实现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为了论证青年马克思思想与成年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对立,以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性,贬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因此,梅洛-庞蒂的理论显然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际,不能为我们所借鉴和采纳。不过梅洛-庞蒂的思想因赢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认同而在西方广泛传播。王雨辰总结说,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性,因此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必然既包括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也包括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思考。”[5]
还有段忠桥认为,“徐崇温同志虽然对开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但他界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已经在妨碍我国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深入研究”[6]。徐崇温所说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引进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但他的概念其实是对柯尔施、梅洛-庞蒂和安德森三者概念的综合,而且当时这个争议性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不过,总体而言,当时西方使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一种马克思主义,而并非徐崇温所说的“非马克思主义”,其中的“西方”指的都是相对于俄国(苏联)而言的西欧大陆,而不是徐崇温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而张一兵教授及其同人曾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义的指称,仅指一种左派批判思潮,但它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而是一场多线索、多形态展开的理论运动。其中的“西方”不仅指地域层面,而且指政治文化层面,它包含“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督教文化”等三层含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特指西方的同“正统”相对立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它们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相关性表现各不相同,可以表现为理论方法的某种继承性,或理论立场的一致性,或主题的一致性,因此它色彩斑驳、内容庞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理论特征为: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总是呈现出某种‘异端性’和多元化倾向”,“更深层次上看,他们还是站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现代性启蒙逻辑的线索,依托新的理论资源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7]。因此,可以说,它实质还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只是它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新道路”的探索是通过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甚至心理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以直接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在2003年张一兵、胡大平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中,他们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便终结了”,在它的深远历史影响下,西方产生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诸种新的理论形态”。[8]而在2009年出版的张一兵主编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中,他们把之前所指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称为“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9]可以看出,张一兵及其同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认识实现了从狭义理解到广义理解的转变。
陈学明认为,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般而言就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一,属于西方的理论家;其二,提出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信奉者;其三,他们的理论必须与承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各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10]所以,他主编的四卷本《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地域意义上的,即泛指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潮和流派”[11]。
鉴于以上的争论,笔者比较赞同王雨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分析,即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也赞同张一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体现的特征分析,即它的色彩斑驳和内容庞杂特点,各思想流派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表现却各不相同,可以是理论方法的某种继承,也可以是一定理论立场的一致性,或主题的一致性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涵盖的范围,笔者赞同陈学明的观点,即从广义上来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陈学明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世界就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要真正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并非易事。而从国内的实际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已大大超出了其最初提出者所确定的界限。多数学者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开放的理论思潮,既然如此,就可以遵从学者的常用习惯,不用再为概念争论不休。重要的问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与我们是一致的,对于我们而言,对其思想价值,包括其民族理论的开发和利用才是应该重视的问题。所以,本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泛指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
作为开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其涉及的流派众多。本书对其所有流派的民族理论都进行梳理不具有现实性,按照专题进行梳理难度也比较大。所以,笔者的研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选择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新左派”这四个对民族理论有比较集中研究的流派进行梳理。除以上四个流派之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反犹主义也有一些研究,著有《反犹主义和犹太人》一书,他的理论思考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有相通之处,本书并未涉及。还有当代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理论也有比较丰富的研究,但是,相对而言,它的影响不如英国“新左派”的影响大,本书也未涉及。另外,总体而言,以上梳理的流派都属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也并未涉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合著有《种族、民族和阶级》一书,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罗默(John Roemer)著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分配》一书。当然,以上论著也不可能穷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容的流派众多,思想庞杂,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和布洛赫[12]这四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消极革命论的批判中,在对“十月革命”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原因的反思中,都把目光转向了阶级意识,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没有形成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然后从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甚至心理层面去反思革命意志丧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系统阐释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葛兰西通过对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比较分析,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需要争夺文化霸权的思想。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虽然不直接涉及民族理论,但是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模式”对于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影响比较大。除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之外,他们也批判和反思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统治和侵略,这一点在其他的流派中也表现突出。就民族理论而言,葛兰西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行了反思,他在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提出了关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相关内容,在反思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提出实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的问题。卢卡奇从哲学高度反思了法西斯种族主义产生和形成的非理性主义根源。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和《我们时代的遗产》等著作中对犹太人问题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研究,对于犹太人问题他既反对同化的道路,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他从宗教的角度引入思考,认为反犹主义源于现代文明危机,只有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才能解决现代文明危机,拯救全人类,同时拯救犹太人。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想象的共同体”构建,以虚假和扭曲的形式来满足人们的乌托邦渴望。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其“社会批判理论”对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理论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不断发展,已经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侧重于批判理论的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侧重于批判理论的重建与现代性批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为代表,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他们的批判理论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独到见解和广泛影响。就民族理论而言,其早期代表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另译作西奥多·W.阿道尔诺)在20世纪4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日渐式微的时候对“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心理学和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而最突出的是哈贝马斯及其弟子霍耐特的相关思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民族、种族间的交往合理化提供了启示,而其弟子霍耐特正是在他的交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为身份认同而斗争的承认理论,弗雷泽则用再分配—承认理论来反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由此引发了学界长达十多年的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辩,而种族身份承认是其中涉及的典型问题。哈贝马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后民族”理论。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以赖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为代表人物,它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产生较早、较有影响的流派之一。这一流派致力于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结合在一起,致力于反思人的心理和性格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解放路径。就民族理论而言,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其开创者赖希对法西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苏联民族主义“倒退”的研究和弗洛姆在赖希研究思想基础上的发展完善。
英国“新左派”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深入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主义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陆续出版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英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就文化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全新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他们所开启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也因此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13]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希望通过反思传统左派(共产党和工党)的思想缺陷和政治弊端来探索符合英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左派”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民族理论研究成果最丰硕、影响最大的流派,霍布斯鲍姆、汤姆·奈恩(Tom Nairn)、霍尔是其主要代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民族性之争”、英国第一代“移民”问题和持续至今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与分裂问题,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撒切尔霸权主义民族认同构建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族性问题,再到当今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和族裔散居问题等,它们都有所涉及。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第一阶段。它主要以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及其影响、苏联多民族国家构建中产生的问题以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为时代背景,围绕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构建、法西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和大众文化批判与民族认同问题等进行讨论。20世纪70年代之后是第二阶段,它主要以全球化、信息化、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时代背景,重点研究了新形势下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产生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问题、种族歧视问题、族裔散居问题和当代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等。前述四个流派围绕以上问题进行的民族理论研究比较集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对其后其他流派的理论有直接的影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精神分析和群众心理性格视角来研究民族理论,富有特色;而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左派”是民族理论成果最丰硕、最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它们已经融入西方主流的民族理论话语中。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理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和弗雷泽的“再分配—承认”理论与西方主流民族理论有缠绕又有区隔,那么“新左派”民族理论可以说是自成一派了。霍布斯鲍姆是现代主义这一当代西方主流民族理论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而霍尔的种族理论也代表了当今民族理论研究的学术前沿,它不仅重新定义了种族理论的研究范式,而且开辟了从政治、意识形态、媒介、文化与身份认同等复杂体系中研究民族理论的新路径。为此,本书选择了以上四个流派进行尝试性研究。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界从整体上来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国内有一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学”关系的论述,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产生的历史时代,简要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兴起的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学派和“社会生活辩证法”思想以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与思潮。[14]另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指在西方世界的民族学传统中,因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而开展的研究,而“生产方式”及其“衔接”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想脉络的重要线索,也是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不断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的重要路径。[15]以上研究虽说是“民族学”,但也包含着民族理论的内容,只是这样的研究还很少,分析也比较简略。
目前学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具体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国家构建及走向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国内外主要集中在哈贝马斯、霍耐特和弗雷泽身上,对英国“新左派”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与安德森、奈恩关于英国“民族性”之争的介绍以及对葛兰西相关理论的少量涉足。
葛兰西的政治思想比哲学思想更引人注目,霍布斯鲍姆指出葛兰西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16]。国外近年来对葛兰西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其政治思想,并逐渐拓展到社会学方向,特别是语言社会学方面。但对于民族理论的内容,虽然有学者指出,“安东尼·葛兰西在民族主义方面也是一个创新者”[17],“把民族主义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的”[18];但是,对于葛兰西民族理论的系统梳理比较少,比较间接,学者们多是围绕葛兰西文化霸权统治这一核心概念来简要介绍和分析文化、语言及教育等与实现民族国家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如论述语言对于建立文化霸权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国家的多民族语言对构建共有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影响[19]。另外还有学者运用文化霸权思想来批判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主义[20]和后殖民主义[21],指出葛兰西思想对新葛兰西主义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22]。国内与葛兰西民族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理论及其影响、“民族—人民”的文艺理论以及民族国家的国际合作思想等方面。它们介绍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影响和现实启示[23],阐述了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艺理论[24]和民族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思想[25],揭示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26]。也有学者研究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对当前世界和国内政治实践的影响,指出“以文化领导权为轴心的统治与颠覆、斗争与谈判等话语权力的博弈,日益以更为丰富的形式活跃于‘全球文化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实践中”[27];文化霸权学说重视文化与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其对市民社会地位的强调、对“民族—人民”的文学家作用的重视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28],其因广泛性、持续性、非强制性的特征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教化功能,对我国民族文化复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29],对我国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极具借鉴价值[30]。
对于汤普森与安德森、奈恩之争的研究和讨论比较多,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和有关学术专著中都有所涉及,但是大部分都是泛泛之谈,只有较少学者论述了1956年之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和汤普森与安德森、奈恩之争的情况[31],专门从民族理论视角,研究这场争论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民族性问题之间的关系的经验教训[32]。
而对于哈贝马斯、霍耐特和弗雷泽的民族理论的研究,涉及交往理论、承认理论与民族认同的成果相对较少,比较集中和丰富的是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理论研究。
有关交往承认理论与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关系方面的内容,有少量比较间接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及协商民主模式虽然“并不是只针对民族问题的,但是,都带有民族、族群问题的烙印”,对于我们理解民族问题有启发意义[33];他对民族国家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剖析,也是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和“话语伦理”的建构为依据的,这对于民族交往的进步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也有切实的指导意义[34]。对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和弗雷泽的再分配—承认理论,学界还处于理论的基本介绍阶段,研究不深入,结合民族理论进行研究的就更少。它们主要介绍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以及其中包含的多元正义思想与多元文化策略[35],较为系统分析了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前提,承认的三种模式(爱、法权、团结),承认的诉求,承认的目标,承认的规范内容[36],承认理论对现代问题的诊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及其重要意义,承认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面临的困境等[37]。有学者指出:“霍耐特这种将承认政治建构在‘至善’之上的思考,也被后来的不少学者认为充满着浓厚的乌托邦式乡愿意味。”[38]另外,对于再分配—承认理论之争,《再分配,还是承认?》《正义的中断》《伤害+侮辱》等译著介绍了相关论文和争议情况。
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争议,有的学者欣然接受他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具体地论证欧洲政治一体化,而也有学者极力批判其理论。支持的学者论证突破现有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建立跨国公民社会的原因[39],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研究培育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欧洲和世界公民身份的可行性路径[40]。《行进中的欧洲:选择民族主义之外的哪种爱国主义?》和《后民族主义民主:寻找一种政治哲学的欧洲联盟》[41]等专著都从理论层面声援哈贝马斯的后民族主义。而《论民族性》[42]和《民族认同与政治理论》[43]都批评后民族主义理论不合时宜。还有些极力支持后民族主义的学者也严肃批评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哈贝马斯的后民族主义理论在向民族主义靠拢[44]。
国内对于哈贝马斯后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也比较活跃。它们具体阐述了后民族国家、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哈贝马斯的后民族思想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交往理性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确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方面要维护建立在商谈伦理基础上的国家话语机制和政治形态,另一方面又为维护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可能”[45],而其宪法爱国主义和协商民主构建了一个话语—法律—民主的集体认同模式[46]。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其各方面的思想进行了评价,揭示其开出的“无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药方[47]和后民族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所暗含的前提和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所具有的参考意义[48]。也有学者针对学界对哈贝马斯的各种批评,进行了较系统而全面的辩护,就哈贝马斯理论对我国政治实践的启示进行了论证[49]。还有的指出哈贝马斯主张“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和“文化民族的归属感”的“双重特征”和两副面孔的结合、并存、并行,既是其历史价值所在,同时也隐藏着很大的危险,他提出用公民国家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案也值得我们反思[50]。但是在政治现实中,国家仍需要以民族为基础,后民族相关政治设想的实现还属于十分遥远的未来,当前民族国家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51]
(二)民族主义理论及评价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霍布斯鲍姆身上。就国内学界的研究而言,它们分析了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概念及其民族问题研究的思维脉络[52],认为其“民族主义”史学包括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化过程、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等[53]。还有一些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霍布斯鲍姆重在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或公民)性以及其缘起的西欧性,它对民族的论述比较客观,但因过于强调现代性和政治性,而否定了民族乃至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力和生命力[54];他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基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有相同和相近之处[55],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为人们全面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56];他从后设逻辑来界定民族并没有在本体论层次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但他的构建性研究进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族研究的集体主义视角,为当今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民族论发展奠定了基础[57]。国外有不少学者对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理论给予赞誉。有学者赞同其基于民族主义认识而对民族国家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58],认可其关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消长关系理论[59]和对民族主义的评述,尤其是直接接触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评论[60]。同时,批评的声音也较多。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论著中比较系统地反驳了霍布斯鲍姆的思想,尤其不赞同其种族和语言民族主义观以及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趋势的预判。还有学者指出学界对霍布斯鲍姆的研究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面,几乎忽视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61]。
(三)种族问题研究
学界围绕以上流派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霍尔身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犹主义研究有少量涉及。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犹主义研究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史》《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等论著都介绍了“反犹主义研究计划”实施的缘由、进程及成果等。《种族批判理论的起源、内涵与局限》一文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种族批判理论深层而直接的理论来源,其思想对美国种族批判理论的兴起影响尤巨,而哈贝马斯早期以交往为基础的批判理论也影响到种族批判理论的后续发展。[62]
国外学界对霍尔种族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简要勾勒霍尔种族思想形成的脉络[63],介绍其《监控危机》的基本观点[64],较粗略地叙述了其随着民族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民族认同理论的变化发展过程[65]。有学者提出霍尔的种族问题研究重新定义了种族研究范式,开辟了种族、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研究的新道路[66],其族裔散居理论对加勒比海学者和从加勒比海地区流散到全球各地的其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67],也有少数学者讨论了其理论存在的问题和缺陷[68]。
就国内学界对霍尔种族理论的研究而言,有的学者介绍了霍尔差异政治学视野中的种族多元文化发展理论,认为其政治理想就是建立差异平等、种族公正的多元文化民主和谐社会[69]。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全面介入现代性认同政治批判,提出系统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为后殖民族裔散居理论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有力的支点[70],也掀起了当代英国恢复黑人种族文化历史地位的浪潮。[71]还有学者分析了霍尔的撒切尔主义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指出霍尔通过媒体的“解码/编码”具体分析抨击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游戏和语言术语。[72]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霍布斯鲍姆、哈贝马斯和霍尔身上。就研究成果而言,国内主要是对他们相关民族理论的介绍,对其基本理论观点和发展脉络的梳理。国外对于他们的研究相对要全面一些,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多元评析和批判,指出现有研究忽视了他们的民族理论。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缺乏系统分析,也缺乏对具体流派的民族理论的专题式研究。鉴于此,笔者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新左派”这四个“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基础性研究,以呈现其民族理论的基本轮廓。
[1] 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11页。
[2] 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4页。
[3] 徐崇温:《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12,第1页。
[4] 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再清理与再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6期。
[5] 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再清理与再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6期。
[6] 段忠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
[7] 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8] 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9~20页。
[9] 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8页。
[10] 参见陈学明《情系马克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198页。
[11] 陈学明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前言第1页。
[12] 关于布洛赫是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学界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如张一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中就把布洛赫归为第二代代表人物,而陈学明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中把布洛赫纳入早期代表人物,他认为布洛赫的思想对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具有与卢卡奇相当的地位。因为他在一战时期所写下的早期代表作《乌托邦的精神》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具有极其密切的思想关系,布洛赫在晚年的访谈中曾明确指出,在青年时期,他们二者相互之间的思想关系就好比是一个连通器,一直保持着思想发展的同步性,以至于很难分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乌托邦的精神》中哪些思想是卢卡奇的,哪些思想是布洛赫的。此外,他的《乌托邦的精神》也的确滋养了后来的整整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及布洛赫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在此参引的是后者的观点。
[13] 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397、407页。
[14] 白振声:《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剖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5] 麻国庆、张少春:《生产方式及其衔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评析与启示》,《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6] 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299页。
[17] 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张英魁、王亚栋、张长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168页。
[18] 玛·奥卡拉汗:《关于种族主义问题》,《民族译丛》1984年第5期。
[19] Alessandro Carlucci,Gramsciand Languages:Unification,Diversity,Hegemony(Boston:Brill,2013).
[20] Mark McNally and John Schwarzmantel,Gramsci and Global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9).
[21] Neelam Srivastava and Baidik Bhattacharya,The Postcolonial Gramsci(New York:Routledge,2012).
[22] Alison J.Ayers,Gramsci,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23] 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4] 周兴杰:《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5] 刘传春:《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演进与逻辑》,人民出版社,2013。
[26] 和磊:《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7] 孙士聪:《反思“葛兰西的悲剧”——文化领导权的文化国际政治维度》,《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夏之卷。
[28] 赖永兵:《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互文性观念为视阈》,《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9] 裴艳丽:《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启示》,《学习月刊》2011年第3期下。
[30] 徐太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析——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31] Wade Matthews,The New Left,National Identity,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Boston:Brill,2013).
[32] 迈克尔·肯尼:《社会主义和民族性问题:英国新左派的经验教训》,王晓曼译,《学海》2011年第2期。
[33] 佟德志:《当代西方族际民主模式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34] 苏平富:《交往行为、话语伦理与民族国家主权的终结——哈贝马斯主权终结论的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5] 王凤才:《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6] A.霍耐特:《完整性与蔑视:基于承认理论的道德概念原则》,赵琰译,《世界哲学》2011年第3期。
[37] 胡云峰:《霍耐特承认理论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复旦大学,2007。
[38] 陈建樾:《认同与承认——基于西方相关政治理论的思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39] Pablo de Greiff,“Habermas on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Ratio Juris,Vol.15,No.4,December,2002.
[40] Andreas Follesdal,“Citizenship:European and Global”,Arena Working Paper,2001,http://www.arenauio.no.
[41] Lacroix,Justine,L’Europe en procès:Quel patriotism au-delà des nationalismes?(Les Editions Du Cerf,2004);Deirdre M.Curtin,Postnational Democracy:The European Unionin Search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
[42] David Miller,On Nation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1997).
[43] Margaret Canovan,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Edward Elgar,Cheltenham,UK and Northampton M.A.,USA,1996).
[44] Patchen Markell,“Socioeconomics Politics Aesthetics Liberal democracy Sociology”,Political Theory,Vol.28,No.1,February,2000.
[45] 王昌树:《论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思想》,《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
[46] 王远河、刘慧芳:《后民族欧洲的认同与民主——哈贝马斯的观点述评》,《世界民族》2013年第4期。
[47] 曹兴、樊沛:《哈贝马斯“无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理念述评》,《世界民族》2015年第1期。
[48] 翟志勇:《哈贝马斯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构建——以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作为考察重点》,《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2期。
[49] 马珂:《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0] 明浩:《超越民族国家——哈贝马斯谈民族国家》,《中国民族报》2012年3月9日第6版。
[51] 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18、119、125页。
[52] 陈献光:《解读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概念——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为文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53] 颜英、何爱国:《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综述》,《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5期。
[54] 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5] 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56] 王冀平:《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
[57] 王军:《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从实体论迈向关系实在论初探》,《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58] Paul Laity,“The Great Persuader”,The Guardian,1 September 2007.
[59] Martin Woollacott,“Where are we going”,The Guardian,7 July 2007.
[60] Catherine Merridale,“We can learn from this dazzling professional”,The Guardian,1 October 2012.
[61] Blake Alcott,“The humanity of Eric Hobsbawm”,The Guardian,2 October 2012.
[62] 伍斌:《种族批判理论的起源、内涵与局限》,《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63] Helen Davis,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London:Thousand Oak,Calif,2004).
[64] James Procter,Stuart Hall(London:Routledge,2004).
[65] Wade Matthews,The New Left,National Identity,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Boston:Brill,2013).
[66] Claire Alexander,Stuart Hall and “Ra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c2011).
[67] Brian Meeks,Culture,Politics,Race and Diaspora:The Thought of Stuart Hall(London:Lawrence & Wishart,2007).
[68] Chris Rojek,Stuart Hall(Cambridge,UK:Polity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2003).
[69] 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0] 陆家俊:《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的对话与超越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1] 张建萍:《流散视阈中斯图亚特·霍尔的种族思想及其变迁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72] 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