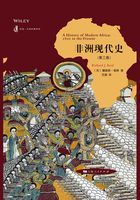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政权、冲突与贸易(2):东北非洲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教王国渐渐地将自己的政治重心向北移动,一个永久都城在贡达建立起来,提格雷省也更完全地融入国中。[37]在很大程度上,是红海的贸易扩张使得现代埃塞俄比亚国的核心向北部移动,但奥罗莫人的迁移也造成了来自南边的不断增压。当奥罗莫人迁移到高原地区后,他们就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他们改变着埃塞俄比亚高原哈贝沙(habesha)社会的性质。他们中许多人是穆斯林,但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正统基督教,这构成了阿姆哈拉和提格雷文明的基础,两种宗教都被吸收进阿姆哈拉文化,并且影响它。一些奥罗莫社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绍阿以及东边悬崖地区的哈贝沙政体发生摩擦;随着时间推移,也有一些奥罗莫人在阿姆哈拉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位置。[38]
英文版原书页码:65-66

19世纪的非洲之角。引自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1976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
18世纪后半叶,这个脆弱帝国的中央政权坍塌了,所罗门统治者——这样叫是由于他们声称自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一个神话——被降低为傀儡。在某种程度上,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瓦解是此前几个世纪中一个过程的顶点。从古代阿克苏姆帝国的衰退开始——从1世纪到8世纪,它曾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北部和厄立特里亚中部的贸易和军事大国,这一地区的中央政府就经历着扩张与收缩的交替时期,但政治和军事力量一直都存在于各省之中,并且还有自治地区、封邑和基本上独立的王国,它们定期进贡,既是向有形的中央政权进贡,也是向一种观念(所罗门王起源神话)进贡。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期间——这一时期在阿姆哈拉语中被称作“巨头时代”,省级统治者完全独立于所罗门中央政权,而且相互之间不断冲突,为的是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资源和中央权力的标志和象征。就是在此时,处于利用新兴长途贸易有利位置的提格雷,成为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主要力量,在18世纪后期控制了贡达,此时贡达的领导权是在“巨头”迈克尔手中,提格雷势力在19世纪早期以后又向北进入朝向海岸的厄立特里亚高原。当提格雷积累了巨量的武器时,南边的绍阿王国正与奥罗莫人的侵犯对抗,并在19世纪前半叶从后者手中夺回了土地。的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绍阿,尤其是在海尔·塞拉西统治时,将自身定位于利用这一地区的贸易,阿姆哈拉人为后来现代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9]
暴力的地方主义——尽管地方主义本身并非暴力,被一个年轻的地方背叛者,出身于较低贵族世系,来自阿姆哈拉偏远的奎拉地区的卡萨所终结。19世纪40年代,卡萨作为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就声望很高,他的士兵连队发展成为一支能够与这一地区统治阶层抗衡的军队。他声称(十分可疑地)自己是所罗门的继承人,并且更名为特沃德罗斯。经过5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激烈战斗,他于1855年宣布自己为皇帝,这一年也被视为“巨头时代”的结束。特沃德罗斯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北部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统一,超过了前一个世纪。尽管完全是通过暴力,在他统治时期的很多时间都放在了镇压暴乱上。在几年的时间里,特沃德罗斯想要规范土地权和税收,剪掉过于强大的正统教会的羽翼,让自己的军队更加职业化和有纪律。与北部非洲的一些同时代人不同,他设想将埃塞俄比亚转变成一个工业和贸易大国,他理解这显然就是使得欧洲“强大”的原因。为了这个目的,他欢迎欧洲人的到来,想利用他们的专门技术使自己的军队“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最终并不成功的引进武器。在对外政策上,他的视野也很开阔——尽管与他的国内志向相比有些不切实际,他寻求与那些和自己相当的欧洲国家在宗教、贸易和政治领域结盟。特沃德罗斯认为伊斯兰教——它体现于埃及人和奥斯曼帝国——是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敌人,在他的要求中包括把厄立特里亚海岸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并宣称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凭借假想的所罗门血统),他苦涩地叹息耶路撒冷落入了他所诅咒的穆斯林手中。[40]
英文版原书页码:67
19世纪60年代早期,地区叛乱十分普遍,这常常有愤怒的神职人员在支持,尤其是在北部。在这里,特沃德罗斯失去了对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高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这形成了一个暴力的恶性循环。特沃德罗斯镇压暴乱越凶残,暴乱也就变得越顽强和广泛,尤其是在农民中间,他们对皇帝军队的抢掠越来越憎恨。在1866—1867年间,特沃德罗斯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还面临着一大批政治敌手,其中包括年轻的绍阿国王迈拿里克。他的领地收缩到了马格达拉“要塞”一带,这位于高原的东部边缘。然而,最终是外来干预而非内部反叛毁灭了他。60年代中期,由于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有过失——给他的回信没有到来,他感到恼怒,受到了羞辱,于是囚禁了一些欧洲人,包括若干英国人,并用链条捆绑他们以等到错误被修正。1867—1868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一支军队——以纳税人付出900万英镑左右为代价,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这支军队在厄立特里亚海岸的祖拉湾登陆,进入高原,打败了特沃德罗斯日益衰败的军队。这位皇帝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落入英国人之手。[41]在这场不寻常的远征中,英国人由于特沃德罗斯拥有众多敌人而得到极大帮助,在通过可能会敌对的提格雷疆域时,由于此地总督拉斯卡萨的协助——他此时正觊觎所罗门王位,行军也变得较为风平浪静。英军解救了欧洲人质并很快撤走,将特沃德罗斯的小儿子阿莱梅乌一起带走。阿莱梅乌在英国拉格比公学接受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教育后,于1879年神秘死去。
在一段短暂的空位期和一场地区势力较量后,提格雷的拉斯卡萨在1872年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延续由特沃德罗斯开始的建立一个统一和扩张主义国家的进程。然而与特沃德罗斯不同,约翰尼斯以外交补充军事力量,并运用古老的地区统治家族通婚的机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他与迈拿里克建立了联姻,迈拿里克觊觎帝位但此时决定要等待时机。约翰尼斯的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内部稳定,但他的视野却被海岸边的埃及人遮挡。两者之间是一种不稳定却共生的关系,因约翰尼斯对现代厄立特里亚及沿海大片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紧张起来。埃及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得到英国人的庇护得以撤离,结果却很快被意大利人取而代之,后者早已在海岸南边的阿萨布取得了立足点。约翰尼斯的北部前线由他信任的副手拉斯阿鲁拉把守,这是他所重点关注的;他的另一个重点关注则是西北边苏丹的马赫迪国家的崛起。的确,约翰尼斯就死于1889年与马赫迪派的战斗中。[42]
英文版原书页码:68
随着约翰尼斯的突然死亡,埃塞俄比亚帝国中的提格雷辉煌就此终结,提格雷人可能到下一个世纪都不会再次争夺埃塞俄比亚的领导权了,权力相对顺利地移至绍阿国王迈拿里克手中。从1889年到1906年,迈拿里克忍受着一场严重中风带来的痛苦(但他一直在位直至1913年死去),创建了现代埃塞俄比亚。他迅速撤回了埃塞俄比亚对海岸的领土要求,并将厄立特里亚割让给意大利人,甚至在1896年的阿德瓦战役成功击退了计划不周的意大利人入侵之后——他是欧洲瓜分非洲时代中唯一一个永久性击败欧洲入侵军队的非洲领袖,他也不能或不愿意继续进军厄立特里亚,去实现前辈的雄心。不管怎样,阿德瓦战役使北部前线得以保留,并确保欧洲承认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迈拿里克不仅使自己的国家避免成为如同这一地区其他地方那样的殖民地,还积极参与到向南和向东开拓广阔疆土,在附近欧洲殖民地当局的同意下划分出自己的新王朝。阿姆哈拉霸权延伸到南边奥罗莫的肥沃疆土,进入了索马里人的奥加登。这个新帝国通过军队的战略性驻防来控制,以谨慎地分配各地总督来统治。如同之前的特沃德罗斯,只是更为成功,迈拿里克渴望一个“现代”埃塞俄比亚,监督建造了一条铁路,在亚的斯亚贝巴建造了一个现代首都,还有银行体系和通讯基础设施。他聘请了欧洲顾问,送埃塞俄比亚人出国受训。[43]迈拿里克的新国家或许是一个城市而非农村的创造,但重要的是欧洲使馆快速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标志着对一个非洲主权国家的承认。在一个外国霸权主义不断蔓延的时代,这是东非或东非之外的任何其他政体都未能做到的壮举。
注释:
[1] 阿卜杜勒·谢里夫《桑给巴尔的奴隶、香料和象牙》(伦敦,1987)。
[2] A.C.乌诺玛和J.B.韦伯斯特《东非:商业的扩展》,收入约翰·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
[3] 理查德·J.雷德《殖民地时期之前东非的战争:19世纪国家层面冲突的模式与含义》(牛津,2007)。
[4] E.A.阿尔帕斯《中东非的象牙与奴隶》(伦敦,1975)。
[5] 理查德·科乐克《19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火器与王子力量》,《非洲史学刊》13:4(1972)。
[6] 这方面有一个稍稍过时、但仍然令人信服的叙述:莫迪凯·阿比尔《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时代:伊斯兰教的挑战和基督教帝国的重新统一,1769—1855》(伦敦,1968);也可以参看斯文·鲁本森《埃塞俄比亚独立的幸存》(伦敦,1976),更为简明的综述可看巴赫鲁·扎韦德《埃塞俄比亚现代史:1855—1991》(牛津,2001)。
英文版原书页码:69
[7] 一系列出色的研究见亨利·梅达尔和谢恩·道尔所编《东非大湖地区的奴隶制》(牛津,2007)。
[8] 简-格奥里格·多伊奇《德属东非没有废除奴隶制的释放奴隶:1884—1914前后》(牛津,2006),第34—35页。
[9] 英国圣公会传教协会档案:G3 A6/01883/71,《奥弗莱厄蒂致威格拉姆的信》1883年2月28日。
[10] 雷德《殖民地时期之前东非的战争:19世纪国家层面冲突的模式与含义》,第46—52页。
[11] 安德鲁·罗伯茨《“尼亚姆韦齐人”》,收入安德鲁·罗伯茨所编《1900年之前的坦桑尼亚》(内罗毕,1968)。那个时代的简述则见V.L.卡梅伦《穿越非洲》,2卷本(伦敦,1877)。
[12] R.W.比彻《19世纪东非的象牙贸易》,《非洲史学刊》8:2(1967)。
[13] 安德鲁·罗伯茨《尼亚姆韦齐人贸易》,收入理查德·格雷和戴维·伯明翰所编《殖民地时期之前的非洲贸易:1900年之前中东非贸易论文集》(伦敦,1970),第73页。
[14] M.阿比尔《南埃塞俄比亚》,收入格雷和伯明翰所编《殖民地时期之前的非洲贸易:1900年之前中东非贸易论文集》;科乐克《19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火器与王子力量》;艾利卡·摩尔-哈雷尔《19世纪后半期埃塞俄比亚奴隶制与苏丹人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考查》,《非洲史研究国际学刊》23:2/3(1999)。W.C.普洛登《在阿比西尼亚和盖拉国的旅行》(伦敦,1868)是一本那个时代的详尽记述。
[15] 最好的记述仍然是哈罗德·G.马库斯《迈拿里克二世的时代与生活:1844—1913的埃塞俄比亚》(牛津,1975)。关于吉布提的联系,一本有趣的洞见之作是查尔斯·尼科尔《别人:非洲的亚瑟·兰波,1880—1891》(伦敦,1998)。
[16] 德里克·纳斯和托马斯·斯皮尔《斯瓦希里人》(费城,1985)。
[17] 诺曼·班尼特《桑给巴尔阿拉伯国的历史》(伦敦,1978);理查德·F.伯顿《桑给巴尔:城市、岛屿和海岸》,2卷本(伦敦,1872)。
[18] 斯蒂芬·勒克尔《文化搬运者:19世纪东非的路上劳工》(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2006)。
[19] 诺曼·班尼特《阿拉伯对抗欧洲人:19世纪中东非的外交与战争》(纽约,1986)。
[20]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介绍是J.-P.克雷蒂安《非洲的大湖:两千年的历史》(纽约,2003);也可参看戴维·斯恩伯鲁恩《绿色之地、美好之地:15世纪时大湖地区的土地变化、性别和社会身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1998)。一本稍早但仍然有用的著述是罗兰·奥利弗《内陆看得见的发展,1500—1840》,收入罗兰·奥利弗和杰维斯·马修所编《东非史》(牛津,1963)第1卷。
[21] M.S.M.基瓦努卡《布干达的历史:从王国建立到1900》(伦敦,1971);理查德·J.雷德《殖民地时期之前布干达的政治力量》(牛津,2002);亨利·梅达尔《19世纪的布干达王国》(巴黎,2007)。
[22] 谢恩·道尔《班约罗的危机与衰败:西乌干达的人口与环境,1860—1955》(牛津,2006)。
[23] 比如参看简·瓦思纳《现代卢旺达的祖先:伊吉耶王国(Nyiginya Kingdom)》(威斯康星州麦迪逊,2004)。
[24] 戴维·威廉·科恩《布苏加(Busoga)的历史传统:穆卡玛(Mukama)和肯图(Kintu)》(牛津,1972);罗纳德·R.阿特金森《种族之根:1800年前乌干达阿乔利人的起源》(费城,1994)。
[25] 理查德·J.雷德《维多利亚湖上的干达人:一种19世纪东非的帝国主义》,《非洲史学刊》39:3(1998)。
英文版原书页码:70
[26] C.H.安布勒《帝国主义时代的肯尼亚族群》(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88)。
[27] 罗伯茨《“尼亚姆韦齐人”》;也可参看R.G.亚伯拉罕斯《坦桑尼亚大尼亚姆韦齐的民族》(伦敦,1967)。
[28] 关于乌扬耶姆比的危机,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著述是斯皮克《尼罗河之源发现日记》,第5章。
[29] 以特定的视角,当时众多的欧洲来源描述了“鲁加鲁加”现象的出现,比如可以参看亨利·莫顿·斯坦利《穿越黑暗大陆》,2卷本(伦敦,1878,1899);以及卡梅伦《穿越非洲》。
[30] 解说米拉伯姆,最好的单一著作仍然是诺曼·R.班尼特《坦桑尼亚的米拉伯姆,1840—1884年时》(伦敦,1971);一本主要依据口头讲述而来的地方著述是J.B.卡比亚《国王米拉伯姆:坦桑尼亚的英雄之一》(内罗毕,1976)。
[31] A.肖特《恩扬古耶马韦与“鲁加鲁加”帝国》,《非洲史学刊》9:2(1968)。
[32] 这一点在一位传教士埃比尼泽·索森未发表的文章中得到了证实,见伦敦传教协会SOAS特别收藏“中非,收信,3号盒,1880年3月28日索森致汤姆森信的附件:《尼亚姆韦齐的历史、国家和民众》。”
[33] 见他的自传(W.H.怀特利译为英文)(内罗毕,1966)。
[34] 最为详尽的集体研究成果之一,是托马斯·斯皮尔和理查德·沃勒所编《作为马赛人:东非的种族与身份》(牛津,1993)。
[35] 理查德·雷德《布干达的战利品俘虏:关于战争中抢夺人口的一些观察,1700—1890》,收入梅达尔和道尔所编《东非大湖地区的奴隶制》。
[36] 当时有一份引人注目的记述:R.P.艾西《乌干达编年史》(伦敦,1894)。
[37] 唐纳德·克拉米《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土地与社会:从13世纪到20世纪》(牛津,2000)。
[38] 穆罕默德·哈桑《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1570—1860年的历史》(剑桥,1990);P.T.W.巴克斯特、简·胡尔廷和亚历山德罗·特留尔齐所编《作为和成为奥罗莫人:历史的和人类学的探查》(乌普萨拉,1996)。
[39] 阿比尔《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时代:伊斯兰教的挑战和基督教帝国的重新统一,1769—1855》;马库斯《迈拿里克二世的时代与生活:1844—1913年的埃塞俄比亚》。
[40] 关于特沃德罗斯的早期作为,见普洛登《在阿比西尼亚和盖拉国的旅行》;后来的分析著述包括H.斯特恩《在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漫游》(伦敦,1862)和H.布兰克《阿比西尼亚被囚纪实》(伦敦,1868)。也可参看唐纳德·克拉米《特沃德罗斯的暴力》,收入B.A.奥高特所编《非洲的战争与社会》(伦敦,1972)。
[41] 斯坦利《库马西与迈格达拉》;克莱门茨·马卡姆《阿比西尼亚探险史》(伦敦,1869)。也可参看达雷尔·贝茨《阿比西尼亚困境》(牛津,1979),以及晚近的菲利普·马斯登《赤脚皇帝:一部埃塞俄比亚悲剧》(伦敦,2007)。斯文·鲁本森等人翻译和编纂《阿克塔·埃修匹加二世:特沃德罗斯与他的同辈人,1855—1868》(亚的斯亚贝巴,1994),是埃塞俄比亚当时材料的精选汇集。
[42] 扎韦德·加布雷-塞拉西《埃塞俄比亚的约翰尼斯四世》(牛津,1975)。
[43] 马库斯《迈拿里克二世的时代与生活:1844—1913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总结之一:巴赫鲁·扎韦德《埃塞俄比亚现代史:1855—1991》;A.B.怀尔德《现代阿比西尼亚》(伦敦,1901),是那个时代富有洞见的欧洲人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