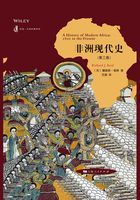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非洲研究简史
非洲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相对年轻的。迟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牛津学者还有无视这个大陆历史的名言,称它是“一些野蛮部族的循环,研究没有回报”[14]。然而,即使他是这种态度,非洲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也在开发之中。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新路径是指一种知识分子对非洲的“现代”解读,无疑非洲人一直都在用自身的语汇理解着自己社会的历史。不过,从20世纪中期以来,无论是好是坏,处于希腊—罗马传统之中的欧洲历史方法论被用于建构非洲历史的尝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专业历史学家和一些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他们中许多人在非洲大学教书,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加纳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开始把非洲历史作为一个严肃研究的领域。这与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正从欧洲殖民统治中争得独立同时,而并非巧合。[15]与重新发现的主权相伴,随之而来的是对非洲悠久历史的新的兴趣。的确,历史被视为国家创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当然,历史长期以来就一直被使用,或者说更为普遍的是被滥用——被政治家、游击队员、政治领袖和各式各样的潜在国家创建者所滥用。在非洲,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对待历史越来越没有热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但是,60年代的“民族主义者史学”则开发了一门精力旺盛的新学科,它一直在挑战种族主义者、以欧洲中心论看待历史者,一直在建构和解说那不计其数的民族和族群的历史旅程,这些民族和族群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非洲”的辽阔区域。
非洲历史学家们利用着各种材料来源。[16]对于殖民地之前的历史,那些可用材料的鉴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少数族群留下了书写记录,但阿拉伯北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是例外。考古被用来查证漫长历史中的物质和文化变化,语言上的变化和传播也被用来辨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化。历史学家们还必须利用外国人写下的文字材料,最早是那些中世纪以来讲阿拉伯语的旅行家和商人的记述,16世纪以后则有欧洲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们的记载,到了20世纪,对殖民地大量记录材料的广泛利用,支撑起历史研究的新途径。然而,学者们还可以利用记录下来的地方口头历史和种种传统——这些是所有族群的核心,[17]以及20世纪记录下来的那些证词。显然,各种材料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局限。考古研究和语言研究一般只能让历史学家窥到近似的时间标尺,以及变化的大致轮廓。外国人的书写材料摆脱不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偏见,以及局外人避免不了的误解,还有一些更是问题多多或迟钝麻木。地方的口述历史本身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和扭曲,在反映所处政治环境的同时,也通常偏向作者自己那一族系。然而,谨慎地使用这些材料,还是被证明极有价值。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这些材料的使用,体现了非洲历史的一个新维度——也是一个同情的维度。
英文版原书页码:6
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去系统建构非洲历史的尝试?对此的回答有可能在本书讲述的不同节点上找到。但这里已有足够的理由说,到了20世纪的开始——此时非洲大陆绝大部分都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信念:非洲没有历史。有一种“真相”几乎持续于殖民地时期的始终:非洲人被认为是“原始的”“野蛮的”,缺乏政治、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成熟。这一时期的欧洲人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一片荒野,包括非洲在内,都被视为在许多层面上是“劣等”的。“劣等”的概念是他们论证殖民统治本身合理的关键,所以非洲人被描述为缺乏历史,是一个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愚昧民族,要靠欧洲人把他们从生物学层面注定的悲惨命运中“援救”出来。另外,绝大多数非洲族群,除了伊斯兰教地区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外,都是文盲社会,于是欧洲人就说一个没有书写、没有文档记录的民族不可能有历史。按照这种观点,非洲的“历史”只是在欧洲把读写能力引入非洲统治阶层后才开始的,绝大部分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开始的。就有读写能力的穆斯林和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而言,他们在文明的程度上要稍高一些,但高得并不多,他们的野蛮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书写语言仅仅是半文明的表达而已。[18]
英文版原书页码:7
这类观念不仅在殖民统治的叙述中发挥作用,而且也塑造着欧洲对非洲殖民地之前历史的理解。在那些确实存在“文明”证据的地方,比如林波波河(Limpopo)以北的大津巴布韦国,或者是非洲东部和东北部的那些王国,欧洲人或认为它们在根本上不是非洲人创建,或认为创建它们的人事实上并不是非洲人。一定是外部影响——通常是肤色浅的外来者,创建了这样的文化,所以大津巴布韦国的精彩石头建筑就是一支神秘的、已经消失的白人部族的手艺,而“埃塞俄比亚人”则拥有白种人祖先。[19]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种假定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20世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就部分地建立在一种确信之上:白人定居者在17世纪发现了这片“空白之地”,这片土地是上帝给予他们的,它上面居住着一些“黑人”,在造物主的序列中这些人并不比野兽高多少。[20]这类观念盛行于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那时候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欧洲人的文化偏光镜来看待非洲的。非洲现代历史的研究者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要考虑这种偏见以何种方式——如果有的话——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改变。
确切探查这类理解的根源何在,这并不容易,它们的根子深扎于欧洲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增长与欧洲人对非洲的种族主义的兴起相伴随。从15世纪到19世纪,非洲人被视为“天然”的奴隶,是不发达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黑色”在“西方”的头脑中变得与奴隶状态和野蛮状态相关联。[21]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较为详细地谈论这方面的一些主题,但此刻我们就要注意,18世纪时欧洲出现了一场关于奴隶贸易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对理解非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以某种方式一直回响到今天。一群人反对奴隶贸易,他们是废奴主义者;另一群人捍卫它,他们是辩护派;但对于非洲社会本身,两派的基本看法却是一致的。辩护派争辩说,由于非洲是一个野蛮和落后的地方,是一个“活地狱”,所以奴隶贸易就是一种赐福的解放形式。把黑人从他们的邪恶环境中带出来,让他们在美洲登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他们还论证说,由于地方战争,不管怎样,非洲都在产生奴隶,做不了任何事情来制止。[22]废奴主义者的立场是:由于非洲是野蛮和落后之地,所以就需要欧洲的干预,这种干预要带给非洲所谓的“三个C”——基督教(Christianity)、商业(Commerce)和文明(Civilization),[23]奴隶贸易导致了暴力和苦难,非洲人必须得到拯救,既脱离奴隶贸易商,也脱离他们自身。这两派都相信非洲的落后,他们的分歧只是解说上的不同。在具体结果和社会思潮两方面,最终都是废奴主义者的立场胜利了,奴隶贸易的确被“废除”了——丹麦人和英国人率先废除,废奴主义者对待非洲的观点在19世纪占了上风。到19世纪结束时,一个观点已经稳固下来:只有通过欧洲人的统治,非洲才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发展。非洲人是孩童,他们必须得到欧洲父母的引导。[24]这至少会成为殖民统治合理性的一种公开论证。
英文版原书页码:8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社会思潮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才受到严肃挑战,其时正当殖民主义的黄昏和非洲独立的黎明。为了今天的斗争——获得国家的主权、稳定和繁荣,也变成了为了过去的斗争,非洲人和一代新的西方学者试图推翻那一堆文化上和历史上的扭曲。这场斗争持续着,尽管有着不可避免的困境和冷嘲热讽,有着时而出现的盲区。目前,当非洲看来在自己的后殖民道路上蹒跚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而“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又用类似于他们18和19世纪前辈的那种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时,这个大陆的悠久历史就尤其能够提供启示了。不幸的是,“现实主义”占了上风,尽管是出于一些毫无疑问的良好动机,但非洲还是太频繁地被决策者和人文学者非历史性地看待,对于非洲历史的强大力量,他们常常忽略,或者是没有兴趣。然而,在一个内部冲突、饥荒加旱灾、经济落后加管理不善、腐败加政治压迫的时代,对非洲前进之路的寻找,就必须从它的过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