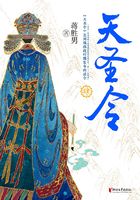
第2章 寇準回京
大中祥符八年的秋天,御苑中秋菊盛开,红叶满枝,百果飘香。皇后刘娥带着妃嫔们坐在亭中,看着孩子们嬉戏。
皇子赵受益已经五周岁了,此时正领着头在假山间疯跑,跟在他身后跌跌撞撞的是楚王元佐的孙子赵宗保,今年才不过三周岁。另外三个稍大的孩子前后护持着这两个孩子,一个亦是楚王的孙子,七岁的赵宗旦;一个是镇王元偓的儿子赵允弼,今年八岁;另一个是刘美的儿子,八岁的刘从德。
刘娥唯恐皇子受益独在宫中,性情孤僻,于是又抱养楚王的孙子赵宗保一同做伴,又让赵宗旦、赵允弼与刘从德当了皇子的伴读,几个孩子常常玩在一起。
先皇太宗皇帝共有九子,此时活着的,除赵恒外,只有长子元佐、六王元偓、八王元俨这三人,因此赵恒对此三王亦是格外垂顾,并让元佐与元偓的子嗣,为皇子伴读。
另一边,才两岁的小公主赵志冲坐在才人李氏怀中,她是李氏所生之女。这小公主生来体弱,一直多病,长到一岁时赵恒亲自抱着她去玉清昭应宫拜在三清门下入了道,起了超长的法号叫清虚灵照法师,又照这个道号起了个很有道家风格的大名叫志冲,这才渐渐养住了,如今长得颇为可爱,只是因为体弱,李氏格外看得紧。看着哥哥们玩耍,小公主也十分想加入,却被李氏抱着,不许她下来。
离四月份的大火,已经过去了半年,一切都在渐渐恢复中。此时坐在亭中的后妃们,谈论的却正是将在年底举行的皇子加冠之礼。杨氏此时已被封为淑妃,问刘后道:“姐姐,受益才五岁,就行加冠礼,这合适吗?”
刘娥叹了一口气,淡淡地道:“这是官家的意思。”
赵恒近年身体越来越不好,就更信所谓的天书祥瑞了,对王钦若也越发倚重。这也是臣子们要君的手法,创造出让上位者感兴趣的一个项目来,极力地夸大它的作用,使上位者把民力物力投入这件事中,而自己主持其事,便能够上下弄权固位了。
而赵恒从开始的设神道以慑外邦,到今日的沉迷,确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当年赵恒因为五个皇子先后早夭,未免有些心灰意冷,不料以祈子的名义建设神殿两年之后,竟然得子,心中未免有几分相信了。再加上这两年来,赵恒渐渐觉得老之将至,而皇子尚年幼,此时的追求神道,确也似秦皇汉武崇信方士一样,有求长寿之意了。
自皇子出生后,宰相们屡次上书,请求早日封王。赵恒亦希望在自己活着的时候,逐步将朝政之事交予皇子。因此决定,今年年底为皇子行加冠元服之礼,待冠礼过后,就可以直接封王理政了。
虽然一般男子加冠之礼多为二十岁成人之后,此时却只得拔苗助长了。
两人正说着,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大娘娘,小娘娘——你们看,我抓到一只大蝴蝶!”两人抬起头来,却见赵受益跌跌撞撞地抓着一只蝴蝶,向着亭子跑过来。
此时李才人也陪坐在亭子的下首,听到这一声叫唤,又见小皇子笑得一脸灿烂地向她冲过来,不由得想站起来去迎他,却见小皇子冲过她的身边,直扑到刘娥的怀中,心头只觉得空空荡荡,心中黯然:“我这是怎么了?可真是糊涂了不成?他怎么可能冲我喊母妃?”
忽然又听得“母亲——”一声娇唤,小公主糯糯软软的身子在她的怀中扭动,娇声道:“母亲,母亲,我也要大蝴蝶,我也要大蝴蝶!”
李氏的心忽然间就落到了实处,笑抱着女儿道:“冲儿乖,待会儿母亲再叫人给你抓蝴蝶去!”
刘娥笑道:“冲儿,来,到大娘娘这边来!”
李氏放下小公主,小公主就乖巧地跑到刘娥身边,叫了一声:“大娘娘!”
刘娥笑对怀中的赵受益道:“我儿乖,你是哥哥,把蝴蝶送给冲儿好不好?”
赵受益昂首道:“好,我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跟小丫头争。”
刘娥笑抚着他的小脑袋道:“对,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再过几个月,爹爹就要给你行冠礼了,行了冠礼,就是大人了,懂吗?”
赵受益响亮地应了一声:“欸!”引得众人都笑了。
此时杨媛亦抱过赵宗保,几个小孩子在草地上滚得一身是草干泥土,粘在后妃们华丽的裙装上。刘娥不以为意,笑嘻嘻地抱着赵受益问侍立一边的三个大孩子道:“师父近日都教什么了?”
赵宗旦素来像个小大人,此时忙回答道:“太傅已经开始教《论语》了。”
刘娥点了点头,又问刘从德:“你舅父近来在做什么?”
刘从德知道问的是钱惟演,忙答道:“舅父在家闭门读书,又与杨官人等把《西昆酬唱集》添了许多内容。”
刘娥笑道:“哦,希圣倒有这样的闲心,几时拿来给我看看。”低头想了一想又道,“我可见不得他这般清闲,你可告诉他准备着,再没几日这般清闲了。”
刘从德已有些懂事,忙跪下谢恩。
过得几日,旨意下来,迁钱惟演为工部侍郎、枢密副使,兼学士。三司使丁谓、翰林学士李迪升为参知政事。
开封城的雪,今年下得特别早,丁谓走出轿子,只觉得一阵寒意袭来,他跺了跺脚,笑道:“今年好雪,明年的庄稼又可大丰收了。”
早已经候在亭中的宰相王钦若拊掌大笑:“我们在亭里说了半日的风花雪月,不及谓之这一句惜时爱民。”
丁谓大笑:“咱自从做了三司使后,每日里锱铢必较,张口钱粮闭口土木,早是俗不可耐,哪及得上王相与各位官人名士风流,才子口角。”说着,大步走进亭子里去,却见三司使林特、兵部侍郎陈彭年等人均已经在了。林特笑道:“谓之这话说得该罚,你自比大俗人,岂不是寒碜我们?”
丁谓哈哈大笑:“不敢,不敢。”
亭中数人俱是当今名士,除治国理政外,亦是各有所长,各有所专。
宰相王钦若,当年主修《册府元龟》,于五代十国百年之乱后,将史料整理收集,传之后世,实为大功。
参知政事丁谓,首撰《景德农田敕》《会计录》等,自本朝以来第一次将天下农田的分布、赋税的多寡做一番普查,记录在案,由此皇帝始知天下农田多少,荒废多少,人户多少,能收赋税多少,对以后制定农事赋税政策大有功用。他又善用心计,任三司使时,任用林特等人推行榷茶法,善于敛财,以至于国库收入大增。种种政绩,甚得皇帝喜欢。
三司使林特,对开国初的茶法进行改革。开国初因为军中急需用钱,令商人以贩茶可加虚估之数,不料此风愈演愈烈,到近年来虚估之数超过实数七倍之多,令天下茶利朝廷只得五十万,倒有三四百万落于把持中间的茶商之手,造成官府无财,百姓被夺利,前些年王小波、李顺起义,亦有此中原因。林特改制茶法之后,虚估数减少了许多,朝廷茶税大增,又加上其他举措,才令得尽管今年大内被烧,国库烧光,居然也能够支应得过去。
兵部侍郎陈彭年,与王钦若在修《册府元龟》时出了极大的力。精通史学,且一生在音韵方面成就极大。他重拾五代失散韵书,与丘雍等人修撰《大宋重修广韵》,此书收字二万六千余。此后大宋词学兴盛,此书功不可没,千载之下研习韵书者,均将此书奉为圭臬。
这拨人出身不是蜀中,就是江南,意气相投,政见相似,便常聚在一起,如今日金明池赏雪饮酒一般。
丁谓走进亭中,林特已经倒满了一杯酒送上,道:“丁相请!”
与王钦若长相丑陋不同,丁谓不但有才,而且相貌清俊,人称鹤相。他为人精明能干,谈吐风趣,记忆力极好,数千言的文字,看过之后即能背诵。在三司时案卷繁多,积年老吏都不能决,他一言就能判定,令众人折服。造玉清昭应宫时,本需要十五年完工,而丁谓令工匠日夜赶工,竟以七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不管所任何职,他一上任,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声闻天子的政绩来。作赋吟诗、绘画、弈棋、博戏、音乐、茶道等无不精通。他任转运使时,将龙凤团茶改制成更为精致的大龙团茶,此后宫中皆用大龙团茶为御茶。又以图作书,写出本朝第一部茶经《北苑茶录》。
两人原本利益一致,相交甚好,只是王钦若为人强势,这些年来更加跋扈,近来见丁谓手握财权,与百官交好,连皇帝也渐渐倚重起来。丁谓的相貌,丁谓的人缘,丁谓的洒脱会玩,都是令王钦若心中暗嫉的。只是丁谓从来不以为意,潇洒如故,倒教王钦若几番寻事,都如拳头打在棉花上。王钦若自己倒疑惑起来:丁谓当真心胸宽广至此?
丁谓一口将酒饮尽,笑道:“好,权当我向各位赔不是,又迟到了,又说错话了。”自己再倒了一杯,向王钦若敬道:“恭喜王相,终于得遂所愿了。”前些时候,因为宰相王旦病故,升王钦若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入阁拜相。
王钦若淡淡一笑,将手中酒一饮而尽,却尽露疲倦之色:“这杯酒到得太晚了,意料中的事,却晚得心中竟然都提不起劲来了。”说着,将手中的酒杯重重一放,恨恨地道:“因了王子明,误我为相十年。”
丁谓知道他仍然记恨着当年的事,十年前皇帝就拟拜他为相,却被王旦极力反对,直到如今王旦病亡,他才得以入阁为相,这十年的等待,对于他来说,的确太长太长了,长到令他心态失衡。然而毕竟王钦若为相,打破了“南人不得入阁”的祖制,使得朝堂之上南北之势为之一变,就这一点来说,丁谓亦是感谢他的。
王钦若用讥诮的眼神看向丁谓:“谓之今日迟来,是否临行前中宫有命,以致延误?”
丁谓心头一震,随后镇定自若地笑道:“正是,临行前宫中询问,小皇子行冠礼之事准备得如何了?”
王钦若举杯轻饮一口,慢条斯理地道:“冠者成人也,而今年方五岁稚龄,就要行冠礼,古往今来未曾见也,老臣只怕到时候这冠礼行到一半,小孩儿哇哇大哭,岂不大失体统?”他初为相,正是要大展拳脚之时,皇帝在那次大火之后身体不好,朝堂上必会倚重更甚。可不承想,如今宫中皇后专权日甚,作为士人,最忌后宫干政,哪怕当日他也曾因为与寇準等人不和,而着力支持刘氏为后。但一介妇人,入主后宫便罢,如今这般,却是手太长了,须得让她明白前朝后宫的区别才是!
丁谓自然听出他的意思来,心念一转,强笑道:“王相博古通今,若论史识,无人能比。虽然说冠者成人也,但自周朝以来,天子诸侯为执掌国政,则未必一定要到二十岁才行冠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此事古已有之。且《士冠礼》中亦有‘诸侯十二而冠’之言。小皇子既受大命,自然聪慧过人,王相多虑了。”
王钦若冷笑一声:“但愿是老夫多虑了,小皇子行过冠礼,便可问政。有人急着要将这五岁孩子推上前台,却是为何?”
丁谓咳嗽一声:“王相,慎言!”不由得看了一眼,不想一抬头,却见地位稍低的几个人早去看远处的红梅了,座中竟然只剩下林特、陈彭年尚在一边。
王钦若双目炯炯地看着丁谓:“老夫熟读史书,古往今来,最惧的是子幼母壮,女主专权。唐代武后之祸,离之不远。谓之,你我身为人臣,不可不防啊!”
丁谓心头猛震,惊诧地道:“王相何出此言?”
王钦若往后一倚,缓缓地道:“老夫要你与老夫联手,阻止后宫擅权。”
丁谓强抑心头波澜,整个身子倾了过去,问道:“如何阻止?”
王钦若微微一笑,伸手指了指上面。
丁谓看着上面,心中领悟道:“天?”王钦若以天书起家,他这话,自然是打算以天意入手了。只不过这是他擅长的,何以叫自己出手?
王钦若点了点头,神秘地一笑。
丁谓会意地点了点头,两人转过话题,只谈风月,不涉政务,过得一会儿,众人赏梅回来,便继续饮酒,说些诗词歌赋。
丁谓不动声色地饮酒,作诗,直到傍晚,才兴尽各自散了。
离开金明池回到府中,已经是日落西山了,丁谓屏退仆从,独自站在空空的书房内,忽然仰天哈哈大笑,笑到全身脱力,笑到眼泪都出来了。
十年了,今日王钦若但恨这十年来得太迟,丁谓又何曾不恨这十年来得太迟了呢?
为了这一天,他等了足足十年。王钦若可为相,他丁谓又为什么不可为相呢?十年来他结交王钦若,以三司使的财力全力支持王钦若东封西祀种种行为,取得王钦若的信任,使得王钦若放心将建造玉清昭应宫的事交给他,而他亦借此机会,早已经培养起自己的势力。
可笑王钦若自以为抓住了皇帝,就足以抓住一切,但他不知道,丁谓的势力,早已经悄悄地自下而上培养起来。可笑王钦若自以为精通史书,却不知道在从丈量土地、兴修土木等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小事做起的丁谓眼中,他也只不过是过于书生意气罢了!
这些年皇帝身体不适,又沉迷于神道,朝中大事尽皆由王钦若把持,最终逼得王旦权柄一退再退,只能告老。如今王钦若正式为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若让皇子行了冠礼,皇后协助问政,哪还有这样的好日子?此人自视甚高,皇帝要让皇子即位,却没有请他辅政的意思,就已经大大刺激了他。
这些年虽然北官的气势略弱,而南官有更多的人上来,可是王钦若为人气量狭小,不能容人,只肯提拔对他俯首听命的,到如今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北官们在朝野上下,到处编派王钦若各种“奸邪”之事。王钦若名声已经在走下坡路,连南官中有志气者也远离他了,再与皇帝意见相左,这相位,他也坐不了多久了。
丁谓虽然当日与王钦若合作过,但是他不会跟王钦若站在同一条船上沉下,对方的船要沉了,他自然要及时脱钩,并且最好拉上另一条船才是。
丁谓以修玉清昭应宫和皇宫之权柄,已经掌控了一部分势力,也早为王钦若所忌。近段日子不断打压于他,如今更逼他在对付皇后的事情上一马当先,这是要拿他填坑。呵呵,他丁谓在王钦若面前低头,也低得够了,现在换他抬一抬头了。
他思忖着,若是王钦若罢相,谁能上位?如果是他继王钦若为相,那么如今所有对王钦若的攻击,接下去就会完全针对他了。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皇帝是否愿意在任命一个南官为相以后,再任命一个南官为相?
若北官再度兴起,朝堂格局必然会再度动荡,这未必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但若南官为相,则北官不会罢休,到时候他们会疯狂地群起而攻之。
所以接下来的宰相必是北官,但皇帝必然会重用一个南官来牵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由他抢在所有人之前,先帮所有人设计好他们都能接受的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既然已经决定对王钦若下手,就必须在扳倒王钦若之后,再找一个愿意与他搭档,甚至成为他的伙伴的北官为相。
十年前,长亭送别寇準的情景又浮在眼前:“平仲兄待谓之大恩,谓之无以为报,唯有他日再在此长亭之中,亲自迎平仲兄归来!”
丁谓推窗,望着窗外最后一抹残阳,微微含笑:“平仲兄,十年了,也该是你回来的时候了。十年了,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你,王旦、王曾、李迪,这些当初自命与你同一阵线的人,都不曾记得你,可是只有谓之不会忘记。你一定会再度回来的。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半个时辰之后,丁谓之子丁珝出府,前往枢密副使钱惟演府中。
次日,枢密副使钱惟演入宫参见刘娥。
半个月后,枢密副使马知节在朝堂当众举发王钦若擅权,泸州都巡检王怀信等平蛮有功,王钦若不但不及时上报请赏,反而扣下不理。
自为相以来,从未有人敢如此当面对他无理,王钦若气得浑身颤抖,回到内阁,便下了批文,将王怀信等人全部除官,以消心头恶气。
三日后,已经发出去的批文,却出现在赵恒的御书房中,赵恒大怒,当面召了王钦若来质问,重责他擅弄权术,令他闭门思过。
十日后,王钦若再度上朝请罪,说了半晌,赵恒方消怒气,不料马知节却拉住王钦若,争扯之间,王钦若袖间数十道本章落在地上,马知节遂骂他奸邪之辈,平时袖藏多道奏章上朝,看皇帝眼色而呈奏章。
副相向敏中,亦是王旦、寇準等人一派的,十余年来受王钦若打压不少,此时见状趁势出面指责王钦若。王钦若口才便给,以一敌二亦是毫不落下风,一时朝堂之上,唇枪舌剑、明刀暗箭纷纷乱放,两派积怨又久,副相李迪等人趁机一泄心头之怒,也加入了对战。
整个朝堂,霎时间乱如蜂窝,只听得嗡嗡嗡一片嘈杂之声,直到赵恒一声怒喝,方才静了下来。
赵恒大怒,拍案而起:“将王钦若、向敏中、马知节统统轰出去!”
王钦若骤然醒悟过来,连忙伏地请罪,却见赵恒拂袖而去。
数日后,表章纷上,王钦若贪污受贿、私藏禁书、假借鬼神之名擅议皇子加冠之事等罪名被人告发,赵恒盛怒之下,将向敏中、马知节、王钦若三人一起罢免,王钦若被贬职,出判杭州。
而此时王钦若的顶头上司,正是曾任参知政事,当年被王钦若陷害下贬的张知白。置王钦若于昔年仇家的手下,正是丁谓之绝妙安排。
到了年底十二月份,有旨意下来,本拟暂停的庆国公赵受益冠礼照旧准时举行。
冠礼在宗庙内举行,冠前十天内,要先卜筮吉日,十日内无吉日,则筮选下一旬的吉日。及冠礼前三日,又用筮法选择主持冠礼的掌冠者、赞冠者。
行礼时,文武百官齐聚宗庙之内,但听得乾安之乐大作,由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着五岁的皇子受益穿着大礼服,下了辇车,散发,自宗庙的台阶上缓步而入,两边台阶上俱是身着大礼服的文武百官。
皇帝升御座之后,皇子先拜见皇帝,然后起身。
礼直官大声唱道:“皇子行元服。”
紧接着肃安之乐大作,通事舍人等人引着皇子到大殿东侧,由掌冠者为其加折上巾(幞头),并由掌冠者唱祝词道:“咨尔元子,肇冠于阼。筮日择宾,德成礼具。於万斯年,承天之祜。”
然后皇子到殿东面,饮执事者所酌之酒,象征性地略进馔食,再回到正殿中。则由掌冠者取下折上巾,再授以远游冠,再唱祝词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学以让,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
皇子坐宴,再饮酒,再回正殿。最后一次除去远游冠,则加以皇子的衮冕,再次唱曰:“三加弥尊,国本以正。无疆惟休,有室大竞。懋昭厥德,保兹永命。”
冠礼成,于大殿北面,拜见生母刘皇后,奉上肉脯等物。由宫人接下,皇后受皇子三拜,送皇后出殿。
再回到正殿中,既行过冠礼,赵恒则再赐名“祯”字,为皇子冠礼后的正式名字。
然后皇子再到宗庙,祭告列祖列宗。
至此,这场烦琐的元服加冠之礼,才告结束。
这对于一个大人来说,也是一场累得够呛的礼仪,对于一个才五周岁的孩子来说,更是吃不消。早从两个月之前,刘娥便先让他演习了数次。此番正式行冠礼时,文武大臣们看着才五周岁的小皇子不哭不闹,一脸端庄肃穆,礼节一丝不差地完成了整个冠礼的经过,不由得心中暗叹:“皇子虽小,果然已经有君王的风范了。”
冠礼过后,赵恒下旨,皇子庆国公赵受益改名赵祯,封为寿春郡王,任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
一个月后,也就是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又下旨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寿春郡王友,辅佐皇子。
再过一个月,又有旨意,命皇子就学的地方为资善堂,设资善堂众辅官。
大中祥符九年年底,下旨改下一年为天禧元年。
天禧元年二月,再封寿春郡王赵祯兼任中书令。
天禧二年二月,寿春郡王赵祯晋封升王。
天禧二年八月,文武百官请立皇太子,赵恒下旨,立皇子升王赵祯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九月中旬,赵恒御天安殿正式册封赵祯为皇太子,祭庙告天。
这一年的年底,寇準回京。
城外长亭,参知政事丁谓已经置酒相迎。
这一次寇準的回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赵恒是个记旧情的人,也曾有让寇準回京之意,数年间每次被王钦若所阻。王钦若只说得一句:“若是寇準回京,对官家信奉天书之事仍然大肆批评阻止,却当如何是好?”赵恒便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丁谓既存了此心,于是就开始寻找机会。自刘承规去后,周怀政接手皇城司,他不比刘承规才能超众,难免少些底气,于是就爱结交朝中大臣,以为外援。
周怀政有一好友,便是永兴军巡检朱能,这次正好被人上告贪污等各项不法之事。朱能自知不妙,忙写信向京中认识的官员们求助。
丁谓听闻此事,大喜,辗转寻人同周怀政说,要帮助朱能,就只有令他献祥瑞,最好是献天书。周怀政亦是不察,于是写信给朱能,叫他依计行事。
过了一段时间,永兴军巡检朱能,就在乾佑山发现了天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祥瑞了。自从大中祥符初年在承天门发现天书之后,各地经常出现祥瑞报告,要么天上发现“五星连珠”,要么地上发现玄武真君的灵异,至于灵芝朱果,更是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先是王钦若献了八千多株,接着副相赵安仁也献了一万多株,到丁谓出判亳州时期达到最高点九万五千多株,以致被人讽刺丁谓在亳州不种庄稼光种灵芝了。
不过天书只出现过一次,祥瑞的物品也罢了,谁也不敢拿白纸黑字的天书来开玩笑。但朱能是地方小官,哪里知道深浅,竟敢依计而行。
而丁谓插手此事的原因,却正是因为朱能的上司,是昔年因反对赵恒信奉天书而罢相被贬出京,此时任永兴军节度使的寇準。永兴军所在发现天书,而且是夹在永兴军上报的奏章当中,报至京中。
王钦若以天书而得势,如今,他一定想不到,一直被他打压的寇準也同样能以天书重返朝中。这真是件有趣的事,丁谓暗忖。
此时刘娥身为皇后,自然也是看到了奏章,诧异地道:“上报此消息的,竟然是寇準?”
枢密副使钱惟演点头笑道:“正是。”
刘娥缓缓放下奏章:“我记得,当年寇準是最反对信奉天书的人吧。不想今日,他竟然也主动制造祥瑞,进奉起天书来。唉,既有这一日,何必那一遭!这十年来兜兜转转,还是走到这一步来!”
钱惟演点头道:“正是有了那一遭,才会有了这一日啊!一个人不经挫折,怎能学得会‘妥协’这二字呢?十年来远离中枢,失去对军国大事插手的权力,十年来只能在地方上做一方大员,对于一个喜欢指点江山的人来说,足够让他改变了。”
刘娥长叹一声,不觉有些惆怅:“当我们开始重视一份真正可贵的坚持时,却发现时光已经让这份坚持面目全非了。”
钱惟演默然:“人总是要变的。”
刘娥看了他一眼:“你也变了吗,希圣?”
钱惟演低下头去,片刻后,他抬起了头看着刘娥,坦然道:“是,臣是变了很多,但是有些事,已经入骨,便是时光也不能改变。”
刘娥看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是,有些事已经入骨,便是时光也不能改变。譬如说,你我之间永远的信任。”她轻轻地拿起寇準的奏章放在右边那一堆已经看过的奏章中,含笑道:“官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果然赵恒很高兴,虽然天书一事,做得实在很不高明,不高明到被许多重臣驳斥,如参知政事鲁宗道上言此为“奸臣妄诞,荧惑圣聪”。河阳军知军孙奭,更是上书请求“速斩朱能,以谢天下”。赵恒握着这道奏章,却是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份祥瑞报告而已,更是寇準的一封降书。
“朕终于降伏这犟头了。”赵恒道,“先帝贬他两次,他才驯服,朕只贬他一次,却要他真心驯服。”
丁谓侍立一边,笑道:“臣早就说过,寇公只是性子直了些,却还懂得做臣子的本分。官家所好,便是臣子所尊。”
赵恒哈哈一笑,令周怀政道:“拟旨,招寇準回京。”又问丁谓:“寇準回京,如何安置?”
丁谓跪下道:“臣斗胆,请官家拜相寇公。”
赵恒大感诧异,微微点头:“嗯,难得你有这份心。”此次王钦若罢相,丁谓继任为相的呼声最高,不想丁谓竟然推荐寇準,赵恒不禁对他有些另眼相看了。
却不知这本就是丁谓的计划,此时王钦若失势,左右有劝丁谓乘此机会入阁为相的。他却知道若是自己登上相位,则南官权柄过重,不但会成为北官攻击的目标,也会令皇帝生疑,不如自退一步,举荐寇準。寇準为人心大、好奉承,只要自己对他恭敬到位,让他不好意思对自己发作,自然就能行事方便,有事也好让寇準顶在前面,反而更好。这相位由王钦若到寇準,再下一任,自己为相就水到渠成了。
况且他当年亦与寇準甚是交好,寇準为人豪爽,不懂经济,经常豪掷巨万,到要用钱时却周转不开。丁谓刻意交好,给寇準出主意,帮他料理钱银之事。寇準虽然轻视南官,却曾举荐帮助过丁谓。
于是此番丁谓上奏赵恒,力荐寇準为相。召寇準回京的事,终于敲定下来。
圣旨下到永兴军中,寇準捧着圣旨站起来,不禁仰天长叹。
这一天终于来了。
而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改变了太多。
他不相信天书,不相信祥瑞,当年被贬出京,他依然自信而执着,时间将证明这是一场闹剧,时间将证明他是对的。
然而一年年地过去,这一场闹剧愈演愈烈,直到演变成正剧。他看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投身于这场全国性的运动。
当一件事情,一两个人说你错了,你还可以认为自己是对的,上百上千个人都说你错了,你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当全国上下都投身于一件事十年之后,你就会否定自己原先的判断。
你为什么要跟所有人不一样?若这件事真的错了,难道天下这么多人都错了吗?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吗?
无数个夜里,寇準开始这样问自己。没有他的日子,朝廷照样运转,运转得叫他心急如焚。执掌国政的,是王钦若这样的奸佞之臣,而他却只是因为固执地反对一件事,而让自己置身圈外不得过问,这,真的是于国有利、于民有利吗?
连他一直敬重的老宰相王旦,也带头敬迎天书,带头赞颂此事了;连他一直倚重的正直之臣李迪、王曾,也随波逐流了;连他一直来往的朋友赵安仁、丁谓,都抢着献灵芝了。
寇準扪心自问,他此刻的坚持让自己失去对政治走向的控制权,他此刻的坚持让王钦若之流更加放纵,他此刻的坚持让自己远离中心。这一份坚持,真的是有必要的吗?
他决定放弃了,所以他接受门客的劝说,在朱能的天书奏表上,违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违心地把这一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作为自己郑重的自荐。
寇準收拾起行装要回京了,仍然有门客劝他:“此时朝中奸人当道,寇公接旨之后,若称病不去,请求外任,乃是上策;若是入见官家,当面奏天书之虚幻,则为中策;若是再入中书,自堕名节,恐怕要入下策了。”
这门客跟随他多年,知他。然而门客知道的,是过去那个凡事随心、毫无顾忌的寇準。此刻的寇準,心境已变。虽然他知道,回京必须面临着种种门客们所说的处境,但是参与天下大事的议政,才是他的志向所在。长久在外,纵然是治得一郡太平,又岂能称他胸怀!名节事小,江山事大。只要他重返中枢,他自信制得住丁谓,也自信仍有能力影响皇帝,改变朝纲,重振正气。因此虽然听了种种劝说,他依然豪情万丈地上路了。
然而,违心的事,并非只是迈出这一小步,就足够了。
离京城只有三日之路,寇準又接到了一道圣旨——令他进京之前,写出一道关于天书祥瑞的赞表。
“天书赞表!”寇準手捧圣旨,只觉得心中一阵阵地发冷。是笑别人,还是笑自己?人一朝堕落下去,迈出了第一步,就必然要迈出第二步吗?
随圣旨同来的,是亲自前来宣旨的皇城司周怀政,还有丁谓的亲信随从。这却是丁谓之计,他若要利用寇準,必须不能让寇準一回京就把他当成目标。只有寇準自己也妥协了,他丁谓才好于中取利。这人一旦走出第一步,后面自然就硬气不起来了。
因此他悄悄向赵恒进言,让他下这旨意。另一边又自做好人,私下派了心腹悄悄地告诉寇準:“只因朝中有人,不愿意寇公入朝为相,因此在官家面前进谗。丁某知道寇公为人,不会拘泥于这种小事,请寇公一定要进京,免得教那等小人遂了心愿!”
“不会拘泥于这种小事,不会拘泥于这种小事!”寇準喃喃道。忽然大笑起来,在案前一坐,喝道:“拿酒来!”
整整三坛的兰陵美酒,倒入腹中,化作一大篇天花乱坠、不知所云的天书赞表。寇準掷笔,狂吐,沉醉不醒。
天书赞表飘飘飞起,坠落在地,周怀政拾起表章,面无表情地离开。
次日,仍在昏昏大睡中的寇準被侍从扶上马车,继续向京城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