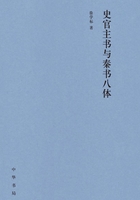
绪论
本书由“史官主书研究”与“秦书八体研究”两大部分构成,“史官主书研究”重在说明“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秦书八体研究”重在逐个解决“秦书八体”中各体的名实问题。尽管两部分内容所主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然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史官主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是我们研究“秦书八体”中各体名实的前提基础。而“秦书八体”中各体名实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坐实“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这一结论。
近世以来,史官文化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大家普遍认为,史官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国学术的根本渊薮。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谓:“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1)中国古学,无论是儒家六艺,还是九流百家,术数方技,无不源于史官,以“史”为本源大宗。龚自珍对此有过清晰完备的论述: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纣时,其史尹挚抱籍以归于周;周之初,始为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劳周室,改质家跻于文家,置太史。史于百官,莫不有职事,三宅之事,佚贰之,谓之四圣。盖微夫上圣睿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经,经之名,周之东有之。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蠭出泉流,汉氏校录,撮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2)
刘师培、龚自珍之外,柳诒徵、金毓黻、朱希祖、戴君仁、李宗侗、徐复观、陈槃等前辈史学大家,皆持此论。
史官文化与史官职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官是史官文化的创造者,史官职能决定了史官文化的性质与内容。对于史官职能问题,论之者众。几乎所有有关史官制度及文化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史官职能的关注。刘知几《史通》、马端临《文献通考》、章学诚《文史通义》、王国维《观堂集林》、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柳诒徵《国史要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这些代表了唐代以来最高学术水平的史学著述,都曾对史官职能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专门研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官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涉及史官职能及专门研究史官职能的论文即有三十篇之多,其中贡献卓著、影响较大者,有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载《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许兆昌《周代史官职官功能的结构分析》(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1999年第4期)、刘隆有《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载《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1期)、谢保成《对史学史中“史”、“史官”认识之澄清》(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等。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拓宽了后来者的视野,给人以启迪。
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云:“(史官)名目既多,职务咸异。”所司繁庶是史官职能的一大特色。柳诒徵据《周礼》的记载,整理出史官的职能共八种:执礼、掌法、授时、典藏、册命、正名、书事、考察。(3)陈锦忠将史官的职能归纳为两大类十八项,天事方面:神事、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政事方面:册命、聘问、约剂、刑法、盟誓、征伐、籍田、射事、典藏、谱系。(4)席涵静归纳为十种:占筮、记事、赐命、册命、典藏、预言、历法、祭祀、礼事、临时差遣。(5)不同的职能由不同类型、不同名目的史官专门负责,而即使是同一类型、同一名目的史官,其职能往往也是多方面的。如张亚初、刘雨二人在其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对西周太史、内史的职能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中,太史的职责主要有:助王册命、赏赐,命百官官箴王阙,保存、整理文化典籍,为王之助手和顾问;内史的职责主要有:进献胙肉于王后,铸造礼器,册告,代王出使,管理旗帜。(6)
然而,更进一步,具体到史官共通的基本职能(7),却鲜有人对此予以特别关注,偶有所及者,除去少数学者零星琐碎的只言片语外,大多表现为对“史”字构形及《周礼》与《说文解字》中个别语句的引申发挥,且观点也极不统一。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王国维《释史》(载《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陈梦家《史字新释》(载《考古》第5期,1936年12月)、劳榦《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载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卷,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徐复观《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载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等,均是试图通过对“史”字构形的研究,从字源上解决“史”的原始职能问题,但这一原始职能并非就是史官制度成熟之后史官的基本职能。章学诚、金毓黻、白寿彝诸家,依据《周礼》“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的记载及《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的说解,分别对史官基本职能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皆守掌故”与“以法存先王之道”是章氏所认为的史官共通的基本职能。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吾谓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只称为史,如汉人所称令史是也。其为诸史之长者,亦不过如汉代之长史、魏晋之掌书记。其以记事为职,古今亦无二致。继则品秩渐崇,入居宫省,出纳王言,乃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称,以别于掌书起草之史。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制,如汉晋之有中书监、令,唐宋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之有大学士,是也。(8)
“记事”是金氏所认为的史官共通的基本职能,并且在金氏看来“掌书起草”与“记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史不止是一种官职,而且是有多种分工的官职,他们的共同任务是,起草文件、宣读文件、记录某些活动、保管各种官文书,在一些宗教活动中,还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9)
“起草文件”“宣读文件”“记录文件”“保管文书”“宗教职章”等,说明了在白寿彝看来史官共通的基本职能是多方面的。
可以说,有关史官基本职能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尚缺乏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笔者以为,史官职能虽多,然作为其基本职能的却只会有一种,这种基本的职能是不同职司,不同名目的史官之所以为“史”,之所以能够统称为“史”的根本原因,是各类史官的共通职能。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谓:“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从史官与文字的关系来分析,史官的基本职能也只会是与文字的应用有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10)可见,史官文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与文字应用有直接关系的史官基本职能所决定的。而文字的应用则包含有“主书”(主文书起草)与“主文”(主文字书写)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作为史官基本职能的到底是什么,是“主书”,还是“主文”,抑或是二者的综合呢?
“张家山汉简”《史律》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史官基本职能提供了最为原始、最为真实、最为直接的论据材料——《史律》规定汉初史学僮所考课的两项内容:“十五篇”与“秦书八体”,就是为“史”者所应当具备的共通的基本业务职能。
《史律》出土之后,李学勤、曹旅宁、高明、赵平安、王子今、臧知非、(日)西川利文、邢义田、游逸飞、(日)大西克也、(日)广濑薰雄等中外学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对《史律》内容进行了考证、利用。其中,有对《史律》内容综合研究者,如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史律〉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有对《史律》中的个别内容进行单独考证者,如赵平安《新出〈史律〉与〈史籀篇〉的性质》(载《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王子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学童”小议》(载《文博》2007年第6期)、(日)广濑薰雄《〈二年律令·史律〉札记》(载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有以《史律》内容考证秦汉史事者,如游逸飞《太史、内史、郡——张家山〈二年律令·史律〉所见汉初政区关系》(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梁方健《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载《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高宗留《汉代官学并非自汉武帝始立——从〈张家山汉简·史律〉谈起》(载《科教文汇》2008年第1期)等。然将《史律》内容用之于对史官基本职能问题的论证,迄今未见一例,这不能不说是《史律》研究的一大缺憾。
本书第一部分“史官主书研究”,主要解决的就是这种史官的基本职能问题——论证了“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首先对研究的对象“史官”作出了明确界定,将史官区分为“五史”与“府史”两大类,进而分析了史官与文字的关系,并将文字的应用析分为“主书”与“主文”两个方面,以此配合“张家山汉简”《史律》中有关史学僮课试内容的记载,论证得出了“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这一结论——《史籀篇》的字书性质,以及“秦书八体”的书体性质,反证了“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其中,将“张家山汉简”《史律》用之于对史官基本职能问题的论证,是该部分的核心内容。
史官基本职能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不同类型、不同名目史官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准确地把握史官文化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与基本脉络,以及深入研究“秦书八体”之各体名实问题,都具有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秦书八体”是指通行于秦及汉初的八种书体,其名源自许慎《说文解字·序》之“自尔秦书有八体”句。据现有文献资料分析,至迟自元代开始,“秦书八体”已经作为一个固定名称确立了下来。许慎《说文解字·序》: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许慎虽然指出了“秦书八体”的具体名称: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但也只是对这八体之“数”与“名”,进行了简单罗列,对于八体中各体的确切所指、用途、得名原因等,未做任何展开说明。历来治《说文解字》者,或各抒己见,或相互因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论。
近世以来,随着秦汉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面世,以及中国早期书法史、文字演变史、文化教育史等研究的日趋深入,“秦书八体”相应地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既有对“秦书八体”进行宏观性系统研究者,如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历史上的字体》(中华书局2011年版)、唐兰《中国文字学·文字的变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秦书八体原委》(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3年版)、陈一梅《〈八体六技〉考——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载《碑林集刊》第11辑,2005年)、陈振濂《大学书法篆书临摹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刘涛《“史书”与“八体六书”》(载刘涛《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年版)、(日)山元宣宏《关于〈说文解字〉叙和〈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书体名称》(载《中国文字研究》2012年)等;也有对“秦书八体”中的某几种书体进行对比研究者,如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形体的演变》(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以及靳永《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载中国书法家协会主编《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理论卷》,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一文中,对“篆隶”二体的论述;而更多的则是对“秦书八体”中的某一种书体进行单独研究,如商承祚《说篆》(载《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马国权《鸟虫书论稿》(载《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丛文俊《鸟凤龙虫书合考》(载《书法研究》1996年第3期)、萧高洪《官印用篆及其演化的文化考察》(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S5期)、张传旭《鸟虫书名实》(载《青少年书法》2004年第2期)、王国华《汉代刚卯殳书管见》(载《书法》1982年第2期)、褚良才《殳书考》(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4期)、王正书《刚卯殳书之我见》(载李国章、赵昌平《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鲁国尧《“隶书”辨》(载《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张同印《隶书名称的历史沿革辨析》(载《书法研究》2000年第6期)、寇克让《隶书正名》(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2期)等。
以上诸家的研究,在论证方法上均存在一个共通的失误,即过多措意于“秦书八体”中各体之间的“名实”差异,而忽略了对“八体并举”的产生年代,以及“秦书八体”性质、用途等的关注,突出表现为没有将“秦书八体”与“史官职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按《说文解字·序》《汉书·艺文志》及“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作为秦及汉初出现的“秦书八体”,是史学僮的两项必修、必课内容之一。史学僮学习“秦书八体”的目的,自然是为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史官服务,由此决定了“史官职能”与“秦书八体”之间,具有了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对应关系,我们足可以从史官的“主书”职能入手,对“秦书八体”之各体的名实由来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专项研究。
从史官的“主书”职能来分析,有关“秦书八体”的诸多传统成说皆大有可商之处。一、篆书。历来论及篆书名实者,无不以秦泰山刻石小篆为标准字样而求篆“名”之由来,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刻石在汉之前只是偶尔为之,非官方一般用字范围。据金其桢《中国碑文化》考证,秦始皇时期总共立了九块记功刻石,西汉碑石也仅仅只有十余块(11)。秦及汉初政府断然不会仅仅为了这偶尔一用的碑石,而规定全国的史学僮每年都要学习刻石文字。二、刻符。以阳陵虎符、杜虎符等兵符上的文字为刻符之正宗,几成定论,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虎符是一种数量极少(每个朝代最多制造三百余枚)、用途郑重的特殊信物,一般史官根本无法接触到它(能够接触到它的主要是帝王与郡国守相),更谈不上制作虎符,在虎符上刻字。秦及汉初政府要求全国的史学僮都要学习这种穷其一生都很难接触到的虎符文字,毫无道理。三、摹印。对摹印的认识,以唐兰的“规摹”之说影响最大:“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位置的疏密,用规摹的方法画出来的。”(12)然而,一方面“摹成”的印文是反字,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会将一种反字作为特殊书体,要求全国的史学僮学习;另一方面,印章制作是中央所属少府的职责,能够到少府机构参与印文制作的史官毕竟是极少数(汉制定员六人),难道秦及汉初政府仅仅为了这极少数史官的职务所需,而规定全国的史学僮都要学习如何摹写印稿——“反字”吗?四、虫书。以往学者大多都把出自汉以前尚方工技之手的装饰性花体字,当作虫书。实际上,无论是从书体作者,还是从幡信功用而言,虫书都不可能是装饰性花体字。五、署书。徐锴《说文系传》卷二十九引萧子良说:“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即是说署书是用来题写宫阙之名的。汉初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究不知此期能有多少宫殿需要题署,以至于萧何专门创造一种书体,并规定每年全国的史学僮都要学习它!六、殳书。以殳书为“铭于戈戟之文”,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认识。然秦立国之初,即颁行销兵令:“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13)将兵器制造权收归中央,并置尚方令掌管兵器制造事宜,尚方之下又设若卢和考工室负责兵器制造的具体工作;汉初,中央所属少府下设考工令室,负责制造弓弩刀铠等兵器。而按《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序》及“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秦及汉初除全国课试第一名的史学僮到中央所属尚书机构担任卒史外,其余为史者一律都到地方郡县去做令史或佐史。这些地方郡县的史官几乎无人能够接触到兵器制作事宜,倘若殳书果真是指“铭于戈戟之文”,那么绝大多数的史学僮学习这种将来用不到的技能又有什么必要呢!
本书第二部分“秦书八体研究”,即是从史官主书角度出发,对“秦书八体”中各体名实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首先对“秦书八体”最初产生的年代、作用、性质等宏观问题逐一论证,得出了“秦书八体,是与‘史官主书’的基本内容相对应的,以官府日常行政用字为主的八种主要官方用字,是‘史官主书’的主要书体内容”这一结论。以此为切入点,对“秦书八体”之各体名实问题进行了顺序研究。认为八体中的“篆书”(包括大篆、小篆)与“隶书”是适用于简册的一般官府文书用字。篆、隶之名皆相对而出,“篆”为“掾”之同源后起字,“掾”是秦代专司文字工作的政府吏员,是官方文案的主要责任者,因这些文案,大多都要直接呈报给始皇帝及中央所属机构,故规定必须以正体来书写,篆书之名也即因此而起。作为与篆书之名同出的“隶书”,也只能是因其使用的对象为“徒隶”而得名;八体中的“刻符”,是指“竹质符”上的墨书文字,而非一般史官接触不到的兵符上的刻铸铭文。刻符之“刻”,并非指的是用刀在符信上锲刻文字,而是指“竹质符”上的“刻齿”;八体中的“虫书”,用于书写幡信。幡信的功能,决定了这种书体不可能是装饰性花体字。虫书之“虫”是指狭义上的蝮虫,之所以称“虫”,是因为这种文字线条屈曲蜿蜒,形如抽象之蝮虫;八体中的“摹印”,是指官方印信及封泥上的文字,因这种文字用于摹写印面,故而命名为摹印;八体中的“署书”,是指用以封检题署、悬法,及署门户等的文字。这种文字在风格上与通常情况下的官方用字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只不过其字形一般都写得较大、风格较庄重而已;八体中的“殳书”,并非是指“兵器铭文”及“刚卯、栒邑权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在秦及汉初尚未以“觚”命名字书文字之前,殳书最大的可能性是对字书文字的命名。
同时,从史官的“主书”职能来分析,传统观点以为史书中所出现的“秦书八体”与秦统一全国后实行的“书同文”政策相矛盾,以及今所见秦代文字资料与“秦书八体”之名不符等一系列问题,也会涣然冰解。因为,“秦书八体”是与“史官主书”主要内容相对应的,不同场合下的官方用字,并非是指这八种书体的文字构造各自不同;“秦书八体”是“史官主书”的主要书体内容,并非是说秦代总共有这八种书体,也并非秦代所有的官方用字全部能够涵盖在这八体之中。
“秦书八体”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深入把握中国早期文字的存在状态,及其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今所能够看到的大量汉代以前文字资料,进行合理归类、系统分析;同时,从“史官主书”角度对“秦书八体”进行研究,将史官与书体结合起来,这一研究思路,也可以为当今史官文化,及书法史、文字史研究者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多沿用史学的归纳、分析、比较等方法。在资料的运用方面,采取“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相结合,在传统的《史记》《汉书》《周礼》等典籍材料之外,大量采用了最新出土的汉以前简牍、金文、封泥、刻石等实物资料。
将史官之于文字的应用析分为“主书”与“主文”两个方面,将“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史学僮课试内容用之于史官基本职能的论述,将史官职能与秦书八体结合起来,从“史官主书”的角度对秦书八体进行系统研究,这些工作目前都还是第一次。笔者在此所做的只能说是一些初步的探讨,难免会存在史料收集方面的疏漏及个人理解上的偏差,以致影响到结论的客观公正,恳请学者前辈予以批评指正!
(1)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卷,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第42页。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古史钩沉论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
(3)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4)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1979—1980年学年度博士论文,转引自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
(5)席涵静:《周代史官研究》,转引自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
(6)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6页。
(7)本书所论“史官基本职能”之“史官”所指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史官制度成熟之后的西周至汉以前这一时间段之内的史官(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史官的界定”有详述);二是对五史与府史两类史官的统称(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节“史官两大类——‘五史’与‘府史’及其相互关系”有详述)。
(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页。
(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页。
(11)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5页。
(1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3)《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