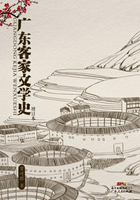
第三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孕育
第一节 张九龄
一、开元贤相
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人们赞颂这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时,很自然也会联想到被誉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虽然,他为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
张九龄(678—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祖籍河北范阳,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遂家曲江。据《新唐书》记载:九龄自幼聪颖,“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 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历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转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起宰相的重任。后遭李林甫等人谗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改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再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病逝于韶州曲江故居,年63岁。
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历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转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起宰相的重任。后遭李林甫等人谗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改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再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病逝于韶州曲江故居,年63岁。
张九龄确实是“材堪经邦”,卓有建树。开元四年(716年),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工程,为开发岭南,繁荣长江中下游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更是以刚直著称。任左拾遗期间,上书宰相姚崇,直言规劝其用人必须慎重,决不能让谄媚逢迎之徒得逞。他指出:“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陷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面结笑言,谈生羽翼,万事至广,千变难知。”可谓是义正词严,切中时弊。唐玄宗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极力反对,因此多次得罪玄宗。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九龄更是明察秋毫,他在上《请诛安禄山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女嫔。守珪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九龄所言中。“安史之乱”成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才后悔莫及,“每思曲江则泣下” ,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如九龄否?”后来,人们将张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
,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如九龄否?”后来,人们将张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
二、《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结为《张曲江集》20卷,有明刊本,清顺治刊本,四部丛刊本。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地方文献丛书》,收入了由刘斯翰作注的《曲江集》,1994年10月《岭南文库》中罗韬选注的《张九龄诗文选》,亦是以《曲江集》为蓝本。
《曲江集》中共有193题222首诗、248篇文,其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从他的诗文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他的心态,但表现手法则诗文稍异。其文直陈时事,直抒己见,主旨明确,语言明朗。其诗则多用比兴,较为含蓄,略显委婉。这明显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诗作走的是《诗经》风雅的道路。
先谈其诗。有人批评张诗“几乎清一色的五言古诗体,而且多用骈句,未脱六朝旧制,这在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之后,更见保守得可以” 。诚然,从形式上来说,张九龄确实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他的12首感遇诗,明显地受到了陈子昂的影响,直接模仿其诗体。然而,从思想内容来说,张诗却展示了自己的世界,表达了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是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诗歌表现,其审美价值、其认识功能、其教育作用,则决不可低估。清衡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时,张九龄的“感遇诗”被列为开篇之作,足见其地位。
。诚然,从形式上来说,张九龄确实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他的12首感遇诗,明显地受到了陈子昂的影响,直接模仿其诗体。然而,从思想内容来说,张诗却展示了自己的世界,表达了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是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诗歌表现,其审美价值、其认识功能、其教育作用,则决不可低估。清衡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时,张九龄的“感遇诗”被列为开篇之作,足见其地位。
在青年时期,九龄怀抱大志,由曲江赴广州应试,路经英德,作《浈阳峡》一诗,抒写情怀:
舟行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里写出了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更是触景生情,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发问:“这样好的美景,却处在这边远之区,谁来赏识呢?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呀!”这完全是以美景“自况”,是夫子自道了。对自己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己的才干,建功立业,这是青年张九龄的真实心理写照!
出仕后不久,九龄“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激起了他的故园情:
水闻南涧险,烟望北林繁。远霭千岩合,幽声百籁喧。
阴泉夏犹冻,阳景昼方暾。懿此高深极,徒令梦想存。
盛明期有报,长往复奚言。
美丽的故园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
张九龄非常热爱岭南的山山水水,热爱自己的家乡,向往结庐名山,与渔樵为伍,过隐居山林、回归大自然的田园生活,《曲江集》中讴歌岭南美景的篇什不少。在岭南文学史上,他是较早较多描绘山川风物的杰出的诗人。其诗作展示了盛唐时期岭南地区的自然风貌,这些篇什中所涉及的曲江、始兴、浈阳都是当今的客家地区,这些诗作也可以目为客地的早期山水诗。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在讴歌美景时的心境:“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自始兴溪夜上赴岭》)这与未入仕途时渴望被赏识、重用的强烈要求相对比,显然是少了些锐气,多了退隐的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张九龄产生烦闷的心绪,从而更感到家山故园的可爱。
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张氏于开元四年辞官回归故里。这时,他常与知己曲江县尉王履震过从。在《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一诗中,他回顾自己的仕途历程,以历史上的失意文人自况,表达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胸怀,既有一种无法再施展抱负的失落感,又有“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的自解,这是心理上的另一种补偿。原诗全文如下:
宅生惟海县,素业守郊园。中览霸王说,上邀明主恩。
一行罢兰径,数载历金门。既负潘生拙,俄从周任言。
逶迤恋轩陛,萧散反丘樊。旧径稀人迹,前池耗水痕。
并看芳树老,惟觉敝庐存。自我栖幽谷,逢君翳覆盆。
孟柯应有命,贾谊得无冤?江上行伤远,林间偶避喧。
地偏人事绝,时霁鸟声繁。独善心俱闭,穷居道共尊。
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幽意加投漆,新诗重赠轩。
平生徇知己,穷达与君论。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与苦恼,宣泄在他那著名的感遇组诗12首中。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其表现手法是以美人香草等传统文学中常见的美好意象作比,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一)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四)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其七)
举一可以反三。从上录的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张九龄内心的创痛。“兰叶”一首,暗喻自己的品质情操;“孤鸿”一首亦是自喻,“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 ,为自己能脱离政治斗争的风险而庆幸;“江南有丹橘”一诗则是对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谗言的怨恨。
,为自己能脱离政治斗争的风险而庆幸;“江南有丹橘”一诗则是对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谗言的怨恨。
张九龄诗歌之可贵,就在于它的“情真”,《曲江集》中的诗篇不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真情”。写自己在政治漩涡中的感受如此,写家人间的亲情更是如此,其《赋得自君之出矣》,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晖。”它从徐干的《室思》篇变化而来,却更富于想象,也更加感人。
在《曲江集》的散文中,《白羽扇赋并序》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向玄宗皇帝表明自己态度而写的名篇。客家人有句谚语:“婚后媒人秋后扇。”在炎热的夏天,扇可使“清风徐来”,人们爱不释手,而到了秋后则必弃置一旁了。汉代才女班婕妤有《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道出了世道炎凉的社会现实。张九龄正是借扇曲折吐露自己的担忧。全文并不长,却写得极有情致:“当时而用,在物所长。彼鸿鹄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烦暑,可致清凉。岂无纨素,采画文章;复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携密迩,摇动馨香。惟众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当?而窃思于圣后,且见持于未央。伊昔皋泽之时,亦有云雷之志,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忘;肃肃白羽,穆如微风,纵秋气之秽夺,终感恩于箧中。”
至于义正词严的政论文《请诛安禄山疏》《上姚令公书》,读者无不佩服张九龄的过人胆识,千载之下令人肃然起敬。而其《祭张燕公文》则可见九龄的忠厚和深情:“想德辉而不见,望仁里而徒泣;树所叹而犹存,人具瞻而永戢”,从心灵深处为张说病薨而万分哀痛。祭文既表彰张说的功绩,又抒写自己深切的怀念,乃是一篇感情真挚、文辞精美的抒情散文。
三、泽被南粤
张九龄是岭南文学的宗师。“五岭以南,当开元盛世时,以诗文名者,曲江公张九龄一人而已。” 在唐以前的岭南文学,虽然亦有些名篇佳构,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赞》、南朝刘删的《泛宫亭湖》《独鹤凌云去》等诗
在唐以前的岭南文学,虽然亦有些名篇佳构,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赞》、南朝刘删的《泛宫亭湖》《独鹤凌云去》等诗 ,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直至盛唐张九龄之后才蔚成风气,他的人品、诗品,都给岭南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直至盛唐张九龄之后才蔚成风气,他的人品、诗品,都给岭南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他的家乡韶州曲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地的客家人以张九龄为荣,自不待言。广东其他地方的客家人,也深深敬佩张九龄。据《乾隆嘉应州志·祠祀》载:嘉应州西北40里有相公坪,“祀唐丞相文献张公。雍正年乡人重修。”又有九贤祠,在嘉应州城内东北隅,祀张九龄、韩愈等9人。“乾隆十五年培风书院成,九贤神主安奉楼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 客家人把张九龄作为值得永远纪念的先贤。旅港嘉属商会出版的《文丛》,梅叟《客人先正诗传》在热情赞颂张九龄的同时,对唐玄宗亦提出尖锐的批评:
客家人把张九龄作为值得永远纪念的先贤。旅港嘉属商会出版的《文丛》,梅叟《客人先正诗传》在热情赞颂张九龄的同时,对唐玄宗亦提出尖锐的批评:
相才相器两堂堂,金鉴千秋式表坊。
帝语独论风度美,知人犹自恨明皇。
当年开济负臣心,海上孤鸿意自深。
曾过曲江祠下拜,眼中桃李总阴阴。
清道光年间诗人林承镌的《梅岭谒张文献公祠》,则将其“相业”与“文章”并举,赞颂张九龄泽被后人:
石破惊开岭外天,斯人斯地并堪传。
岂徒相业追姚宋,自有文章敌许燕。
七宝昔曾登讲座,一祠今更靖蛮烟。
最怜剑阁銮舆回,遥祭孤臣瘴海边。
一线中原路远通,衣冠肃拜往来同。
瓣香心事应怜我,箧扇遭逢尚忆公。
风度千秋犹想象,云容半岭剧溟蒙。
试登绝顶东西望,落落尘寰眼界空。
张九龄的诗歌对后代广东客家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继承《诗经》传统;二是其描绘广东客地风光的篇什,为客地的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具有“冲淡”的风格,具有闲静、幽远的韵味。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张九龄“感遇诗”一类的作品,对客家人(包括客籍文人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在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仅以《咏燕》一诗为例,作简略的说明。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为什么自比“微眇”的海燕?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张九龄的远祖家在中原,本是“晋司空(张华)之后”。张华,范阳人,“强记默识,博学多闻,当时推为第一”,晋惠帝时官至司空,是有名望的大臣。后因赵王司马伦谋废贾后,张华不从,遂遭杀害。这样的一位远祖,对张九龄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他的近祖定居广东后,却都是职低位微的官吏,其父张弘愈只不过是新州索虏丞而已。曲江,地处岭表,远离长安而较近海隅,故张九龄以“海燕”自况。“乘春亦暂来”,是感激唐玄宗的知遇之恩。一个“暂”字,道出了张九龄的心态,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清醒预见。尽管“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有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他始终不会忘记自己卑微的出身。“岂知泥滓贱”的反问,仿佛是用《易》提醒自己:“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张九龄深知自己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无权贵集团作依托,他斗不过那些心怀叵测、惯用权术的小人,从而发出了“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感喟。
这首五言诗影响深远,而理解各异。孟棨《本事诗·怨愤》:“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深识器之,李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咏燕诗以致意。”《全唐诗话》亦有记述,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燕诗以贻林甫,云云。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而今人黄志辉、龙思谋则力排此说,他们在《粤北历代名人诗选》中提出:“张九龄为人正直,‘每见帝,极言得失’,该不至于要向李林甫乞怜。所谓‘惶恐’献诗,贻诗‘致意’之传闻,不应轻信。”“可能只求自我解脱而作” ,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我认为张九龄的《咏燕诗》,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心与物竞”的内心表白,是善良的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明哲保身的思想表现。他不是向李林甫乞怜,而是在设想:“鹰隼们”大概不会再节外生枝,再“搅是搅非”了吧!这首诗透露出张九龄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在张九龄的其他诗作亦时有表现。如:
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复,修干欲何施?
高冈地复迥,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
《杂诗·其一》
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
鸿鹄虽自远,哀音非所求。贵人弃疵贱,下士尝殷忧。
《感遇诗·其六》
张九龄的这种思想和心态具有典型意义。长期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通过个人奋斗,能达到张九龄那样高的地位者,乃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客家人乃是南迁移民,虽然可向中原地区追溯祖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难以得到支持,没有什么靠山。张九龄在政治上感到势单力薄,在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政治斗争后,会产生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不愿与亦不屑与小人计较的想法,是毫不足怪的。《咏燕》诗体现了张九龄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而这种个人的品格又因为张九龄的地位和影响,而成为后来许多客家人的群体性格:不忘贫贱,不怕艰苦,终日乾乾,善良天真,洁身自好,而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鹰隼”又只是徒唤奈何,作“莫相猜”的慨叹,这不能不说是软弱性的一种表现。这恐怕不必为贤者讳,亦不必为我们客家人讳。
文学是人们心灵的镜子。广东客家文学不少作品中的这种思想和情绪,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此有关。张九龄在思想、心理方面对广东客家文学的影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