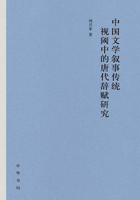
本书说明
本书的写作缘起,要追溯到十多年前。2007年春,我负笈沪上,师从董乃斌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学伊始,先生即把我们几个博士生召集到一起,询问我们今后的学习计划。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陆机与六朝文学之关联,对汉魏六朝的赋有过一番摸索,并由此对赋这种文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此想法与先生交流后,先生建议我不妨将眼界放宽些,看看唐代赋的创作情况究竟如何。对《文苑英华》《全唐文》中的唐赋作品作一番爬梳后,我认识到李梦阳等人关于“唐无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唐不仅有赋,且呈现出繁荣之景象。因此,以唐赋为研究对象,应该大有可为。我本拟以《唐代赋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企图对唐代赋体文学的发展历史与演变规律作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此论题牵涉面太广,头绪太繁,在有限的时间内驾驭起来存在很大的难度,或许需要寻找一个相对小些的切入口了。
在此期间,董先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我们几个博士生也有幸得以参与其中。这个课题是针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而提出的。董先生的观点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与西方的、现代的所谓“纯文学”有所不同。中国古人的文学观是一种泛文学观,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也比现在通行的文学概念要宽大。古代某些文体若以纯文学定义衡量可能不符文学标准,但实际上它们却存在多少不等的文学性,古人在创作它们的时候往往既出于实用,又考虑到结构和修辞等文学要求,所以中国文学史不应该无视它们、排斥它们。中国自古文史一家,诗中有史,史中有文。因此中国文学史从源头起就存在着抒情、叙事两大传统。也可以说,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就是同源共生、互动互促的。董先生主张用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来贯穿中国文学史,以取代抒情传统唯一、独尊的观点。此观点看似回归常识,却显示出先生宏通的历史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本由旅美学者陈世骧明确倡导(其原话为“中国文学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曾引起港台学者的热烈响应。我们课题组经过多次交流与探讨,认识逐渐趋于统一与明朗: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抒情传统说”的确存在偏颇与局限,它并不是唯一、独尊的传统,中国文学史确实存在一个与之共生并行、互促互挽的叙事传统。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呼吁加强叙事传统的研究,进而对中国文学史的面貌作重新认识与描述。当我们从叙事视角审视中国文学史时,小说戏曲文体自应受到重视,但若把范围仅限于此,又显然不够,因为叙事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表达方式,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并不一定只限于西方叙事学所侧重和强调的“讲有因果关系的故事”。叙事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样式都与“事”有着不解之缘,文学与“事”之关系可远可近,可密可疏,几乎达到了无“事”不文的境地。诗词赋等非叙事性文体,甚至那些章表奏议之类应用性文章,因其蕴含着程度不等的叙事性,也应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叙事传统的研究范围之中。
受董先生思想的启发,我于是将唐赋设定在中国文学抒叙两大传统同源共生、互动互渗的视阈下进行观照。赋是中国文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它既是诗体的流衍,又是楚辞的后裔。赋的外形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是句式自由而繁多的文章,它的内质却是诗化的。一方面,因为赋往往要详细逼真地描摹外在客观世界,所以其自身自然而且必然地具有丰富的叙事特性;另一方面,赋的诗化内质又使其叙事带有作者浓郁的情感色彩。辞赋正不妨被视为中国文学最典型的抒叙结合的文体。如果从中国文学史抒叙两大传统的角度考察赋体文学,那么,就基因而言,赋似乎应该属于抒情传统,以前的研究者也多如是看。然而赋者古诗之流,古诗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叙事特性,这就使赋与叙事传统早就有着极深的瓜葛,辞赋文体对整个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能忽视的作用。以唐赋为对象更详尽地阐述赋的叙事特征,把唐赋放在中国文学史存在着叙事、抒情两大传统的理论预设下进行审视,我们明白,赋这种文体既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又可以说是这一传统得以壮大成熟的有功之臣。以上就是我以《唐赋叙事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所在。
我的博士论文篇幅比较长,董先生选了其中的一章,作了调整修改,放到他承担的国家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去。这个最终成果即以《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为书名被收入2011年度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华书局出版。
2010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并成为由傅修延老师领衔的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的一员。傅老师是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先行者,在构建中国自身的叙事谱系方面有非常自觉的意识与大胆的探索。中国叙事学研究团队有非常浓郁的学术氛围,体现之一即是“读书会”,时间固定为每周四晚上,十余年坚持不断。读书会多围绕与叙事学相关的论著进行学习交流。以此为契机,一方面,我较为系统地研读了西方叙事学著作,对西方叙事学理论有了比较全面的掌握,并认识到西方叙事学尽管是以小说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其中的某些理论亦可试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另一方面,大量阅读中国古代的文论著作,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传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其间,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并获批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视阈中的唐代辞赋研究》,经过近六年时间的研究,项目于2019年6月顺利结题,本书即是该项目结题的最终成果。与博士论文相比,本书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文本的阅读分析、理论的总结提升、视野的拓宽增进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其突出者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研究观点的进一步明确。首先,“叙事”概念更为明晰,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叙事传统中进行考辨。“叙事”一词在中国出现较早,它有依序行事、展现动态的进展过程、排比阐释、博物知类等语义;同时,我们所谓的“叙事”,主要着眼于话语层面而非文体层面,即将叙事作为作品话语的作用、功能,这一点与西方颇异其趣。西方所谓叙事,主要叙述一个有因有果、首尾相合的故事,强调矛盾冲突、结构、情节、人物个性的描写,凸显时间性与再现性。中国所叙之“事”,有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这主要体现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作品中,它要求较细致地描绘所述之事,展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有时描述与作品相关的事态、事象、事境、事由、事脉等,注重截取事件片段、场景以叙述。其次,对中国文学不仅存在悠久漫长的抒情传统,同样也存在悠远深厚的叙事传统的认识更为明确与深入。董乃斌、傅修延两位先生分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2015年)、《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2016年),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这种认识。董先生以历来被视为抒情传统载体的诗歌为对象,着力探索其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忽视的叙事表现,并充分论述其与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关系,进而更准确地判断其在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傅先生打破了西方人擅于叙事、中国人长于抒情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认为中国人不仅长于抒情,也擅于叙事,并对中西叙事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的叙事传统,也有助于国人讲好中国故事。正是在中国文学史存在着叙事、抒情两大传统的理论视阈下对唐赋进行审视,我们发现,唐赋在虚拟人物、假设情事、铺排叙述、叙事语调、叙事形态、叙事格局等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研究内容的大幅度增加。如第二章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咏史赋、寓言赋、纪游赋、当代传闻赋、游艺赋、节日赋、记梦赋等不同题材赋作的叙事性,以觇唐代赋家在题材选择上鲜明的叙事倾向。第三章第二节“律赋叙事能力的突破”中“概叙”“事境”部分,是在大量翻检古代文论与深入阅读赋体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总结阐述的。第四章第三节注意到唐赋卒章显志的现象频见,并借用西方“副文本”“介入性叙述者”等相关理论,分析这种叙事范式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影响;第四节的写作深受傅修延先生关于听觉叙事理论的影响,傅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听觉叙事研究》,通过阐扬听觉的艺术价值,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其主要任务在于“重听”经典,倾听其中对声音事件的摹写与想象。从听觉角度出发,考察唐赋与听觉叙事之间的密切关联,如俗赋的基于口头韵诵传播的听觉叙事、文人赋对外部世界声音的传神描摹等,由此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在辞赋创作中除了从视觉上对所述对象的形貌、情态进行铺排式描叙从而呈现出图像叙事的特征外,也注重从听觉角度为辞赋叙事打开全新视界。第五节着重阐论唐赋叙事存在“事在赋内”与“事在赋外”两种情况,说明唐代赋家在表达情感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事”在背后作为支撑。分析掌握这或显或隐之“事”,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的情意有着极大的帮助。第六章第六节考察敦煌俗赋与变文的关联,作为讲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在叙事的繁复细化、语言的通俗浅显、表达的程式化等方面呈现出趋同性的倾向,而这些正是口头传统的基本内涵,由此也印证了唐人(包括赋家)在讲述故事时,不仅有典雅的文人叙事的一面,同时也保留着活泼的民间叙事的色彩。新增附录“中国历代赋学叙事观之资料汇编”,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赋与叙事之关联问题有更为直观明晰之了解。
博士毕业十余年,教学与科研并进,除了在此课题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外,我还承担了傅修延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之子课题《中西诗歌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的研究任务,在这过程中,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交融互渗的问题及辞赋、诗歌等文体与这两大传统的关系问题,时时在我心头萦绕,其间既有苦思的艰辛,亦有收获的欢愉。不管怎样,关于唐赋叙事传统的研究要暂告一段落了,但对诗歌叙事传统的研究仍在路途上,这或许就是“叙事”的魅力所在,“传统”的影响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