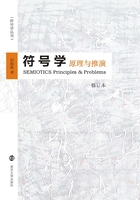
7.文本
符号很少会单独出现,一般总是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如果这样的符号组成一个“合一的表意单元”,就可以称为“文本”。先前学界常认为“文本”这个术语等同于“讲述”(discourse,或译“语篇”)(26),此术语无论中西文,都过于倾向于语言,不适合作为所有符号组合的通称。信息论中则把符号结合起来的整体称为“超符号”(super-sign),此术语意义不明确,各人用法不同。近年“超符号”术语渐渐只用于难以分解的符号组合,例如图像。(27)而“文本”一词,渐渐作为“符号组合”意义通用。
此词西文text原意是“编织品”(something woven)。(28)中文定译“文本”极不合适,“文字”意味太浓,而符号文本却可以是任何符号编织组成。
在符号学史上,对文本概念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两个符号学派别:一是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斯图加特学派”,这派的领军人班斯(Max Bense)早在1962年就把这一批德国符号学家的贡献编成文集《文本理论》;二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他们把文本看做符号与文化联系的最主要方式,洛特曼在1970年出版了《艺术文本结构》,其中有好几篇文章着重讨论文本。由于当代符号学界的共同努力,符号学的分析单元,重点从单独符号转向符号文本。
在符号学中,“文本”一词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最窄的意义,与中文的“文本”相近,指的是文字文本。文本不是其物质存在,因此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是同一“文本”。(29)文字文本有个空间和语义的边框,因此不包括注解、标题、序言、出版信息。此意义至今在使用,巴尔特与格雷马斯研究的“文本”基本上是最窄概念,即文字文本。(30)巴尔特问:“在图像之中、之下、周围是否总有文本(texte)?”(31)他指的是图像的文字说明。因此,必须根据上下文判别“文本”何义。
比较宽的定义,是指任何符号表意组合,不管是印刷的、写作的、编辑出来的文化产品,从手稿档案,到唱片、绘画、乐谱、电影、化学公式,等等。符号学中往往使用宽定义。提倡文本符号学的俄国符号学派,从巴赫金到洛特曼,到乌斯宾斯基,都是持最宽定义。巴赫金说:“文本是直接的现实(思维和经验的现实),在文本中,思维与规律可以独立地构成。没有文本,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32)塔尔图学派的洛特曼的定义最为简明:“文本”就是“整体符号”(integral sign);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更宽的定义,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33)因此,任何携带意义等待解释的都是文本。
本书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
1.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本书的这个定义虽然短,实际上牵涉六个因素: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此处暂时无法把每一点都在学理上讲清楚,本书会一点点处理,最后予以总结。
文本要如何组成才能有意义,实际上取决于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看到的文本,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的存在,而是意义关系。文本使符号表意跨越时间空间的间隔,成为一个过程。反过来说,通过表意过程,此符号组合就获得了“文本性”(textuality)。
鲍德朗德认为,“文本性”包括以下七种品质:结构上的整合性;概念上的一贯性;发出的意图性;接收的“可接受性”;解释的情境性;文化的文本间性;文本本身的信息性。(34)这个“七性质”说法把符号学所有要处理的问题一网打尽了,无非是说,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独的符号,而是符号文本。
上述标准的头一条“结构上的整合性”,是后面六条的保证。但后面的六条是否就能保证第一条呢?艾柯就提出过“伪组合”理论。某些“文本”的组合缺乏“整合性”,各部分之间关系不明。他举的例子是蒙德里安的画和勋伯格的十二音阶音乐。实际上,很多符号组合都让人怀疑是否有“整合性”:长轴山水切出一块难道不能形成单独文本?电影剪辑不是可以剪出好几种版本?裁剪后照片比原幅照片整合性更多还是更少?七十回《水浒传》是否真不如一百二十回“全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实验戏剧的一种“发生”戏剧(Happenings),没有预定情节,演到哪里算哪里,无始无终,有意取消文本的“整合性”。(35)
笔者认为,“文本性”是接收者对符号表意的一种构筑态度,接收者在解释意义组合时,必须考虑发送者的意图(例如画家的画框范围),也可考虑文化对体裁的规定性(例如绝句应当只有四句),但是最后他的解释需要一个整体:文本的构成并不取决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接收方式。例如,地理上的一整条线路构成此人上路时考虑的文本,某个路标与周围的某些路况构成一个文本;如果他坚持读到底,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文本,如果他中止阅读的话,一个章节也构成一个文本。文本作为符号组合,实际上是文本形态与解释“协调”的结果。
这看来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理解,但实际上关系重大,会导致很多理论困难。例如“有机论”问题:文本的组合究竟有多紧密,能使文本各部分服务于整体?本书会在第四章讨论“有机论”问题。其次是与“语境”和“伴随信息”的关系:究竟什么地方应当作为文本的边界,边界外的各种因素(例如标题、题词、注解)是否算文本的一部分?本书会在第六章仔细讨论“伴随文本”与“全文本”问题。
因此,符号文本是接收者对符号组合进行“文本化”(textualization)的结果,而文本化是符号化的必要方式。文本自身的结构是否“完整”只有参照意义,文本的组合关系,是解释出来的。一个交通警察、一个抢银行的强盗、一个看风景的行人,会在同一个街景中找出不同的组合,因为他们需要追求不同的意义。本书上一节说到“片面化”,文本化就是片面化的结合。接收者不仅挑拣符号的各种可感知方面,而且挑拣感知的成分。一个足球运动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己方与对方各个队员的相互位置与运动速度,并且迅速判断这个“文本”的意义。体育界行话,称此人善于“读”比赛,此语很符合符号学。显然,一个后卫与一个前锋,必须对同一个局面读出很不同的“文本”。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卷《老子王弼注》论卷,对文本问题理解深刻。此书讨论老子“数舆乃无舆”说,认为“即庄之‘指马不得马’”。钱又引《那先比丘经》:“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指出:“不持分散眢论,可以得一”;“正持分散眢论,可以破‘聚’”。(36)“分散眢论”是钱锺书对拉丁文Fallacia Divisionis(分解谬见)的翻译。整体并不是部分的聚加:一个个数车幅,看不出车轮;一条条指出马腿,指出的并不是马。
那么,有没有不与其他符号组合,单独构成文本的“独立”符号?一个交通信号,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命令,“一叶知秋”;有些符号似乎没有明显的组合因素,例如“瑞雪兆丰”、“当头棒喝”。我们略一仔细考查,就会发现完全孤立的符号,不可能表达意义。要表达意义,符号必然形成组合:一个交通灯必然与其他信号(例如路口的位置、信号灯的架子)组合成交通信号;一个微笑的嘴唇必然与面容的其他部分组合成“满脸堆笑”或“皮笑肉不笑”;一个手势必然与脸部身姿表情相结合为一个决绝的命令或一个临终请求;“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显然迦叶看到的不只是花,而是佛祖、花、拈花手势的组合。
最后,“大局面”符号表意是一种超大符号文本。整个文化场景,甚至整个历史阶段的意义行为,被当做一个文本。本书最后几章将进入各种“大局面文本”,例如文化演变、历史进程等。
(1) 关于无语在儿童教育学上的符号意义,请参见Jean Umiker-Sebeok,“Silence Is Golden?The Changing Role of Non-Talk in Preschool Conversations”,in ed,Mary Ritchie Key,The Relation Between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The Hague:Mouton,pp.295-314。
(2) Thomas Sebeok,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18.
(3) 韦世林:《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微妙关系初探》,《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2—47页。
(4) 欲言还止(aposiopesis)旧译“脱绝”。例如“滚,不然……”不说,意思反而充分表达。2011年8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语词与图像研究所举行国际会议,专门讨论了此课题。
(5) 钱锺书:《管锥编》,《周易正义》一二,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卷一,第55页。
(6) Brian Rotman,Signifying Nothing:the Semiotics of Zero,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
(7)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76,p.55.
(8)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此词组在该书中译成“符号-功能体”。巴尔特讨论的,是符号载体的“使用功能”。
(9) “不存在符号,只有符号功能。符号这一概念是日常语言的虚构物,其位置应当由符号功能取而代之。”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34.
(10)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6-17.
(11) 池上嘉彦在《符号学入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中说,买了钢琴或百科全书而不用,放在那里做样子,是购买了符号的外延意义,而不是其内涵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使用了它们的实用符号意义(排场),而不是它们的艺术符号意义。
(12)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31.
(13) Jan Mukarovsky,Structure,Sign and Fun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56.
(14) 参见Robert S. Corrington,Nature's Self:Our Journey from Origin to Spirit,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6。
(15) Peter Bugajilev,“Signs in Dress”,in(eds)L. Matejka and I.R. Titunik,Semiotics of Art,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9,p.14.
(16)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
(17) 同上,第295页。
(18)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31.
(19)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
(20) 谢冬冰:《表现性的符号形式:卡西尔-朗格美学的一种解读》(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把这一派的符号学称作“表现性的”,应当说是很准确的,卡西尔与朗格很强调符号的情感表现。
(21)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308.
(22)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28.
(23) Charles Morris,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4.
(24) 卡罗琳·凯奇:《杂志封面女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25) 这是2007届博士生苗艳在符号学作业中举的例子,特此致谢。
(26) Janos S. Petofi,“Text,Discourse”,in(ed)Thomas A. Sebeok,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86,pp.1180-1187.
(27) “超符号”这个词被许多理论家用作别的意义,例如“超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巨大的表意”或“不能分成内容单元的符号组合”,见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32。
(28) Yuri Lotman,The Structure of Artistic Tex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6.
(29) Alec McHoul,“Text”,in 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ed)Paul Bouissa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09.
(30) A. J. Greimas & Joseph Courtés,Semiotics and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340.
(31) 罗兰·巴尔特:“图像修辞学”,《语言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8年。在《显义与晦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7页)一书中,此处译为“文字”。
(32) Quoted in Tzvetan 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1,p.17.
(33) “Anything that can be interpreted”,Boris Uspensky,“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s”,in(eds)Jan van der Eng and Mojnir Grygar,Structure of Texts and Semiotic of Culture,The Hague:Mouton,1973,p.6.
(34) Robert de Beaugrande,Text,Discourse and Process,Norwood NJ:Ablex,1980.
(35) Zoltán Szilassy,American Theater of the 1960′s,Carbonda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pp.64-68.
(36) 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一卷,第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