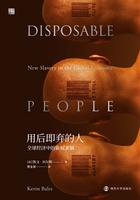
2012年版序言
在本书第一次出版前夕,萨勒玛·明特·萨卢姆(Salma Mint Sa-loum)逃出了奴隶制。她的奴隶状态似乎更像是19世纪的,而不是21世纪的。与“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中的奴隶一样,她穿越荒野来到一条宽阔的河流面前,自由在河对岸等着。但是她要穿过的“约旦河”不是俄亥俄河,而是塞内加尔河,因为萨勒玛在毛里塔尼亚生为奴隶。
跟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一样,萨勒玛逃向自由后不久,便义无反顾地重回危险之中,一个接一个地拯救她的孩子们。在她离开塞内加尔后,她祈祷自己能够在美国找到一处安身之所。正是在辛辛那提,靠近俄亥俄河的两岸,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我五岁就开始工作,过去常常做我母亲做过的事。我清洗盘子并帮助我的母亲,给年幼的孩子洗衣服,为母亲收拾柴火。我为主人工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人的利益。
有时候,我会听到父母谈论主人们。他们会说希望这一切在将来某天会结束。但其实他们并不想要这一切都结束,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想要一切结束,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去哪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够投奔。他们想要却不能离开,不,并不。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离开,因为即使他们逃走,主人们也会把他们抓回来。
我的父母从未提过逃亡,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这件事。我是唯一一个想过如何逃走的。在我30岁时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有一天,我逃走了,但被他们抓了回来。
我第一次逃走那天,非常疲惫。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我一定要逃走,一定要这么做。前一天,他们在毒打我的母亲,只是因为她做的饭咸了。(我逃走那天)是在深夜,在完成所有工作后很晚很晚的夜里。我对母亲什么都没说。
因为迷路,萨勒玛被邻居抓到并送回给她的主人。她交代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来后,我手脚被捆,有一个人负责打我。在那之后,我很长时间不会说话。他们也不让我吃任何东西。主人告诉他们,不要给她任何东西吃。我不记得究竟有多久,可能是四天。我记得我的母亲常常深夜偷一些东西带给我。我待在他们捆奴隶的地方,他们在打你之前会把你放在这里。他们在沙地上立起一块钢,在沙地上立起一块非常坚硬的钢,就像钢柱,然后把我的手脚绑在钢柱上毒打我,接着把我扔在那里。母亲时常会偷一点东西过来,但并不是一直如此。她会过来用手喂一些粗麦粉到我嘴里。
他们拿着自制的鞭打奴隶的工具——一个缠着皮革的木棍——打我。他们将皮革切成条,然后缠到木棍上,一个木棍上会缠很多条,每条可能有12英尺长。他们会拿着木棍,用皮鞭抽打我们。
当我被绑在那里时,我就想,如果这一次不死的话,我还会重来一次,再次逃走。我知道我一定会的。我始终想的都是这些,他们打完我后,我将会重新来过。我一直在想,如果大难不死,我一定还会逃走。这就是我脑子里所想的一切。
萨勒玛只是20世纪末数百万个隐形的奴隶中的一个,写作本书是一场发现之旅,它找到了这些奴隶,并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融入我们当今的世界的。这场旅行带我见到了萨勒玛和其他的奴隶或前奴隶,在整个过程中我成为担起旧任务的新人:废奴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