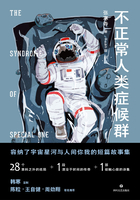
克莱尔小姐,新年快乐
“克莱尔小姐,新年快乐。”
在战地医院醒过来之后,这是闯进克莱尔脑海里的第一句话——未婚夫安迪中士认识她的时候,就是用这句话搭讪的。
护士告诉克莱尔今天是1月3日,她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好像,”克莱尔的声音沙哑,心底升起恐惧,“看不见了。”
护士握着她的左手:“我很抱歉,破片手榴弹的冲击波损伤了您的眼球,医生不得不摘除它们。”
“不!”克莱尔双手乱抓,语带呜咽。她想哭,但发现自己无法哭泣。
护士安慰她说:“医生正在为您准备电子眼球的植入手术。”
记忆支离破碎,克莱尔勉强能够记得,指挥体系的瞬间崩溃导致机械化部队来不及驰援。她当时紧紧跟在安迪身后,一边扶着自己摇来晃去的头盔,一边盯着安迪后背那支上下颠簸的火箭筒。安迪不断喊着口令,指挥其他人寻找掩体,就在这时,一颗手榴弹突然朝他们飞了过来。那一瞬间,克莱尔奋力朝安迪身上撞去……“安迪中士呢?他怎么样了?他受伤了吗?”
“他只受了点轻伤,就在隔壁的病房。”
克莱尔长舒一口气:“太好了,太好了……”身上的知觉渐渐恢复,胸口又痒又痛,“护士小姐,能扶我坐起来吗?”
“好的,”护士抬住克莱尔的腋下,转动病床底部的摇臂,慢慢将她的身体升了起来,“这样可以吗?”
“谢谢你,护士。”克莱尔轻轻触碰了一下蒙在眼睛上的纱布,那儿只是两个空洞。然后,她意识到了什么,“护士,我的右手好像也没有知觉。”
护士迟疑着没有立即回答。
“护士小姐,你还在吗?”
“是这样的,克莱尔小姐,”护士的语气低沉下去,似乎要宣布一个很糟糕的消息,“那颗手榴弹的杀伤力非常大,它不仅破坏了你的眼球,还炸掉了你的右半边身体。”
克莱尔突然感到从自己灵魂深处传来的空虚感,听到周围若有若无的嘲笑声。她伸出左手按在自己本应是右臂的地方——坚硬而冰冷。
“医生为您换上了机械器官,目前运作良好,现在的机械器官很发达,什么都能实现,它们可以——”
“可以什么?!”克莱尔抓住护士的衣角,歇斯底里地咆哮,“是可以让我看起来像马戏团的小丑,还是可以让我去广场上演讲感动那些老太太?”
护士不敢回答:“医生说您的正常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
“出去!你出去!”
克莱尔再也无法入睡。她不知道自己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合上双眼,又或者,半人半机器的自己,还需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时间。她伸缩自己的右手和右腿,只听到轴承运转的声音;她按在自己的胸口,肉体和机械相接的部分,凹凸不平:一边是铿铿有声的金属,一边是爬满疤痕的皮肤。
她觉得自己是个怪物。她甚至庆幸双眼瞎掉了,也就看不到自己丑陋可怕的模样。
“克莱尔……”
是安迪的声音。
“不……你不要过来!”克莱尔拉起被子,将自己盖住。
“克莱尔。”安迪又叫了一声。
“求求你,安迪,”克莱尔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为什么?”
“我很可怕……我很丑……”
克莱尔感觉安迪走到了她床边,他说:“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我的。”
那是三年前的新年。克莱尔第一次到军营为士兵们做体检,安迪最先跑到她面前,说了句“新年快乐”,然后脱掉上衣,露出满身疤痕——难道这能做新年礼物吗?没想到克莱尔脱口而出:“噢,天哪,你好丑。”周围的人都放声大笑,安迪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们算扯平了。”
克莱尔掀开一个被角,伸出右手——又是一阵“咔咔”声:“这样的我,你能接受吗?”
安迪握住她的手,顺着手腕抚摸到手臂,再到肩膀,最后捧住克莱尔的脸庞:“既然我们一样,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克莱尔感到安迪的手冰凉,透出金属的气息。
克莱尔的身体开始出现排异反应。她的肉体部分强烈地厌恶与之相连的机械体,就像克莱尔本人一样,迫切地想把那些电线、金属板、齿轮、螺丝钉统统赶出这具躯壳。
医生为她注射了大量抗排异的药物,同时护士每隔几个小时都要用冰块为她的机械体降温。不然,用医生的话说:“可能会因为过热而烧死你。”
“烧死我吧!”克莱尔大声喊,“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
她无法承受这种矛盾的痛苦,左半边身体频繁地抽搐,难以忍耐的痛痒时刻都在折磨着她;而另一边的机械体时不时爆发出轰鸣,不受控制地捶打床沿;还有严重的幻肢痛。“我的右臂,我的右脚,你们去哪儿了?”克莱尔尖叫,整个医院都听得到她的声音。
“安迪!难道你不痛吗?”
安迪一直很安静,也或许是坚韧的军人品格不允许他表现出来。“我痛的话,就会想起你给我打针的时候,没有比那更痛的了。”
克莱尔被士兵们称作“蹩脚军医”,因为她的打针技术一直饱受诟病。不管是接种疫苗还是打青霉素,针一刺进皮肤,不管是谁都会痛得死去活来。最夸张的时候,大家宁愿在其他军医面前排出几十米的长队,也不愿到克莱尔那里“受刑”。
只有安迪是例外,他每次都找克莱尔,然后因为叫得太大声而被投诉。
“你这个白痴……”克莱尔咬着自己的机械手,发音含混不清。
到了第三天,克莱尔不再配合治疗。
“医生,让我安乐死吧。”克莱尔身上肌肉和机械接合的地方渗出血液,染红了她的衣服。她的机械足将床单刺得到处是洞。
护士按照医生的指示将克莱尔的四肢都固定在床上,防止她自戕,但换来的只是她更多痛苦的呻吟。
安迪坐在床边,按住克莱尔的身体:“我知道你很痛苦,请再忍耐几天,会好起来的。”
克莱尔僵直脖子,似乎想挺起身来咬人:“不,你不懂!你的身体上也有机械,但你根本就不痛!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唯独把这种痛苦降临在我的身上?”
“克莱尔,痛是生命的讯号,说明你的身体还想活下去。这是你告诉我的。”
那确实是她告诉安迪的。他们正式约会之后,安迪第一次去战地医院看望她,还带了一枝玫瑰花。等到安迪走进乱作一团、满是伤员、人人哭喊的病房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朵花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子。克莱尔抱歉道,没有时间陪他,这些伤员都是刚刚才从战场上撤回来的,大部分都是重度烧伤。安迪扔下玫瑰给她帮忙,他健硕的身体在这个拥挤而嘈杂的地方显得格外笨拙。忙碌的间隙,他忍不住问克莱尔:“在这么压抑的地方,听到这么多痛苦的叫喊,你不觉得绝望吗?”
“安迪,痛是生命的讯号,他们在叫喊,说明他们需要我,他们想活下去。”
此刻只剩半副身体的克莱尔拉住安迪的手:“亲爱的,我的身体想活下去,但我不想。你告诉我,我就算活下去,又能怎样?我的身体毁了,我的一半是机器!我凭什么告诉别人我还是以前那个我?你会接受一个半人半机器的妻子吗?你告诉我!”
安迪没有说话,甚至听不到他的呼吸声。
“你怎么不说话?”
“克莱尔,你要知道,”安迪似乎在紧张地措辞,“人和人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外貌,不是因为你有健美的身体、好看的高鼻梁、蓝色的眼睛,就与众不同,而是因为这里,”他碰了碰克莱尔的头,“我希望你继续在我身边,也是因为这里。”
“你是说大脑吗?”克莱尔的声音听起来咬牙切齿。
“不,我是说记忆。”
“记忆?”
“是的。你看不见对吗?”
“明知故问。”
“但你还是能知道在你身边的人是我,因为我有我们俩之间的记忆,全部都有。而且,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拥有这些。对你来说,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原因。所以,你也一样,不管你的身体怎样,哪怕敲起来梆梆响,你也是我的克莱尔。”
这样的状况又持续了两天。每当克莱尔疼痛难忍的时候,安迪就陪着她回忆两个人的浪漫往事——不,对他们来说,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这样一个随时可能生离死别的地方,又如何浪漫得起来?
终于,医生通知他们,已经做好了电子眼植入手术的全部准备。
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克莱尔说:“我马上就要看到我们两个的丑样了。”
“放心吧,亲爱的,我已经把自己和镜子都藏好了。”
花了很长时间,克莱尔的视觉神经才与电子眼完全接合。揭下纱布的第一个小时,她看到的东西都没有色彩并且散乱不堪,无法分辨。
最终,一切在她眼前定形。
她首先看到的是护士,厚嘴唇,双下巴。
然后看到的是医生,光秃秃的头顶,鹰钩鼻。
最后看到一个站在他们身后的机器人。
“那是什么?”克莱尔问。
“他是安迪。”护士回答。
克莱尔疑惑地摇摇头:“不,安迪是我的未婚夫,他是个中士,差不多六英尺高,络腮胡……”
“他就是安迪。”护士再次强调。
“不,”克莱尔有不祥的预感,她觉得自己应该哭,但电子眼没有这样的功能,“我救了他!”
“他救了你。”医生开口了,“手榴弹爆炸前,安迪推开了你。送到医院的时候,你身体的一部分炸没了,但他受的伤更严重,只在病房里坚持了三个小时就死了。”
“你说谎!”
“他临死前希望我们暂时保留他的声音和记忆,我们刚好有闲置的机器人,导入并不麻烦。”
克莱尔看着那个机器人的手,这些天握住自己的就是那只机械手,伏在自己耳边诉说往事的也是那颗铁皮头颅,甚至抱着她残破的身体替她分担痛苦的也是那具钢铁般冰冷的躯壳。
机器人走到克莱尔身前,俯视着她。
“我是半人半机器,都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克莱尔用机械手牵起机器人的手,“你却已经是整个的机器了。”
但我还是能知道在我身边的人是你,因为你有我们俩之间的记忆,全部都有。而且,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拥有这些。
“安迪。”克莱尔轻声喊。
机器人的指示灯闪了一下:“克莱尔。”
“安迪,我们重新认识了。”
“克莱尔小姐,”新年的阳光洒在机器人的外壳上,磨损的漆面微微泛光,“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