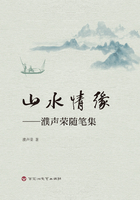
外婆
“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来打捞(劫)了!”
“日本鬼子已经到了何家屋里,快走呀!”
日本鬼子驻扎在排龙山小学,已有七八天了。父母亲同许多人一道,往农庆里广西方向躲日本去了。父亲挑着一担箩筐,一头装的是维弟,一头装的是被窝衣衫,母亲拿的一包零碎。农庆里那边有个亲戚,离我们家有三四十里,就在广西边境上,准备在那里住一段时间。
我当时已有六岁,跟着外公外婆住。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跟着外公外婆就往黄家岭上走,经过锅里塘、码口里,沿着山坡往山上爬。外公挑着一担衣衫被窝,赶着牛,外婆同我在后面跟着。到了黄家岭岭脚,就同外婆藏到外公开掘的园子外围的荆棘蓬下。外公挑着东西继续往岭上爬。
日本鬼子驻扎在排龙山,曾出来打过两次捞,一次走到何家屋里,一次走到码口里就转回去了。估计这次也不会走很远,故我们认为躲到外公园子篱笆刺蓬窝里是安全的。
由于前两次打捞,大家都没有准备,日本鬼子在附近很快抢到猪、牛、鸡鸭和粮食,故很快就回去了。而这次大家事先都有了准备,住在排龙山附近的村民许多都临时出外躲避了,因而这次日本鬼子行进速度非常快,当我们到达岭脚时,他们已到鼎仙观的坡上,不到一顿饭功夫,鬼子就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蹲在刺蓬窝下,他们站在上面。走在前面的是文明公公,是外公的堂叔,他被日本鬼子抓来当挑夫和带路。在他后面是两个日本人,拿着上刺刀的枪,一个个子较高较胖,满脸胡子,一个较矮较瘦较白净。未等他们说话,我主动站起来说话了,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后来,外婆对别人说,我当时说了:“我们没得钱,什么东西都没有。”日本人对我们看了看,当时外婆已50多岁,又用锅底的锅煤把脸上擦的一片黑,显得老态百出,日本人没有说话,押着文明公公继续往前走了。
一段时间,我外婆逢人就说,说我胆子大,见到日本人不怕,还敢说话。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这事。
日本人来到零陵后,各区乡都组织了自卫队,打击骚扰日本兵。在东湘桥还与日本人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我们村里就有一个自卫队员被打死了,遗体抬回来放到彭家小学校门口,我们害怕不敢上去看,站得远远的。
也听说,有的自卫队员半夜到排龙山兵营摸哨,打黑枪,搞得日本兵不得安宁。排龙山到我们这一带都是丘陵地带,但再往南就是五岭山脉的大山,山高沟深林密,只要往大山一跑,日本兵怎么也逮不着。
我的祖父、四祖父、五祖父和我堂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这时都在外地同日本人作战,我的四祖父是在江西与日本兵作战牺牲的,遗体后来运回葬在青山里。
当时,日本兵向南侵略已是强弩之末。故日本兵在排龙山、东湘桥一线待了一个来月之后就退回零陵了。
近日看了《长沙保卫战》电视剧,在国难当头,不甘当亡国奴的先人前辈,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前仆后继,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狼狈败退的场面,真是解气。
我家离外婆家仅半里路,故常去外婆家。当父亲在衡阳邮局工作时,母亲也跟了去,我就住在外婆家。
这个时候,我的外婆叫坝塘里外婆,她姓谢,是农庆里大户人家的女儿,但很小就嫁给我外公了,相当于童养媳。我外公叫黄尚国,家很穷,自己的水田不足一亩,主要靠租别人的田来种,割禾时与田主对半分谷。我外公非常能吃苦耐劳。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在黄家岭山坡较为平缓灌木丛生的地方,花了三年多的时光,开挖出了五六亩山地,周围栽了一圈荆棘刺蓬,形成一个园。据外婆说,除了插田割禾忙几亩水田之事,一年到头都在山上开荒,光篼子锄头就挖坏了五六把,吃住都在岭上。
我们那儿务农的锄头,除一般常用的锄头外,还有一种较宽较薄较轻用于铲草皮的锄头,还有一种用来挖树篼和开荒的锄头。这种锄头的出刃有一尺多长,较厚较窄,非常的重,小孩一般拿不动。
外公开荒出来的山地园子,也是我小时经常跟去劳作和玩耍的地方。
我还有一个外婆,在里洞龙家,外公姓龙,外婆姓什么就不知道了。我母亲是龙家外婆生的。龙家外公重男轻女,生了第二个女儿后就决定给人。恰巧我黄家外公养鸭子,一路赶养到里洞龙家,认识了龙家外公。黄家外婆生了两个孩子都未带大,夭折了,就想抱养一个孩子,借人家的福气而给自己带来好运。因此不满一个月的母亲——龙满秀,就被黄家外婆抚养。因此,我就有了两个外婆,龙家外婆和黄家外婆。
黄家外婆住坝塘里,离我家约半里。因而,常到外婆家,总能得到好吃的。割禾季节,外公顺道抓到一些麻怪(青蛙)或鱼仔,这些都是吃饭的好菜,做鱼或青蛙一般要放腌的酸辣椒,生姜蒜苗,往往从菜园摘一些紫苏叶,一块和炒,味道好极了!俗话说“鱼仔好下饭,顶锅都刮烂”,言下之意,连饭的锅巴都铲来吃了。另外,来村子卖麦芽糖的(我们叫白糖)可以用打下的新谷换,一升谷子可以换到一斤糖。外婆舍不得吃,总把麦芽糖放到下面装有生石灰的缸瓮里,生石灰上面垫一张草纸,糖放在草纸上。因生石灰吸水气,放几天糖或饼干之类的点心,可以变得干脆,不黏手,可以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来吃。
冬春季节去外婆家,最常吃到的是烤红薯。我们那儿做饭烧柴火,就是山岭上砍来的不成材的灌木杂树或茅草,燃烧后的木炭灰,把红薯埋在里面,一两个小时后,就成香甜软糯的烤红薯了,特别是冬季挂在屋梁上风干的红薯,特别的甜。
秋收后,外婆把红薯南瓜做一些红薯干、南瓜干,还做一些饼,上面洒一些芝麻,放到冬春时节,或炸、或烤、或蒸,都是非常的美味。
有时到外婆家,实在没糖没点心,也没有红薯可吃,外婆会给你一根黄瓜,或削一块萝卜给你。有时实在拿不出什么,她也会从腌菜坛里夹一把干豆角一根酸黄瓜给你。
外婆是腌菜的能手,各种蔬菜都能腌,即使有时没钱买盐,她也能把菜腌出来还不坏。我还吃过年成好时,过年腌的猪头肉、猪下水,以及烘制的腊鱼、腊肉等各类荤腥菜。这些东西往往留到阳春三月农忙时节来吃。
外婆家菜园较小,大宗菜都栽在黄家岭上的园子里,如南瓜、冬瓜、豆角之类都在岭上。外婆家没有果园。但龙家外婆的山地很宽,屋前屋后的菜园果园都很大。外婆家里橙子、柚子树都很多,结的柚子都很甜。秋冬季节去外婆家,水果随你拿,只要你拿得动。外婆家屋外生的两种树,给我印象深刻,一是桂花树,每年中秋节时分,满山飘香。外婆往往会摘一些桂花,用白糖泡在坛子里,待到过年吃糍巴或端午吃粽子时,人们早已忘记这些桂花糖,才感到这种美味的可贵。前些年回家见到荣华表侄,问及屋后还有桂花树没,他说还有,去年给城里卖了一棵,得了一万多元。什么时候我再能闻到那十里桂花香!一是椿树,种在果园的四周,椿树长得笔直,已有十来米高,是盖房作梁的上等木料。我那时很小,外婆对我说:“宝崽,你将来长大发财盖房时,砍两棵去作梁。”
发财盖房那毕竟是遥远的事。但那次随母亲去外婆家,回来时却扛了一根寿竹,有五六米长,放在我屋天井木架上,用来晾晒衣服。当我从长沙读书毕业,要去陕西工作时,那根竹杆还一直在那里用着。
我们家乡竹子种类甚多,我能叫得上名字的就有十来种。
一般在屋前或屋后栽有一大丛竹子,我们叫它吊竹或棉竹,云贵一带叫它凤尾竹。长到一定高度时它的头会垂下来,长得不够高也不大,用处也不大,常用来剖开捆挷东西。
楠竹,也叫毛竹,是竹子中最大的一种,竹径可以长到20公分,高达十余米,用途最广。一般电影电视片中都可见到,可做建材,可作各种家具,各种工艺品。竹笋无论是冬笋还是春笋都是山珍美味。
寿竹,它的特点是长得较高,竹径不大,一般不超过十公分,但匀称,不像毛竹首尾直径差别较大,故用做晒衣的竹杆最好不过。它也可用来制作各种用具。
慧竹,矮小且竹径不大,而叶子很大,常摘它的叶子包粽子用。
此外,还有翠竹、紫竹、斑竹等等,这些都不大,竹径一两公分,用途不大,多用来做豆角、扁豆、白茹、丝瓜等瓜菜的竹架。
紫竹有时被男人们用来做吸烟的烟杆,做出来还很漂亮。
翠竹在大山岭上长得较多,一般春天发新笋时,去扯来做菜吃。把笋壳剥掉,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晒成笋干,与腊肉或菌子炒来吃,味道鲜美极了!
斑竹其貌不扬,但人们往往对它赋予感情色彩。毛泽东写的七律:“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说的我家乡的斑竹和凄美的传说故事。舜帝葬在故乡的九嶷山上,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因寻找舜帝,从中原来到九嶷,想要找到舜帝的陵墓,但最终没有找到。在返回途中,双双投水自尽于洞庭湖。为了纪念她们,人们将舜陵改称零陵。这是零陵来源的另一个版本。
母亲去世时,我不到九岁。她是得肺病而亡。送母亲安葬,我没有哭,没有感到多少悲伤,原因之一是感到母亲对我太严了,缺少关爱。当时,外婆在送丧时哭道:“德根不哭你啊,将来哭的日子没眼泪!”(意思是将来要哭到把眼泪哭干,有他哭的。)
外婆常对人说,我德根命苦啊,六岁时他母亲就叫他跟她去砍柴,还要挑两个煮粑粑(两小捆柴)。我说她,牙仔还小,还没长起来。他母亲说,从小不吃苦,长大没出息。
我十一二岁就当大人出工,插田、割禾、犁田犁地、烧石灰砍楂刺,我都会做,但毕竟人小力气单薄。尤其夏季割禾抢收抢种时节,早晨天麻麻亮就要起来,天黑才回家吃饭,中午送饭吃,不能休息。要连续半个多月,有时累到连路都走不动,饭也不想吃。这个时候,外婆是我的救命菩萨,有时晌午时候,实在累得不行,就在田里直接跑到外婆家。外婆一见我就会说:“宝崽,在床上睏一下!”一躺下去,就不知人事了。这时,外婆会打盆水,拿洗澡帕沾上水,帮我把身上、脚上的泥巴擦去,把我的脚也放到床上,很舒服地睡一觉。同时,外婆会设法通知外公,我不去田里了,由外公来收尾了。
共和国成立时,我们那里搞土改,我家划为贫农,外公家为雇农。当时,田地统计时,人均稻田1.5亩,旱地三分,山地水塘没有分,还是各大姓家族共有。可以说是鱼米之乡,但就是一年忙到底,还是吃不饱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想不通,因为土改了,有了田和地,没有人剥削我们了,为什么反而不如过去了。
随着年龄长大和外出读书、工作,才知道这种没有饭吃的苦日子,完全是人为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农村开始统购统销。本来是农民收割后,留够自己吃的再“卖余粮”,根据自己情况,有多少余粮,就卖多少。但当时的农村干部为了争当先进,强迫大家多卖,直到搞得各家把谷子卖光,“放下镰刀没饭吃”,吃杂粮,瓜菜代饭,是50年代的普遍现象。60年代则又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当时选择农村干部的标准是“谁最穷”。家中没有一分田,靠给别人打工,甚至乞讨的农民选拔来当村乡干部,一般都是文盲。他们有两大特点:听上面的话,不管对与错,都坚决服从;第二,斗地主狠,对不同意见则无情打击。时间一长,群众难免要反对,不服气,不听话。我们村里有四大姓:濮、彭、黄、宋。除了宋姓家族外,其他三姓都是既有地主富农,也有贫雇农。宗族势力逐渐渗透至各项工作中,平均、对等体现在各项工作中。宋姓家族人员成为干部的最佳人选。历史上的恩怨,犬牙交错地纠缠在各个氏族中。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回家听说这样一件事。在我们邻县道县,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全部杀掉,甚至对其子弟也要杀掉,说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此股歪风传到了零陵,也刮到我们村里。造反派连续开了两天会,研究杀人名单,杀哪些人,会上吵得非常凶,造反者都主张不杀本姓地主,而杀其他姓的地主,而当名单定下后,先杀谁,由谁杀,又吵得不可开交。好在中央派47军到了道县和我们周围几个县,才制止了这场杀戮。我们濮姓家族有两户地主,就是我的大祖父和六祖父两家。事后,听我们濮姓家族几位贫农说,不是他们顶着,他们早被杀了。就当时来说,我大祖父和六祖父早已去世,而他们的子孙何罪之有?
我们濮家同彭、黄、宋三姓家族,都有联姻亲戚关系,而彭与黄、黄与宋都有世代恩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架斗殴现象。
在我们家乡,宗族观念特浓,出了是非,打起架来,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帮同姓家族成为惯例。村干部的选择也是如此,不问干部人品能力如何,而是看对我们家族是否有利。
冬天,红薯、乔麦是必吃的主粮。红薯一般有两种吃法,一是红薯挖回家后,把它切成丝晒干,做米饭时放到饭上面蒸着吃;二是把红薯蒸着吃,或切成块放在米饭上蒸着吃。吃饭时,大家要先吃一碗红薯,然后再吃米饭。红薯吃多了往往胃里反酸水。
每当这个时候,外婆对我说:“宝崽,你吃饭,莫吃红薯。灶里给你烧了两个红薯,等下熟了,你再吃。”
红薯是高产作物,当时一亩地可产几千斤。保管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在房后或屋里挖有地窖,把红薯放在窖里保存;一种是用土灰把红薯埋起来,埋的量较少;还有一种是带有红薯藤子的红薯,把它挂到屋梁或柱子上。前一种是大量的,最后一种是很少量的。但这种挂起来的红薯,经风干后,很甜,最好吃,特别是烧着吃,或烤着吃,外面有一层糖,是我们细伢子最喜欢吃的。
把红薯放在地窖里,也发生过灾难。因为地窖密闭,且红薯放在里面常释放出二氧化碳,如打开地窖通风不够,人下到里面,常中毒而亡。
外婆把红薯常做成两种小吃:一是把红薯蒸熟,退皮,把红薯压成10至20厘米薄饼,上面洒些芝麻,晒干,做成红薯渍菜,又甜又香。可以当下吃,也可以贮藏起来,放到来年吃,冬天如用炭火烤一下,又糯又香,更好吃;二是把红薯切成条,晒干,吃的时候,用河中粗砂砾拌在一起炒,有如现在街上炒板栗,吃起来又脆又香。用红薯酿酒,也是农村常用的方法,特别是有点酒瘾的农民。在冬天农闲时节,炒点小菜,爆点花生米,喝两盅,也是非常惬意的生活。但六七十年代红薯成了宝贵的粮食,不敢随便拿来做酒消遣了。
我之所以能出去读书,主要是外婆坚持的结果。她常对人说,要送德根读书,他母亲死得早,他一点点大就做事,送他读书,吃碗轻巧饭。她对我外公说:“去跟濮治说,德根要读书,他那一点田,我们帮忙做了就是了。”
父亲一直想让我留在家里种田,作为家中主要劳力。他常对我说,我们家祖辈,高祖父曾祖父都是种田的,以此教育我,让我安心种田。外婆见到我奶奶时也说:“亲家母,德根太小,农村太苦,还是要送他去读书啊!”后来,我奶奶也对我父亲说,送我去读书。这样我才离开农村。
外公当时老了,生产队的事做不了,就给生产队放牛。因为吃不饱饭,他利用放牛机会,常在山上采一些野菜野果拿回来吃,或用竹刷子打一些“土地麻怪”拿回来煮着吃。所谓“土地麻怪”就是一种小青蛙,拇指大,褐色,过去常打来喂鸡鸭。当时,既无油,又无调料,煮着非常难吃,外婆和舅娘不吃。中了毒了,得了病了,自己扯点草药吃。外公会给牛看病,十里八里乡村都知道,给牛看病吃的药都是外公亲自采挖的。50年代初,乡政府还给外公配了一个女助手,陪他一起出外给牛治病。我小时候在外婆家,看到过有人来外公家拿药,一般是一剂药一升米。我们那儿一升米约两市斤重,应该说,还是很便宜的。
外公为人耿直,劳苦一生,不愿求人。外公从生病到去世,时间很短,不声不响就走了。维弟说,与其说外公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如果有饱饭吃,外公死不了!
1966年春节我回家时,外公已去世。我对外婆说,外公生病和去世怎么不告诉我。外婆说:“宝崽,你外公常说,你们在外面也很不容易,挣不了几个钱,花销很大的。”“至今连老婆都未讨,家也没成。你外公不想打扰你,叫我不要告诉你。你知道了,你肯定要回来。这么远,路费要很多啊!”“我们也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说死就死了啊!”
外婆还告诉我,外公也曾为我的婚事操心。他对外婆说,给顺生说说,把他的妹妹说给德根。顺生是我表弟,他妹妹比我要小七八岁。顺生没有答应,说我年龄大又说我太远了。外公知道后说:“他还不愿意,我德根哪点配不上她?”为婚姻之事,外婆每次见我就说。她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德根老母亲死得早,现在谁也不关心他的婚姻,可怜啊!”
外婆出生在农庆里谢姓大户人家,离我们家有三四十里。谢家重男轻女。外婆很小就给了外公做童养媳。外婆是典型的农村家庭妇女。因为外公家穷,自己只有几分田,主要靠租种别人的田生活,外公年轻时,在黄家岭脚开荒了五六亩山地。以后,我家的两亩水田,父母在衡阳工作,无人耕种也交给了外公来种。这样,外公家的生活过得还算可以。外婆生育了两个子女,都半途夭折,以后抱养了我母亲,但还是没有生育,后来过继我外公的弟弟(我叫小外公)的儿子——名林舅父做儿子。名林舅父的老婆是讨到我濮家屋里的姑娘,按辈分我应叫姑姑。我们那儿把姑姑、叔叔叫满满,所以,对她我有时叫舅娘,有时叫满满。
外婆主持家务,主要是种菜、养猪,年轻时候协助外公开荒种地,年岁大了后,一般不出外做农活。据外婆说,是外公不让她出去干农活,外公说她干的那点活,外公少休息一下,就干出来了。农村最忙的时候是两项农活,插田与割禾。插田是时间紧,也就是三五天,最多也就七八天,要把秧插下去,否则误了农时。割禾则要十天半月。稻子熟了要尽快收割回来,否则遇到连阴雨天气,谷子会生芽,会毁了一年的收成,那是要命的事。所以割禾时节,我们要天不亮起床出工,天黑许久才回家吃饭。外婆中午送饭和茶水到田里,收工时外婆常去田里接我们,帮助拿一些轻的东西回家。晚饭早已做好,并烧好热水和茶水,男人们则在井眼里(泉水井)或水塘里洗澡,女人怕凉,则要热水洗澡。
在这段时间,外婆会做许多好吃的,荤腥是少不了的。肉、鸡、鱼至少每天有一样。不知什么时候烘干的小鱼和小辣椒炒在一起,其味鲜无比,又开胃,又下饭。外婆腌菜腌得好是远近有名的。她还会在冬天腌一些肉菜。肉菜有两种,一是冬天春节前后,自家杀猪留下的猪头肉猪下水,将其卤好后,放上盐,在坛子里腌起来;二是出外参加别人家的红白喜事,吃酒打包回来的肉,外婆会将肉重新改刀、调味,放点生姜和白酒把它腌起来。到农忙时,特别是五黄六月油水少的时节,从坛子里夹出来,放在米饭上蒸好,每人一块,唯独外婆自己没有。这个时候,大家往往眼瞧着外婆,外婆则说:“你们吃呀,多吃点饭,我有的。”
这样的情形,我年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不知出现过多少次。当时不觉得什么,以后似乎习惯了,反而觉得就应该这样。如今回想起来,这种大爱,常使我流泪不止。
外婆同外公一样,一生刚强,有苦自己吃,有难自己扛,不愿求人。但心地善良,她不信佛,也不吃斋,我奶奶信佛吃斋。外婆愿意帮助比她困难的。躲日本时,从衡阳祁阳一带逃难来的农民,她尽力接济他们,粮食、衣服、用具,尽其所能。
从我记事起,我未见外婆与外公吵过架,也未见外婆与别人吵过架、骂过人。外婆说话不多,声音不大。因此,外婆的人缘很好,在黄姓家族中威望较高,说话比外公还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