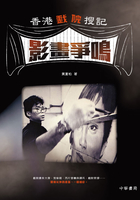
1.1 影畫爭鳴
戲院外牆的喧鬧繽紛
當各片畫板繪畫完畢,便於影片公映前一天黃昏,運送到戲院,掛畫工人把上一期的畫板卸下,再把新的一批逐幅懸上,落畫上畫,入黑後,完整的大牌便在大道上放亮,率先引得附近坊眾圍觀。
楔子
回溯舊文,早於2002年秋季遊歷三藩市後,寫下短文〈Castro〉,淺談當地著名的Castro戲院,投到《明報》副刊「自由談」欄目,於12月8日刊出。若以時間論,那大概是首度撰寫戲院文字。翌年,讀過台灣出版的《陳子福手繪電影海報集》後,又寫下另一短文投到同一欄目,文章於12月29日刊出,內容如下:
當最後一張畫板拉上繫到鐵架上,偌大的電影廣告畫便告完成。天亮後,大道上又是一片煥然一新的景觀,過路人都向電影院這邊投以殷切的目光。
看陳子福的手繪電影海報,便想到那些年在電影院外牆的巨大電影廣告畫。精細描摹的筆法,粗中有細的着色技巧,都是一個時代的特色。獲台灣電影史家稱為「國寶級電影手繪海報藝術家」的陳子福,五十多年前便為各式各樣公映的電影繪畫宣傳海報,以他細緻的畫筆、無盡的心思,影片角色的一悲一喜、場面的一動一靜,全都躍然紙上,海報圖像豐富,色彩鮮明,好好的演繹宣傳的角色。
陳先生曾為大量台語電影繪畫海報,隨着這些電影大量散佚,這些海報以它傳真的畫像留下珍貴的影史資料。1999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中,更特別舉辦了他的手繪海報展覽。
數十年前,手繪海報是電影海報的主流,科技進步,照片漸漸代替了手繪畫像,即使在電影院高懸的廣告畫亦然。今天,這種廣告畫差不多已絕跡,代之而起是教人目眩的燈箱廣告。1987年拆卸的舊普慶戲院,最教人難忘的一點,正是它的大型廣告畫,那年《電影雙周刊》的紀念專題,亦特別走訪了當時的廣告畫師黃金。
乘着電車於大道穿行,映入眼簾的一幀又一幀電影院大型廣告畫,像無形的揚聲器,喧喧鬧鬧,百家爭鳴,疾呼即日公映、下期上映的好戲碼,好一幅熱鬧的大道景觀。
隨着最後一幅畫板從鐵架上拆下,大型電影廣告畫便分崩離析。大道又復歸平靜。
重讀才發現當時我是用「電影院」而非「戲院」,是否受該本來自台灣的讀物影響,竟捨下香港慣常用的詞彙「戲院」?文字的緣起在於陳子福的手繪海報,但我成長的年代,海報大多用照片製作,看着陳氏的作品,腦海想起懸掛於戲院外牆的大型廣告看板,它們由人手繪畫,畫像傳真,直長形廣告架上呈現的,就如一張倍大的海報。
文中提到「乘着電車於大道穿行,映入眼簾的一幀又一幀電影院大型廣告畫」,浮於腦海的畫面,是銅鑼灣翡翠戲院及百樂戲院的廣告看板。標題「影畫爭鳴」則是移花接木。猶記多年前一個菲林牌子曾舉辦攝影比賽,每週選出一張入圍作品,其中一星期的作品照下大道上橫七豎八的招牌,標題是「百家爭鳴」,名字早植入腦,寫這篇談說戲院廣告看板的文章,它又走出來,說的是「影」與「畫」,而鬧區又常有兩三家戲院立於同一街道上,確有「爭鳴」之勢。
廣告看板製作流程
戲院外牆的廣告看板,行內人稱為「大牌」,一般包含幾個元素:明星頭像、影片場面、與電影相關的文字資料(如戲名、宣傳語句、演員導演名字及出品公司)。大牌的圖像主要取材自電影海報或劇照,畫師偶有觀看試片,了解影片的類型、內容,製作氣氛匹配的畫稿。但畫師工作繁忙,影期緊迫,日以繼夜趕工,往往難以騰出時間看試片。
大牌的畫稿一般由主筆起草,亦偶有邀請知名人士起草,畫師姜志名便藏有一幅由董培新所起的大牌草稿。為大牌起稿,主要是確定主題、圖像佈局及文字擺位,一幅看板不僅是一幅畫,更肩負宣傳影片、吸引觀眾入場的使命,必須焦點明確,一矢中的地傳遞信息,其中一位受訪畫師甄卓岩說,須視乎影片是恐怖、驚慄或愛情類,便在構圖和顏色上花心思,營造脗合的氣氛。
經歷那個年代的人,定然記得戲院大牌的吸引力,尤其旺區的龍頭大院,大牌有時把整幢戲院大樓覆蓋。大牌上的圖像,都是從海報、劇照放大而來,倍大模式純屬手作經營:先在劇照上編方格,再在畫板上畫下對應並倍大了的方格,然後把劇照每個方格內的圖像按比例放大到畫板上。為了更準確的捕捉面部輪廓,有時候會在格仔內加入斜線,仔細定位,才能畫出像真度高的圖像。若當年你有留意戲院大堂張貼的劇照,就不難發現部分仍留有鉛筆編畫的小方格。

(圖片提供:姜志名)
 銅鑼灣翡翠、明珠戲院的大牌,攝於1991年。
銅鑼灣翡翠、明珠戲院的大牌,攝於1991年。
廣告大牌是由不同數目的畫板組成,畫板的大小基本劃一為4呎乘6呎,行內人稱為「四六呎板」。各家戲院的廣告畫架大小不一,所用的畫板數量亦有別,由數十塊到過百塊不等,無論有多少塊,基調都是「化零為整」─把多幅畫板組成大畫。繪畫時則是「化整為零」,因為畫室空間有限,只能逐塊板來繪畫,見頭不見身,見手不見腳,除了放圖要準,畫師繪畫時,要注意整體感,否則,畫板併合時,才發現色調、光暗不對,上下兩幅板的圖像,貌與神均離題萬丈,便難以補救。
早年戲院廣告畫是畫在帆布上的,電影下片後便拆除,用水洗去顏料,晾乾後再用。其後廣告畫轉移畫在木板上,木板亦非用完即棄,回收後會用白油「打底」,還原為白板,多次重用。
顏料亦與時並進。早年採用的粉劑顏料,需混入塗膠,以沸水攪拌混合。當時的顏料並無防水功能,但廣告大牌懸於室外,風吹雨打,若電影映期長,期間又經歷風雨飄搖的日子,看板上的人像難免面目模糊。後來會噴上膠劑,增加防水能力。
大牌上,除了圖畫,還有文字。一般而言,畫圖和寫字是由兩位不同的師傅負責,寫字的師傅會採用不同的字款,髹出戲名、宣傳語句等。擔任戲院美術的,還要處理大堂各類文字書寫工作,例如每個月的早場、公餘場戲碼、畫片箱內的「片芯」等。

(圖片提供:姜志名)
 畫師於逼仄的畫室繪畫廣告大牌。
畫師於逼仄的畫室繪畫廣告大牌。
行頭窄,僅有七家主力公司
當各片畫板繪畫完畢,便於影片公映前一天黃昏,運送到戲院,掛畫工人把上一期的畫板卸下,再把新的一批逐幅懸上,落畫上畫,入黑後,完整的大牌便在大道上放亮,率先引得附近坊眾圍觀。
早年,部分較具規模的戲院設有美術部,負責繪畫廣告大牌及處理各項院內的美術工作,後來,繪畫工作大多由外邊的美術廣告公司承接。1981年底,《電影雙周刊》曾訪問當時從事繪畫廣告大牌的聯合電影廣告公司負責人侯詠彬,他指出,當時麗聲院線及邵氏院線麾下戲院的廣告大牌,均由院線本身的美術部負責繪畫,至於嘉禾則交由外間的公司處理。而他營運的公司,主要為倫敦、總統及普慶等戲院繪畫大牌。[1]
訪問中,他不止一次提到戲院廣告畫「行頭窄」:「我們這一行行頭很窄,全港只有幾間公司專做這些大牌,行內的人很少。」又指出:「這一行行頭窄,有事找我們行家會通知,即使出了名對我們也不起什麼作用……這行來來去去都是這班人,有誰搶你生意?沒有什麼競爭的。」
當時和侯詠彬一起經營聯合電影廣告公司的甄卓岩,和筆者分享了工作經歷(見本書〈訪甄卓岩〉一文)。他特別記下七八十年代香港七家主力負責戲院大牌工作的美術廣告公司,除了他與侯經營的聯合,還有劉煒堂的孔雀、林祖裔的美林、張金戈的金馬、陳炳森的野馬、黃金的綜藝,以及吳達元的恆裕。他說這七家公司已包辦了全港大部分戲院的大牌。
回看八十年代,業界仍呈現一片熱鬧,不過,侯詠彬在上述《電影雙周刊》的訪問已披露:「這一行的前途如何?我看不會有大的發展,特別是如果迷你戲院普及起來,這一行就更難做。現時新人不多,亦沒有嚴格的學徒制度,個別新人做了一段時間便轉向其他方面發展。」
進入廿一世紀,戲院的模式已變,多映廳影城壓倒性的成為主流,鬧區的戲院,銀幕總數或許遠勝往昔,但影畫已經不再爭鳴。
[1] 〈侯詠彬雙手拼出畫千丈〉,第73期《電影雙周刊》(1981年11月12日),P.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