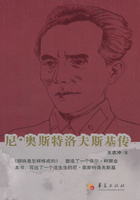
第8章 邂逅“冬妮亚”
其实,早在成为同学之前,柳芭和柯里亚就早已互相“久仰大名”,有所交往。柳芭听说过,外来户奥斯特洛夫斯基家的小儿子柯里亚酷爱读书,还擅长讲故事。柯里亚则知道,有个叫柳芭的女孩,受父亲的影响,是个书迷;她的父亲费德洛维奇·阿列克山德尔·鲍里索维奇爱书如命,藏书不少。
费德洛维奇是车站值班长,全家共十口人:费德洛维奇夫妇、奶奶、七个子女(两女五男)。柳芭是大姐,生于1907年,比柯里亚小3岁。这个家庭算不上富裕,但长期以来,父亲热衷于选书、买书、藏书。多年积累,如今居然有了个私人藏书室,从古典名著到高尔基的作品,大量收藏,另有一些法国和英国的著作,更珍贵的是有一部小百科全书。他在当时,在这一带,已堪称藏书家了。
应该说,柯里亚和发辫长长的活泼女孩柳芭成为好友,是基于对书的同样酷爱。
二人友谊的建立,有两件事情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一是入学不久,那天轮到柳芭值日。她大清早走进教室,惊讶地发现柯里亚先到,而且已经打扫完毕,连课桌椅都重新摆放好了。后来,柳芭还听说,另外几个女生同样得到过柯里亚的关心帮助。二是如前所述,柯里亚很欣赏柳芭在那次话剧演出中的演技。这么着,他俩熟悉了,话题多了。尤其是谈到读书,越发觉得对方是博览群书之人,并且没有贪多嚼不烂,而是经过大脑思索,具有自己的看法。柯里亚脱口而出的俄罗斯谚语“学问是光,不学心不亮”,柳芭觉得挺经得起咀嚼。这样一来,谈兴浓了,交往多了,友谊深了。不知不觉,柯里亚几乎每天都会到柳芭家去,她家的藏书室吸引着男孩子。柳芭的爸爸费德洛维奇,以及她的六个弟弟妹妹也非常喜欢这位小客人。
正如柳芭的一个妹妹塔吉雅娜后来回忆的那样:“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经常上我家,几乎每天必到。他来找大姐,借书还书。我不记得他有不带书的时候。他总是在读书。”
柯里亚和柳芭开始交往的具体情况,柳芭本人写过回忆录。我们惊喜地发觉,这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与冬妮亚的邂逅场面何其相像。
早在上学前,我就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了。当时他在发电厂工作。这是1918年的事。我们首次不期而遇的情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酷似。
当时我经常去池塘那边,在抽水站外、老柳树附近游泳。有一次我来到这里,看见有个小伙子坐在柳树底下钓鱼。我走近问他,鱼上不上钩。他回答说:
“当然上钩。不过要是被人一搅乱,那就什么也钓不着了。”
接着,我们聊了起来。那会儿我手里拿着一本书。他问我是什么书。随后,我们就一起读起来。书名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过肯定不是《牛虻》。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后来他专门拿来过这本书并为我念了几页。我们正在读书的当儿,有两个中学生过来了。其中一个大概是铁路工厂里小头头的儿子尤里克,另一个是斯达西克。他俩有意要和我结识,所以出言不逊,嘲弄柯里亚。柯里亚惩治了他们,揍了一个,把另一个身穿白色校服的摔进了池塘。当时,我邀请柯里亚去我家,但他回绝了。他不愿意穿着工作服去,说穿得太破旧,不好意思。后来,过了两个星期,他才来到我家,但已经穿着一新。这是他用自己挣的工钱买的。
柯里亚还告诉我,他怎样从窗口偷走德国人的手枪,藏了起来。
后来,他教我用这支枪射击,说以后兴许用得着。其实,我可不敢真的朝着谁开枪。
关于被捕的事,他也曾亲口告诉我。获得自由以后,他在我们家的养蜂场里躲了两天,还给我描述为了救一个水兵,他在狱中挨毒打的遭遇,整整谈了一晚上。
他被捕的消息,我最初是从女友普洛吉琳娜那儿获悉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后来,我找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哥哥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久,他便带着奥斯特洛夫斯基上了机车。……我同柯里亚从未吵过架,我们也没有在窄轨铁路那儿见过面。
其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使得柳芭全家难以忘怀。
正是1919年,德国占领者掌控着乌克兰大地上的许多城镇。舍佩托夫卡这个铁路枢纽站,车来车往,似乎更加繁忙了。人们发觉,被大量掠夺、运往德国的,是肥壮的牲畜、精选的小麦、洁白的砂糖、乌克兰的特产——玫瑰色猪油等。而这里百物飞涨,甚至有价无货,工农大众生活越来越困苦,怨声载道,以各种方式奋起反抗。恰恰在如此艰难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的费德洛维奇竟然病倒了,得了斑疹伤寒。更糟糕的是,药品已成为德国占领者重点管制的特殊商品,一般老百姓根本买不到。
15岁的柯里亚,也为同学的爸爸患了病却无处买药而着急。他有办法出把力吗?
他没有一天不来探视。柳芭一家住的是公房,在男孩子眼里,是一所非常好的大房子。他见费德洛维奇起不了床,还时不时地昏迷过去,愈发焦虑。可是在当地买不着需要的药品呀!火车不是老在这里那里开来开去吗?火车司机、乘务员,自己认识的多得很呀!
男孩说服了柳芭一家,不花钱乘上列车,去外地找药买药,居然没过多久,他们就买到药从基辅返回了。
费德洛维奇总算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对柯里亚另眼相看了。卧床个把月,他全身疲软,无力起身,他让柯里亚坐在旁边别走。
热心又能干的男孩子,给他讲述了一个个多半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听着,觉得挺感动的,竟提起精神,给柯里亚讲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来。两个人就此成了“忘年交”。
柯里亚上班、上学,同时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当这里红旗飘飘,出现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时候,他兴奋异常,缠住革命委员会主席——就是那个木匠出身的革命家,那个登台演讲,使柯里亚激动地高喊“我投布尔什维克一票”的林尼克——要求做点儿革命工作。
林尼克也特别喜欢这个老相识,常常信任地委托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当红军撤退,革委会转入地下的时候,他也几乎成了“少年地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