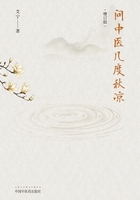
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脚踏实地搞好中医,中国文化就不会咽气。
中医不能到明丽、高耸的医院去,中医是一种不能离开土地的医学,不能不接“地气”。
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不但是那时不可想象的,就是现在也是难以办到的。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调查了解人们的健康状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
“赤脚医生”的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草药到处都有,“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并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付一般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老百姓是很实际的,民间的中医情结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在中国百姓的看病选择中已经完成了。百姓在看病上既找中医又找西医的做法不是出于盲目和愚昧,而是出于效率和实用,那就是杀牛用牛刀,杀鸡用鸡刀,杀鸡不用牛刀。在这点上西医不如百姓明白,如果西医把自己视为杀牛刀的话,那么从哪个角度讲中医的存在也不威胁西医,倒是西医总去杀鸡,却落得个费力不讨好,有损尊严。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的西医也是中国人。当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躁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好多病人采用“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有时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能起死回生。中医的存在对中国的西医也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百姓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顺应民意和自然而已。一般说来,人们找西医,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儿,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医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代。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商量治疗方案,已成为一部分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的。比如肚子疼,先去医院做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那里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
作为中医一定要显示出中医特色来,如果你没有中医的长处却有西医的弊端,人们为什么要找你呢?中医本来就是平民性强的,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女儿说,80%的病都可以用普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医治。因此,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西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中医的生存之道真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母亲的家庭作坊我想到现今的社区门诊。作为基层医疗单位,西医的社区门诊是竞争不过中医作坊的。建立社区门诊是西医的尴尬,因为西医不是这么存在的。西医的长处是紧密依托设备的技术,是高投入培养的精英,百姓趋的是西医人才和技术的“高”,这在社区门诊是无法体现的。而凡病就用精英、用尖端设备,又是对西医资源的浪费。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家庭医生”,这不又回到了我母亲的角色?
“家庭医生”可以像我母亲那样与群众关系密切,同呼吸,共命运,情感相连,真正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得到病人的极大信任。而人致病的原因有时是一个很微小的因素,改变这一因素就会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我一个朋友领着女儿来找我女儿看病,说是孩子可能得了肾炎,女孩说腰疼得厉害。女儿摸了脉后说,受凉了,穿上棉衣就好了。女孩的母亲说,不用到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女儿说,穿上棉衣后要是还疼你再去检查也不迟。
中医不可能灭绝是在于任谁也养不起太多的西医这样的“大医生”,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不仅是中国百姓支付不起,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
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呢,就先把窝头扔了,取消中医的理论是吃不到面包毋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当前我们的医疗问题是由中西医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医离开了土地,离开了群众;西医偏离了自然,并用技术支持人类整体偏离自然。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扑方式,击破西医给人类设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