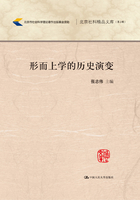
一、形而上学的概念
形而上学曾经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看作是哲学其他学科乃至人类所有知识的基础和根据,只是到了20世纪之后才衰落了。然而,尽管形而上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是它的概念却是不够清晰的,始终未能达到一般的确定性。换言之,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究竟研究什么问题、它的对象是什么等等这样一些构成了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普遍的共识,这就使形而上学在哲学中乃至人类知识的领域中形成了一道十分奇特的景观。为此我们首先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亦即对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概念做一番简要的梳理,这些概念包括形而上学、本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存在、实体、本体等等。
1.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本身的产生就富有传奇色彩。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有一部代表作叫做《形而上学》,通常我们也称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的创始人。然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生前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学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作“第一哲学”、“智慧”或“神学”。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暴毙,他建立的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一分为三,希腊也掀起了反马其顿的浪潮,曾经做过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亚里士多德首当其冲,于是他逃离了雅典,次年在流亡中去世,他的手稿亦不知所终。直到200年后,公元前一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最后被运到了罗马,当时任职于罗马图书馆的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于是开始着手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安德罗尼柯在整理完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学(phusike)的手稿之后,整理他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名之为ta meta ta phusika,即“自然学之后诸卷”,后来被人们简化为metaphusike。安德罗尼柯之所以名之为“自然学之后”,可能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只有研究了有关自然的所有学问之后才能研究第一哲学。十分凑巧的是,在希腊语中meta-这个前缀不仅有“在……之后”的意思,亦有“元(基础)……”、“超越……”的意思,而这些含义恰好与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意思是相近的。于是,metaphusike便成了第一哲学的代名词。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代表作的拉丁文本名为《第一哲学沉思集》,法文本叫做《形而上学的沉思》,就是这个原因。
在汉语中,形而上学有两种含义,一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一是与辩证法相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汉译属于外来语,像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一样源于日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由于在日语中采用了很多汉字,尤其是学术语言,因而很方便地转用于汉语之中。以“形而上学”翻译metaphysics第一次出现在1884年的日文《哲学词典》,日本学者借用了理学的概念,其根据是朱熹所说的:“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也可以追溯到《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研究形而下的对象的是物理学,研究形而上的对象的就是形而上学。1911年出版的汉语《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称“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1906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成日语时,形而上学又有了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对的含义。1912年恩格斯的文章翻译成汉语,在1933年沈志远的《新哲学词典》和艾思奇1939年的《研究提纲》中,形而上学基本上是这样使用的。
恩格斯这样使用形而上学概念与黑格尔有关。黑格尔将近代形而上学称为知性思维,以区别于他的辩证思维,而恩格斯则泛化了这个概念,遂使形而上学变成了与辩证法相对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学术界一般情况下只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与我们的研究主题相关,我们主要在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或学科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
亚里士多德作为形而上学的创始人,几乎探索了与形而上学有关的所有问题,形而上学后来的多种含义基本上都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关于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和探索不动的动者的“神学”。顾名思义,自然哲学以自然万物为其研究对象,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万物的基础、根据或最高的原因,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而上学被看作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根据和前提,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哲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家们对于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批判,不过形而上学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例如海德格尔要求重提存在问题,英美语言哲学在经过了反形而上学的激进阶段之后,亦重新恢复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
2.本体论(存在论)
“本体论”(ontology)这个概念实际上直到17世纪初才开始为人们所使用。人们公认本体论(ontologia)一词是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leneus,1547—1628)在《哲学辞典》(Lexicon philosophicum,1613)第16页中最早使用的 ,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然而郭克兰纽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在一位不太知名的作者Jacob Lorhard(1561—1609)1606年出版的Ogdoas Scholastica一书中,已经使用了ontologia。
,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然而郭克兰纽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在一位不太知名的作者Jacob Lorhard(1561—1609)1606年出版的Ogdoas Scholastica一书中,已经使用了ontologia。 由此可见,ontology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的本义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而这恰恰体现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内涵。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存在的科学”,因为to on这个希腊语词本来就具有“存在”和“诸存在物”两方面的含义,所以中文既译作“本体论”,也译作“万有论”。然而由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十分复杂,至少本体论不是恰当的译名。
由此可见,ontology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的本义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而这恰恰体现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内涵。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存在的科学”,因为to on这个希腊语词本来就具有“存在”和“诸存在物”两方面的含义,所以中文既译作“本体论”,也译作“万有论”。然而由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十分复杂,至少本体论不是恰当的译名。
显然,如果从狭义上看,或者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on)的理论(logos)”,因而译作“存在论”更为恰当,因而将ontologia译作“本体论”通常为严谨的哲学史研究者们所不取,他们主张严格准确地译之为“存在论”(亦有学者如王路主张根据to be的系词用法译之为“是论”)。但是无论人们有意还是无意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本体论,实际上本体论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或充分地体现存在论的意义。质言之,将ontology译作本体论并非仅仅是汉语的翻译问题,在西方哲学中亦有其根源。诚如海德格尔所说,一部形而上学史乃是存在的遗忘史,自近代ontologia这个概念出现以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并没有研究存在,更多地在研究“实体”。所以学者们在翻译海德格尔著作的时候,通常会把海德格尔之前的ontology译作“本体论”,而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ontology译作“存在论”。 像许多西方哲学概念一样,ontology的汉语翻译的确容易引起误解,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实际上在西方哲学中我们通常以“本体”翻译noumena,而“本体”(noumena)与“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ontology的对象,但是并不能涵盖其对象的全部意义。
像许多西方哲学概念一样,ontology的汉语翻译的确容易引起误解,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实际上在西方哲学中我们通常以“本体”翻译noumena,而“本体”(noumena)与“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ontology的对象,但是并不能涵盖其对象的全部意义。
尽管人们以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两者实际上亦有差别。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本体论作为研究存在的理论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因而形而上学应该比本体论更加宽泛。不过在弄清楚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后,我们采取了约定俗成的方式,有时在同义语上使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两个概念。
3.存在
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存在”概念的是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认巴门尼德为形而上学的奠基者。如前所述,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主要是研究存在的学科,然而存在却又是西方哲学中最富于歧义的概念。
“存在”是Being的译名,这个概念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其语言学上的原因。“存在”乃是由系动词演变而来的名词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作为西方语言的产物,起源于印欧语系所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亦即命题或语句最普遍、最基本的系词结构。
在人类语言的形成史中,最初出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些孤立的音节,然后是一些简单的语句。由于这些原始的语汇还没有明确区分为动词与名词,它们主要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因而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极其抽象的名词概念例如逻各斯(logos)、努斯(nous)、理念(idea)、形式(eidos)等等都有其源远流长的感性起源。 随着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活动的逐渐扩大和复杂化,语言也得到了进化和发展,人们需要将对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传达更多的信息,表达更复杂丰富的东西,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对于事物与其属性等等之间各种关系的表述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就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
随着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活动的逐渐扩大和复杂化,语言也得到了进化和发展,人们需要将对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传达更多的信息,表达更复杂丰富的东西,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对于事物与其属性等等之间各种关系的表述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就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 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曾经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抽象的普遍意义的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 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的普遍抽象的意义。
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曾经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抽象的普遍意义的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 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的普遍抽象的意义。
我们经常说:天是蓝的,水是绿的,我是快乐的,苏格拉底是人,这是一棵树,如此等等。在这些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即使它有时态上的变化,如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但是这恰恰说明“是”总是“是”,它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存在”“是什么”,它类似我们所说的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于是通过巴门尼德以及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arche)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即“存在”的形而上学,并且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史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由于近年来关于“存在”的译名引起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也是因为“存在”的译名的确有问题,所以我们在此简单讨论一下“存在”概念的翻译问题。
如前所述,“存在”源自希腊语的to on,即英语的Being,它源于连接主词和宾词的系动词,表示主词与宾词之间的某种关系,如XX是XX, XX有XX, XX在XX。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汉语语词来翻译这个系动词,只好根据主词与宾词之间不同的关系,分别翻译为“是”、“有”和“在”,其名词形式的约定俗成的译名就是“存在”。不过,这个译名不仅难以表现原文的多重含义,而且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通常我们把to on(Being)翻译为“存在”,而在汉语中,“存在”,包括“存”和“在”,都具有非常浓厚的空间色彩:存留、残存、存款、现存、存疑、保存;留在、在意、位置、在于……然而,“存在”的本义恰恰是非空间性的,或者说,空间性的存在是存在者,非空间性的存在才是存在。由此有些学者如王路教授主张直译之为“是”,但就汉语的表达方式而论,以“是”为哲学概念不是很顺畅。其实不只是汉语翻译容易引起误解,存在着空间化的危险,西方语言本身也是如此,这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了,而是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有了上述的说明,我们主张以约定俗成为原则,仍然译之为“存在”。
总之,“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印欧语系特有的语言结构在哲学上的体现。就西方语言来说,只要哲学家们开始追问普遍一般的东西,只要哲学家们开始对变化之中的不变的东西感兴趣,只要哲学家们希望发现永恒绝对的真理,那么存在就注定要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
4.实体
实体(substance)源于拉丁语对希腊哲学概念ousia的翻译。希腊文ousia这个词是从系动词eimi的阴性主格单数分词形式ousa变过来的,是这个分词的名词化。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亦把ousia看作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他用了两个短语来表达ousia的含义:ti esti(是什么)和to ti en einai(是其所是)。通常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ousia翻译为“实体”是成问题的,因为ousia既不“实”,也没有“体”,它主要指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亚里士多德以范畴来规定存在的存在意义,存在有十种意义,与此相对应,范畴表有十个范畴,ousia就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核心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说,ousia乃是亚里士多德规定存在的意义的核心范畴,而范畴体系就构成了世界的逻辑结构。另外,在《形而上学》第12卷中,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永恒的、不运动的、可分离的存在的第一实体,这部分内容通常被人们称为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由此,我们便涉及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其二是带有超越意义的最高的实体,这两个方面对于后来的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希腊的哲学概念被翻译为拉丁语并相继进入西欧各国的语言时,其含义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ousia之所以被翻译成为拉丁语substantia,与亚里士多德关于ousia的基本规定有关。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将ousia规定为只能充当主词(主语)而不能充当宾词(宾语)的东西,即判断中的绝对主语。主语或主体在希腊语中是hupokeimenon,其词义是躺在下面的东西,即基层或基质。西语中的substance其字面含义则是“站在下面的支撑者”。经过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洗礼”,“实体”概念在近代哲学中从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形而上学最高甚至唯一的对象。例如笛卡尔把实体规定为能够自己存在而其存在不需要其他东西的东西,并且以上帝作为无限的实体,以心灵和物体作为有限的实体。斯宾诺莎则以唯一的实体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
形而上学涉及许多哲学概念,每个概念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我们在此不可能一一详细说明,仅就形而上学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简要的讨论,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基础性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