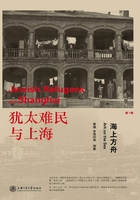
上海不要签证避难幸运八年 Not a Visa Needed, Shanghai Provided Easy Access to 8-Year Refuge
来自美国的杰里先生(Jerry Lindenstraus),曾是当年得以从纳粹德国逃难到上海的幸运儿之一。70后的今天,他深情回忆起全家艰难的逃往旅程,以及在“上海方舟”中度过的艰难而又温馨的岁月。他想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孙辈,没有上海就没有现在的他们。
Mr. Jerry Lindenstraus from the US was one of the lucky fellows who had fled to Shanghai from Nazi Germany. Today, 70 years have passed, he looks back with deep feeling the hard escape journey of his family and the tough but heartwarming days in “Shanghai's Ark”. He tells his own story to his grandchildren, hoping them to know that if there had not been Shanghai, they would not have lived today's life.
我的名字叫杰里·林登施特劳斯(Jerry Lindenstraus),是当年那些得以从纳粹德国逃难到上海的幸运儿之一。70多年过去了,在上海这艘接纳和庇佑了数万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中度过的那些艰难而又温馨的岁月,至今仍镌刻于脑海之中。
1929年,我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我家创立于1875的家族百货公司被强制折价卖掉。眼看着失去了生活的主要来源,1938年,我的父亲开始计划离开德国。举目望去,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迫于纳粹德国的淫威拒绝接受犹太人避难,而唯有世界的东方有一座叫作上海的城市向苦难中的犹太人敞开宽广而温暖的胸怀。到上海去!父亲终于下定了决心。父亲带着继母、我和其他7个家庭成员,乘坐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游轮,在海上整整航行了30天,历尽千辛万苦,于1940年8月抵达了当时全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到达的国际化城市上海,与大约2万多德国和奥地利难民一样,终于摆脱噩梦,并在此安顿了下来。

摩西会堂
一开始,我父亲和继母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个小公寓,但是这需要付出较为昂贵的租金。因为离开德国时,当局不允许我们把钱带出来,为了保证今后的生活,父亲在临行前给他一位在伦敦的表兄寄了1500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并希望他在我们到达上海后把这些钱寄来。而父亲的这位表兄却始终没有寄出,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没有了钱别说租住法租界的公寓了,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我们不得不搬到虹口区。这是一个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地区,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设立了一个犹太难民隔离区,2万多犹太难民被迫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隔都,虽然没有围墙,但进出都要受到日本人的盘查。对于大人们来说,适应当下的生活,并且生存下去是一件非常头大的事。由于工作岗位很少,生活来源有限,很多难民不得不靠当街变卖他们的随身物品而生存下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当时的生活则要容易许多。困境中的犹太人仍然非常重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大多被送到上海犹太难民子弟协会的学校读书。我所在的学校被大家亲切地称作为嘉道理学校,因为是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嘉道理先生捐赠了这所学校,让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犹太孩子有了一个可以接受教育的地方。记得当时学校实行的是英文教学,要听懂课就必须要学好英语,所有的老师都是德裔犹太人,教学上很尽心,学生也都很努力,我们的英语提高得很快。这是一所很棒的学校,我们在里面做运动,比如足球、乒乓,我还在合唱团里唱歌。
上海的夏天很闷热潮湿。我们和中国邻居住在一样的弄堂和石库门房子里。我们的住所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外屋的屋顶上。但是我们的中国邻居条件更差,他们时不时地会被日本兵骚扰,有时还会被他们打。生活随着战争的推进而愈发艰难。我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没有牛油和巧克力,热带疾病很猖獗,并且可得到的药物也少得可怜,我染上了疟疾。我们与中国邻居之间和睦相处,关系非常好,他们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由于中文太难学,一些中国商人为了与我们交往和经商,就向我们学习一些德语。当时,虽然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极其艰难,但并没有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在一些慈善机构的资助下,我们有自己的剧院、报纸,甚至还有维也纳式的咖啡馆,还不时开展一些体育运动。
突然有一天战争结束了,日本人连夜撤离上海,我们也获得了自由。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得到了美国部队里的工作,包括时年17岁的我。我在部队里是一个信差,也是一部军用自行车的骄傲主人。我是第一批得以离开上海去南美哥伦比亚寻找我的母亲的人,如果当时我知道上海会成为如今这个世界上最大最现代的城市中的一个,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离开这里。我总是告诉在纽约的孙辈,如果不是上海和中国人民,我和他们都不可能会在纽约—这个我已经居住了60年的城市。

摩西会堂内景
昔日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摩西会堂,现在已成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对这个地方我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因为我父亲在抵达上海过世后,我曾经连续6个月每天在摩西会堂为他吟诵卡迪什(犹太教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也是我举行成人礼的地方。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落成之时,我被邀请参加启动仪式。当年的诵经坛,如今已是博物馆的一部分,站在这里,我感慨万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上海生活的8年,并且将永远感激上海和中国人民。
(黎犁根据犹太幸存者杰里的发言整理、韩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