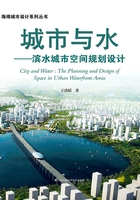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水系建设与那些伟大的建设者

水是生命之源,城市之眼,一城风光全在于水的灵性。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名城无不因水而兴,因水而活,适如“八水”之于长安(图2-0-1)、洛水之于洛阳;宋室南渡,弃六朝建康专营之前沿,转而退居杭州(行在)也因为有这自五代以来就经营不辍的钱塘西湖。同样,水的退去或过于频繁之水患,也是导致中国古都堕化为废都的主要原因。黄河三门峡之低效漕运使长安古都最终陷于东迁,无水运天险之汴京则又毁于洪泛。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而言,治水成效、粮食运转及储备能力,直接决定了中国古都的空间分布结构。相比于陆地运输,漕运因其便捷、运力大、费用低,历来备受重视。自汉以来,中国的粮食物资运输大多仰赖漕运(包括海漕),南北人工水系和东西天然水系的综合运转及管理,漕运畅通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首都的稳定和发达程度。故而,历代王朝都对提高漕运和水利管理能力不遗余力。
关中平原古称沃野,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系环绕,农业发达,孕育了最早的农耕文明。秦代开挖的郑国渠更加高效地灌溉了关中平原的沃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孕育了文明古都。随着汉末连年的战乱,关中平原的农耕用地被大量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已不具秦汉时期的生产能力。关中农耕地力下降、农业过度开发及人口增长,是导致经济中心东移,以及汉代以后两京并列,“就食”制度长期存在的三个主要原因。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同时汉匈战争以及经营西域都对汉帝国粮食供应提出极高要求,关中农业瓶颈矛盾凸显。西汉政府一方面大修水利,进一步开发关中农业之潜力;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漕运能力,由东部主要产粮区调运粮食进京。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取道渭河,但渭河水道浅、多沙,运输功能很差,加之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随即采纳,史称漕渠。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四十多里,将沣河、滈河拦蓄池内。昆明池除用以操练水兵外,还具有调剂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生活及景观用水三方面功能。漕渠后来一直作为西汉后期粮食运输的主要渠道,年运输量达四百万石。东汉时期,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同时,南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了唐代,国力的昌盛、文化的繁荣,使得长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发展到空前庞大的规模,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日益膨胀,尤其在唐朝鼎盛时期,关中平原的粮食供应已大大不能满足都城的需求,“所出不足以给京师”,[1]于是出现了“就食洛阳”的现象,皇帝常常要携宫廷及繁冗的政治机构到洛阳“讨食”。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中原腹地农业发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洛阳位于中部,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交通优势明显,南接江淮,北达北京,成为全国的漕运枢纽。从东南江淮一带运来的粮食和物资能够直达洛阳,而因为三门峡天险的存在,粮食到达洛阳后,运往长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有很大程度的折损,于是,洛阳作为陪都的城市地位日渐突出。唐中期,武则天在洛阳登基后,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东移,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超过长安。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提到“自唐则天后,洛阳牡丹始盛”,可见一斑。大运河的繁荣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更成就了洛阳城的繁荣。
北宋建都开封,进一步缩短了漕运的路线。鉴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方针,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不需接运,宋朝开创了我国漕运史的最高纪录。到了元代,首都迁移到北京,而原来的大运河要绕到洛阳才能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元代重修了京杭大运河,使得水道缩短了900多千米,同时在京城引白浮泉水以利漕运。船只可从南方直达大都城的积水潭,进入城市的核心地区,积水潭成为新的航运码头,像唐时的广运潭一样,商贾云集,南方的物资在此交换,此处成为大都城新的商业中心,促进了元大都和南方的经济交流。明、清两代沿用了京杭大运河,对其淤塞段进行疏凿,保证了这条南北大动脉的畅通。
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凿,带动了整个国家上下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交换,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格局由西向东(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沿河流展开的基本迁移规律。河流为沿岸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交汇的地方,杭州、镇江、扬州、苏州、淮安、济南、北京等无一例外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城市。

图2-0-1 “关中八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