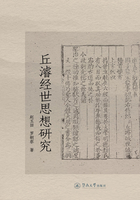
第一节 “灾害型社会”陷阱
论及“成化症候”,首先当从成化帝这位皇帝论起,继而当是“灾害型社会”。如此,我们对“成化症候”的认识才不会感到“突然”。
一、成化帝“身后评”
“成化”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的年号。朱见深的父亲是明英宗朱祁镇,也算是“大名鼎鼎”的皇帝。正统十四年(1449),面对蒙古瓦剌部挑衅。是时,政治上还不成熟的年轻的明英宗朱祁镇受太监王振蛊惑,御驾亲征,率领50万大军出击蒙古瓦剌部。这位“天真”的皇帝幻想一举荡平瓦剌蒙古势力,扫除明朝北部威胁,一劳永逸。然而,出师未捷,连遭惨败,50万明朝大军遭到瓦剌大军围追堵截,死亡过半,明英宗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国不可一日无主,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以绝瓦剌部首领也先要挟之心。1450年,瓦剌部送回明英宗。景泰八年(1457),做了八年“太上皇”的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亦称“南宫之变”)再次当上皇帝,改年号天顺。天顺八年(1464)正月,38岁的明英宗驾鹤西去,年仅16岁的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君临天下。第二年(1465),改年号为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在位23年,享年41岁。
关于成化帝的政治评价,明清官修正史基本持肯定观点,认为他是一位天平天子,还是一位不错的皇帝。如明修《明宪宗实录》称赞成化帝宽厚有容,用人不疑,且“一闻四方水旱,蹙然不乐,亟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以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必累日乃下,稍有矜疑,辄以宽宥……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 。清修《明史》则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祚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修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清修《明史》则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祚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修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然而,否定成化帝的评价也不少,在此不赘述。
然而,否定成化帝的评价也不少,在此不赘述。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明宪宗并非励精图治之人,却是用情专一的痴情皇帝。他始终宠爱万贵妃,信用宦官,致使政治黑暗,生出许多事来。如《剑桥中国明代史》称,成化帝大脸蛋,反应有些迟钝,说话严重口吃,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一生宠爱大他19岁的万贵妃,贪婪钱财,建立皇庄,“传奉官”满天飞,听任宦官外戚胡作非为。凡此种种,威胁王朝利益的邪恶得以产生。 当代明史学家方志远指出:“成化帝即位时,明朝立国已近百年。经过太祖、太宗的长期经营,以及洪熙、宣德、正统时的政策调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模式;‘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势力迅速分化,北边无强敌压境,东南的倭寇也尚未形成气候;经过军事力量的打击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安抚,闹腾一时的荆襄流民和广西瑶民也得到了平息。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时期,成化帝继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太平家业……喜读书、乐戏曲、昵方术、擅书画、好收藏,一切太平天子喜欢的东西成化帝都喜欢而且学有专长……可以说,是一个内向口吃却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
当代明史学家方志远指出:“成化帝即位时,明朝立国已近百年。经过太祖、太宗的长期经营,以及洪熙、宣德、正统时的政策调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模式;‘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势力迅速分化,北边无强敌压境,东南的倭寇也尚未形成气候;经过军事力量的打击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安抚,闹腾一时的荆襄流民和广西瑶民也得到了平息。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时期,成化帝继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太平家业……喜读书、乐戏曲、昵方术、擅书画、好收藏,一切太平天子喜欢的东西成化帝都喜欢而且学有专长……可以说,是一个内向口吃却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 明史学家赵轶峰认为:“即位之初,成化帝先后平反于谦的冤狱、恢复团营之制,起用前朝被贬正臣,颇有振作之意。但不久以后,他就沉溺于神仙声色之中,又设立由宦官掌握的西厂,从事特务监察活动,致使朝政日益紊乱,政局黑暗。”
明史学家赵轶峰认为:“即位之初,成化帝先后平反于谦的冤狱、恢复团营之制,起用前朝被贬正臣,颇有振作之意。但不久以后,他就沉溺于神仙声色之中,又设立由宦官掌握的西厂,从事特务监察活动,致使朝政日益紊乱,政局黑暗。”
如何评价成化帝?学界暂未有一致定论。不过,一个事实不容置疑——身为皇子的朱见深,养于深宫,在宦官与“妇人”护翼下成长;为皇储时的朱见深,因为父皇政治变故,储位一再废立,他并没能得到完整系统的皇储教育。 即位之时,朱见深尚未成年,政治上懵懵懂懂,缺乏主见。然而,他能为景帝上尊号,为于谦冤狱平反,亲贤臣远小人,政治气象一新。这些举措,至于是不是出于成化帝本意,无从考知。然而,当时的皇帝是他。随后,他的“文艺范”情结越发强烈,看戏听曲画画,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他对“爱情”更为专注,与万贵妃朝朝暮暮。要紧的是,他是皇帝,他要治理偌大个国家,方方面面都要用心,而他对政治和社会缺少必要的认识与经验,治国较为任性和放任,似乎有些盲目,几乎没有明确的治国目标和基本政治手段,只是在明初基本政治架构的有力支撑下,在部分尚有道德责任心与政治理想的官员的护持下,才能勉强维持大明帝国运转下去。事实上,成化帝虽为自己留下天平天子的名声,却为大明帝国留下了“灾害型社会”。
即位之时,朱见深尚未成年,政治上懵懵懂懂,缺乏主见。然而,他能为景帝上尊号,为于谦冤狱平反,亲贤臣远小人,政治气象一新。这些举措,至于是不是出于成化帝本意,无从考知。然而,当时的皇帝是他。随后,他的“文艺范”情结越发强烈,看戏听曲画画,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他对“爱情”更为专注,与万贵妃朝朝暮暮。要紧的是,他是皇帝,他要治理偌大个国家,方方面面都要用心,而他对政治和社会缺少必要的认识与经验,治国较为任性和放任,似乎有些盲目,几乎没有明确的治国目标和基本政治手段,只是在明初基本政治架构的有力支撑下,在部分尚有道德责任心与政治理想的官员的护持下,才能勉强维持大明帝国运转下去。事实上,成化帝虽为自己留下天平天子的名声,却为大明帝国留下了“灾害型社会”。
二、“灾害型社会”陷阱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一个王朝)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血流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也。” 严复所论,值得我们深思。尽管人地关系不是分析历史人物“功过”及考察社会治乱兴衰原因的唯一标准与视角,但是,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治乱与政治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不可小觑,更不能漠视。严复所论“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之“券”,在明代亦有大相类似之“券”。
严复所论,值得我们深思。尽管人地关系不是分析历史人物“功过”及考察社会治乱兴衰原因的唯一标准与视角,但是,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治乱与政治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不可小觑,更不能漠视。严复所论“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之“券”,在明代亦有大相类似之“券”。
明初,时逢元明之际大乱之后,灾荒与兵燹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地广人稀,君臣励精图治,朝廷鼓励垦荒,蠲免赋税,减轻徭役,民众经济生活向好,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然而,正统(1436—1449)以来,局面发生改变,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过快,人地矛盾加剧,民生日趋贫困,灾荒累积,灾区不断增多与扩大,灾民与流民数量剧增,乡村动荡不安。如正统二年,“行在户部主事刘善言:比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有八九。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远役,以故举家逃窜”。 正统五年,“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奏:直隶真定、保定等府所属州县人民饥窘特甚,有鬻其子女以养老亲者,割别之际,相持而泣,诚所不忍。臣已倡率郡邑官员助资赎还数十口,然不能尽赎……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直隶真定府所属三十二州县民,缺食者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余户”。
正统五年,“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奏:直隶真定、保定等府所属州县人民饥窘特甚,有鬻其子女以养老亲者,割别之际,相持而泣,诚所不忍。臣已倡率郡邑官员助资赎还数十口,然不能尽赎……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直隶真定府所属三十二州县民,缺食者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余户”。 正统十二年,监察御史陈璞等奏:“山东、湖广等布政司,直隶淮安等府、州、县,连被水旱,人民艰食。或采食野菜树皮苟度朝昏,或鬻卖妻妾子女不顾廉耻,或流移他乡趁食佣工骨肉离散,甚至相聚为盗。”
正统十二年,监察御史陈璞等奏:“山东、湖广等布政司,直隶淮安等府、州、县,连被水旱,人民艰食。或采食野菜树皮苟度朝昏,或鬻卖妻妾子女不顾廉耻,或流移他乡趁食佣工骨肉离散,甚至相聚为盗。” 景泰以后,明代灾荒严重程度有增无减。如天顺元年(1457),官员奏报:“今山东、直隶等处,连年灾伤,人民缺食,穷乏至极,艰窘莫甚。园林桑枣、坟茔树砖砍掘无存。易食已绝,无可度日,不免逃窜。携男抱女,衣不遮身,披草荐蒲席,匍匐而行,流徙他乡,乞食街巷。欲卖子女,率皆缺食,谁为之买,父母妻子不能相顾,哀号分离,转死沟壑,饿殍道路,欲便埋葬,又被他人割食,以致一家父子自相食。皆言往昔曾遭饥饿,未有如今日也。”
景泰以后,明代灾荒严重程度有增无减。如天顺元年(1457),官员奏报:“今山东、直隶等处,连年灾伤,人民缺食,穷乏至极,艰窘莫甚。园林桑枣、坟茔树砖砍掘无存。易食已绝,无可度日,不免逃窜。携男抱女,衣不遮身,披草荐蒲席,匍匐而行,流徙他乡,乞食街巷。欲卖子女,率皆缺食,谁为之买,父母妻子不能相顾,哀号分离,转死沟壑,饿殍道路,欲便埋葬,又被他人割食,以致一家父子自相食。皆言往昔曾遭饥饿,未有如今日也。” 时人称:是时“田野不辟,圩岸不修,故稍遇饥馑,即流殍满路,盗贼纵横”。
时人称:是时“田野不辟,圩岸不修,故稍遇饥馑,即流殍满路,盗贼纵横”。
成化以来,气候转冷, 生态环境灾变频率加快,各地水旱灾害明显增多,灾民人数剧增。据鞠明库研究:“明前期年均发生自然灾害约为15.5次,中期年均24.2次,后期年均19.1次。明后期的灾害频度虽高于明前期,但低于明中期。”
生态环境灾变频率加快,各地水旱灾害明显增多,灾民人数剧增。据鞠明库研究:“明前期年均发生自然灾害约为15.5次,中期年均24.2次,后期年均19.1次。明后期的灾害频度虽高于明前期,但低于明中期。” 天灾次数增多,饥荒日趋严重,民生更加困苦,饥民数量剧增。如成化九年八月,官员叶冕称:“顺德、广平、大名、河间、真定、保定六府赈济过饥民六十九万一千七百三十六户,用粮七十五万三百石有奇。”
天灾次数增多,饥荒日趋严重,民生更加困苦,饥民数量剧增。如成化九年八月,官员叶冕称:“顺德、广平、大名、河间、真定、保定六府赈济过饥民六十九万一千七百三十六户,用粮七十五万三百石有奇。” 而且,灾区面积大,跨州连府,甚至一地连年灾荒。凡此,灾区民生极为悲惨。如成化九年,都察院司务顾祥奏:“山东地方人民饥荒之甚,有扫草子、剥树皮、割死尸以充食者。”
而且,灾区面积大,跨州连府,甚至一地连年灾荒。凡此,灾区民生极为悲惨。如成化九年,都察院司务顾祥奏:“山东地方人民饥荒之甚,有扫草子、剥树皮、割死尸以充食者。” 再如成化二十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一府逃移者约30万人,其中安邑、猗氏两县饿死男女多达六千七百余口,蒲解等州、临晋等县饿莩盈途,不可数计,以至于“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弃其子女于井而逃者”。
再如成化二十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一府逃移者约30万人,其中安邑、猗氏两县饿死男女多达六千七百余口,蒲解等州、临晋等县饿莩盈途,不可数计,以至于“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弃其子女于井而逃者”。 而且,灾荒背景下,灾民、饥民、流民,还有“盗贼”,一并汇成冲击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成化时期,民众聚众“暴乱”抢劫之事屡屡发生。如成化十三年,兵部奏:“近闻通州、河西务,南抵德州、临清,所在盗起,水陆路阻。加以顺天、河间、东昌等府岁饥民困,不早为扑灭,驯致滋蔓,贻患实深。”
而且,灾荒背景下,灾民、饥民、流民,还有“盗贼”,一并汇成冲击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成化时期,民众聚众“暴乱”抢劫之事屡屡发生。如成化十三年,兵部奏:“近闻通州、河西务,南抵德州、临清,所在盗起,水陆路阻。加以顺天、河间、东昌等府岁饥民困,不早为扑灭,驯致滋蔓,贻患实深。” 加之疫病流行威胁及社会失范效应。
加之疫病流行威胁及社会失范效应。
成化中后期,灾荒愈重,流民遍野,灾区饿殍剧增,灾区人吃人事件频发。若以灾年人吃人事件为考察对象,不难发现,成化二十年以后,特别是成化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之间,是灾区人吃人事件的高发期。成化二十一年左右,中原等地持续发生罕见灾荒,区域灾区化严重,而且动辄数省发生灾荒。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汪奎等奏:“陕西、山西、河南等处连年水旱,死徙太半。今陕西、山西虽止征税三分,然其所存之民,亦仅三分,其与全征无异……陕西、山西、河南等处饥民流亡,多入汉中郧阳、荆襄山林之间,树皮草根食之已尽,骨肉自相噉食。”
研究表明,成化以前,“人吃人”事件不多;成化以后,不绝于书。如成化二十年七月,“巡抚陕西右副御史郑时等奏:陕西连年亢旱,至今益甚,饿莩塞途,或气尚未绝已为人所割食。见者流涕,闻者心痛,日复一日。” 可以说,成化时期标志着明代进入灾年“人吃人”的恐怖历史时期。酿成成化时期“灾年人吃人”悲剧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连年灾荒,人民贫困至极,饥饿至极;二是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社会控制失措;三是灾民的社会心理错位、精神状态消极偏激。“人相食”本身及其影响对于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具有颠覆性,造成民众心理创伤是长期的巨大的,对于灾民心理恢复及灾区社会道德重建的负效应是无可估量的。
可以说,成化时期标志着明代进入灾年“人吃人”的恐怖历史时期。酿成成化时期“灾年人吃人”悲剧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连年灾荒,人民贫困至极,饥饿至极;二是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社会控制失措;三是灾民的社会心理错位、精神状态消极偏激。“人相食”本身及其影响对于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具有颠覆性,造成民众心理创伤是长期的巨大的,对于灾民心理恢复及灾区社会道德重建的负效应是无可估量的。
成化时期,灾荒问题已不再是区域性问题,而成为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三荒现象”已经形成。所谓“三荒现象”,系指“灾荒”“人荒”“地荒”三者在空间上耦合、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一类极其悲惨的灾区民生状态与乡村聚落荒废的现象。其中,“灾荒”是指天灾频发,饥荒严重;“人荒”是指饥民逃荒,灾区人口锐减;“地荒”是指耕地抛荒,土地荒芜。“三荒”发生次序为:“灾荒”发生,“人荒”随之出现,“地荒”接踵而至。灾区乡村社会遂呈自然化倾向,终是村落萧疏,荒草弥漫。“三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乡村,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与生态环境恶性互动而形成的灾区社会自然化现象。实质上,“三荒现象”是一种表象,其生成与持续,是“灾害型社会”使然。明代社会仍为乡村制导,乡村社会乃是左右明代社会治乱及安危的决定性力量。成化以来,乡村贫困化,农民贫困化,朝廷救灾能力弱化,政府在救灾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天灾反倒成为左右明代乡村社会治乱的决定性因素,而明代又是乡村制导社会。这种社会状态,本书称之为“灾害型社会”。“灾害型社会”里,相对于自然灾害破坏力而言,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与民生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甚至严重缺失,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完全受制于自然状况与自然灾害程度。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得出,从最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而言,成化以来的明代社会,已是“灾害型社会”定型时期。
由弘治(1488—1505)而正德(1506—1521)而嘉靖(1522—1566),各地水旱灾相仍。由于政府财力日蹙,救荒多为空谈,造成饥荒连年,“灾区”蔓延。如嘉靖初,江南闹水灾,大学士杨廷和等称:“淮扬、邳诸州府见今水旱非常,高低远近一望皆水,军民房屋田土概被 没,百里之内寂无爨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得钱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从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麦熟时尚数月,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近传凤阳、泗州、洪泽饥民啸聚者不下二千余人,劫掠过客舡,无敢谁何。”
没,百里之内寂无爨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得钱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从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麦熟时尚数月,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近传凤阳、泗州、洪泽饥民啸聚者不下二千余人,劫掠过客舡,无敢谁何。” 嘉靖末年以来,“三荒”问题普遍化,“灾害型社会”进入崩解阶段。如时人林俊(1452—1527)称:“近年以来,灾异迭兴,两京地震……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甚。人民流徙别郡,京、襄等处日数万计。甚者阖县无人,可者十去七八,仓廪悬磬,拯救无法,树皮草根食取已竭,饥荒填路,恶气熏天,道路闻之,莫不流涕。而巡抚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当先期奏闻,伏候圣裁。顾乃茫然无知,恝不加意,执至若此,尚犹顾盼徘徊,专事蒙蔽,视民饥馑而不恤,轻国重地而不言。”
嘉靖末年以来,“三荒”问题普遍化,“灾害型社会”进入崩解阶段。如时人林俊(1452—1527)称:“近年以来,灾异迭兴,两京地震……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甚。人民流徙别郡,京、襄等处日数万计。甚者阖县无人,可者十去七八,仓廪悬磬,拯救无法,树皮草根食取已竭,饥荒填路,恶气熏天,道路闻之,莫不流涕。而巡抚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当先期奏闻,伏候圣裁。顾乃茫然无知,恝不加意,执至若此,尚犹顾盼徘徊,专事蒙蔽,视民饥馑而不恤,轻国重地而不言。” 万历后期,明朝进入覆亡最后阶段。不仅表现在政治腐败与阶级矛盾激化,还表现在“灾害型社会”区域扩大化,灾荒问题全国化,社会动荡加剧。如官员冯琦称:“自去年(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突无烟。据廵抚汪应蛟揭称,坐而待赈者十八万人……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今闾阎空矣!山泽空矣!郡县空矣!部帑空矣!国之空虚,如秋禾之脉液将干,遇风则速落;民之穷困,如衰人之血气巳竭,遇病则难支。”
万历后期,明朝进入覆亡最后阶段。不仅表现在政治腐败与阶级矛盾激化,还表现在“灾害型社会”区域扩大化,灾荒问题全国化,社会动荡加剧。如官员冯琦称:“自去年(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突无烟。据廵抚汪应蛟揭称,坐而待赈者十八万人……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今闾阎空矣!山泽空矣!郡县空矣!部帑空矣!国之空虚,如秋禾之脉液将干,遇风则速落;民之穷困,如衰人之血气巳竭,遇病则难支。”
明代仍是乡村制导社会。成化以来,大明帝国天灾频发,政府救灾不力,农民贫困问题严重化,灾荒问题更加恶化,“灾区”此起彼伏且已呈常态化、扩大化及严重化趋势。灾民生存无法保障,朝廷控制灾区与救助灾民的能力严重弱化乃至丧失,进而催生部分地区进入“灾害型社会”状态。所谓“灾害型社会”,系指自然灾害成为左右社会安危的主要因素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成化以来的明代社会开始陷入“灾害型社会”。是时,以农民为灾民主体、以乡村为主要灾区的“灾区社会”成为刺激并加重整个明代社会“灾变”的“新的灾因”,成为新的“灾区”及“灾民”的主要策源地,成为左右明代社会安危的主要“因素”。成化以来,“灾害型社会”由“点”至“面”,继而使大明帝国陷入“灾害型社会”陷阱。笔者认为,成化以来,以“灾害型社会”为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开启早期商业化进程。同时,在密集灾荒的侵袭下,又重复着“灾害型社会”自我否定及自我修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