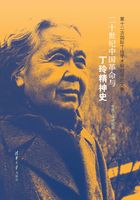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二、《写作提纲》手稿提供的信息
1.与最初的创作思路一脉相承
丁玲在创作《母亲》之初,就有明确的思路:“书里包括的时代,将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以及几个小村镇。人物大半将以几家豪绅地主做中心,也带便的写到其他的人。” 如今看到的《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依然沿用了这个思路。
如今看到的《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依然沿用了这个思路。
2.充分展示《母亲》第一部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脉络
已出版的《母亲》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围绕着武陵城乡于姓和江姓两大家族,在第三部“写作提纲”中均能找到。或者说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均是第一部中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如“于三老爷”,在第一部中还是一个开明绅士,积极参与反满维新,创办学社,出版报纸,开办女学……,为寻求真理,出走上海等。当然作者通过一些细节,也写了他的“假洋鬼子”的另一面,如虽然他已剪掉辫子,但家里随时预备一顶带假发辫的礼帽,以备官场之需;通过丫环的哭诉,暴露出他们欺压穷人的本性。因此,到第三部《写作提纲》里,“于三老爷”变坏,“恶化”,“为财而牺牲女儿,侄女,兄弟失和”,“冷视曼贞”等,就顺理成章了。
江文彬在《母亲》第一部中没有正面亮相,但却为他的出场做了厚厚的铺垫。通过他的太太杜淑贞邀请学校中众姐妹到他家做客,曼贞起初不愿去,引出江家的字号和财产:“你不晓得她是江泰昌的老板娘吗?在武陵算得数一数二的人家了。她铺子大还不算什么,田地可真不少,少算点一年也该有七八千租,……我们虽说也靠田上吃饭。可总是读书人,百事都还讲点恕道,也讲点礼貌。她们那些,真是不堪闻问。只不晓得搬来武陵了怎么样。现在我们那边县里的几家堂户,戏文真多,作孽得很。” 因为“母亲”的好友夏真仁等同学很想“去看看武陵财主家”,于是大家一起赴约,看到这个大工商地主家庭的奢靡生活。他的家“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大门倒不觉得怎样辉煌,可是一走过了第二道屏门,转入大厅时,便是那耀眼的彩绘的雕梁,脚下是铺着美丽图案的花砖,厅中一式紫檀木的桌椅,那正中八尺高的紫檀木的屏风,全是用翠玉珊瑚砌成人物花草风景。杜淑贞穿着得很不凡的从厅后转了出来……”
因为“母亲”的好友夏真仁等同学很想“去看看武陵财主家”,于是大家一起赴约,看到这个大工商地主家庭的奢靡生活。他的家“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大门倒不觉得怎样辉煌,可是一走过了第二道屏门,转入大厅时,便是那耀眼的彩绘的雕梁,脚下是铺着美丽图案的花砖,厅中一式紫檀木的桌椅,那正中八尺高的紫檀木的屏风,全是用翠玉珊瑚砌成人物花草风景。杜淑贞穿着得很不凡的从厅后转了出来……” 还描写了她家几重院子,花厅,西洋奏乐的座钟,以及喝茶的细瓷盖碗,还有穿着打扮似别人家小姐的丫环,等等。
还描写了她家几重院子,花厅,西洋奏乐的座钟,以及喝茶的细瓷盖碗,还有穿着打扮似别人家小姐的丫环,等等。
书中还写到杜淑贞的养女:“才两岁,是从育婴堂抱回来的,不过好看得很,比好些孩子都有趣,杜淑贞爱到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这两句可不是“闲来之笔”,从“养女”知道杜淑贞不能生育,但因她“本是一个大商的女儿”,又能干,所以做稳了太太的位置。在《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里才有了江文彬买小老婆,以及“江文彬之小老婆嫁了旅长”等情节。
这两句可不是“闲来之笔”,从“养女”知道杜淑贞不能生育,但因她“本是一个大商的女儿”,又能干,所以做稳了太太的位置。在《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里才有了江文彬买小老婆,以及“江文彬之小老婆嫁了旅长”等情节。
笔者以为,《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杜鉴秋就是延续第一部的杜淑贞。在《母亲》第一部中介绍杜淑贞是“曼贞的远房妯娌” ,是“武陵的首富”
,是“武陵的首富” ,是“江泰昌的老板娘”
,是“江泰昌的老板娘” , “很能干呢,当家已有两年”
, “很能干呢,当家已有两年” ,有一些“阔太太架子”
,有一些“阔太太架子” 。她本来与曼贞和许多女伴都上了女子师范学校,但觉得太苦,“在第二学期来了半个月之后便也退了学”
。她本来与曼贞和许多女伴都上了女子师范学校,但觉得太苦,“在第二学期来了半个月之后便也退了学” 。“她虽说自己不能读书,却愿意有几个读书的朋友”
。“她虽说自己不能读书,却愿意有几个读书的朋友” 。便一个一个近乎央求似的,邀请曼贞等去她家作客。不仅热情款待,还提议结拜姐妹:“都要志同道合,大家一条心,将来有帮手,要做什么事也容易些。我现在虽说不能上学,可是心还不死,愿意同你们一块儿,人不中用,就在别的方面出点力也行的,你们以为怎么样?”这时的杜淑贞还有些雄心壮志。后来她们果然结拜了九姐妹。《母亲》第一部借夏真仁(即向警予)与曼贞讨论结拜人选时,说出这九个人是:曼贞、夏真仁、蒋玉、于敏芝、吴文英、夏真仁嫂子、唐蕴、杨毅、杜淑贞。在《丁母回忆录》中提到的九个人是白友(即向警予)、曼贞、琳、敏、兰、莲、婉、伦、华。这些人都是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
。便一个一个近乎央求似的,邀请曼贞等去她家作客。不仅热情款待,还提议结拜姐妹:“都要志同道合,大家一条心,将来有帮手,要做什么事也容易些。我现在虽说不能上学,可是心还不死,愿意同你们一块儿,人不中用,就在别的方面出点力也行的,你们以为怎么样?”这时的杜淑贞还有些雄心壮志。后来她们果然结拜了九姐妹。《母亲》第一部借夏真仁(即向警予)与曼贞讨论结拜人选时,说出这九个人是:曼贞、夏真仁、蒋玉、于敏芝、吴文英、夏真仁嫂子、唐蕴、杨毅、杜淑贞。在《丁母回忆录》中提到的九个人是白友(即向警予)、曼贞、琳、敏、兰、莲、婉、伦、华。这些人都是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
笔者以为,“杜淑贞”这个形象便是综合几位女友的特点,其中“琳”的影子多一些。《母亲》第一部描写“杜淑贞”出身大商人家庭,又是大豪绅家的儿媳,既管理着大家族的出租放债,又愿意结交读书人做朋友,为公益事业出力,“算盘打得非常熟” 。至于“琳”,《丁母回忆录》里这样说到她:精明能干,会管理,尤胜会计工作;富有,夫家在本地以及省城、汉口等地有买卖生意;本人在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与曼贞是同窗好友,热心公益事业,协助曼贞成立妇女俭德会,开办女子工读学校;大革命失败后,加上身体原因,有些心灰意冷,外出学道。而《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杜鉴秋”则“矛盾、动摇”,“消极求道”。
。至于“琳”,《丁母回忆录》里这样说到她:精明能干,会管理,尤胜会计工作;富有,夫家在本地以及省城、汉口等地有买卖生意;本人在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与曼贞是同窗好友,热心公益事业,协助曼贞成立妇女俭德会,开办女子工读学校;大革命失败后,加上身体原因,有些心灰意冷,外出学道。而《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杜鉴秋”则“矛盾、动摇”,“消极求道”。
丁玲说过,“《母亲》是真人真事,但写成文学作品还需要提炼,要写出特点来,才能生动” 。在提到另一部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书里面那些人物是不是真人呢?说老实话,都不是真人。自然,也各有各的模特儿”
。在提到另一部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书里面那些人物是不是真人呢?说老实话,都不是真人。自然,也各有各的模特儿” 。应该说,杜鉴秋的模特儿就是“琳”,就是母亲实际生活中的女友蒋毅仁。《丁母回忆录》中极力夸赞“琳”:“个个说琳具有办事之天才,能废物利用,佩服之至”
。应该说,杜鉴秋的模特儿就是“琳”,就是母亲实际生活中的女友蒋毅仁。《丁母回忆录》中极力夸赞“琳”:“个个说琳具有办事之天才,能废物利用,佩服之至” ;称赞她“典换首饰”捐款为工读学校买纺纱机器,感谢她为女儿出外求学慷慨解囊。她们的友谊在办学中逐步加深:“我与琳觉彼此交情有增,伊佩我言行一致,不自私,我觉他见解不错,做事非常热心。”
;称赞她“典换首饰”捐款为工读学校买纺纱机器,感谢她为女儿出外求学慷慨解囊。她们的友谊在办学中逐步加深:“我与琳觉彼此交情有增,伊佩我言行一致,不自私,我觉他见解不错,做事非常热心。” “琳之为人,对于我可算第一个知己”
“琳之为人,对于我可算第一个知己” , “我和他可以说管鲍之交”
, “我和他可以说管鲍之交” 。丁母也写了“琳”为大家庭琐事缠身的烦闷,经常奔走于省城和汉口等地,特别是她“自觉身体上有了病,生趣全无,就东奔西走出去访道,想研个究竟,常和些修道人来往”
。丁母也写了“琳”为大家庭琐事缠身的烦闷,经常奔走于省城和汉口等地,特别是她“自觉身体上有了病,生趣全无,就东奔西走出去访道,想研个究竟,常和些修道人来往” 。1935年丁母在南京陪伴软禁中的女儿,“琳来函给我说伊已组织十来人在某名山打坐百日,惟缺少经费,盼望你接济我百余元”
。1935年丁母在南京陪伴软禁中的女儿,“琳来函给我说伊已组织十来人在某名山打坐百日,惟缺少经费,盼望你接济我百余元” 。母亲叹道:“唉!可怜,可怜!他怎知我母女近况,以为有什么好事,……然而无论如何应设法的,寄去百余元。”
。母亲叹道:“唉!可怜,可怜!他怎知我母女近况,以为有什么好事,……然而无论如何应设法的,寄去百余元。” 这些都是《母亲》的素材。丁玲初登文坛,一举成名后,曾于1929年春夏邀蒋毅仁和母亲一同到上海、杭州等地游玩。这个人物形象自然成为了“杜鉴秋”的模特儿。
这些都是《母亲》的素材。丁玲初登文坛,一举成名后,曾于1929年春夏邀蒋毅仁和母亲一同到上海、杭州等地游玩。这个人物形象自然成为了“杜鉴秋”的模特儿。
“母亲”在第三部里仍是重点人物。《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写她“革命虽失败,并不灰心”,还写她“援救三小姐”,“义斥江文彬释放仆人”。在得知女婿遇害,女儿遭难后,虽然“人情炎凉,亲戚幸灾乐祸”,靠卖用具“艰苦度日”,但仍“镇静的生活着,含着希望”。尤其在听了“关于小菡之谣言”后,“母亲之态度”旁边添加的文字“母亲怕听谣言,怕证实谣言。不敢想像谣言,母亲写信问,毁信,信上附笔问候了,又涂去,重写,母亲相信谣言,母亲假装不信,母亲自慰,自欺,但她明白,她用理性处理了这些疑问”。这些均源自真实的生活。
笔者以为,《母亲》第一部里的“杜淑贞”和《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里的“杜鉴秋”,都是为了衬托“母亲”这个形象。她们同样是大家闺秀,蒋家大地主家的媳妇,同样具有初步的民主自由思想,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勇敢迈进女子师范学堂。但经过大革命洗礼,“母亲”愈加坚强,“对革命心向往之”,“杜鉴秋”们却感到“生趣全无”,转而“消极求道”。
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母亲”的形象在第三部中继续发展,她“只有对革命心向往之”。
3.《提纲》中增加了作者被绑架后的经历
丁玲1932年6月11日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说:“开始想写这部书,是在去年从湖南又回到上海来的时候。虽说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却听了许多家乡亲戚间的动人故事,全是一些农村经济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途穷的一些骇人的奇闻。这里面也杂得有贫农抗租的斗争和其它的斗争消息。” 也就是说,开始构思是在1931年5月前后,至动笔写的时间是1932年6月。构思发生的故事最迟至“小菡送子归来”。从《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第二章“小菡恶耗”之后发生的事都是新增加的内容。这其中有“母亲”面对飞来横祸的各种心理活动,也有友人对“母亲”的慰藉。值得关注的是“沈从文过常不见,出书求名”。
也就是说,开始构思是在1931年5月前后,至动笔写的时间是1932年6月。构思发生的故事最迟至“小菡送子归来”。从《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第二章“小菡恶耗”之后发生的事都是新增加的内容。这其中有“母亲”面对飞来横祸的各种心理活动,也有友人对“母亲”的慰藉。值得关注的是“沈从文过常不见,出书求名”。
丁玲对于沈从文产生的“一点芥蒂”,由此开始。主要是有人告诉她两件事,一件是,上海“左联”为营救丁玲,请王会悟“给沈从文写信,托其南下共商营救事宜,被复信拒绝,情态十分冷淡,根据胡适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探问,否认丁的被捕,并表示与丁已经没有共同言语,不打算参与其事” 。另一件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
。另一件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 。告诉她这两件事的一位是王会悟,一位就是丁玲的母亲。一个是挚友,一个是亲人,都是丁玲最信任的,因而对这两件事深信不疑,虽然从理性上,丁玲知道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
。告诉她这两件事的一位是王会悟,一位就是丁玲的母亲。一个是挚友,一个是亲人,都是丁玲最信任的,因而对这两件事深信不疑,虽然从理性上,丁玲知道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 ,但在南京苜蓿园与沈从文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
,但在南京苜蓿园与沈从文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 。当时沈从文看到丁玲的身体没有复元,说可以去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帮忙,被丁玲谢绝。到陕北后,她与朋友们讲起南京的经历时说,“有许多事使我感到所谓友情的虚伪与可怕”
。当时沈从文看到丁玲的身体没有复元,说可以去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帮忙,被丁玲谢绝。到陕北后,她与朋友们讲起南京的经历时说,“有许多事使我感到所谓友情的虚伪与可怕” 。所以她准备把这个情节写到《母亲》第三部中。
。所以她准备把这个情节写到《母亲》第三部中。
另外,作者遭遇了被绑架和南京三年的软禁经历,在《母亲》第三部中“整写白色恐怖之利害人情冷暖”会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