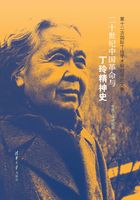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二、女性凄厉、绝望的呐喊——白薇作品中的情爱与革命
以出生时代来看,白薇略长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白薇出生于1894年,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等都出生于1900年前后。 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相比,白薇早年的命运更带有旧时代的特征,而她的反叛,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白薇的父亲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并在辛亥革命前回到故乡创办新式的两等小学,让白薇和妹妹入学学习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新知识,也阅读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的故事,但却在白薇16岁时强迫她完婚。白薇婚后几年的生活如同所有命运乖舛的传统媳妇,在饥饿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最后白薇不堪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趁夜摸黑逃回娘家,在母亲与二舅的帮助下,于1915年进入位于衡阳的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8年自师范学校毕业时,为逃避父亲要她回乡履行婚姻的安排,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只身逃往日本。在异国贫病交加的求学岁月中,她靠着在富人家当女佣赚取生活费和学费,考入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理科。1924年,白薇认识了诗人杨骚,两人展开了长达十年充满爱欲与怨恨的情感纠葛。
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相比,白薇早年的命运更带有旧时代的特征,而她的反叛,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白薇的父亲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并在辛亥革命前回到故乡创办新式的两等小学,让白薇和妹妹入学学习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新知识,也阅读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的故事,但却在白薇16岁时强迫她完婚。白薇婚后几年的生活如同所有命运乖舛的传统媳妇,在饥饿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最后白薇不堪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趁夜摸黑逃回娘家,在母亲与二舅的帮助下,于1915年进入位于衡阳的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8年自师范学校毕业时,为逃避父亲要她回乡履行婚姻的安排,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只身逃往日本。在异国贫病交加的求学岁月中,她靠着在富人家当女佣赚取生活费和学费,考入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理科。1924年,白薇认识了诗人杨骚,两人展开了长达十年充满爱欲与怨恨的情感纠葛。
相较于“五四”时期的冰心、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等拥有更多传统家庭的支持,白薇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出走的娜拉面对女性命运最激烈的交战,她既与传统思维对抗,又面对女性孤身在社会中闯荡时,最严峻的贫与病的威胁。 沉重的生存压力与极欲抒发的苦闷,使原本拿着解剖刀和显微镜的生物系女学生走上了创作之路:
沉重的生存压力与极欲抒发的苦闷,使原本拿着解剖刀和显微镜的生物系女学生走上了创作之路:
异国风光,一年又一年地摧折了我孤苦的肝胆,经济力的铁蹄,蹂躏了一个苦学生的心脏;金钱与势力的天盖下,压坏了人性的天真,压倒了真理、正义与同情,也压碎了骨肉亲子的爱。我在这直接间接的压力下,几乎被压死了。于是我开始对“人情”“社会”怀疑,怀恨。
……
把我的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吧!用些试验药。点只火酒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吧!……
啊,不能!我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层!
……
我需要一样武器,象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而是解剖验明人类社会的武器!我要那武器刻出我一切的痛苦,刻出人类的痛苦,尤其是要刻出被压迫者的痛苦!同时要那武器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高贵的人层一点讨伐!
逼使她必须与饥饿、贫病苦苦战斗的是在她生命中影响至深的两个男人——父亲和情人杨骚。前者代表父权对女性命运的规范和宰制,颜海平在评论白薇时即特别注意到她的一生都在抗拒父亲对她命运的安排,首先从婆家出逃,拒绝了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希望白薇以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妻子回到丈夫的身边,成为家族财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白薇再次出逃,这次远到日本,等到白薇留学日本之后,父亲甚至愿意运用财力和社会关系,让白薇成为湖南省议会中的一员,但白薇仍不愿屈从。 与其说白薇是倔强地不肯向曾经强迫她结婚的父亲低头,不如说她是拒绝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收编和控制,倘若接受了父亲的帮助便意味着不再有反抗的正当理由。拒绝了父亲,成为“孤女”的白薇只得独自面对社会残酷的现实。相较于对父亲的决绝态度,白薇对情人杨骚则在爱恋的甜蜜、背弃的怨恨和杨骚追悔后的宽待中周而复始地轮回,但杨骚留给她的却是背叛的痛苦与几乎致命的淋病,这让原本就已无所依傍,单打独斗的白薇更堕入贫病、绝望的深渊。
与其说白薇是倔强地不肯向曾经强迫她结婚的父亲低头,不如说她是拒绝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收编和控制,倘若接受了父亲的帮助便意味着不再有反抗的正当理由。拒绝了父亲,成为“孤女”的白薇只得独自面对社会残酷的现实。相较于对父亲的决绝态度,白薇对情人杨骚则在爱恋的甜蜜、背弃的怨恨和杨骚追悔后的宽待中周而复始地轮回,但杨骚留给她的却是背叛的痛苦与几乎致命的淋病,这让原本就已无所依傍,单打独斗的白薇更堕入贫病、绝望的深渊。
在白薇的生命经历和创作中,可以看到鲜明而深刻的“五四”印记,她对父亲的决绝反叛与对杨骚的热切爱恋是“五四”女性个性解放的表征。她在1926年出版剧曲《琳丽》,这部作品以现实和虚幻交错的方式,道出男主人公琴澜和女主人公琳丽、璃丽姊妹的三角恋情,以及三人对爱情态度的差异,其中隐藏着她与杨骚爱情的痛苦根源之一——风流多情的杨骚总是不断在白薇之外拥有其他女人,而兴之所至的不告而别与翩然归来也让白薇无所适从。 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两位女性主人公恰巧代表了作者本人对爱情、对男性的双重态度。琳丽志在为爱情献身……璃丽则始终保持清醒的怀疑:‘男人都是不专的。’这两位名字相近的人物,显然是女性内心矛盾的戏剧化身……”
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两位女性主人公恰巧代表了作者本人对爱情、对男性的双重态度。琳丽志在为爱情献身……璃丽则始终保持清醒的怀疑:‘男人都是不专的。’这两位名字相近的人物,显然是女性内心矛盾的戏剧化身……” 尽管白薇有着双重态度的矛盾,但她显然在琳丽身上投注更热烈的情感。琳丽被白薇塑造成一个唯爱至上的女子,她讴歌爱情的神圣与美好:“在虚无的母亲胎里久睡过的我,更得了个绝大绝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人生只有 ‘情’是靠得住的,所以我这回特别地执着我的爱。”
尽管白薇有着双重态度的矛盾,但她显然在琳丽身上投注更热烈的情感。琳丽被白薇塑造成一个唯爱至上的女子,她讴歌爱情的神圣与美好:“在虚无的母亲胎里久睡过的我,更得了个绝大绝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人生只有 ‘情’是靠得住的,所以我这回特别地执着我的爱。” “我这回只是为了爱生的,不但我本身是爱,恐怕我死后,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也只是一团晶莹的爱。离开爱还有什么生命?离开爱能创造血与泪的艺术么?”
“我这回只是为了爱生的,不但我本身是爱,恐怕我死后,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也只是一团晶莹的爱。离开爱还有什么生命?离开爱能创造血与泪的艺术么?” “人性最深妙的美,好像只存在两性间。”
“人性最深妙的美,好像只存在两性间。” 这个执着而美丽的女子,最后为爱殉情而死。而在白薇的1936年出版的自传性小说《悲剧生涯》中,她也陈述美好恋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之感:
这个执着而美丽的女子,最后为爱殉情而死。而在白薇的1936年出版的自传性小说《悲剧生涯》中,她也陈述美好恋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之感:
友情,恋爱,纯洁的同居,突进地展开更深层更伟大的光景,激发了我们更强烈的感情,排除了互相的忧郁,桃色的希望,也摆布在我们面前,勇敢迈进的血在我们充满着愉快的生活里跳。我们都像小孩一样地生活着,愉快着,没有眼泪,只有欢喜。在他,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快乐的日子;在我,也认为这是我生平顶快心的一回事。我觉得人间没有别的更大的幸福快乐,只有两个知己,互相爱着的异性很纯洁的同住在一起。这就是顶上的幸福快乐。我们的心境是怎样甜蜜呵!
在这些歌咏爱情的篇章中,经常伴随着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如琳丽在冬夜的花前月下沈思独语,或如《悲剧生涯》中的苇(白薇的化身)在秋山的密林飞瀑中奔跑徜徉,既是对大自然真心美好的赞叹,也带有挣脱现实种种人事枷锁,回归人性本真自然的愿望,这些赞美自然景物的文字甚至留有早期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的痕迹。同时,白薇将精神性的纯洁爱情作为理想爱情的最高标准,也与冯沅君有相近之处。 这些热烈而真诚,对于自然与爱的赞歌,很具有“五四”话语的特征。
这些热烈而真诚,对于自然与爱的赞歌,很具有“五四”话语的特征。
然而,白薇的生命经验与处境毕竟比“五四”女作家更加艰难与孤独,让她形成一种孤军奋战的女性独特视角,也让她的作品比“五四”女作家走得更远,她总是敏锐地感受到她与世界的对立,并因此形成她一贯的女性本位的叙述模式。当“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将爱人视为反抗封建观念的精神同盟之时 ,白薇却赤裸裸地展示女性在爱情中承受来自男性与社会的种种伤害,也同时自省女性在爱情中的软弱。她在《悲剧生涯》中巨细靡遗地诉说“展”对“苇”热烈的示爱、毫无理由地不告而别、狠心的辱骂和遗弃以及全无预警地回到身边再次示爱,如此一再反复。而在此过程中苇自剖内心对展诚挚的爱,因展对爱情的不忠感到被背叛的痛苦,因展的不告而别感到爱情的不可靠和不可解,因展的误解和辱骂感到难以言说的愤怒,因展的无情遗弃而陷入贫病交加的绝望深渊,个人的情热与爱人的回报产生抑郁的苦闷和激烈的撞击,使整部小说呈现情爱的烧灼状态。刘剑梅以“歇斯底里的女性写作”来概括白薇的书写特色
,白薇却赤裸裸地展示女性在爱情中承受来自男性与社会的种种伤害,也同时自省女性在爱情中的软弱。她在《悲剧生涯》中巨细靡遗地诉说“展”对“苇”热烈的示爱、毫无理由地不告而别、狠心的辱骂和遗弃以及全无预警地回到身边再次示爱,如此一再反复。而在此过程中苇自剖内心对展诚挚的爱,因展对爱情的不忠感到被背叛的痛苦,因展的不告而别感到爱情的不可靠和不可解,因展的误解和辱骂感到难以言说的愤怒,因展的无情遗弃而陷入贫病交加的绝望深渊,个人的情热与爱人的回报产生抑郁的苦闷和激烈的撞击,使整部小说呈现情爱的烧灼状态。刘剑梅以“歇斯底里的女性写作”来概括白薇的书写特色![[美] 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 113~12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9。](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B00D2/15367253104216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6546-6rHRgguBYL1HhKEbcsFUgYfPwRlwn3z0-0-429c29427e17ceabe03de38e546fd6d2) ,这正是女性痛苦心灵的本色。然而当苇面对展的一再忏悔和甜蜜誓言,她却没有斩断情丝的坚强决心,这其中既包含着她对展真挚的情爱,也包含着女性青春生命面对爱情时的身心欲望:
,这正是女性痛苦心灵的本色。然而当苇面对展的一再忏悔和甜蜜誓言,她却没有斩断情丝的坚强决心,这其中既包含着她对展真挚的情爱,也包含着女性青春生命面对爱情时的身心欲望:
她感到刻苦禁欲的她底生命力的强烈,迸发,有如三月的柳树五月的榴花,是多么需要春风来温暖?多么需要一个意同道合的伴侣常在一起呵!?生命力的膨胀使她濒于发狂的势子,巴不得能赶快有一个舒适的“爱之巢”,以缓和她平生积压的苦闷,过些人生应有的生活。
爱与不爱对苇来说都是痛苦,这样大胆而坦率地表白生命的真实渴望,是“五四”女作家远远无法企及的,也可以说是“五四”个性解放最极致的表现。
尽管白薇真心向往也赞叹爱情的纯洁美好,但现实的爱情却让她对“五四”高举的爱情理想旗帜彻底幻灭。爱情不是女性个性解放与独立自主的象征,而是让她认清社会丑陋现实的一纸试剂。因此对白薇来说,这部作品的写作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意图,她在出版自序中说明她不惜自我暴露拼死写下这部作品的原因,在于她所面对的世界充满对女性的各种臆测、妄断和流言,“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但她坚决地掌握说话的权利,表明自己与这个社会战斗的决心:
一个出走后而又在前进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毁谤和打击而消灭的。她不怕艰难,毒箭,山崩地裂地压碎;她不顾无谓的评价,不稀罕声名。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热烈的向上的心,反抗一切使她及使社会发展的障碍,要奋斗到底!……
因此她以为这部作品“是思想不同的青年男女的风流帐,也是时代的产儿的两性解剖图;是典型的个性清楚的轮廓,也是工作和爱情深刻的矛盾;是整个半殖民地的动荡和殖民地化的民族性的淡写,也是一个想前进的纯真情热的女子的红情忏悔录” 。她透过自己坎坷曲折的生命道路,展现中国的娜拉出走后所遭遇的真实的社会问题,以此揭穿五四时期爱情话语美好虚幻的假象与空虚。
。她透过自己坎坷曲折的生命道路,展现中国的娜拉出走后所遭遇的真实的社会问题,以此揭穿五四时期爱情话语美好虚幻的假象与空虚。
因此当白薇把写作主题放置到呈现中国社会问题时,她最关注的仍是女性的命运。让她在文坛奠定名声的是1928年发表的剧作《打出幽灵塔》,阿英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说明这部作品“是反对土豪劣绅,是暴露土豪劣绅的家庭里的黑暗,是表现着潜藏在黑暗中的一种斗争的力量——完全的站在 ‘被压榨阶级’的立场上在说话” ,而孟悦、戴锦华则从反封建与性别的角度论述剧作中的女主人公月林走的是一条“确立性别自我”的道路,强调“全剧从父/女这一不仅是亲子冲突而且也是两性冲突的立场上,补充了 ‘五四’反封建意识型态所简化、淡化的一个角度,即封建统治不仅是一种杀子统治,而同时是一种性别奴役、性别虐待,甚至,杀子不过是维持性别奴役权的一种手段”
,而孟悦、戴锦华则从反封建与性别的角度论述剧作中的女主人公月林走的是一条“确立性别自我”的道路,强调“全剧从父/女这一不仅是亲子冲突而且也是两性冲突的立场上,补充了 ‘五四’反封建意识型态所简化、淡化的一个角度,即封建统治不仅是一种杀子统治,而同时是一种性别奴役、性别虐待,甚至,杀子不过是维持性别奴役权的一种手段” 。无疑是更接近白薇的创作精神。
。无疑是更接近白薇的创作精神。
剧作名称“打出幽灵塔”本身便充满反封建的象征,而剧作中鲜明地呈现出这样一个女性世界:觉醒的女性靠着自己的拼搏,以及同性支持的力量打出幽灵塔。小说中所有女性的生命原本都被地主胡荣生所豢养、压制和玩弄,包括当年被胡荣生蹂躏的少女萧森、被叔父强嫁给胡荣生的第七个侍妾郑少梅、胡荣生买来的养女,其实是他当年蹂躏的少女萧森所生下的女儿月林,以及家中许许多多连名字都没有的侍妾和婢女。萧森靠着自己的忍辱努力,担任妇女联合会委员,进行妇女启蒙与救援的工作,剧本第一幕萧森拜访胡家,先后和月林及郑少梅谈话,她不但鼓舞当时软弱无助的月林“不应该被旧环境所苦恼。环境需要我们改造,人生也需要我们去改造” ,也以不断提问的方式确认和坚定郑少梅离婚的决心。在萧森的帮助下,郑少梅不但得以脱离胡家,并且获得到前方当看护妇的工作机会,生活终能自立。而剧本主线描写月林对养父——其实是生父胡荣生的反抗,月林依傍的是生母萧森的启蒙和鼓励,以及女性个人孤注一掷的搏斗。作品中有两个男人同时爱着月林,一个是胡荣生的儿子胡巧鸣,一个是农协委员凌侠,但胡巧鸣在阻止胡荣生调戏月林时被亲生父亲所杀,凌侠则被诬为杀人凶手而入狱,两人都在胡荣生的压制之下,无法保护月林。因目睹爱人被杀而精神崩溃的月林被胡荣生幽禁,她的姨娘郑少梅、婢女红桃和凌侠纷纷劝她设法出逃求助于萧森,但被月林断然拒绝,她看似癫狂而绝望地诉说自己的命运:“决走不脱的。我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
,也以不断提问的方式确认和坚定郑少梅离婚的决心。在萧森的帮助下,郑少梅不但得以脱离胡家,并且获得到前方当看护妇的工作机会,生活终能自立。而剧本主线描写月林对养父——其实是生父胡荣生的反抗,月林依傍的是生母萧森的启蒙和鼓励,以及女性个人孤注一掷的搏斗。作品中有两个男人同时爱着月林,一个是胡荣生的儿子胡巧鸣,一个是农协委员凌侠,但胡巧鸣在阻止胡荣生调戏月林时被亲生父亲所杀,凌侠则被诬为杀人凶手而入狱,两人都在胡荣生的压制之下,无法保护月林。因目睹爱人被杀而精神崩溃的月林被胡荣生幽禁,她的姨娘郑少梅、婢女红桃和凌侠纷纷劝她设法出逃求助于萧森,但被月林断然拒绝,她看似癫狂而绝望地诉说自己的命运:“决走不脱的。我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 实则有另一番复仇的计划:“不管……我要除掉这恶人……牺牲我这条性命也要除掉这恶人!……是,我这样才行!我不走,决不走!”
实则有另一番复仇的计划:“不管……我要除掉这恶人……牺牲我这条性命也要除掉这恶人!……是,我这样才行!我不走,决不走!” 这样的安排也透露着白薇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爱情终究是不可靠的(尽管胡巧鸣和凌侠并非不愿帮助月林,而是无法也无力帮助月林),女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同时也展现白薇直面黑暗现实,与敌人正面交锋,决不妥协的倔强与勇气。
这样的安排也透露着白薇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爱情终究是不可靠的(尽管胡巧鸣和凌侠并非不愿帮助月林,而是无法也无力帮助月林),女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同时也展现白薇直面黑暗现实,与敌人正面交锋,决不妥协的倔强与勇气。
和《打出幽灵塔》同样发表在1928年的小说《炸弹与征鸟》,白薇以20年代大革命为背景,描写革命阵营中的女性处境,并藉此思考女性在面对封建专制文化与爱情之外,新的生命出路与困境。《炸弹与征鸟》透过“余玥”和“余彬”两姊妹不同的个性和生命历程,从不同角度映照出相同的女性问题。作为“征鸟”的余玥明显带有白薇个人的生命经验,她被父亲强嫁给暴虐的丈夫,因不堪虐待而出逃,从此展开追寻人生理想和革命理想的长征,她从北京、天津南下香港,来到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又一路北上衡阳,途中因听闻革命阵营分裂的消息而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和彷徨,但终于辗转到达革命大本营的汉口。对余玥来说,她未必对革命实质的内涵和理想有多么清楚的认识和坚定的决心,但革命毋宁是女性生命困顿的出口,用以摆脱婚姻束缚和爱情纠缠的方法,因此她愿意在革命阵营中为妇女工作尽一己之力。但是她很快就发现革命阵营内部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感到所在的中央党部妇女部只是一个游街空喊口号、不干实际工作、有名无实的机关,因而退出了妇女部。离开妇女部之后,余玥在余彬的介绍下到G师长下工作,却引来众多男人对她的追求和觊觎。相较于余玥曲折的生命道路,作为“炸弹”的余彬因年纪较小,幸运地逃过父母之命的婚姻安排,当姊姊余玥还在和传统婚姻搏斗时,热情而大胆的她早已在革命热潮的号召下来到汉口,进入妇女协会交际部工作。但她很快地发现革命之地聚集的是“踊跃的革命青年,胡涂的饭碗官僚,和四方来找职业的男男女女” ,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被革命阵营当作消遣娱乐,在游艺会表现婉转歌喉和曼妙舞姿的交际花罢了!她找不到充实自我和实践理想的方法,不禁怀疑“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革命时妇女底工作领域,是如此狭小而卑下吗?革命时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如此不自由,如此尽做男子的傀儡吗?”
,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被革命阵营当作消遣娱乐,在游艺会表现婉转歌喉和曼妙舞姿的交际花罢了!她找不到充实自我和实践理想的方法,不禁怀疑“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革命时妇女底工作领域,是如此狭小而卑下吗?革命时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如此不自由,如此尽做男子的傀儡吗?” 于是她感叹自己的命运与姊姊所差无几:“姊姊是旧礼教的牺牲品,我就是新时代的烂铜锣!”
于是她感叹自己的命运与姊姊所差无几:“姊姊是旧礼教的牺牲品,我就是新时代的烂铜锣!” 在理想幻灭、生命空虚却又不知如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余彬终于堕落在追逐、勾引和掌握男人的恋爱游戏中。与余彬的堕落不同,余玥面对众男人的追求始终不为所动,但在小说最末,革命同志马腾向她发表一番革命现实如何艰难的道理,激起了余玥工作的斗志,而马腾交付她的工作是要她和G部长好,藉此机会搜集情报。
在理想幻灭、生命空虚却又不知如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余彬终于堕落在追逐、勾引和掌握男人的恋爱游戏中。与余彬的堕落不同,余玥面对众男人的追求始终不为所动,但在小说最末,革命同志马腾向她发表一番革命现实如何艰难的道理,激起了余玥工作的斗志,而马腾交付她的工作是要她和G部长好,藉此机会搜集情报。
在20年代大革命期间,白薇在汉口的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实际参与着革命阵营的工作。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白薇在汉口时期工作与生活的详细内容,但她肯定对当时复杂的革命现状感到困惑,对阵营内部良莠不齐的革命素质感到不满,也对革命分裂后的政治情势感到幻灭。在这困惑与幻灭的心情中,她找不到革命与她一向关注的女性生命困境有何共同的前景,因此《炸弹与征鸟》流露的是对革命与女性命运的双重绝望,在她笔下,革命阵营或把女性当作恋爱追求的对象,或把女性当做工作之余消遣娱乐的玩伴,或把女性当作套取敌人情报的工具,他们所注目和利用的仅仅是女性美丽的外貌与身体,而非女性的才干。而余玥、余彬两姊妹在革命阵营的幻灭或堕落,也说明白薇终究无法在当时的革命中找到女性生命的安顿之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薇并不算是文学成就特别突出的作家,她的情绪骚乱和思想激荡总是影响她对作品的整体掌握和控制,使得她的叙述无法在平稳的状态中进行,而不断出现断裂、跳跃、反复纠结缠绕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正好反映女性生命的艰难和直视现实问题时混乱痛苦的精神状态。对白薇来说,她的写作就如同她的生命,是孤女在茫茫人世间的困兽之斗,在反抗封建文化,从家庭出走之后,在爱情的失落和伤害之后,在革命理想幻灭之后,出走的娜拉仍将孤独而倔强地活下去,于是她的作品可以说是女性最凄厉、绝望的呐喊,道出女性最真实最严酷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