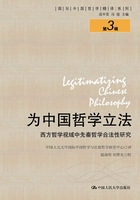
用英语讲儒学:柯雄文论儒家的“自我”
安乐哲(Roger T.Ames)[1] 著
秦国帅 译
在中国哲学的形成时期,一种气化宇宙论普遍存在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实践与哲学文献之中,并随这一源初时期的哲学主题同步演进。因此,在这一宇宙论的框架内探讨早期文本的中心主题和论点会为走向它们的哲学入口提供一条恰当的进路。反过来说,如果哲学的主体内容与这一不断演进的宇宙论相脱节,那么中国哲学的早期发展就会被放置到一个异质于其自身感受性的视域当中,并阻碍对之形成一种深入细致的理解,即哲学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如何独具中国特色。
从表面看,这一结论可以立刻被观察到,但由之而来的哲学启示却是基础性的、渗透性的,因而,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中国的宇宙论。中国古典哲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含混其词的特质,当然,当我们剔除古典的希腊式宇宙论假设时这一情况也会随之发生,然而,通过辩证其意义,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即它可以消除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某些哲学中心词汇的歧义。在这两种相对的古典传统当中,或许最本质的不同在于,西方古典传统以凸显“实体”作为本体论根据,而中国古典气化宇宙论却显示出了一种流动性的“过程”倾向。
西方古典视域下的这一推论,即形式的、不动的实在优先于流动的表象,相对于质化和连续性,更倾向于赋予量化和离散性以优先性。[2]事物的本性是原子式的:量化的离散性之功能就在于通过本质的和偶然的属性来解析事物的本性。整体是由离散且黏合的部分组成的。集体是一系列具有自身完整性的单个个人的组合。这种离散性和量化的优先性需要停滞性和恒久性来保证,它是实体性相对于过程性的优先性。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定义为具有某些自同的身份特征,并有一些充分的前社会的、前文化的和持久的理由来确保他们的这种集体身份。反之,离散性和量化的这种优先性,对形式上被定义之概念的明晰性和不变之真理的必然性——这两者都与一个量上离散的和可测度的世界更加意气相投[3]——表现出了关切。
一、提出问题
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学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在以“自我”和“人性”为中心点的古典儒学中,“人”的意义是什么?[4]我也想参与这场关于如何理解儒家的“人”的持续辩论,但与其说抱有一丝解决它的希望,倒不如说是试图厘清问题,辩证几个关键却又含混的说法。
在这场争论中,艾琳·布卢姆(Irene Bloom)是争论一方的代表。她认为,孟子论证的“人性”就是所有人普遍分有的那种东西——这是一种对人的一般的、本质的理解,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在西方哲学中也是常见的。她的主要观点是把孟子纳入那些赞颂我们共同人性的哲学家之列,并确保孟子跨越时间、跨越文化都是可译的这一地位。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争论的另一方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宇宙论和解释背景之内,儒家关于人的观念在根本上与我们一般常识性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才能寻找到一个词汇来确切地表述它。英语,由于暗含了大量关于离散个体性的假设,阻碍了我们试图以之来清楚地表达儒家感受性的初衷。然而,我认为,对于这种细致的工作,学者柯雄文(Antonio S.Cua)已经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这篇短文中,我追随柯雄文进入儒家文献,并在他努力的基础上再进行一番探索和尝试,试图来发现一种可以讲儒学的英语词汇。
二、孟子和人的本质
艾琳·布卢姆所坚持的论点,即人性“表达了孟子的这样一种思想:何为既一般且独特的属人的”[6],即使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下面的摘要充分体现了她的主旨思想:
很明显,布卢姆认为,在儒家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对孟子来说,一般性和差异性都必须予以考虑。对于她的立场,我认为它需要一个非中国式的宇宙论预设来保证,进而会促使对一个最不熟悉的关于人的例子形成一种熟悉的理解。实际上,我认为站在柯雄文的立场上理解儒家的人这一关系性概念并不是很容易,它需要一种完全的格式塔式的转换,这种转换使学习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能够把儒家的“自我”与我们默认的、常识性的何为人的理解区分开来。
我举一个例子,以此来表明布卢姆对儒家人的解释如何会牺牲儒家完全异质的预设,并以之来强化我们自有的、未加批判的预设。布卢姆在其著作中,对儒家的人有一种“遗传学上的”或者“本质上生物学上的”理解。当孟子宣称人人一般地具有“道德心的天赋”以及“这些能力由天所赋予”时,他是在确证一种遗传学状况和遗传能力的一般性。所有人的这种基本特性又被“圣人与我在类上是相同的”这一说法所强化。[8]
实际上,这是一种夹杂着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人的理解的、含混其词的说法,然而,通过详细阐明我们说“潜能”以及这种“潜能”存在于何处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含混其词的说法就可以被厘清。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前述的第一种立场会将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本质主义的、天赋主义的理解强加到孟子身上,进而因此假定每个人都有一种被给予的特性,通过这种特性,这个人就宣称他有一种不可被剥夺的人性。这样一种立场就是把人理解为实现被给予的潜能的存在过程。而当布卢姆谈到分有的、一般的“潜能”时,这似乎正是她所想的。
第二种关于“成人”的关系性、完成性观念主张,个体只有当在与别人交往的活动中像人那样去行动时才算作一个人——成人意味着事情的了结和完成。重要的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这第二种关系性、完成性观念同样没有排除预设,也就是说,作为人,我们天生地具有一些相对而言相似的、初始的、生物学上的状况,并且这些状况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都是赤身裸体的血肉之躯,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这构成了我们最终的人际关系网络。我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在这种状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这两种不同解读,它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第一种立场把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和宗教的感受性——看作被给予的潜能;第二种关系性的范例主张,大体上来说,发展为正在出现的潜能提供资源,这种潜能与文化濡化的交往性过程同步前进,而恰恰是濡化过程使人变成独一无二的人。毕竟,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人是在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里演进,变通也不会被预先阻停。
布卢姆坚决反对任何对本性和培养、生物和文化的二元分离,而她这一立场的长处就在于对生物学范例的重视。问题是,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生物学范例。第一,亚里士多德关于种(相)及其本质(本性)的观念,它给予我们自然的分类,并充当了由个体性到个体的原则。[9]第二,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截然相反的后达尔文式的观念,这种观点是对早期范例的修订,它需要对一些差异性的复合进行完全估算,而这些差异性来自经过自然选择的不同个体,不同个体同时又作为基础以之在不同种之间产生一个不受约束的、突发的杂合性。在第二种范例中,复合差异性的宽广度和重要性又由于人类的干预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布卢姆认为,对孟子人的观念的这种遗传性理解,通过《孟子》一书中处处可见的对自然隐喻的诉求就可以得到证明:
就像这个预设所展示的,玉米种子只会长成玉米,而不会长成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当语境被分解成因式的时候,植物栽培很明显依赖的是人类活动巨大且持久的干预。这就是野生植物群与种植农业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考虑到语境以及细节性过程的描述,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橡果变成了松鼠的食物而不是橡树,大多数鸡蛋变成了煎蛋而不是小鸡。
三、中国宇宙论和“成人”
关于“人”和“成人”之间的区别,通过观察常识性假设在哪种意义上意味着成为一个人,我们就会更清楚二者相区别的关键所在。在白话英语中,我们说“大家请站起来”,而在现代汉语中,这里存在早期过程宇宙论的一个提示词。表达方式“每个人”和“大家”,虽然在无意识中隐而不显,但却存在巨大的对立,一方面是个体化的进而离散的“人”,另一方面是安置性的、关系性的“成人”,在家庭和集体关系内,他必须对其恒常协作的交往角色作出一个持久的承诺,这样才能成长和实现自我,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因而这种不同是基础性的、默认的。
《荀子》中记有一则逸事,可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来澄清离散的“人”的单方完整性与“成人”的集体多方性之间的区别,因为在这则逸事中,“人”和“成人”都被包括在内。《荀子》记载的逸事如下:孔子独自阐发了仁的含义,以之作为自己哲学的主题,并与其徒弟就这一主要术语的含义进行了讨论。他的第一个学生认为,仁是一种利他主义,意味着“爱其他人”——爱人。这并没有给孔子留下特别的印象。第二个学生调转方向,坚持认为仁意味着在某人的个人活动中把标准定得足够高,即让“别人爱自己”——使人爱己,这个弟子的看法得到了孔子的赞许。然后,轮到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了,他站出来,淡淡地说,仁意味着“爱自己”——自爱。孔子非常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关于仁的最为充分的定义。
当然,在离散的个人当中,很难说自爱是一种美德。但上述逸事的关键之处在于“成人”的集体多方性,“自爱”既不是爱其他人的利他主义,也不是排除他人只爱自己的自我主义。实际上,这种自我指向的爱,虽然嵌入了“我”的意味,但却是反身的、双向的,它承担着内在而非外在的关系,扮演着构成性而非偶然性的角色。“自爱”意味着珍惜我承诺去培养的那些特殊的角色和关系,并以之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来源和基础——是在我与配偶、孩子、学生、同事等的关系中爱自己。与“人”相对,在我称之为“成人”的这个范例中,个人自我以及兴盛的家庭的实现是同构的、互为必需的。
在《荀子》这一段中发现的反身二项式的使用(如“自爱”)把一个人放置到了他的关系当中,这种用法在早期儒家文本中非常常见。实际上,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建议,在翻译儒家哲学文献的时候,我们应当使用“自我—”的前缀形式,就像“自我反省”,或“—自我”的后缀形式,就像“反省自我”,以此防止“自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被称为一种精心谋划的策略,这种策略可以防止将一个实体性的、至高无上的“自我”客观存在化。这里,我引用芬格莱特的几句话:
四、柯雄文论儒家的人
柯雄文同意芬格莱特上述引文的观点,承认“在儒家伦理学中,试图找到对自我的理论化使用方式是白费力气的”,反身的“自我—”风格而非理论化的自我是“实践的、反身的语言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提供给我们“一种方式用以清晰地表达个人修身的一方面”[12]。对柯雄文来说,反身词汇是儒家伦理学的一个组成元素,儒家伦理学允许某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
虽然这在英语的表达中有些许别扭,但柯雄文仍力主推荐当涉及儒家的人的时候,使用反身的二项式“自我—”或“—自我”,这种用法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一个反身的二项式比如“自我培养”是动词状形容词,解决了任何存在于自我与他者、载体与行动、性格与行为、意识倾向与结果、手段与方法之间的严重分离问题。与之相似,“培养自我”不同于“培养这个自我”之处就在于,当“自我”被看作某人行动的直接目标时,它避免了主体与客体相分离这一现象的发生。
在英语中,儒家文献里的仁虽然经常被选择性地翻译成“完成的人”或“完成的行动”,但是自我与他者、载体与行动同样的不可分离性仍旧存在于其中。这里,柯雄文进一步为我们澄清了这一点,他把仁理解为一种不可复制的“理想的主题”,而不是某种理想的准则,通过这种理解,他更加强调了仁的行动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这一本质:
通过借用荀子对“共名”和“别名”的区分,柯雄文找到了澄清儒家关系性自我或人的观念的一种方式[15],这是他迈出的“唯名论者”式的重要一步。这种语言上的区分可以容许我们对儒家人的观念作出一个概括,而不会将某种一般的或本体的状况强加到什么是人这一问题上。例如,我们可以作出一个一般的概括,即儒家人的观念不但是不可化约的,而且同时还保留着个体的独特性和发生性本质。通过使用反身的“自我—”形式作为订正和详述别名的方式,同时允许对“自我”的一般讨论而不再需要任何假设的实体,我们就能够避免强加给儒家传统的那种只默认地存在于我们人的观念中的预设。
在求诸反身形式时,如果不介绍共名与别名的这种区分,那么我们就会遇到约翰·杜威(Joln Dewey)所提示我们注意的那个关于默认的问题。柯雄文将成就于关系中的人的观念归之于儒家,而杜威本人在描述人的方式上极易与此产生共鸣:
在杜威看来,总是作为自我来行动的真理进入了总是向着自我来行动的虚构之间,当我们含混其词时,一种错误就发生了。实际上,关于整体的、现成的灵魂的教条一直作为“一种信条”而存在于“自我的固定性与单纯性之中”,因而,阻止了我们去认识“自我性成分的相对流动性和多样性”。[17]
如果不摆脱我们自己关于自我的常识性观念,“自我”的反身使用就只会延续一个离散的、现成的人这样一种错误。就如杜威所观察到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以此来表明当我们把未加批判性理解的“自我—”前缀于其中的一个词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未加批判的预设有一种清醒的意识,那么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反身形式“自我—”或“—自我”只是用来解决自我本质化这一问题的,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预设搁置一边。并且,只有把关于儒家的人的讨论置入其自身的气化宇宙论之中,我们才能理解把假设性的自我作为人类行为的基础与儒家的人是不相关的。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夏威夷州,火奴鲁鲁
注释
[1] 安乐哲(Roger T.Ames),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哲学系教授,《东西方哲学》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比较哲学、美国哲学。邮箱:rtames@hawaii.edu
[2] Jean-Paul Redding, "Words for Atoms, Atoms for Words—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on the Origins of Atomism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Absence of Atomism in Ancient China."这篇当时未发表的论文提交给了于1998年5月28日—30日在奥里根大学召开的名为“通过比较进行思考:古希腊和中国”大会。See also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Variorum, 1995, I: 2-3; David L.Hall, "The Import of Analysis in Classincal ChinaA Pragmatic Appraisal, " in Analysis in China, ed. Bo Mou, La Salle, Open Court, 2000, pp.153-168.
[3] 量上离散的优先性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目标,在《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一书中,他力求论证意识流“联结和交换”的现实性。See William James, William James: The Essential Writings, ed. Bruce W.Wilshire, Albany, SUNY Press, 1984, pp.47-81.
[4] 这场论战的文章已经结集出版并被译为中文,由江文思(James Behuniak, Jr.)和安乐哲编辑为《孟子心性之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 Irene Bloom, "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 "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7, no.1(1997): 21.
[6] Irene Bloom, "Bi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Men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 in Mencius: Contexts and Interpretations, ed. Alan K.L.Ch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91.
[7] Irene Bloom, "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 p.22.
[8] Irene Bloom, "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 p.27.对布卢姆观点的概述,参见James Behuniak, Jr., Mencius on Becoming Human, Albany, SUNY Press, 2005, 158n9。
[9] 本性在不同的古典哲学家那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是一般说来,指生长过程,即某物生长出的非精神性物质以及根据其生长而来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原理。
[10] Irene Bloom: "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p.24.
[11] Herbert Fingarette, "Comment and Response," in Rules, Rituals,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Dedicated to Herbert Fingarette, ed. Mary I.Bockover, La Salle, Open Court, 1991, pp.198-199.
[12] Antonio S.Cua,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Self-Deception, " in Self and Deception: A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Enquiry, ed. Roger T.Ames and Wimal Dissanayake, Albany, SUNY Press, 1996, p.187.
[13] Antonio S.Cua,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Self-Deception," in Self and Deception: A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Enquiry, ed. Roger T.Ames and Wimal Dissanayake, p.188.
[14] Ibid., pp.190-191.同时参见Antonio S.Cua, Dimensions of Moral Greativity. Paradigms, Principles and Ideals,第七、八章,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 Antonio S.Cua, "The Problem of Conceptual Unity in Hsuen Tzu and Li Kou's Solution,"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9, no.2 (1989): 122-125.
[16] John 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New York, Dover, 2002, p.138.
[17] Ibid, pp.136-138.
[18] John 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p.138.
[19] Ibid., 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