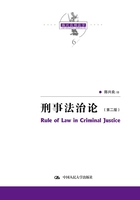
一、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理念嬗变
任何一项制度的改变,都必然是理念先导。只有在正确的司法理念指导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才能顺利地进行。中国当前首先面临的是观念转变的问题,即从传统的以专政为核心的司法理念向法治的以人为本、以法为本的司法理念转变。这一转变可以提供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思想资源。在我看来,司法观念的嬗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社会保护向人权保障倾斜
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必有其追求的价值内容,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例外。刑事司法制度的价值诉求,无非是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个基本方面。在不同社会,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在一个以社会为本位,注重社会秩序维持的社会里,社会保护被确立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因此难免以牺牲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为代价,甚至不惜践踏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在一个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的维护的社会里,人权保障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存在根基。为维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即使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在所不惜。当然,从理论上说,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和谐地统一起来,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也确实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统一。但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取舍之间凸显出一个社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中国古代社会以注重社会秩序轻视个人自由而著称,被称为是一种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因而法律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家族法。对此,中国学者瞿同祖指出:从家法与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系中,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每一家庭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1]在这种法律制度的建构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而家庭以及由其构成的社会却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刑法注重对社会利益的保护是势所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中国是一个政治国家的一元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作为专政工具必然以保护社会利益为根本使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引入了市场机制,中国正在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一的、一元的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的社会结构转型。因此,个人的命运,包括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越来越受到关注。这种从社会保护向人权保障的倾斜,在刑事立法上得以体现。在刑法中,权利保障的刑法价值被突出到一个极其显要的位置上,尤其是1997年《刑法》第3条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同时也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对刑罚权的限制功能。在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包括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都得以加强,注重调动有关诉讼当事人与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积极性。刑事诉讼的职权因素有所减弱,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有所加强。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法治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应当并且正在成为其重要的价值诉求。
(二)从实质合理性向形式合理性转变
合理性(rationality)是德国著名学者韦伯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念。韦伯把合理性的概念应用于社会结构分析时,作出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在对待法的态度上,也存在着韦伯所说的“法逻辑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要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2]。法是用来满足社会正义的,但法又有自身的形式特征。例如,法的对象是一般的,当一般正义得以满足的时候,个别正义可能难以兼顾。在这种情况下,是牺牲个别正义以保全法的形式,还是相反?这也正是人治与法治的分野:人治不是说没有法,甚至也可能存在完备的法制,而在于是否以法为终极的判断标准,即法治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会牺牲社会的实质正义。法治意味着一套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形式合理性具有强烈的冲动。而在以人治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有较为完备的法典,但由于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对伦理道德的实质正义的追求的结果必然将形式的法予以弃置,因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韦伯所说的“卡迪司法”(Kadi-Justiz,Kadi系伊斯兰教国家的审判官)。韦伯指出:儒家主导的中国法文化缺乏自然法与形式法的逻辑(Rechtslogik),儒家司法是根据被审者的实际身份以及实际情况,或者根据实际结果的公正与适当来判决的一种“所罗门式的”卡迪司法。[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基于对某种政治理想的追求,法治的观念在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甚至社会长期处在“无法”的状态。随着走向法治,法律纷纷出台,但这种法如何能够得以切实贯彻而不至于成为虚置的文本,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在刑事法领域,法律施行是得到国家权力保证的,因而贯彻得好一些。但这里也始终存在一个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可以说,形式合理性的理念正在逐渐生成,实质合理性的冲动正在受到抑制。在刑法领域,长期以来坚守的是社会危害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甚至是刑法的基石。凡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有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认定为犯罪;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依照类推定罪。在某种意义上说,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的设立,就是实质合理性的冲动压倒形式合理性的结果。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类推制度的废止,在刑法中形式合理性的诉求战胜了实质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以形式的法来实现的,因而对于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来说,具有实质的价值内容。尽管实行罪刑法定会使个别或者少数严重的危害社会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而逃脱法律制裁,似乎在实质合理性上有所丧失,但这是一种必要的代价。非此不能实现法治的价值,以破坏法治而实现的实质合理性是得不偿失的。在刑事诉讼法上,长期以来坚守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追求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由于犯罪案件是一种已逝的存在,在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事实的复原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不能原样复原。[4]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实质正义,只能通过一套严密设计的司法程序与法律规则进行法律推导,包括推定,如无罪推定等原则的适用。因此,程序正义虽然是形式的合理性,但都是为了保证更大程度的实体正义。如果摆脱司法程序,以追求所谓实体正义为名践踏司法程序、违背法律规则,法治必然被破坏殆尽。由于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程序的价值受到重视,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思维正在形成。
(三)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偏重
实体与程序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两种法律制度设计:前者解决案件处理的公正标准问题,后者解决案件处理的正当程序问题,两者不可偏废。但在中国刑事司法活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严重地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于程序法的轻视,除了在学理上没有正确地认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5]以外,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国家的司法权力与个人的诉讼权利之间的关系。质言之,轻视程序实际上是忽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正如我国学者指出: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则属于限权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6]因此,根据刑法获取的国家刑罚权,只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一定的司法程序才能得以行使。在诉讼活动中,国家的司法权力与个人的诉讼权利相对抗。在这一对抗中,司法权力强大,而个人权利弱小。为保证司法公正,必须通过诉讼程序严格规范司法机关的活动。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重视程序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并逐渐地为司法人员所认同。我认为,程序理念的形成并深入人心,是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严格的程序,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法治。在程序正义的理念中,不仅对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应当遵循法定程序提出了严格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应当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此,程序并不仅仅是一种法律程式,而是具有实体内容的一种法律制度。
以上三个方面的观念嬗变表明,在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观念、形式合理性的观念、程序正义的观念正在中国形成,构成刑事法治的基本观念。
注释
[1]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28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参见[德]韦伯:《儒教与道教》,王蓉芬译,1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4]我国学者提出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问题,实事求是之事,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如何转化为法律事实?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何以具有同一性?凡此种种,都需探讨。由于人的思维的非至上性,案件事实的完全复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代价太大。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实事求是原则引申出来的判决要建立在弄清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的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只是一种司法理想。这一原则把司法理想与司法操作相混淆,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难实现的。参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15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关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存在主从论、同等论与阶位论等各种观点。主从论为传统观点,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理论基础;同等论即实体法和程序法为同等关系;阶位论,即实体法和程序法为逻辑上的阶位关系的观点正在取代主从论而受到中国诉讼法学界的重视。参见李佑标:《试论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7年卷),28页以下,北京,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
[6]参见汪建成:《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新解》,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7年卷),25页,北京,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