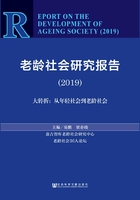
R.6 养老政策再设计
曾红颖[1]
摘要:老龄社会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未来一定会有养老需求爆发的峰值出现,有了这个预判,我们迎接老龄化冲击的准备就会更充分。根据人口结构演变,如果养老需求爆发的峰值在10年、15年后到来,那么企业不一定现在就要注重机构养老等的“硬件”,而是要关注开拓养生市场、补足养老市场需求匮乏的短板。
关键词:养老机构 养老需求 养老政策
一 政策有何用
养老政策在市场上应起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调节市场准入。很多养老企业需要大量用地,必然存在拿地资格问题。现在的市场环境中,有的人想变相拿地就涉及土地性质的问题,还有经营方向、业务模式、卫生、医疗、食品安全等。这些都会影响养老市场的准入条件,由现行的政策划定具体边界。
第二,降低运营成本。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高端养老院还是社区养老设施都存在大量闲置的现象。有效需求不足让企业感受到较大运营压力,很多企业反映运营成本高加剧了运营压力,包括水、电、气、暖、消防,还有对于养老设施的一些空间要求和一些必要设施配置,都是影响这个行业、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存在较高的制度门槛。
第三,规范市场秩序。政府应制定一种标准,特别是服务标准,明确市场主体可以在什么条件下竞争。政府能做的不仅仅是补贴,还应该考虑在确立标准的前提下为哪种企业赋能。这就预示着养老市场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市场格局。
目前,养老市场中以社会公益性质的机构参与为主,多由政府举办,这是政府通过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直接将政策作用于养老领域。另一个重要方面,政策的影响和效果要通过市场主体——企业来展示。由企业服务到市场需求的实现,这个过程也应是政策作用的效果。
二 养老市场研判
(一)养老机构数量庞大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按照国际标准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已近20年。这期间我们做了什么?先看养老市场的“硬件”。根据2017年民政统计年鉴,2016年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提供的床位730.2万张,使用人数327.6万人,所有床位的使用率是44.8%。城市养老服务机构入住率是50.1%,农村是62.9%。还有体量占比最大的社区养老机构,入住率最低的只有24.6%;民间非营利组织举办的机构大概10万家,还有基于社区的其他机构,入住率33%左右。
老龄办提供的2017年数据显示,包括城市、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以及社会福利院、光荣院、康养院到军休所,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5.5万家,注册登记服务机构2.9万家。
(二)市场缺乏龙头,极度分散
这么庞大的市场规模,给大家的感觉是我国老龄化问题太严重了,老龄社会真的来了。但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支点从各层面来看都有一定问题。
和君咨询养老中心的研究显示,目前养老产业市场主要的六个类型的企业——地产企业、保险企业、央企国企、复合型企业、服务型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有介入,大家都在超前布局上考虑很多,这六类都是有实力的市场主体。
重量级的竞争者不断涌入并进行全方位的布局,前20家赫赫有名的企业床位占有率共计2.78%,说明当前的养老市场是一个极度分散的市场,尚未出现引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三)企业运营模式尚不成熟
从运营模式来看,50%以上的民办养老机制只能维持收支平衡,40%的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能盈利的不足9%。从资本市场来看,Wind的数据能查到300万份年报,但是输入“养老”一个都没有。如果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可盈利的运营模式,资本市场一定会深入研究。
我们在观察和调研中核算过北京某区养老驿站提供服务的成本支出。这个区现有10家驿站,按照北京养老驿站布局的要求,2018~2020年需要布局37家养老驿站,覆盖6.5万老人。现在这10家驿站运行10个月,共服务了3.4万人次。每个驿站每月平均服务490人次、每天15~20人次。驿站运营成本开办场地100~1000平方米(社区驿站要求最低面积100平方米),人工、通信、水电及其他运行成本每个月最低10万元。北京一个社工的工资是7000元,10个驿站的支付水平都没达到平均工资水平。
三 机构养老峰值未至 健康养生正是刚需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3%,我国已经中度老龄化了。其中65周岁以上的1.5亿人,占总人口的11.4%。享受高龄补贴的2682万人,享受护理补贴的61.3万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354万人,这是我们政府做的一些工作。
在我们现有的服务体系设计里,机构养老是一个刚需,但还未到大规模爆发时间。简单按照人口的出生结构算一下,1958年出生的人2018年进入60岁,他们正好赶上改革开放40年,也赶上了计划生育。这些人收入要比前20年迈入60岁台阶的老人经济条件更好。现有家庭结构不支撑在家由子女养老,因为少子,但收入水平有保障,能接受社会机构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但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现在人们普遍感觉60岁基本不需要养老服务,80岁可能才真正需要。如果这批人是我们机构养老的用户,70岁考虑入住机构那就是2028年,今年60岁的人到2028年有8000万人。如果他们75岁入住机构,那就是2033年,按照现在的年龄往前推一下,应该是新增5600万。看人口结构,机构养老的刚需虽然必然会集中爆发,但以医疗照护为主的机构养老的刚需时点还未到来。
目前的银发经济其实可以有非常多的选择。养老床位是被动消费,现在65岁以上的人有着非常强烈的养生需求,想到处去玩但需要健康。我们做了养老文献的回溯,老人消费中28%属于健康消费。健康消费可以做什么?就是消费产品和消费服务。
(一)养老政策演变及背后的逻辑
1999年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一个分界线,1999年之后是老龄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2013年政府提出了老龄产业的概念,养老事业原来由政府做的可以由市场供给。随后2015年提出医养结合,相对来讲,医养结合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降低大家去医院的成本,在机构里提供服务要比在医疗体系里提供服务便宜。
但这只是医疗应对养老的变化,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主体都在关注这一点。医疗卫生产业,以前有一个算法叫暮年费用,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月会花掉人一生医疗费用的90%,这种支出效益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才要改变这种模式,老年时期是医疗的支出重头,这实际上是医疗产业,不能直接叫养老或者健康产业。2017年十九大提出了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养老成为大健康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家层面的养老政策最早于1983年出台,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印发《关于老龄工作情况及今后活动计划要点》,最近的一份是2018年10月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城乡养老设施规划的标准》。我们共检索、整理了350份国家层面养老政策,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初步统计,发文单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的有10份,这是最高层级的;由国务院发的有22份;由发改委发的有18份;民政发的最多,217份,养老一直由民政主管。在这些政策中,25份涉及待遇问题,35份涉及养老金管理问题,和卫生相关的55份,和健康相关的18份,和标准相关的74份,我们还整理了差不多1000份的各地养老政策。
通过我们对这些文件的初步分析发现,政府职能还在强化管理,对养老产业发展做出引导的很少。虽然希望通过市场去提供多样化的供给,但是目前来讲,各层级的制度壁垒还没有破除,行业管理面临的瓶颈还不少。
在养老市场问题上,政府对关键问题、痛点的判断没有达成共识,反映到政策层面就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并没找到市场痛点。
(二)养老政策如何再设计
综上可以看出,养老政策需要再设计,那么要如何设计?
第一,养老政策应从规范市场向引导市场创造需求转变。当前中国社会的简单需求可以得到基本满足,贫困人口只有3000万,而且扶贫的力度加大,吃不上饭的几乎没有。美国20世纪60年代提出叫“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是对需求的再塑造。日本提出一个概念叫“饱和社会”,在饱和社会里应怎么创造需求?日本给出的答案是把那些熟悉的东西变得让人不熟悉。所以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创造需求才是最关键的。
养老政策以前总在规范市场这个层面上下功夫,现在是老年人兜里有钱但不愿拿出来消费,因为没有创造出让他值得消费的新增需求。在新增需求中,养老服务质量、服务标准都很重要,但这些需求的落地还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的监督管理。
第二,养老政策应由解决问题向激励市场解决问题转变。原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做法是政府率先冲上来,但政府的运行机制容易陷入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养老政策应该激励解决问题的那些人,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大家经常提的一个问题——养老市场不充分,有国有的、有民非的、有事业单位的,很多人在身份的问题上备受困扰。其实可以借鉴互联网经济的经验,就好像京东的自营业务和平台业务一样,市场上的自营业务要做得好、做成标准、做成规范、做成需求引导就把市场问题解决,而平台提供各式各样的商品或服务完全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市场。
今天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国有和民营合力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要在身份问题上纠结。
第三,养老政策应该由表达公益向传递尊重转变。政府应转变落实养老政策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想法,应该由表达公益到传递尊重,通过政策推动、撬动市场参与养老产业,在过程中政策要不断助推,而不是代替。属于老龄社会基础体制建设的问题,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险、服务标准、服务人员和服务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等需要不断摸索经验,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等。
老龄社会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未来一定会有养老需求爆发的峰值出现,有了这个预判,我们迎接老龄化冲击的准备就会更充分。根据人口结构演变,如果养老需求爆发的峰值在10年、15年后到来,企业不一定现在就要注重机构养老等的“硬件”,而是要关注开拓养生市场、补足养老市场需求匮乏的短板。
[1] 曾红颖,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