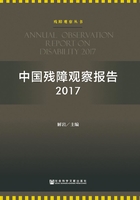
第七章 年度造词
词语、语言和文化,对这三者的探究,引无数学者竞折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引无数人竞造词。是现象狂欢,还是心态无奈?是文化沙漠,还是传播媒介?是情感表达,还是现实写照?造词的背后,表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语言和文化。
残障,一个足够丰富、充实的领域,以人为载体,延伸并触及社会各个角落,为新词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需谨慎拆解、细心提取后标新立异,唯恐哗众取宠。
残商DQ
文/蔡聪
残商不是电商,DQ也不是冰激凌。它如同智商与情商,是人造出来的概念,用以衡量残障人士如何看待并处理残障身份与社会的关系,是否达成个人的利益诉求。
在过去的年代里,残障人是没有什么机会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因此大多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就是“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纯靠个人的努力及社会资源来克服障碍。残障并未给其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全是阻碍、困难与羞耻。因此,取得世俗标准的成功的残障人,诸如大多残障的企业家,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残障,如同很多小品中进入城市的“凤凰男”面对乡下穷亲戚时的尴尬,只能尽可能远离社群。他们回报残障社群的方式也是通过捐赠钱款、提供工作机会等,但会小心翼翼地保持自身与残障社群的距离,以割裂个人与残障的标签。
随着近年来媒介渠道与内容的发展,透过“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获得社会关注度,并将之转化为个人发展的资源与利益,已经不再是少数残障人士的特权。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让更多残障人拥有了机会,也让更多残障人可以谈论自己的残障。只是大家谈论的经历比较雷同,大多是从残障带来人生冲击开始,可能是先天,可能是后天,然后在描述或凄惨或绝望的境遇后,因为某个契机、某种情感的觉醒开始奋斗,通过努力做到某些非残障人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情,最终以此或明示或暗示地给予他人激励。譬如地震中失去双腿却能游泳,事故中失去双臂苦练双脚弹钢琴,言语有障碍偏要挑战演讲,纵然失明也要生下孩子等。可能残障人本身并没有将自己固化在这样的叙事模型里,但市场通过选择与教育,进行了残障人的选择,也反过来加固了市场。尽管有不少残障人已经开始在私下抱怨说自强也要休息,但当站在公众的视野中时,他们仍然要以最饱满的热情、最真挚的呐喊,在顺应中或主动或被动地确保个人的利益。无关对错,只是因为机会太少,残障人太多。
2017年走入公众视野的两名残障人,让我们看到了长久以来公众透露出的一丝审残疲劳,也看到了在社会开放度更高的新时代下残障青年人可能给残障叙事带来的新的可能。先是2017年2月15日晚播出的网络综艺节目《奇葩大会》,公益从业者视障人蔡聪以《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残疾”人》为题进行的演讲,以打破刻板印象为主题,引起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与报道。这个7分多钟的演讲还得到了《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的转载。
2017年5月12日,在网络问答平台知乎上“穿短裙露假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一问题下,一个打破传统凄惨、表示这种体验很酷的回答在短短两天内收获了数万个赞,作者是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本科学生谢仁慈,其随之迅速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观察两位残障人士被广泛关注并称赞的表象,均是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从个人故事到理念层面均试图传播残障视角的新思想、新观念。但从公众的评论来看,大多仍旧感动于其纯天然的积极与乐观和自我不够努力的感喟,只是从形式上看到了新鲜的“身残志坚”,它轻松而幽默,不会带给人太多压力,但是本质上是否有所撼动,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标尺上观察。事实上,这也并非一两个个体能够改变的事情。
再看两人引发广泛关注后的走向,蔡聪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谢仁慈也不例外。两人均在采访中强调残障人的权利、平等。但随后,谢仁慈更多出现在综艺节目之中,比如湖南台《儿行千里》;而蔡聪更多出现在社会类节目之中,比如凤凰公益、中国网等频道关于融合教育、无障碍等的探讨,事实上这是媒体采访的延续,也是此前他一直担负的工作。谢仁慈在同年10月出版了个人自传及人生感悟类图书《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蔡聪则忙于年底在上海、兰州、沈阳等地高校的演讲,内容集中在大学生与公益、残障与社会发展等。
两人的共同点有很多。比如蔡聪是一加一发展过程中倾力培养的残障领导人,接受过多年人权教育;而谢仁慈从学法律,到结识一加一,参加残障青年人的意识培训。这应该是他们在公众层面能够谈论残障并以全新的方式谈论残障的基础。但是不卖惨、不比惨,能够谈论平等与权利的残障青年人越来越多,能够走入公共视野的是否也会越来越多,还有待更多样本,以确定他们这种并不愤怒的、平静的、幽默自黑的方式,是不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或许在未来它能成为残商教育中的重要一课。
两人的不同点也有不少。比如蔡聪是从隔离教育中走出,在DPO中从事残障倡导工作已有八年,从媒体报道来看,参与该节目是工作中有计划的一步;而谢仁慈从小生活在主流环境里,还是一个学生,“走红”也属无意。这也决定了两人后续面对媒体与公众时的表现不同。
显然,两人能够引发广泛的关注,跟其残障身份,跟其谈论残障的方式对公众产生了冲击是分不开的。但这可能只是一时新鲜,透过表面去看人们在评论中对信息的解码与再次编码,仍能看到传统的普遍认为残障人的不能,从而惊叹感动于个体的能的“超常化”框架。在这种新鲜感的背后,能否争取到更多空间,发展出更多残障标签以外的角色,从个人利益到机构利益,到社群发展的协调与统一,无一不考验着其残商。
近年来,随着环境的进一步开放,残障人展示自己能力的渠道越来越多。因为“第一法则”效应,在变革时代下,率先接触到机会或者进入公众视野的残障人,自然占有更多优势。比如先有机会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学生和在考试中表现突出的视障学生,同样会吸引更多的关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转变观念的人们仍然在用自身的框架与新时代、新机会中走出的残障人的框架不断碰撞,是在碰撞中收下人们同情与怜悯的捐赠、特殊照顾和敬佩,还是在对抗中再次被远离,或者不断在碰壁中寻找、尝试、妥协,最终并肩,确实十分考验残障人的残商。而不管是残商、智商还是情商,其实都是各方与各方、人性与利益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