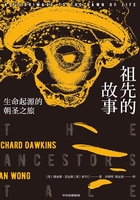
黑猩猩
在大约700万年到500万年前的非洲某地,我们人类朝圣者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会面。这里是第1会合点,我们第一次遇见其他朝圣物种的地方。确切地说,是两个物种,因为我们在这里遇见的朝圣小队包括两种现存生物的代表:黑猩猩和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anzee),后者也叫倭黑猩猩(bonobo)。在跟我们会合之前,这些朝圣者已经彼此相遇,它们相遇的时间距今约200万年,比跟我们相遇的时间晚近得多。我们的共同祖先即1号共祖,是我们在25万代以前的远祖,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就像我将为其他共祖做的估计一样。
在我们走向第1会合点的时候,黑猩猩朝圣者们正从另一个方向接近同一地点。不幸的是,我们对另一个方向所知甚少。尽管从非洲出土了数千枚原始人类化石或化石碎片,但确定属于黑猩猩家系且晚于1号共祖的化石只有几颗来自肯尼亚的牙齿。这也许是因为黑猩猩是森林动物,而森林里的落叶层对于化石来说不算友好。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意味着黑猩猩的朝圣之旅相当迷茫,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跟图尔卡纳男孩、1470号、普莱斯夫人、露西、小脚丫、亲爱的男孩等人类化石同时代的黑猩猩化石。
不管怎样,在我们的幻想世界里,黑猩猩朝圣者们和人类在中新世(Miocene)的森林空地上相遇。它们深褐色的眼睛,连同我们颜色各异的眼睛,一同凝视着1号共祖:那既是它们的祖先,也是我们的祖先。在试图想象1号共祖模样的时候,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它到底更像现代黑猩猩还是更像现代人?是介于两者之间,还是完全不同?
尽管这些猜测让人愉悦,而我也不想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但谨慎的答案是,1号共祖可能更像黑猩猩,哪怕背后的理由只是黑猩猩比我们更像其他猿类。不管是活着的生物还是化石,人类都是猿类中的异类。我想说的是,自人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以来,人类家系比黑猩猩家系发生了更多可见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像很多普通人做的那样,假定我们的祖先就是黑猩猩,或者在各个方面都像黑猩猩。所谓“缺失的一环”这种说法我们提示着这种误解的存在。你仍然会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好吧,如果我们是黑猩猩进化而来的,那为什么现在还有黑猩猩呢?”
所以,当我们和黑猩猩/倭黑猩猩朝圣者在会合点相遇,在那片中新世的林间空地上遇见我们共同的祖先,它很可能毛茸茸的就像黑猩猩一样,而且大脑的尺寸也跟黑猩猩相当。虽然不情愿,我们还是把前一章末尾那几种猜测放在一边,假定它四足行走,尽管未必跟今天黑猩猩的行动方式一模一样。它很可能既在树上生活,也在地面上花不少时间,也许就像乔纳森·金登所说的那样以蹲姿觅食。所有现有的证据都表明,它只在非洲生活。它很可能会按照当地的传统使用和制造工具,就像现代黑猩猩仍然在做的那样。它很可能是杂食性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捕猎,但它更喜欢水果。
虽然有人见过倭黑猩猩杀死小羚羊(duiker),但更为常见的是普通黑猩猩的捕猎行为,包括针对疣猴(colobus monkey)的高度协调的集体追踪行动。但对于这两个物种来说,肉食只是水果的补充,后者才是它们的主食。珍·古道尔 最先发现了黑猩猩的捕猎行为和族群间的战争,也正是她最先报道黑猩猩会用自制的工具钓白蚁,如今它们这个习惯已经举世闻名。目前还没发现倭黑猩猩有类似的行为,但这也许是因为目前对它们的研究相对较少。非洲不同地区的普通黑猩猩发展出了当地特色的工具使用传统。珍·古道尔研究的那些会钓白蚁的动物位于非洲东部,而位于西部的其他群体发展出了不同的地区传统技能,它们会用石块、木槌或者砧骨砸开坚果。这是一项需要技巧的工作。你得足够用力才能砸开果壳,又不能用力过度把果肉砸得稀烂。
最先发现了黑猩猩的捕猎行为和族群间的战争,也正是她最先报道黑猩猩会用自制的工具钓白蚁,如今它们这个习惯已经举世闻名。目前还没发现倭黑猩猩有类似的行为,但这也许是因为目前对它们的研究相对较少。非洲不同地区的普通黑猩猩发展出了当地特色的工具使用传统。珍·古道尔研究的那些会钓白蚁的动物位于非洲东部,而位于西部的其他群体发展出了不同的地区传统技能,它们会用石块、木槌或者砧骨砸开坚果。这是一项需要技巧的工作。你得足够用力才能砸开果壳,又不能用力过度把果肉砸得稀烂。
顺带一提,虽然黑猩猩砸坚果常常被当作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但达尔文出版于1871年的《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的第三章写道:
人们常说没有动物使用任何工具,但在自然环境下的黑猩猩会用石块砸开当地一种有点像核桃的坚果。
达尔文引用的证据简略而笼统,出自1843年《波士顿自然历史杂志》(Boston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登载的一名利比亚传教士的报道,文中只说“黑色类人猿,或非洲黑色大猩猩”喜欢某种不明坚果,并且“会用石头砸开它们,动作跟人一模一样”。
关于黑猩猩这种砸坚果、钓白蚁以及其他类似的习惯,特别有趣的一点在于特定地方的群体有着在当地代代流传的特定习俗。这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这种地域文化还包括了社会习惯和行为。比如,位于坦桑尼亚马哈勒山(Mahale Mountains)的一个群体有一种特别的社会性梳毛行为,被称为“握手梳毛”(grooming hand clasp)。在乌干达基巴莱森林(Kibale forest),另一个黑猩猩群体也表现出同样的仪式。但珍·古道尔在贡贝溪(Gombe Stream)做过大量研究的那个种群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有趣的是,在一群圈养的黑猩猩中也自发地出现了这个姿势并且传播开来。
在野外情况下,如果两种现代黑猩猩都像我们一样会使用工具,那就鼓励我们猜测1号共祖很可能也会这么做。我想很可能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尚未发现倭黑猩猩在野外环境下使用工具,但在圈养条件下它们把工具用得很熟练。不同地区的黑猩猩使用不同的工具这一事实也提醒着我们,如果某个特定地区缺乏这样的传统,不应该把它作为反面的证据。毕竟,珍·古道尔在贡贝溪从来没见过黑猩猩砸坚果。如果把西非砸坚果的传统介绍给它们,很可能它们也会这么干。我怀疑倭黑猩猩也是同样的情况。也许只是因为在野外对它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些迹象足以表明,1号共祖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野生猩猩同样使用工具,而且不同地区的种群有不同的习惯,这意味着地区传统的存在,也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对1号共祖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信心。而且,正如珍·古道尔还有其他人报道的那样,对工具的使用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和鸟类中间。
黑猩猩家系在今天的两个代表都属于森林猿类(forest apes),而我们则属于大草原猿类(savannah apes),更像狒狒,只不过狒狒属于猴子而不是猿。如今倭黑猩猩的分布范围局限于刚果河(River Congo)大拐弯以南和刚果河支流开赛河(Kasai River)以北的区域,而黑猩猩的活动范围好像一条宽得多的带子,位于刚果河之北,西至大西洋,东至东非大裂谷(Rift Valley),横穿整个大陆。
我们将在《丽鱼的故事》里看到,当前达尔文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一个祖先物种分裂成两个子物种,最初通常有一个偶然的隔离,而且经常是地理隔离。如果没有地理屏障,两个基因库之间的生殖混合就会使它们融为一体。在几百万年前,很可能是刚果河充当了这种阻碍基因流(gene flow)的屏障,协助两种黑猩猩物种在进化上发生分化。
其他类人猿家系也同样因为地理隔离而各自分成两个物种:西部大猩猩(western gorilla)和东部大猩猩(eastern gorilla),以及婆罗洲猩猩(Bornean orang utan)和苏门答腊猩猩(Sumatran orang utan)。这也许会让我们怀疑是不是存在过某种地理隔离,使得后来发展成人类的种群跟后来发展成黑猩猩的种群分开。一个备选是东非大裂谷的出现及其导致的东西气候差异。不过最近的发现使这个想法显得过时了。发现于肯尼亚的50万年前的黑猩猩牙齿说明,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黑猩猩不是一个纯粹的西非物种,而早期原始人类也不单单分布在东非:“托迈”的头骨来自乍得,在大裂谷以西数千千米外。更年轻但也更不为人知的羚羊河南方古猿也是如此。
不管是由于东非大裂谷还是由于其他某种地质隔离的出现,总之猿类的某个祖先种群必定曾经一分为二,留下人类在一边,黑猩猩(包括倭黑猩猩)在另一边作为这次分裂的见证,而我们的基因组里遍布着这次分裂的痕迹,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将展现其中的细节。
《黑猩猩的故事》序
我们为黑猩猩着迷,是因为它们跟我们很像。《黑猩猩的故事》将比较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而这会帮助我们确定第1会合点的年代。而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解决两个问题,因为在进行这种基因组比较时常常会遇到这两个问题。
最常遇到的那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黑猩猩的基因组跟我们有多少差异?这个问题相当棘手,主要在于很难对问题进行定义。也许可以用同一本书的两个版本来做一个合理的类比。书籍的编辑工作既会涉及句子的删减和词语的替换,也会包括各种复制–粘贴,比如挪动一段话甚至一整章的位置。这就使得我们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数值评估两个最终版本的差异。跟书籍的编辑类似,在进化过程中会有大段的DNA在基因组内移动。比如,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我们的2号染色体是由两条类人猿染色体粘接而成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有23对染色体,而其他类人猿都有24对染色体。很难说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还是只是一个小突变,毕竟所有原先的基因都得到了保留。
小段DNA会被复制或删除,而据估计,这种得失位(插入或缺失差异)的数量大约有500万个,大概占基因组的3%。但若是据此声称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组有3%的差异,却是误导性的,因为毕竟在某种意义上,一段重复的片段根本算不上什么差异。假如这本书里有一页重复的内容(比如说这页有400字),那它跟原书之间的差异应该算是400个还是一个?让我们把这种语义问题丢在一边,只看人类和黑猩猩匹配的DNA片段中单个字母的小差异。跟插入或缺失差异比起来,这种“单核苷酸变化”(single nucleotide change)要多得多,大约有3 500万个,但它们在基因组中占的比例更小,只有1%多一点。在这个非常局限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黑猩猩和人有大约98%到99%的相似性。但是请记住,这个数字不光去除了得失位,而且还不包含那些在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差异极大,以致完全无法匹配的序列。在基因密度较低的区域,特别是Y染色体上,这样的序列很常见。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这些遗传差异所在的位置。这再次涉及标准问题,因为我们的DNA里有大约一半是寄生的“垃圾”,而剩下的部分里又有很大部分很可能从未被使用过。传统意义上的基因,即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只占了人类(以及黑猩猩)DNA的1%~2%。也许另有8%的DNA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其中有些用于调控基因表达的开启或关闭,另一些有着目前仍然未知的功能。换句话说,我们的DNA中只有大约10%的序列有着活跃的功能。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这些区域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反而是基因组剩下的90%才是我们跟黑猩猩的主要差异所在,因为在这里可以发生任何突变,而不会有太大影响。对于自然选择来说,这里累积的变化是不可见的。
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是,人类和黑猩猩之间那些“有意义”的遗传差异位于何处,即哪些差异造成了我们截然不同的外形和行为。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我们的各种DNA序列实际发挥的功能,而这是未来的生物学家们的一个主要任务,甚至可能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初步研究表明,许多重要的差异并不怎么影响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反而影响了负责启动和关闭基因表达的DNA序列。《小鼠的故事》关注的正是这个有趣的问题。在下面这个《黑猩猩的故事》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少数重要突变,而是大量虽然没有功能却可以随时间自由累积的突变。正是这些突变使得我们可以确定当前会合点的年代。
黑猩猩的故事
“突变”一词会让人们联想起一些怪异生物的图像,也许出自某些肆无忌惮的实验,也许是作为某个放射性灾难的结果大批涌现,但真相多少有些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是突变体。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DNA包含了一些新的变化,而当他们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这些DNA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变化的,这些新变化就是突变。幸亏有这些突变提供原材料,而后经过自然选择成千上万年的雕琢,才生成了旅途中这些朝圣者的身体。我们每个人继承了多少新突变?这正是《黑猩猩的故事》所讲述的主题。我们对它有特别的兴趣,因为我们要用这个“突变率”(mutation rate)来校准人类进化的时间尺度。
突变有许多种,也各有不同的突变率。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只关心单字母突变,这类突变大都来自DNA复制过程中的错误。平均而言,每复制多少个DNA字母会出现一个未被纠正的错别字?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生物化学的研究观察可以告诉我们它的范围,大概每复制10亿到1 000亿个字母会出现一个错误。问题在于这个错误率是变动的,而且这样小的一个数值实际上很难准确测量,因为这要求我们考察海量的复制事件。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只关注一小段DNA经历几千万次复制之后积累的变化情况。当我们比对人类和黑猩猩的同一个基因时,这正是我们间接在做的事。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我们可以关注同一个基因在几千万个个体中的差异,比如有一份研究统计了美国所有新出现的血友病突变。最后,利用现代DNA测序技术,我们可以对一个孩子基因组中的60亿个DNA字母进行测序,把它跟孩子父母的DNA序列进行比较,从而直接统计出我们传递给后代的突变数目。这种直接的方法正在动摇原先测定的年代,使人类进化史上一些节点的年头加倍。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明白一些背后的细节。
在进入分子时代之前,化石证据使人们把黑猩猩祖先和人类祖先的分歧点定在超过1 500万年之前。1967年,来自伯克利的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艾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发表了一篇如今非常著名的论文来挑战这一年代,声称分子层面的相似性支持更近的年代,即500万年前。萨里奇和威尔逊当时并不能直接测序解读DNA,他们甚至没有使用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序列,而是采用了一种间接指标,即抗体识别特定蛋白的反应强度,他们用的是血液中的白蛋白。任何拥有免疫系统的动物都可以用于这样的研究,他们选的是家兔。这是一个巧妙的技术。先给家兔注射比方说人类的白蛋白,然后收集它们体内的抗体。这些抗人蛋白的抗体当然会跟人的白蛋白有强烈的抗原抗体反应,但同时也会跟黑猩猩、大猩猩和猴子的白蛋白有更弱一些的反应。反应的强度就可以被用来衡量不同物种间白蛋白的相似性。

1. 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这幅公牛图出自法国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洞窟。这些被发现于1940年的岩画有超过16 000年的历史,它们展现出创作者对动物形体和运动的深刻理解,以及一种良好的艺术感觉。目前并不清楚这些图画的创作目的。

2. 他们牵着手吗?
这些距今360万年的人类祖先足迹位于坦桑尼亚的拉托里,由玛丽·利基于1978年发现。这些脚印印在火山灰上,后来变成了化石,它们一直向前延伸了大概70米,很可能是由南方古猿阿法种留下的。

3. 能留下化石真是一件幸事!
来自澄江化石群的一种蠕虫(Palaeoscolex sinensis)的化石,细致地呈现了其柔软躯体的结构细节。澄江化石群可以追溯到早寒武世,距今大约5.25亿年。

4. 生命的希望
乍得沙赫人头骨,昵称“托迈”,由米歇尔·布吕内和同事在2001年发现于乍得的萨赫尔地区。

5. 3号共祖
3号共祖的复原图。这是一种大型四足猿,它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生活。就像所有大型猿一样,它应该具有相当的智力。

6.8号共祖
8号共祖是一种体形与猫相似的夜行灵长类动物,很可能也在白天活动。它应该是凭借朝前的眼睛和善于抓握的手脚在树枝上觅食的。

7. 如果火星人来到马达加斯加,他会觉得自己像是回到家乡了吗?
马达加斯加岛穆龙达瓦市的面包树大道。这种面包树(Adansonia grandidieri)是马达加斯加特有的6种面包树之一。

8. 白垩纪–古近纪大灭绝时期的地球,显示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位置[378]。
在白垩纪末期,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分裂成的大陆大致近似今天各大洲的形状,只不过欧洲仍然是一座大岛,而印度还在前往亚洲的路上。当时的气候温暖和顺,包括两极地区也是如此。实际上整个中生代都是这样,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暖流分布。

9. 在“延伸的表型”里游泳
欧洲河狸(Castor fibe)。

10. 令人惊奇的“鲸”
在自然环境中怡然自得的河马(Hippopotamus amphibius)。现今在非洲还生活着倭河马(Hexaprotodon liberiensis)。化石证据表明,在马达加斯加也许曾有3种河马一直存活到全新世。

11. 尺寸至关重要
雌性南象海豹(左)和雄性南象海豹(右)。

12.
本书第一版中的复原图(展现的是一种鼩鼱大小的夜行性生物,攀爬在低处的树枝上捕捉昆虫为食。它具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典型特征。请注意图片背景中的被子植物,它们是最晚进化诞生的主要植物类群。

13. 13号共祖
是2013年更新的复原图。


14. 这两幅地图展现了海底岩石的年龄,依据的是岩石剩磁。
上方地图显示的是6 800万年前的地球,下方地图则是今天的地球。图中的伪彩色条带表明,随着新海底的形成,白垩纪时期的海底岩石被推向大洋两侧,从而使大西洋加宽。同样的运动也发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15-A

15-B

15-C

15-D

15-E

15-F

15-G

15-H
15.自然实验
有袋类和它们的胎盘哺乳类“对应种”。
15-A:袋狼(Thylacinuscynocephalus)
15-B:灰狼(Canis lupus)
15-C:纹袋貂(Dactylopsila trivirgata)
15-D:臭鼬(Conepatushumboldtii)
15-E:袋鼹(Notoryctes typhlops)
15-F:金毛鼹(Eremitalpa granti)
15-G:蜜袋鼯(Petaurusbreviceps)
15-H:鼯鼠(Glaucomys sabrinus)。

16. 人脑对手的重视
彭菲尔德的“矮人”:按照人类身体各部位的感知觉所占据的大脑皮层区域的大小重新分配躯体的比例。

17. 同样天才的技巧?
匙吻鲟。

18. 感受过去时光的指纹
一只熔岩蜥蜴在岩石上晒太阳,而这些岩石是在火山喷发后数秒内形成的。

19. 16号共祖
这是一种形似蜥蜴的生物,行走的时候四肢外展。这幅复原图的背景是干旱的石炭纪地貌。请注意前景中的那一窝属于羊膜动物的卵。

20. 17号共祖
这位共祖很像火蜥蜴,但其前后足可能都有五根足趾。就像大多数现代两栖类那样,它很可能生活在潮湿的地方或者附近。背景是石松、木贼和树蕨,这些正是早石炭世沼泽森林中的典型植物。

21. 对非连续思维的一记重击
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周围的剑螈种群。圆点区域表示过渡地带。本图改自Stebbins(2003)。

22. 18号共祖
如复原图所示,陆地脊椎动物由肉鳍鱼进化而来。除了背鳍和不对称的尾鳍,它所有的鳍上都有明显的肉叶,也因而得名。

23. 它们“理应”再年轻2亿年
距今3.9亿年的扎海尔米行迹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四足动物脚印化石。据信这些足迹是在一个浅浅的潟湖底留下的。目前仍不清楚这些足迹是什么动物留下的,但它显然具有足趾,最左侧的脚印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24. “哪怕看到恐龙在街上散步也不过如此”
矛尾鱼,腔棘鱼的一种。摄于印度洋上科摩罗群岛海岸附近。

25-A

25-B

25-C

25-D

25-E

25-F
25. 动物的形态像橡皮泥一样灵活可塑
硬骨鱼的各种形态。
25-A:喙吻鳗
25-B:进食后的黑叉齿鱼
25-C:鲽鱼
25-D:翻车鱼
25-E:叶海龙
25-F:宽咽鱼。

26. 一个特别利落的实验
颜色发红的尼雷尔朴丽鱼(左图)和颜色发蓝的嗜虫朴丽鱼(下图)。用单色光使它们的颜色显得黯淡后,它们便可以成功杂交。


27. 每个圆表示一个基因
丽鱼的无根单倍型网络,引自Verheyen et al. [295]


28. 这是疯狂的艺术家设计的吧?
无沟双髻鲨(Sphyrna mokarran)和小齿锯鳐(Pristis microdon)。

29. 幽灵般的外形
米氏叶吻银鲛(Callorhynchus milii)有着标志性的大脑袋和看似不协调的硕大胸鳍。

30. 就像副教授拿到了永久教职?
成年的蓝海鞘(Rhopalaea crassa)。

31. 一个“火星物种”。其奇异之处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不是的样子,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我们自己
一只红色网瘤海星(Oreaster reticulatus)。它为五重轴对称提供了一个美丽的例子。

32. 23号共祖
这位共祖据信拥有脊索(一个坚硬的软骨棒),从它原始的大脑一直延伸到尾部,贯穿整个躯干。就像现代的文昌鱼一样,它应该具有厚厚的肌节(V形的肌肉块),而且应该也利用鳃过滤食物。

33. 26号共祖
这位共祖形如蠕虫,这里显示它生活在海底。它的身体由连续的重复单元构成,身体一端是头部,有一个贯穿身体的消化系统。头上应该有一个作为口部的开口,周围可能有一些辅助进食的附属结构。它可能还有眼睛。

34. 被工蚁带回巢穴的树叶好似一条宽阔的、沙沙作响的绿色河流
切叶蚁带着切下来的叶片返回蚁穴。请注意叶片上搭便车的最小的工蚁。

35. 难道火星人不会把他们分成1∶3的两组吗?
从左到右:康多利萨·赖斯(Condoleeza Rice)、科林·鲍威尔、乔治·W. 布什(George W.Bush)、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36. 细胞“以为”自己属于另一个体节
同源异形突变果蝇。

37. 进化的奇葩
一种发现于南极的蛭形轮虫(Philodina gregaria)的光镜照片。

38. 天鹅绒虫
现代有爪动物,一种南栉蚕。

39. 我们如何看待这个?
一种狄更逊水母(Dickinsonia costata),属于埃迪卡拉动物群。

40. 乘风远航
蓝色的银币水母中央可以充气,四周由触手环绕。和它的近亲帆水母一样,银币水母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改良的水螅体,而非一个群落。

41. 水母舰队
西太平洋帕劳群岛,硝水母聚集在水面上。

42. 没有多少动物可以声称自己重绘了世界地图
大堡礁上的赫伦岛。

43. 海底理发店里的信用
在红海里,裂唇鱼正在一条玫瑰副绯鲤(Parupeneus rubescens)身上工作。

44. 美化世上的海洋
一只栉水母,其长而黏的触手伸向左方,超出了画面。彩虹色来自它身体上起推进作用的“毛梳”对光线的衍射。

45. 让女神自惭形秽
爱神带水母。

46. 31号共祖
据信31号共组就是一团朝外的领细胞(参见《海绵的故事》),舞动着毛发一样的纤毛来收集细菌。这些多细胞动物进行有性生殖,在这幅复原图中可以看到在细胞群落深处自由游动的精子和卵细胞。

47. 阿氏偕老同穴
玻璃海绵阿氏偕老同穴(Euplectella aspergillum)骨针的细节。

48. 蘑菇的狂欢
白鬼笔,这是一种担子菌。

49. 38号共祖
这是一种真核单细胞生物,细胞核位于右侧底部,周围是内质网片层。细胞结构通过一种细胞骨架(图中的白色线条)来维持。这位共祖很可能既可以利用鞭子一样的鞭毛游动,也可以伸出伪足来移动。

50. 如果你曾见过一棵……
巨杉,位于美国加州红杉国家公园。

51. 把自己打成结
转运RNA的电脑图像,通过自配对形成一个小型双螺旋结构。

52-A

52-B

52-C

52-D

52-E
52. 几乎不顾一切地想要进化出眼睛
一些眼睛的例子。
52-A:珍珠鹦鹉螺(针孔型眼)
52-B:三叶虫化石(镜眼虫,拥有由方解石镜片构成的复眼,图中复眼上部仍有一些镜片保留在原位)
52-C:蚋(复眼)
52-D绿鹦鲷(鱼眼)
52-E:大雕鸮(角膜眼)。
萨里奇和威尔逊的兔子们向我们揭示,人、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分子水平上的相似性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它们之间的差异大概只有猿类跟旧世界猴之间差异的六分之一。事实上,可以经由化石实体证据确定猿类跟旧世界猴的分离时间为大约3 000万年前,因此萨里奇和威尔逊可以用这个数据来校准人类和黑猩猩的白蛋白分离的时间,于是得到了500万年前这个结论。这是运用“分子钟”的典型例子,我们将在《天鹅绒虫的故事》的序言里认真讨论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所研究的物种之间差异很大时,分子钟就会遇到麻烦,因为这些物种的分子进化速度可能天差地别。而且,用本来就问题重重的化石来做校准也同样会带来问题。不过,在猿和猴子的例子里这些都不成问题。萨里奇和威尔逊的估计也确实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着遗传学家们发展出更复杂的技术对DNA序列进行测序和分析,更多类似的研究也多多少少倾向于赞同他们的估计。近期,关于黑猩猩和人类基因分歧时间的平均估计大概在700万年前或者600万年前。
如果只考虑这些分歧时间的表面价值,我们可以用它们来计算年均突变率,前提是需要忽略那些受到自然选择的突变。只要用人类和黑猩猩序列间差异的总数,除以分歧的时间即可,不过要记得,任何两个现代物种之间分离的时间都两倍于它们跟二者的共同祖先相距的时间,因为自在共同祖先那里分道扬镳开始,突变是在两条岔路上同时累积的。人跟黑猩猩之间的单字母差异占基因组的1.23%,其中大多数对于自然选择来说都是不可见的。根据萨里奇和威尔逊的估算,人和黑猩猩的分歧时间是在600多万年前,为了计算简易,我们姑且认为二者的总分歧时间约为1 230万年,差异比例和分歧总时间可以约掉,最后得到的突变率正好是每年每10亿个DNA字母中出现一个单字母突变。
关于萨里奇和威尔逊测量突变率的间接方法就介绍到这里。那么直接测量呢?跟间接结果一致吗?最近一份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奥古斯丁·孔(Augustine Kong)和同事们对大量冰岛家庭做了测序,看到孩子跟父母的遗传差异平均为每8 000万个DNA字母出现1个突变 。如果以25年作为人类一代人的平均时间(野生黑猩猩也是如此),这就对应着每年每20亿个DNA字母中出现1个突变:大约是萨里奇和威尔逊估计的突变率的一半。如果假设人类一代人的平均时间是30年,这个数字跟历史上欧洲人的情况更为吻合,也和我们对狩猎–采集种群的研究一致,那么最后得到的年均突变率还会更小。
。如果以25年作为人类一代人的平均时间(野生黑猩猩也是如此),这就对应着每年每20亿个DNA字母中出现1个突变:大约是萨里奇和威尔逊估计的突变率的一半。如果假设人类一代人的平均时间是30年,这个数字跟历史上欧洲人的情况更为吻合,也和我们对狩猎–采集种群的研究一致,那么最后得到的年均突变率还会更小。
我们应该对这些数字多加小心。基因组测序本身会引入错误,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测序仪的错误跟真正的突变相混淆。但通过事先采取办法避免这类错误,大多数研究都趋向大致相同的答案:每年每20亿个DNA字母中出现1个突变。而且,对一个野生黑猩猩种群的类似研究也得到了跟雷克雅未克基本相同的突变率。对大型种群中疾病所致突变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最妙的是,对古代DNA的分析也支持这个结果。来自莱比锡斯万特·帕博研究组的付巧妹和同事们比较了现代人的DNA和提取自一根古代人大腿骨的DNA。这根大腿骨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河岸,被侵蚀暴露了出来。跟那时候的古人相比,我们多了4.5万年的时间积累新突变,因此两个基因组之间的差异——“缺失的突变”——可以被用来估计突变率。再一次,他们发现突变率大约为每年每20亿个字母之中有1个突变。跟之前通过分子钟计算所得的突变率比起来,新结果慢了一半,而显然不是最近才有这种较慢的突变率。乍一看,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麻烦,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麻烦并非无法解决。
我们应该为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突变率之间这两倍的差异感到忧心吗?从许多方面来看,不必如此。考虑到计算本身的困难,这两个突变率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太大,而且两个数值都跟生物化学对细胞分裂过程中复制错误的估计相吻合。不管怎样,对学习人类史前史的学生来说,突变率的腰斩有着重要意义。在追溯我们和黑猩猩共同祖先的这段路上,如果这个突变率一直是适用的,那么意味着萨里奇和威尔逊对分歧时间的估计是不准确的,应该加倍才对。我们也不会再认为人和黑猩猩的分歧发生在600万年前,而应该在大约1 200万年前。其他一些事件的发生年代也同样变得更加久远。比如,原先人们认为尼安德特人跟古人的分裂发生在35万年前,对突变率的新估计则说明它可能更应该发生在70万年前。
也许有办法调和两种估计的分歧。也许我们的突变率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更高一些,后来在形成人类家系的过程中渐渐降低,也许在通往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家系路径上也是如此。作为这个想法的一个版本,“人科减速”(hominoid slowdown)假说早在1985年就由分子人类学家莫里斯·古德曼(Morris Goodman)提了出来。古德曼的减速假说并不是专门为了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困境。他最初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跟其他动物(比如牛)比起来,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类)总体上表现出更低的突变率。减速并非异想天开,它确实有可能发生。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有着跟我们大致相同的代际突变率,但我们和现代黑猩猩每代的时间却更长,那相应地就表现出年均突变率的下降。不管采用哪种解释,就现在看来某种分子减速确实颇为可能。这会使得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的分歧点比萨里奇的估计更古老,但也许不至于有两倍那么多。我们目前的猜想是,平均而言我们的遗传分歧发生在大约1 000万年前。上一章里,我们在引用这些年代的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比如我们最近一次走出非洲的年代。不管具体的年代数字是否完全准确,人类突变率比我们原先以为的要低,而我们对年代的估计比原以为的更多变,这是没有争议的。
《黑猩猩的故事》后记
在《黑猩猩的故事》里,我们提出,人类和黑猩猩基因的平均分歧时间比我们原先以为的更久远,早在1 000万年前甚至更久之前我们就已经分道扬镳。但在这一章开头我们所引用的第1会合点的年代却是700万年到500万年前。这个明显的矛盾有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已经知道在成员互相交配的单个群体中,甚至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同一个基因不同拷贝的历史合并点可能在几百万年前,而当一个物种一分为二的时候,每个种群中的基因其实都携带着先前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基因的分离可以比物种的分离早几百万年。
只要引入几个假设将问题简化,我们就可以估计物种分歧和基因分歧相差多长时间。艾尔温·斯卡利(Aylwyn Scally)和同事们最近在分析大猩猩基因组的时候观察到,人类基因和大猩猩基因分歧的时间大约在1 200万年前。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我们假设物种的隔离彻底而迅速,这就意味着物种隔离大约发生在900万年前。相应地,如果认为人和黑猩猩的平均遗传分歧时间在1 000万年前,那么推算出的物种隔离时间就近至600万年前,具体数值取决于当时的种群规模。一般而言,平均基因分歧时间可能比种群分裂早上几百万年。尽管对于最开始的几次会合点来说这是相当大的时间差异,但随着我们的会合点开始以数千万年乃至数亿年来计量,这种差异就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所以,这种年代上的矛盾很容易解决。但是,遗传历史还会带来另一种影响,也会引出明显的矛盾。它涉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倭黑猩猩所在的位置正适合讲述这个故事。
倭黑猩猩的故事
倭黑猩猩(Pan paniscus)看起来跟普通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很像,在1929年之前它们都不被认作独立物种。尽管倭黑猩猩有着另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名字即侏儒黑猩猩,但它们并不明显比普通黑猩猩矮小。跟普通黑猩猩比起来,它的身体比例略有不同,习性也有差异,而这正是它的故事线索。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妙语总结道:“普通黑猩猩通过权为解决性问题;倭黑猩猩通过性解决权为问题……”倭黑猩猩把性作为社会交往的货币,多少有些像我们对钱的使用。他们用交配行为或交配姿态来平息纷争、彰显地位以及巩固跟其他成员的关系,不管对方是多大年龄或哪种性别,就连幼崽也不例外。恋童癖对倭黑猩猩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实际上各种“爱癖”(philia)对它们来说都不成问题。根据德瓦尔的描述,他在一群圈养的倭黑猩猩中观察到,每到喂食时间,管理员刚一靠近,雄性倭黑猩猩就立刻勃起。他推测这是在为性行为介导的食物交换做准备。雌性倭黑猩猩则成对组合,开始进行所谓的阴部摩擦(genital-genital rubbing):
两只雌性倭黑猩猩面对面,其中一只手足并用地挂在同伴身上,由对方四脚撑地把她举起来,然后双方开始一起左右摩擦肿胀的阴部,同时咧嘴尖叫着,这也许代表着她们的高潮体验。
自由恋爱的倭黑猩猩这种“嬉皮士”形象在善良的人群中引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这些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长大成人的,也许他们属于“中世纪动物寓言书”所代表的思想流派,以为动物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我们上道德课,总之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跟倭黑猩猩的关系比跟普通黑猩猩更近。我们当中的玛格丽特·米德 觉得这些温和的典范更可亲近,远胜那些热衷屠戮猴子的父权制黑猩猩。不幸的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种一厢情愿跟动物学的标准看法相违背。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大约200万年前有一位共同祖先,比1号共祖晚得多。这通常被看作倭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跟我们亲缘距离相等的证据。这是一个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普遍原则,本书第一版里《倭黑猩猩的故事》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但在这一版里多了两个小转折,我们必须承认在第一版里对它们有所忽视。这两个转折都有可能动摇动物学的教条,因此我们很乐于把这个任务交给倭黑猩猩,来解释我们的疏忽。
觉得这些温和的典范更可亲近,远胜那些热衷屠戮猴子的父权制黑猩猩。不幸的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种一厢情愿跟动物学的标准看法相违背。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大约200万年前有一位共同祖先,比1号共祖晚得多。这通常被看作倭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跟我们亲缘距离相等的证据。这是一个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普遍原则,本书第一版里《倭黑猩猩的故事》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但在这一版里多了两个小转折,我们必须承认在第一版里对它们有所忽视。这两个转折都有可能动摇动物学的教条,因此我们很乐于把这个任务交给倭黑猩猩,来解释我们的疏忽。
第一个转折来自我们对个体家系图即家谱的认识。在我们自己的家谱里,我们倾向于将亲戚们按照跟我们关系的远近来分类。这略微有些误导性。比如以你的远房表兄弟为例(你几乎一定有几个远房表兄弟,哪怕你不认识他们),也许跟你想的不一样,他们跟你的血缘距离并不完全相等。这是因为你们有不止一位共同祖先。实际上,他们的每一位祖先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你的祖先。你的某位快出五服的族兄弟也许沿着另外一条家系路径就是跟你隔了6代的表兄弟,另一位也许沿着三条不同的路径都是跟你隔了8代的远亲,诸如此类。具体的细节无关紧要,要点在于,家谱中真实的血缘亲疏程度并不是离散的,反而是一种平均的度量,一个模糊的连续体。
系谱学家们大多选择无视这些,而只关注最近的联系。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你的族兄弟同时还是你隔了6代的远房表兄弟这一事实直接被忽视了。但对于特别遥远的亲戚来说,他们之间最近的联系,亦即我们所称的共祖,并不是一种衡量一般关系的好办法。两个物种的杂交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接下来以归谬法说明一个例子。假如在约200万年前曾有一只特别敢于冒险的准倭黑猩猩(proto-bonobo)跟我们的某位南方古猿祖先进行了交配,生出了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女儿,这个女儿又杂交进入了后来会进化成人类的种群 ,也就是在也许几十万“正常”的祖先中间混入了一位混血儿。在概率上,这对今天的物种几乎没有影响。我们甚至可能没有继承她的一丁点儿DNA。不管怎样,我们如果基于最近共同祖先建立进化树,就会发现人类成了倭黑猩猩的姊妹种,反倒是普通黑猩猩成为人类和倭黑猩猩的远房表亲。这就使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之间明显的相似性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是在归谬的场景下,我们也希望把倭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共同作为我们最近的亲戚,哪怕人类跟倭黑猩猩有一丝更近的联系。尽管这是一个故意编造的荒谬例子,但杂交确实会在许多物种之间发生。即使今天所有的动物学家都把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当作真正的独立物种,但在圈养条件下它们确实可以杂交,而且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不久之前的进化史上就时有发生,只不过很难找到过硬的证据。
,也就是在也许几十万“正常”的祖先中间混入了一位混血儿。在概率上,这对今天的物种几乎没有影响。我们甚至可能没有继承她的一丁点儿DNA。不管怎样,我们如果基于最近共同祖先建立进化树,就会发现人类成了倭黑猩猩的姊妹种,反倒是普通黑猩猩成为人类和倭黑猩猩的远房表亲。这就使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之间明显的相似性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是在归谬的场景下,我们也希望把倭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共同作为我们最近的亲戚,哪怕人类跟倭黑猩猩有一丝更近的联系。尽管这是一个故意编造的荒谬例子,但杂交确实会在许多物种之间发生。即使今天所有的动物学家都把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当作真正的独立物种,但在圈养条件下它们确实可以杂交,而且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不久之前的进化史上就时有发生,只不过很难找到过硬的证据。
我们承认,这里关于混血和家谱的讨论相当理论化,特别是我们根本不指望弄清楚历史上联系这三个物种的所有杂交路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转而偏爱DNA,以及随着DNA的节奏而起舞的那些身体外在特征。我们撞到的第二个转折点就在这里。比如,历史上混血的存在就意味着从某些基因的角度来看,对于欧洲人来说尼安德特人是比非洲人更近的表亲。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有更广泛的意义。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互相冲突的关系模式常常跨越物种,哪怕像倭黑猩猩、普通黑猩猩、大猩猩和人类这样迥异的物种。而且这种冲突这并不依赖混血或杂交,而只需要一个被称为“不完全谱系分选”(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的重要过程。如果可以轻松地为树状家系图的不同分支(“支系”)做上标记,那么对这一效应的描述会更加容易。就像之前我们在《夏娃的故事》的序言里遇到的ABO血型基因,它的家系图上有“A”和“B”两个不同分支。我们曾以基因的视角看到,不管这些基因来自哪个物种,一条“A”跟另一条“A”的关系总是比跟另一条“B”更近。比如,一条来自人类的“A”和一条来自倭黑猩猩的“A”,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它们跟一条来自黑猩猩的“B”的关系更近。如果假设人类和倭黑猩猩丢掉了其他血型而只保留了“A”,同时黑猩猩丢掉了其他血型而只留下了“B”,那么从ABO基因的角度(以及输血设备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倭黑猩猩是最近的亲属,所有黑猩猩跟人类或倭黑猩猩都不相干。尽管与外观特征相矛盾,但这个生物学特征会把人类跟倭黑猩猩置于同一联盟之下。
对于血型基因来说,不太可能发生这种特殊的基因丢失,因为让上述每个物种的基因家系图上都同时保留A和B两个支系的是自然选择。这是很不寻常的情况,因为大多数基因都会持续不断地生成新的支系,这些支系往往只存在一段时间,直到最终某一条支系获得了绝对的胜利,其他支系全部走向灭绝,这样的话,只有我们祖先的种群里包含过多种遗传支系,实情也确是如此。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这种偶然灭绝现象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出乎意料的亲缘关系。
现在我们有能力窥探到基因组的秘密,确实发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即便是以前认为没有争议的基因也是如此。亲缘关系明确的物种,比如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分子水平上也依然表现出不完全的谱系分选。实际上,我们基因组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序列反对人类和黑猩猩作为彼此最近的亲属,它们或者把人和大猩猩联系得更加紧密,或者把黑猩猩和大猩猩放在一起。尽管很少得到传统分类学家的认可,但这注定意味着我们的外在特征也表现出进化关系的矛盾。凯·普吕弗(Kay Prüfer)和同事们做过的一个计算跟我们的故事关系更紧密相关。他们在2012年对倭黑猩猩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发现人类有1.6%的DNA更接近倭黑猩猩而非普通黑猩猩。最关键的是,我们有1.7%的DNA更接近普通黑猩猩而非倭黑猩猩。所以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生物水平上我们跟黑猩猩的关系(略微)近于倭黑猩猩。
这个颠覆性的结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证据,说明为什么在进化上真正重要的单元不是个体或物种,而是“基因”。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是DNA序列片段,因为哪怕是在单个基因内部,不同的字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遗传模式。实际上,根据普吕弗和同事们的估计,“人类约有25%的基因内部包含的片段跟两种黑猩猩之中的一种比跟另一种更为接近”。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担心甚至不安的问题。不论是家谱,还是遗传论证,尤其是后者,似乎已经颠覆了生命进化树这一概念的存在前提,也动摇了我们关于会合点的概念。我们将在《长臂猿的故事》的后记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只需要记住,遗传水平上亲缘关系的冲突通常只牵涉到基因组的一小部分。我们有超过70%的基因都支持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而非大猩猩作为我们最近的亲属,而我们基因组中超过90%的序列都确认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跟我们的亲缘关系是相等的。我们可以根据多数基因的观点建立生命树。或者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棵生命树,它能在真正的统计意义上呈现出最多的信息;当我们第一次接触某种生物的时候,它能告诉我们应该预期看到什么样的生物;它还让我们事先知道,不应该期待某个特定的遗传或形态特征将我们跟倭黑猩猩的关系拉得比跟普通黑猩猩还近。
顺便一提,并不应该由上述的遗传论证推论出我们跟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同等相似。自我们的共同祖先亦即1号共祖以来,如果黑猩猩的变化多于倭黑猩猩的变化,我们也许会像倭黑猩猩多于像黑猩猩,反之亦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我们跟黑猩猩属的两个表兄弟在不同的方向各有相同的地方,也许比例大致相当。但作为一个经验法则,我们不应该指望跟其中某一个比另一个更亲近,不管是在血缘上还是在外表上。这个法则适用于我们的历史之旅中的每一个朝圣者团体。
在重新出发前往我们的史前坎特伯雷之前,还有最后一项考核。我们一直在论证,必须从DNA及其物质表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朝圣者,把生物之间的关系看作家系图之间的平均。不过,这跟共祖以及会合点的概念多少有些冲突。一群个体的最近共同祖先或共祖是家谱上的概念,针对的是一群个体的家系图,而非基因家系图。为什么要用共祖来决定我们旅程的步伐节奏?
在这本书中,尽管我们采用基因家系图来定位我们和其他生物的关系,但用它来测定我们旅程中的年代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基因组中不同片段的合并点的时间差异极大。基因分歧的时间可以相差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没错,我们是可以采用一个平均值,但这个平均值跟历史上任何有意义的时间点都没有关系。或者我们可以把会合点定在物种形成的时间。然而这依然是一个缺乏明确定义的时间,因为物种的隔离很少是瞬时完成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哪怕是像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样“真正”的物种,也依然保留着种间杂交的能力。很少存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我们可以宣称某个物种从此一分为二。规定一个确切的物种形成时间,几乎就是在生物连续体上强行规定一个人为选择的值。如果我们想选择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一个里程碑,唯有一个选择,即两个现代物种最近共享的那个系谱学祖先所在的那个历史时间点。这个点会比平均遗传分歧时间更晚,而且由于杂交的存在,还晚于大多数人对“物种形成时间”的估计。但由于我们的共祖代表着历史上某个精确无疑的时刻,由它们来决定我们朝圣的步伐是我们能做出的最有原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