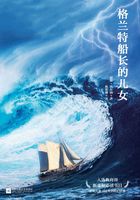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横穿智利
格里那凡爵士的旅行队由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引领着。带队的骡夫头头是一个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年的英国人。他干的行当就是租骡子给旅行者,并带着他们翻过前方高低岩的各处隘口,过了山隘之后,他便把旅行者们交给一个熟悉阿根廷大草原的向导。这个英国人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同骡子、同印第安人打交道并生活在一起,但却并没忘记自己的母语,因此,格里那凡爵士与他交流起来没有任何困难,这对爵士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巴加内尔的西班牙文当地人还是听不懂。
骡夫头头在智利语中被称为“卡塔巴”。这个原籍英国的卡塔巴雇用着两名当地的骡夫,土语称之为“培翁”,还雇着一个帮手,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培翁负责照管驮行李的骡子,小男孩则骑着当地称之为“马德琳娜”的挂着铃铛的小母马,走在骡队的前头,身后跟着十匹骡子。十匹骡子中,七匹由旅行者们骑着,卡塔巴自己骑了一匹,还有两匹驮着行李和几匹布。这几匹布是为了与平原地区的商号套近乎所必备的。培翁们照例是徒步行走的。有如此这般的装备,横穿智利的旅途,在安全与速度方面,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翻越安第斯山并非易事,必须有强壮的骡子才行。翻山越岭的骡子中,最好的当属阿根廷的骡子,它们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培育,比原始品种强壮得多。它们对饲料并不挑剔,每天只喝一次水,八小时可走十英里,驮着十四阿罗伯 的东西也毫不在乎。
的东西也毫不在乎。
连接两大洋的这条路上,没有客栈。路上吃的是肉干、辣椒拌饭和可能在途中碰到的猎物;喝的则是山中的瀑布水和平原上的溪水,内中滴上几滴甜酒。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牛角壶,装着些这种甜酒,给水提提味儿。不过,旅行者必须注意,含酒精的饮料则不能多喝,因为在这种地区,人的神经系统很容易受到刺激,喝含酒精的饮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被子、褥子全都用绣花宽边带系在马鞍子上;马鞍子是当地产的,土语称之为“勒加驮”,系当地产的羊皮制成的,一面硝光了,另一面仍留着羊毛。旅行者用这暖和的被褥紧裹着,不用担心夜间的潮湿,可以睡得很香甜。
格里那凡爵士是个能屈能伸的人,他很会旅行,也能适应各地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他替自己和同伴们准备好了智利服装。巴加内尔和小罗伯特这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把头一套进那智利大斗篷,脚一蹬进长皮靴,就乐得什么似的。大斗篷土语称为“篷罩”,系一大块格子花呢,中间挖了个洞;皮靴是用小马后腿上的皮制成的。另外,他们一行人骑的骡子打扮得非常漂亮,嘴里咬着的是阿拉伯式的嚼铁,两端系着皮制的缰绳,可以当作鞭子使用;头上配有金光闪闪的络头;背上搭着颜色鲜艳的褡裢,里面装着当天食用的干粮。巴加内尔一向粗心大意,骑上去时,总要挨骡子踢上几下。待他爬上鞍子时,他就优哉游哉地那么坐着,腰间挂着他那形影不离的大望远镜,脚紧踩着脚蹬,缰绳松松的,任由骡子信步走着。他对自己的坐骑十分满意,因为它是经过很好的训练的。而小罗伯特则不然,他一爬上骡背,便俨然是一流骑手似的。
全队开始出发了。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尽管烈日当空,但是由于海水的调节作用,空气却很凉爽。这一小队人马沿着塔尔卡瓦诺湾的曲折海岸迅速前行,再往南去三十英里,就到三十七度线的末端了。第一天,大家疾速行进在干涸了的滩涂地的芦苇丛中,彼此间并不搭话。临别时的赠言依然萦绕在旅行者们的脑海之中。邓肯号冒出的黑烟,渐渐地在天际消失,但仍依稀可辨。大家都一言不发,只有那位勤奋好学的地理学家在自问自答地练习着他那西班牙语。
不仅仅是旅行者们不言声,连那位卡塔巴也少言寡语,这是他的职业使然,他对培翁都很少说话。两个培翁堪称行家里手,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见骡子停下,他们便吆喝一声,催促它们快走;再不走,就极其准确地扔一个石子去砸它们,它们便赶忙往前走去。如果兜带松了,或是缰绳出溜了,培翁们便脱下斗篷,蒙住骡子脑袋,把兜带或缰绳弄弄好,然后让骡子继续往前走去。
骡夫们的习惯是,早晨八点吃早饭,出发,一直走到下午四点,停下,过夜。格里那凡尊重他们的这一习惯。这一天,当卡塔巴发出歇息的信号时,这一小队人正走到海湾南端的阿罗哥城,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离开过海水拍击着海岸的海洋边缘。他们还得往西走上二十英里,一直走到卡内罗湾,才到三十七度线的端点。他们已经走遍了滨海地区,但是并未寻找到一点沉船的痕迹。再往下走,也同样是一无所获,因此,他们便以阿罗哥城为出发点,向东寻去,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
他们进入阿罗哥城,找了一家十分简陋的小客栈下榻。
阿罗哥城是阿罗加尼亚的首都。该国国土长一百五十英里,宽三十英里,居民为毛鲁什族 ,系智利族的一支支脉,诗人爱尔西拉
,系智利族的一支支脉,诗人爱尔西拉 曾经赞美过他们。毛鲁什族人身体强健,性格高傲,是南北美洲中从未受过外族统治的唯一的一族。阿罗哥城曾一度隶属于西班牙人,但当地居民却从未屈服过;他们当时就像现在抵御智利人一样抵抗着西班牙人,其独立的旗帜——蓝底白星旗始终在那座构筑起防御工事的山顶上高高地飘扬着。
曾经赞美过他们。毛鲁什族人身体强健,性格高傲,是南北美洲中从未受过外族统治的唯一的一族。阿罗哥城曾一度隶属于西班牙人,但当地居民却从未屈服过;他们当时就像现在抵御智利人一样抵抗着西班牙人,其独立的旗帜——蓝底白星旗始终在那座构筑起防御工事的山顶上高高地飘扬着。
趁别人在准备晚饭的时候,格里那凡爵士、巴加内尔和那个卡塔巴在茅草顶的房屋之间散着步。阿罗哥城除了一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可看的了。格里那凡爵士尝试着打听一点有关沉船的事,但却一无所获。巴加内尔说的西班牙语当地居民听不懂,因为阿罗哥城的居民说的是一种直到麦哲伦海峡都通用的土语——阿罗加尼亚语,不会西班牙语,巴加内尔讲的西班牙语再流利也不管用。格里那凡爵士挺失望的,既然无法交流,就只好自己用眼睛多看多观察了。他感到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可以随意观察,看到了毛鲁什族各种类型的人。他们身材高大,脸扁平扁平的,肤色呈古铜色,下巴无毛,目光充满疑惑,脑袋宽大,又黑又长的头发披散着。他们成天无所事事的样子,仿佛是一些处于和平时期无用武之地的战士;而女人们却很能吃苦,终日忙忙碌碌,刷马、擦拭武器、耕田犁地、打猎等,全都由她们去干。此外,她们还得抽空编制斗篷——那种蓝蓝的“篷罩”。这种篷罩编织一件费时约两年,最便宜的也得卖上一百美元。
总的说来,毛鲁什人风俗粗野不羁,人类的坏习惯他们全都沾染上了,唯一的美德就是热爱独立自主。
“他们可真像是斯巴达 人啊!”巴加内尔散步归来,围坐在院子里吃饭时,不禁赞扬道。
人啊!”巴加内尔散步归来,围坐在院子里吃饭时,不禁赞扬道。
大家都觉得这位地理学家言过其实,赞扬得有点过分。后来,他还说,在游览该城时,他那颗法兰西人的心跳动得十分激烈,弄得大家更加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少校问他为何他的那颗心会如此激烈地跳动,他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他有一位同乡不久前曾经当过阿罗加尼亚国王。少校问他此人姓甚名谁。巴加内尔不无自豪地说此人名叫多伦斯,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好人,满脸的络腮胡子,早年曾在白里各 当过律师,后来当上了阿罗加尼亚的国王,后来又被赶下了御座,罪名是“忘恩负义”。少校闻言,不觉鄙夷地一笑,巴加内尔却正儿八经地回答他说,一个律师做一个好国王,也许要比一个国王想当个好律师容易得多。大家听了他的解说,忍俊不禁,举起玉米酒,每人喝了几滴,以祝愿阿罗加尼亚的废王奥莱利·安托尼一世身体健康。数小时之后,大家纷纷裹上自己的篷罩,进入了梦乡。
当过律师,后来当上了阿罗加尼亚的国王,后来又被赶下了御座,罪名是“忘恩负义”。少校闻言,不觉鄙夷地一笑,巴加内尔却正儿八经地回答他说,一个律师做一个好国王,也许要比一个国王想当个好律师容易得多。大家听了他的解说,忍俊不禁,举起玉米酒,每人喝了几滴,以祝愿阿罗加尼亚的废王奥莱利·安托尼一世身体健康。数小时之后,大家纷纷裹上自己的篷罩,进入了梦乡。
翌日,早晨八点,马德琳娜打头,培翁押后,这一小队人马又向东踏上了三十七度线的路径。他们穿越了阿罗加尼亚的那片满地葡萄树和成群的肥羊的丰饶地区,然后,人烟逐渐稀少。走上一英里多路,也难得见到闻名全美洲的印第安人驯马人——“拉斯特勒阿多”的茅草棚。他们有时会看到一个废弃了的驿站,那是在平原上游荡的土人们用作避风躲雨的地方。这一天,他们遇上了两条河——杜克拉河和巴尔河挡住了去路。但卡塔巴发现了一处浅滩,领着大伙儿顺利地趟过河去。前方天际,安第斯山脉隐约可见;向此延伸的尖峰以及一座座圆圆的山峦影影绰绰的。安第斯山脉是整个新大陆的脊梁骨,他们此刻所见到的是这巨大的脊梁骨的最低矮的部分。
到了下午四点,他们已经一口气走了三十五英里,便在旷野中的一丛巨大的野石榴树下停了下来。骡子卸去了鞍辔,松了缰绳,自由自在地跑到草地上去吃草了;大家解开褡裢吃起了肉干和辣椒饭,然后,把被褥解开,铺在地上,安然入睡。培翁和卡塔巴轮流担任守夜者。
天气如此之好,旅行者们,包括小罗伯特在内,全都健健康康,而且旅途又十分顺利,所以大家认为应该乘兴勇往直前。因此,第三天,大家行进的速度更加快了。渡过了伯尔激流之后,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便在西班牙属的智利和土人所属的独立智利之间的标标河边过夜。这一天他们又走了三十五英里地。地理状况依然如前,肥沃的土地上,长满了宫人草、木本紫罗兰、曼陀罗花、金花仙人掌。鹭鸶、鸱枭和躲避鹞鹰的黄雀和鹫鹏栖息于此。丛莽之中,有黑斑虎 出没。但是,却未见什么土著人,难得遇上几个被称为“瓜索”的,也就是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他们光脚上捆扎着大马刺,刺得马儿浑身是血,策马飞奔,一闪而过。沿途找不到一个可以打听点事的人,什么消息也无法获得。格里那凡爵士决定无须浪费时间去做无益的查访,因为他推测,如果格兰特船长真的成了印第安人的俘虏了,那他早就被掳往安第斯山那边去了。只有翻过山去,到了山那边的草原里去访查,也许才会有所收获。因此,只好坚持不懈地继续向前,迅速地往前赶。
出没。但是,却未见什么土著人,难得遇上几个被称为“瓜索”的,也就是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他们光脚上捆扎着大马刺,刺得马儿浑身是血,策马飞奔,一闪而过。沿途找不到一个可以打听点事的人,什么消息也无法获得。格里那凡爵士决定无须浪费时间去做无益的查访,因为他推测,如果格兰特船长真的成了印第安人的俘虏了,那他早就被掳往安第斯山那边去了。只有翻过山去,到了山那边的草原里去访查,也许才会有所收获。因此,只好坚持不懈地继续向前,迅速地往前赶。
17日,依然按头几日的时间和习惯顺序出发上路了。小罗伯特总是独出心裁,不遵守秩序,一高兴起来,便会冲到马德琳娜前面去,没少让自己的那头坐骑吃苦头。待到格里那凡爵士大声呵斥了,他才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的顺序位置。
道路开始变得崎岖了一些。地面高低起伏,说明前面就是山路了,而且溪流也多了起来,都在随坡就势地淙淙地流淌着。巴加内尔不时地翻看地图,有些溪流地图上没有标明,他一看便气不打一处来,火气很大,令人觉得又可爱又可笑。
“一条溪流竟然没有名字,这不就等于是没有身份证吗!”他气愤地说,“在地理学的法律上,这就表示它并不存在。”
因此,他便毫不谦让地给那些没有名字的河流冠上了名称,标在了地图上,而且他所标示的名称都是用的西班牙文,听起来既好听又响亮。
“西班牙语真妙!”他老这么说,“多么美好的语言啊!这种语言像是由金属构成的,里面起码含有百分之七十八的铜,百分之二十二的锡,如同铸钟的青铜一般!”
“这么美好的语言,您学得颇有进步吧?”格里那凡爵士问他道。
“当然有进步啰,亲爱的爵士。啊!若不是因为语音语调的问题!……别人也就能听得懂我说的话了!”
为了把语言语调弄准确了,巴加内尔一路上不停地大声练着,嗓子都有点哑了。但他并未因此就忘记提出他对地理学上的一些看法。他真的是深谙地理学,看来世界上,在这个方面,他可真是独一无二、无出其右的了。只要格里那凡爵士一向卡塔巴提个什么问题,想了解当地的一个什么特点,他的这位博学的同伴就会抢先回答了他的问题,说得还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把个卡塔巴惊得目瞪口呆,钦佩不已。
这一天,将近十点钟光景,他们遇上了一条横切着他们所走的那条直线上的路。格里那凡爵士自然而然地便问起了这条路来。而巴加内尔也自然而然地抢先答道:
“这条路是从荣伯尔通向洛杉矶的。”
格里那凡爵士看着卡塔巴。
“没错,完全正确。”卡塔巴回答道。
接着,格里那凡爵士又转向巴加内尔问道:
“这里您来过?”
“当然来过。”巴加内尔一本正经地说。
“也是骑骡子来的?”
“不是,是坐着安乐椅来的。”
卡塔巴没有听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只好耸了耸肩膀,回到队伍里去了。
下午五点光景,这支队伍在一处不太深的山坳坳里歇了下来。山坳位于小罗哈城北面几英里路的地方。这儿已是安第斯山的最低的阶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