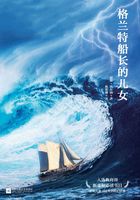
第九章 麦哲伦海峡
众人得知巴加内尔愿意留下之后,无不高兴异常。小罗伯特更是兴奋不已,一下子跳了起来,搂住巴加内尔的脖子,几乎把我们的这位可敬可爱的秘书先生弄得站立不稳,说道:“好个可爱的孩子,我要教教他地理学方面的知识。”
我们知道,约翰·孟格尔已经在负责把小罗伯特培养成一名好水手,格里那凡爵士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少校则要把他训练成一个沉着稳重的孩子,海伦夫人要把他教育成为一个慷慨大度的人,玛丽·格兰特则要把弟弟培养成一个知恩图报、绝不辜负这些热心仁爱的老师们的学生。如此看来,小罗伯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绅士。
邓肯号很快便加满燃料,离开了这片凄风苦雨的海域,向西驶去,沿着巴西海岸航行着。9月7日,突然刮起一阵顺风,把它吹送过了赤道线,驶入了南半球。
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就这样顺利地在进行着。船上的人一个个都怀着极大的希望。在这寻找失踪的格兰特船长的远航中,成功的希望在日益增长。最有信心的当属孟格尔船长。不过,他的信心源自他的愿望——真心实意地要让玛丽·格兰特小姐得到幸福与安慰。他对这位少女格外地关怀;他想把自己的这份感情隐藏起来,但是,到头来,除了玛丽·格兰特和他两人并不觉得而外,其他的人全都心知肚明。
而我们的那位知识渊博的地理学家巴加内尔先生,他也许是南半球上最幸福的人;他成天地在研究地图,把方形厅的桌子全都铺满了,致使奥比内先生每天都因为无法布置餐桌而与他发生争执。不过,楼舱里的人则全都支持巴加内尔,当然,少校不在此列,因为少校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尤其是到了用餐的时候。另外,巴加内尔还在大副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大堆破旧书籍,其中有几本西班牙文著作,于是,他便下决心学习塞万提斯 的语言,而这种语言,船上的人全都不懂。他觉得学会西班牙文有利于他在智利沿海地区的调查研究。他具有语言天分,希望到康塞普西翁之后,能够流利地运用这种语言。因此,他在抓紧时间拼命地学,大家一天到晚听见他在叽里呱啦地练着这种语言。
的语言,而这种语言,船上的人全都不懂。他觉得学会西班牙文有利于他在智利沿海地区的调查研究。他具有语言天分,希望到康塞普西翁之后,能够流利地运用这种语言。因此,他在抓紧时间拼命地学,大家一天到晚听见他在叽里呱啦地练着这种语言。
每当他闲下来时,他就教小罗伯特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并把邓肯号途经的那一带海岸的历史讲给他听。
9月10日,邓肯号正驶经南纬五度七十三分、西经三十一度十五分的海面。这一天,格里那凡爵士听到了也许连知识渊博的人都不一定知道的历史事实。巴加内尔在给大家讲解美洲发现史。他在讲述邓肯号所追寻其足迹的那些大航海家时,首先提及了哥伦布。讲到最后,他说这位著名的热那亚 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惊讶不已,但巴加内尔却言之凿凿地说道:
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惊讶不已,但巴加内尔却言之凿凿地说道:
“这一点是绝对确实无疑的,我这并不是想要抹杀哥伦布的光荣业绩,但是,事实该怎么样就应该是怎么样。在15世纪末,人们一心一意地只想着一件事:如何找到一条前往亚洲的更便捷的道路?如何更方便地从西方走到东方?总之,如何才能找出一条捷径,前往‘香料之国’ ?这就是哥伦布想要解决的问题。他一共航行了四次;他到达了美洲,在库马纳、洪都拉斯、莫斯基托、尼加拉瓜、维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这就是哥伦布想要解决的问题。他一共航行了四次;他到达了美洲,在库马纳、洪都拉斯、莫斯基托、尼加拉瓜、维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一带登陆,而他却把这一带海岸全都误以为是日本和中国的地方。所以一直到死,哥伦布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死后连他的名字都未能留给这新大陆作为纪念!”
一带登陆,而他却把这一带海岸全都误以为是日本和中国的地方。所以一直到死,哥伦布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死后连他的名字都未能留给这新大陆作为纪念!”
“我打心底里愿意相信您所说的这番话,亲爱的巴加内尔。”格里那凡爵士说道,“可是,您毕竟还是让我感到惊讶。我倒想请问您,对于哥伦布的这一发现,后来是哪些航海家给弄明白了的呢?”
“是哥伦布死后的那些人。其中,首先是与哥伦布一起航行的奥热达,还有品吞、威斯普奇、门多萨、巴斯提达斯、加伯拉尔、索利斯、巴尔伯等。这些航海家都沿着美洲东海岸航行,由此向南地勘测美洲海岸的情况。他们早在三百六十年前,就同我们今天一样,被这股海流推着,向前行驶着。你们知道不,朋友们?我们穿越的赤道线的地方,正是15世纪末品吞所驶过的地方。我们现已接近南纬八度,而品吞当年正是在南纬八度驶抵巴西陆地的。一年后,葡萄牙人加伯拉尔一直往下,抵达色居罗港。后来,威斯普奇在他1502年的第三次远航过程中,更加向南边驶去。而到了1508年,品吞和索利斯共同航行,探测了美洲沿岸各地。1514年,索利斯发现了拉巴拉塔河口,在那儿被当地土著人给吃掉了,绕过美洲南端的光荣业绩只好留给麦哲伦去完成了。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于1519年率领着一支由五条船组成的船队,沿着巴塔戈尼亚的海岸往南驶去,终于发现了德塞多港、圣朱利安港。在圣朱利安港停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麦哲伦又率队航行到南纬五十二度的海域,发现了一千一百童女峡,即现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1520年11月8日,麦哲伦穿过海峡,进入了太平洋。他看见天边有一片新的海面在阳光下闪烁,其喜悦、激动简直难以用语言来描述。”
“啊,我真想生活在那个时候,巴加内尔先生。”小罗伯特听了这番描述,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说道。
“我也与您具有同感呀,我的孩子。如果老天让我早生三百年,我想我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我们就要深感遗憾了,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说道,“如果您早生三百年的话,也就不可能在这儿跟我们讲述这段动人的故事了!”
“这倒无伤大雅,夫人,没有我,也会有别人代替我来讲述的。此人甚至还会告诉您,西海岸的探险应归功于皮萨尔 兄弟。这两位勇敢的探险家创建了许多宏伟的城市:库斯科、基多、利马、圣地亚哥、比利亚里卡、瓦尔帕莱索,以及邓肯号将要抵达的康塞普西翁。当时,皮萨尔兄弟的发现与麦哲伦的发现正好联系起来了,因此地图上才有了美洲的海岸线,旧大陆的学者们对此非常高兴。”
兄弟。这两位勇敢的探险家创建了许多宏伟的城市:库斯科、基多、利马、圣地亚哥、比利亚里卡、瓦尔帕莱索,以及邓肯号将要抵达的康塞普西翁。当时,皮萨尔兄弟的发现与麦哲伦的发现正好联系起来了,因此地图上才有了美洲的海岸线,旧大陆的学者们对此非常高兴。”
“哼!要是我,我就不会高兴。”小罗伯特嘟囔着。
“那为什么呀?”玛丽眼睛紧盯着自己那爱听这类探险故事的弟弟问道。
“是呀,我的孩子,您为什么会不高兴呀?”格里那凡爵士面带微笑地问道。
“因为要是我的话,我就一定还要看看麦哲伦海峡南边都有些什么。”
“啊,我真想生活在那个时候,巴加内尔先生。”小罗伯特听了这番描述,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说道。
“对极了,小朋友。”巴内加尔说道,“我也是呀,我也想要知道美洲大陆是否一直延伸到南极,还是像德勒克所推测的那样,与南极中间还隔着一片海洋……这位德勒克是您的同乡,爵士……所以,假若罗伯特·格兰特和雅克·巴加内尔生在17世纪的话,他们肯定是会跟随着索珍和勒美尔一道出发的,因为这两位荷兰航海家正是想要揭开地理学上的这个谜的。”
“他俩也是大学者吗?”海伦夫人问道。
“不,他们是两个大胆的商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探险在科学上的意义。当时,荷兰有个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对穿过麦哲伦海峡的所有贸易往来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你们知道,在当时,西方国家到东方的亚洲,只有穿越麦哲伦海峡这一条通道,所以这种控制权成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垄断。有一些商人便想摆脱这种垄断,另辟蹊径,想另找一个海峡通过。其中有一位,名叫伊萨克·勒美尔,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十分聪慧的人。他便出资组织一次远航,让他的侄子雅各伯·勒美尔和一位优秀的水手来指挥,这个水手名叫索珍,祖籍霍恩。这两位勇敢的航海家于1615年6月起航,大约比麦哲伦晚了近一百年,他们在火地岛和斯达腾岛之间发现了勒美尔海峡。1616年2月16日,他们绕过了有名的合恩角,亦称‘风暴角’,比好望角 更加名副其实。”
更加名副其实。”
“说真的,我好想去那儿探探险啊!”小罗伯特羡慕地说。
“您要是去了那儿,孩子,您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的。”巴加内尔说得愈加带劲儿,“您想想呀,有什么能与一个航海家在自己的海图上把自己的新发现一点一点地标出来更令人高兴的呀!他看看陆地在逐渐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一个一个的小岛,一个一个的海岬,仿佛是从波涛之中涌现了出来似的!开始时,标出的界线十分模糊,断断续续,互不连贯!这儿是一片隔离开的土地,那儿是一个孤立的小港,稍远处是一个偏僻的海湾。随后,随着陆陆续续有了新的发现,这些孤立的地方便连成了一线,海图上的虚线转而成了实线,海岸线呈现出了弓形,海角也与实实在在的海边陆地连接了起来。最后,一片新的大陆呈现在地球上,有湖泊,有河流,有山峦,有峡谷,有平原,有村落,有乡镇,有都市,瑰丽壮观,煞是好看!啊!朋友们,新大陆的发现者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们同发明家一样,功不可没!只是非常可惜,现在,这种伟大的事业,如同矿山一样,被人家开采殆尽了。新大陆,新世界,全都被人家找到了,被人家踏勘过了,我们是地理学上的迟到者,已经是无用武之地了!”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亲爱的巴加内尔。”格里那凡爵士说道。
“哪里还有用武之地嘛!”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就大有用武之地呀!”
此时此刻,邓肯号正在威斯普奇和麦哲伦等伟人所经过的航道上疾速行驶着。9月15日,邓肯号越过了冬至线,正对着那著名的麦哲伦海峡的入口。巴塔戈尼亚的南部海岸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眼前,但只是呈现出一条细线,影影绰绰地浮现在水天相连处。邓肯号在十海里之外沿着这一带的海岸在往南驶去,即使举起巴加内尔的那架大望远镜,也只能看见那美洲海岸的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
9月25日,邓肯号已经驶抵与麦哲伦海峡同一纬度的地方。它毫不犹豫地驶进了海峡。一般来说,汽船都喜欢经由这条路线进入太平洋。海峡的真正长度只有三百七十六海里,海水都很深,即使大吨位的船只也都可以靠近海岸行驶。而且海底平坦,淡水站又很多;内河湖泊也不少,鱼类资源丰富,森林遍布,猎物众多;停泊点也很多,而且安全而便利。总而言之,这个海峡优点多多,是勒美尔海峡和多暗礁多风暴的合恩角所无法比拟的。
驶入海峡的最初几个小时,也就是说,在开头的六十至八十海里的航程中,一直到驶抵格利高里角为止,海岸都是既低矮又平坦的,而且多沙。雅克·巴加内尔贪婪地观察着这个海峡,没有漏掉它的任何一点。在海峡中得行驶三十六个小时,两岸风光旖旎,令人赏心悦目,我们的这位学者是不会在南半球那灿烂阳光下对观赏感到厌烦的。北岸没有人烟,而南边火地岛的光秃秃的岩石上有几个穷兮兮的火地岛人在游荡。巴加内尔没有看到巴塔戈尼亚人,不免感到有点失望,但他的同伴们却并不以为然。
“在巴塔戈尼亚不见巴塔戈尼亚人,那还叫什么巴塔戈尼亚呀!”他说道。
“您先别着急,我可敬的地理学家。”格里那凡爵士说,“我们总会见到巴塔戈尼亚人的。”
“那可不一定。”
“为什么呀?巴塔戈尼亚人是存在的呀?”海伦夫人说。
“我表示怀疑,夫人,因为我并没有看见他们。”
“至少,巴塔戈尼亚这个名称源自西班牙文的‘巴塔贡’,而‘巴塔贡’也就是‘大脚板’的意思。巴塔戈尼亚人既然被人称作‘大脚板’,那就说明他们是存在的,并非出自人们的想象。”
“唉,名字是无关紧要的。”巴加内尔回答道,他像是故意坚持己见以引起争论似的,“何况,别人并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应该叫什么名字!”
“这叫什么话嘛!”格里那凡爵士反驳道,“少校,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不知道。”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道,“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您真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少校。”巴加内尔又说,“您最终会知道的。这地方的土著人被称为巴塔戈尼亚人,是麦哲伦给他们取的名字,而火地岛人则称他们为提尔门人,智利人称他们为高卡惠人,卡门一带的移民称他们为特惠尔什人,阿罗加尼亚人称他们为惠利什人,旅行家波根维尔称他们为寿哈,法尔克纳称他们为特惠尔里特。他们自己则称呼自己为伊纳肯,‘伊纳肯’在古地方言中也就是‘人’的意思。我倒想请问你们,这么多称谓有谁能弄得清楚?再说,一个民族竟然会有这么多名称,那它是否真的存在,岂不令人怀疑?”
“好一番感慨!”海伦夫人说。
“就算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的议论是不无道理的。”格里那凡爵士说道,“但他总不能不承认,巴塔戈尼亚人的名称虽然很多,颇有问题,可他们的身材之高大起码是为大家所确认的吧!”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巴加内尔回答。
“他们的身材确实很高呀。”格里那凡爵士说。
“是不是很高,我不清楚。”
“那是不是很矮小呀?”海伦夫人问。
“没有人敢肯定。”
“那就是不高不矮啰?”麦克那布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说道。
“这我仍然不清楚。”
“您这也太过分了。”格里那凡爵士大声说道,“亲眼见到过巴塔戈尼亚人的旅行家们就……”
“亲眼见到过巴塔戈尼亚人的旅行家们的说法就不尽相同。”地理学家坚持己见,回答道,“麦哲伦就说过,他的头还到不了巴塔戈尼亚人的腰间哩!”
“这不就说明他们身材极其高大吗?”
“是呀,可是德勒克却说,最高的巴塔戈尼亚人还没有普通的英国人高。”
“哼!跟英国人比个什么劲儿呀。”少校没好气地说。
“加文迪施肯定地说,巴塔戈尼亚人高大魁梧。”巴加内尔又说道,“霍金斯说他们宛如巨人一般。勒美尔和索珍说他们身高达十一英尺。”
“这不就对了吗?这些人的话总是可信的吧?”格里那凡爵士说。
“是的。但是,伍德、纳波罗和法尔克纳却说他们是中等身材,这话也不能不信呀!拜伦·拉吉罗德、波根维尔、瓦利斯、卡特莱说巴塔戈尼亚人身高一般为六点六英尺,而了解这一带地域的学者多比尼先生则说他们是中等身材,身高为五点四英尺,他们的话也不可不信的吧?”
“那么,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哪一种接近事实呢?”海伦夫人问道。
“哪一种接近事实?”巴加内尔说,“真实的情况是,巴塔戈尼亚人上身长下身短。因此,有人打趣地说,巴塔戈尼亚人坐着有六英尺高,站着却只剩下五英尺了。”
“哈哈!这话十分俏皮,我亲爱的学者。”格里那凡爵士说。
“更俏皮的话应该是,他们并不存在,这么一来,各种矛盾的说法就统一起来了。为了结束这场辩论,朋友们,我想再说一句,让大家都觉得开心:麦哲伦海峡漂亮极了,即使没有巴塔戈尼亚人,它也不失其美丽的!”
此刻,邓肯号正绕着布伦瑞克半岛行驶,两边的风景美不胜收。邓肯号绕过了格利高里角后又行驶了七十海里,把奔德·亚利纳大监牢给抛在了右舷外边了。在有一段航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智利国旗和教堂的钟楼在森林中隐现。此刻,海峡两边突兀着花岗岩巉岩,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高山,山脚隐没在森林之中,山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高耸入云;西南面的塔尔恩峰,凌空兀立,高达六千五百英尺;入夜时分,黄昏暮霭时间很长;阳光渐渐地融为多种色度,柔和温馨;天上逐渐地变得群星灿烂;南极的星座为航海者指引着道路。在矇胧的夜色中,星光代替了文明海岸的灯塔,邓肯号并未在沿途许多的方便港湾停泊,而是大胆地继续向前驶去。有时,它的帆架掠过俯临水面的南极榉的枝梢;有时,它的螺旋桨拍击着水波,惊起了各种水鸟。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些断垣残壁,几座坍塌了的建筑物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庞大,这都是殖民地废弃了的凄凉遗迹,在向那片丰饶的海岸和猎物多多的森林表示着抗议。邓肯号此刻正行驶在饥饿港前。
1581年,西班牙人萨明多带着四百个移民来到这儿定居,建立起圣菲利普城。由于严寒和饥饿,定居者纷纷死去。到了1587年,这儿只剩下了一个人。他在废墟的荒凉寂寥之中,苦苦地挣扎了六个年头!
日出时分,邓肯号在重重的山峡中行驶着,两岸是茂密的森林,榉树、榛树、枫树交错混杂地生长在一起。密林中不时地冒出一座座青葱翠绿的圆圆的山岭,野花野草在散发着清香,弥漫在空中!远处可见布兰克纪念塔高高地矗立着。邓肯号经过了圣尼古拉湾口。此湾原本由波根维尔命名为“法国人湾”;海湾远处,可见大群的海豹和鲸鱼在水中嬉戏;鲸鱼看来体积庞大,因为在四海里之外都能看见它们喷出的水柱。最后,邓肯号绕过了佛罗瓦德角,角上还密密麻麻地满布着尖利的残冰。海峡对岸,火地岛上,高达六千英尺的萨明多峰突兀而立。那是一丛巉岩,被带状的云层给分隔开来,宛如一座座“空中岛屿”。到了佛罗瓦德角,美洲大陆就真的走到了尽头,因为合恩角只不过是位于南纬五十六度的荒凉海域中的一块大石岩罢了。
绕过尖端,海峡变得狭窄了。它的一边为布伦瑞克半岛,另一边是德索拉西翁岛。后者系一长形岛,两边为成百上千的小岛所环绕,如同一头大鲸鱼搁浅在卵石滩上一样。如此支离破碎的南美洲的顶端,与非洲、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整齐而清晰的尖端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伸入两大洋之间的这个大土角,不知当年是遭到了什么天灾,竟全变得如此支离破碎。
离开这片肥地沃土之后,眼前所见的是连绵不断的光秃秃的海岸,满目荒凉,被一片似迷宫般的成千上万的港汊啃啮成了月牙形。邓肯号在这迷宫般的航道中转来绕去,但没有迟疑,也未出错,把喷出来的一股股的浓烟排出,混杂在被巉岩划破的海雾之中。在这片荒凉的海岸上,有一些西班牙人开设的商行,邓肯号并未减速地从这些商行前驶过。绕过塔马尔角之后,峡道变宽,邓肯号有了旋转的余地了。它绕过了纳波罗群岛的陡峭岸壁,靠近南岸行驶。最后,在进入海湾航行了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它终于见到了皮拉尔角的巉岩突然崛起在德索拉西翁岛的末端。邓肯号面前呈现出一片大海洋,波光闪烁。雅克·巴加内尔激动不已,挥动着手臂,尽情地欢呼着,如同麦哲伦当年在他的那条三位一体号被太平洋上的微风吹得倾斜时的心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