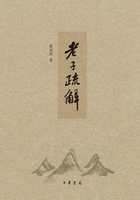
十八章
故大道废,
安有仁义。
知(智)慧出,
安有[大伪]。①
六亲不和,
安又(有)孝茲(慈)。
国家窲(昏)乱,
安有贞臣。②
所以,大道废弃了,
才有了仁义的推崇。
智慧出现了,
才有了大伪的发生。
六亲失和了,
才有了孝慈的倡行。
国家昏乱了,
才有了贞臣的名称。
【校释】
①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智)慧出,安有[大伪]。
帛书乙本此节文字末句残损二字,据甲本当为“大伪”;补损阙后,其字句如上。甲本二“安”字皆作“案”(通“安”),“慧”作“快”(或为“慧”之误)。
郭店楚简(丙)本此节文字为:“古大道癹,安又樖义。”脱“智慧出,安有大伪”句。“古”为“故”之借字,“癹”为“废”(廢)之借字,“樖”为“仁”之古字。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勘校以帛书本,二“有”字前均少一“安”字,“慧智”则或为“智慧”传写之误,诚如马叙伦《老子校诂》云:“譣(yàn,王念孙《广雅疏证》云:‘譣,经传通作验。’——引者注)弼注曰‘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是作‘慧智’者,传写误倒耳。”
※传世本中,略异于王弼本者则如:泰州广明幢本,二“有”字上并有“焉”字,“慧智”作“智惠”,整节文字为:“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惠出,焉有大伪。”傅奕本、陆希声本,二“有”字上并有“焉”字,“慧智”作“智慧”,整节文字为:“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慧出,焉有大伪。”易州景龙碑本,“仁”作“人”;“慧智”作“智惠”,整节文字为:“大道废,有人义;智惠出,有大伪。”范应元本,“义”字下、“伪”字下并有“焉”字,“慧智”作“知惠”,整节文字为:“大道废,有仁义焉;知惠出,有大伪焉。”《经典释文》本、司马光本,“慧智”作“知慧”,“慧智出”为“知慧出”。易州景福碑本、河上公(影宋)本、强思齐本、宋李荣本、文如海本,“慧智”作“智惠”,“慧智出”为“智惠出”。邢州开元幢本、周至至元碑本、楼观台碑本、磻溪大德幢本、北京延祐石刻本、遂州龙兴观碑本、河上公(道藏)本、李约本、唐李荣本、唐《御注》本、唐《御疏》本、张君相本、杜光庭本、道藏无注本、陈景元本、吕惠卿本、苏辙本、陈象古本、宋《御解》本、邵若愚本、李霖本、白玉蟾本、彭耜本、董思靖本、林希逸本、无名氏本、吕知常本、寇才质本、赵秉文本、时雍本、李道纯本、邓锜本、杜道坚本、王守正本、吴澄本、林志坚本、张嗣成本、明《御注》本、危大有本、释德清本、薛蕙本、焦竑本、周如砥本、潘静观本,“慧智”作“智慧”,“慧智出”为“智慧出”。
“废”,失、失却之意;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夏纪·诬徒》“道术之废也”云:“废,失。”“安”,则、于是之意,此处之“安”与十七章“信不足,安有不信”之“安”用法及语义皆同。“大道废,安有仁义”,谓大道失去了,才有了仁义的讲求。
“知(智)慧出,安有大伪”,谓智慧出现了,才有了大伪的发生。
②六亲不和,安又(有)孝茲(慈)。国家 (昏)乱,安有贞臣。
(昏)乱,安有贞臣。
帛书乙本字句如上。甲本二“安”字皆作“案”(通“安”),“孝”作“畜”(通“孝”),“国”作“邦”。
郭店楚简(丙)本此节文字为:“六新不和,安又孝窳;邦窴皈[乱,安]又正臣。”“新”,通“亲”(親);“窳”,“慈”之借字;“皈”,借作“昏”;“皈”下残损二字,据帛书本当为“乱,安”;“正”,与“贞”音近义同。其用字与帛书本多有异,但句脉、文义相侔。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昬乱,有忠臣。”与帛书本勘校,两“有”之上均少一“安”(案)字,“贞”作“忠”。其整节文字与帛书本略从同。
※诸传世本多同于王弼本,其略异者则如:泰州广明幢本,上一“有”字上有“焉”字,“六亲不和,有孝慈”为“六亲不和,焉有孝慈”。李道纯本、吴澄本、明《御注》本、《永乐大典》本、危大有本、潘静观本,“慈”作“子”,“六亲不和,有孝慈”为“六亲不和,有孝子”。范应元本,“慈”、“臣”下各有一“焉”字,“昬”作“昏”,“忠”作“贞”,整节文字为:“六亲不和,有孝慈焉。国家昏乱,有贞臣焉。”傅奕本,“昬”作“昏”,“忠”作“贞”,“国家昬乱,有忠臣”为“国家昏乱,有贞臣”。此外,尚有若干传世本“昬”作“昏”(“昏”为“昬”之别构),兹不罗举。
“六亲”,王弼注云:“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茲”,同“兹”,通“慈”。“六亲不和,安又(有)孝茲(慈)”,谓六亲不相合睦,才有了孝慈的倡导。
“贞”,正;孔颖达疏《左传·襄公九年》“元亨利贞”云:“贞,正也。”“贞臣”,忠贞守固之臣;朱熹《楚辞集注》注《楚辞·九章·惜往日》“属贞臣而日娭”云:“贞臣,正固之臣。”“国家窲(昏)乱,安有贞臣”,谓国家昏乱了,才有了“贞臣”的名称。
【疏解】
本章开篇即称“故”,由此略可窥知其同上章文义相贯之紧切。“大道”略相应于上章之“太上”,“有仁义”略相应于“其次,亲誉之”。然而“有仁义”已是“大道废”,上章所提及的“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与“大道”相去之远就更不待言了。事实上,老子在此章把人间世之所历分作了两个时期,一是现实的“大道废”的时期,一是这之前的“大道”未“废”的时期——老子确信这一寄托了他的理想的时期的存在,并因此一再提示人们向之作一种“复归”的努力。
诚然,老子并不彰扬“仁义”、“孝慈”、“贞臣”,但他也决非要导人于不“仁”、不“义”、不“孝”、不“慈”、不“贞”。在他这里,“大道”——“法自然”之“道”——是对“仁”与不“仁”、“义”与不“义”、“孝”与不“孝”、“慈”与不“慈”、“贞”与不“贞”之对立的超出;他对“仁义”、“孝慈”、“贞臣”诸名目的讥贬,不是站在“仁义”、“孝慈”、“贞臣”的对立面,而是立于“大道”之“自然”的圆融。这“大道”之“自然”的圆融见之于“德”是“不德”而“有德”的“上德”,其不讲求“仁义”等乃在于对“仁义”等的讲求已是孜孜于“不失德”的“下德”。
老子是希望六亲和洽而国家清平的,不过在他看来,这和洽、清平决非人类之“智慧”所可为。他把“智慧出”关联于“大道废”,因而对于他来说,“仁义”——以其不在“自然”的意味上——便可能导致“大伪”。“智慧”系于人为,人之所以在伦理之名分、礼乐之制作、典章之确立、法令之制订上有所施为是因为人有“智慧”。老子否认“智慧”有其“自然”之根,因此由“智慧”而出的伦理、礼乐、典章、法令等,皆被视为与“自然”相悖的人为之“文”。晚周“文敝”的现实对老子的刺激是痛切而深固的,以至他从现实推向终极,在根柢处否定了“文”的价值。“文”必至于“敝”的逻辑使他把“自然”与人为的分别径直归结为“真”与“伪”的相去,所以克除“文敝”以去“伪”,对于他也正是返向“自然”而摒弃人为。
孔子也曾叹及“大道”,其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单以“大道之行”、“谋闭而不兴”全然呼应于老子所谓“大道废”、“智慧出”而言,孔、老所称之“大道”未尝不相通,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昭示的人的当有作为,显然已不再能为“自然”之说所包举。老子所向慕的“大道”乃是“法自然”之“道”,而孔子所赞述的“大道”则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之“道”,前者所诱导于人的唯在扫“文”以“复朴”,后者所诲示于人的却是“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其闻“道”之言皆由克除“文敝”而发,而对于人而至于人文的寄望则相去殊多,此为孔、老“大道”相通却又相异之大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