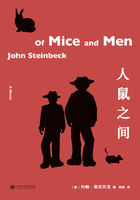
第2章
在索莱达往南几英里外,萨利纳斯河探向山坡,水流幽深碧绿。那水还是暖的,因为它们曾闪着粼粼波光,在阳光下流淌过黄色的沙床,之后才汇入这狭窄的深潭。河岸一侧,山脚下金黄的坡地起伏延绵,伸向雄壮多岩的加比兰山脉。而在靠近山谷的一侧,沿岸一字排开的全都是树——有柳树,每逢春归便清新嫩绿,低垂的枝条上还挂着冬日洪水留下的痕迹;有美国梧桐,树干斑驳发白,枝条横斜,笼在水潭上方。树下的沙岸上,落叶如此厚,如此松脆,哪怕是蜥蜴,穿行其间也免不了发出巨大的沙沙声响。黄昏时分,兔子钻出灌木丛到沙岸小坐,潮湿的平原上会布满浣熊夜行的足迹、农场狗儿的梅花掌印,以及趁夜前来饮水的鹿儿那分叉的楔形蹄印。
一条小路穿过柳林,钻进美国梧桐间。那是小孩子踩出来的,他们从农场下到深潭来游泳;也是流浪者踏出来的,日暮时分,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离开公路,来到水边扎营露宿。一株巨大的美国梧桐伸出低矮的横枝,跟前是无数次营火留下的灰堆。横枝早已被人们坐得光溜平滑。
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微风穿过树叶,夜色初起。阴影从山脚爬向山顶。沙岸上,兔子们静静蹲踞着,好像小小的灰色石雕。这时,州际公路方向传来声响,有脚步踏上了松脆的梧桐落叶。兔子悄无声息地匆匆躲藏起来。一只仿如踩着高跷的鹭笨拙地蹿上半空,重重拍打着翅膀向下游飞去。转眼间,一切都沉寂下来。两个男人出现在小路上,渐渐走近绿色水潭前的空地。
他们一前一后走下小路,就算已经到了开阔的地面,依然一个跟在另一个身后。两人都穿着牛仔工装裤和钉铜纽扣的牛仔工装外套。都戴着黑色无檐帽,肩上挂着卷得紧紧的铺盖卷儿。走在前面的是个小个子,行动敏捷,面孔黝黑,眼睛左右张望个不停,五官锐利分明。他的一切都线条明晰——瘦小的个头、有力的双手、细长的胳膊、瘦骨支棱的鼻子。后面一个却刚好相反,那是个巨人,面容柔和,大眼睛黯淡无神,宽肩斜溜。走起路来脚步很重,多少有点拖沓,像拖着脚步的熊。胳膊松松地垂在身体两侧,并不前后摆动。
突然,前一个停下脚步,后一个差点儿就越过他去。小个子摘下帽子,伸出食指抹了一把吸汗带,弹去水汽。他的巨人同伴扔下铺盖卷儿,晃动着身体冲到绿色水潭边,整张脸埋进水里喝起来,大口大口地灌着,仿佛埋头狂饮的马。小个子男人急忙走到他身边。
“莱尼!”他厉声说,“莱尼,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喝这么多。”莱尼照旧扎在水潭里狂饮。小个子男人弯下腰,推推他的肩膀:“莱尼。你会生病的,就像昨天晚上。”
莱尼整个脑袋都扎进了水里——连同头上的帽子一起。然后才起身,在岸边坐下。水从帽子滴落到他的蓝色外套上,顺着脊背滚下去。“真好。”他说,“你也喝啊,乔治。你也来啊,痛痛快快喝一顿。”他快活地笑着。
乔治摘下肩上的铺盖卷儿,轻轻放在岸边。“也不知道这水干不干净。”他说,“看着有点脏。”
莱尼把他的大手伸进水里,晃动手指,搅起细细的水花。水波漾开,穿过水潭,抵达对岸,又荡回来。莱尼看着它们来来去去。“看,乔治。看我弄的。”
乔治在潭边跪下,掬起水,飞快地轻啜两口。“尝着还不错。”他承认,“但也不像真正流动的活水。永远不要喝不流的水,莱尼。”他不抱希望地说,“你渴起来连臭水沟的水都喝。”他捧起一捧水,扑在脸上,搓了搓脸、下巴底下和脖子背后。然后,重新戴好帽子,往后挪了挪,屈起双腿,环抱双手,拢住膝盖。莱尼认真看着,一丝不苟地照着做。往后挪开一点,屈起双腿,双手环抱膝盖,再看一看乔治,对照自己做得对不对。帽子还要稍稍向下拉一点,贴近眼睛——乔治就是这么戴帽子的。
乔治愁眉苦脸地盯着水面。日头的余晖映红了他的眼眶。他怒气冲冲:“我们本来应该已经在农场了,肯定的。那狗娘养的巴士司机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是,就从公路下去一点儿路。’他这么说。‘没错,就一点儿路。’该死的,差不多四英里。就是这样!就是不想在农场门口停车,就是。该死的连车都懒得停。我怀疑他懒到根本连在索莱达都不想停。就这么把我们赶下车,说什么‘没错,跟着公路走,就一点儿路’。还不止四英里,我敢打赌。这么该死的大热天。”
莱尼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脸色。“乔治?”
“嗯,干吗?”
“我们要去哪里,乔治?”
小个子男人猛地揪下帽子,怒冲冲地瞪着莱尼。“你是又忘了,是吧?我非得再跟你说一遍,是吧?耶稣基督啊,你这笨蛋王八蛋!”
“我忘了。”莱尼轻声说,“我努力不要忘。跟上帝发誓,我努力了的,乔治。”
“好——好。我再跟你说一遍。还能怎么办呢。大概我这辈子都要不停地跟你说,等你忘掉,然后我再跟你说。”
“我努力了,一直一直努力,”莱尼说,“可没有用。我记得兔子,乔治。”
“见鬼的兔子。你就记得兔子。好!现在,你听着,这次你要记住了,免得我们再惹上麻烦。你记得我们到霍华德街那个破地方,看到那块黑板吧?”
莱尼的脸上绽出一个高兴的微笑。“啊呀,当然,乔治。我记得那个……可是……我们在那里干什么来着?我记得有几个女孩经过,你说……你说……”
“见鬼,别管我说什么了。你记得吧?我们到莫里和雷迪介绍所[1],他们给了我们工卡和汽车票。”
“噢,当然,乔治。这下我记起来了。”他赶忙把手伸进外套侧面的口袋里。他小声说,“乔治……我的卡找不到了。肯定被我弄掉了。”他绝望地垂头看着地面。
“不在你那儿,你这笨蛋王八蛋。我们俩的都在我这儿。你以为我会让你自己拿工卡?”
莱尼松了口气,咧开嘴,笑了。“我……我以为我放在口袋里了。”他的手又伸进了衣袋。
乔治警觉地盯着他。“你从口袋里掏出的什么?”
“我口袋里什么都没有。”莱尼机灵地说。
“我知道没有。在你手里。你手里拿的什么——藏的什么?”
“什么都没拿,乔治。真的。”
“过来,拿过来。”
莱尼握着拳头,藏到身后。“就是只老鼠,乔治。”
“老鼠?活老鼠?”
“呃——呃。就是只死老鼠,乔治。我没弄死它。真的!我找到的。我找到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拿过来!”乔治说。
“哦,让我留着吧,乔治。”
“拿过来!”
莱尼握拢的拳头一点点服从了。乔治拎起死老鼠,扔进池塘对面的灌木丛。“你要个死老鼠到底是想干吗?”
“走路的时候,我可以用大拇指摸一摸。”莱尼说。
“噢,跟我一起走路你没老鼠摸就不行是吧。现在想起我们要去哪里了?”
莱尼看起来吓坏了,羞窘地把脸重新埋回膝盖间。“我又忘了。”
“耶稣基督啊。”乔治无奈地说,“好吧——听着,我们要去一个农场做工,跟之前我们在北边那个农场差不多的地方。”
“北边?”
“威德。”
“噢,当然。我记得。在威德。”
“我们要去的那个农场,就在这里再下去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我们要去找老板。现在,听着——我会把工卡给他,不过你一个字都不要说。你就站着,什么都不说。要是给他发现你是个多蠢的王八蛋,我们就没活儿干了。只要他没听过你说话,光看到你干活,我们就能留下来。懂了吗?”
“当然,乔治。我当然懂。”
“好。那要是我们现在去见老板,你要做什么?”
“我……我……”莱尼在想,因为动脑子,脸绷得紧紧的。“我……什么都不说,就站着。”
“好孩子,漂亮。你再说个两三遍,确保不要忘了。”
莱尼独自低声复述:“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好。”乔治说,“还有,你也不能再干坏事,就像在威德干的那种。”
莱尼满脸迷惑。“像我在威德干的那种?”
“噢,所以你是把那个也忘掉了,是吗?得了,我也不提醒你,免得你又来一次。”
莱尼脸上掠过一丝恍然大悟。“他们把我们赶出威德了。”他胜利地大声说。
“把我们赶走,见鬼。”乔治恼火地说,“我们跑掉了。他们到处找我们,可没逮住。”
莱尼乐得咯咯笑。“我没忘,跟你打赌。”
乔治仰面躺倒在沙地上,十指交叉,抱着后脑勺。莱尼学着他躺下,又勾起头,看自己做对了没有。“上帝啊,你真是个大麻烦。”乔治说,“要不是拖着你这个尾巴,我能过得更自在,日子好过得很。我能过得很自在,说不定还能有个姑娘。”
莱尼默不作声地躺了会儿,然后,满怀希望地说:“我们会在一个农场工作,乔治。”
“没错。你懂了。不过,我们要先在这里睡一晚,我自然有道理。”
此刻,白天正飞快逝去。太阳已经沉入山谷,只有加比兰山脉的峰顶被余晖映得发红。一条水蛇沿着水潭边滑行,头竖着,像个小小的潜望镜。芦苇在水波中轻轻摇摆。远处的公路上,一个人大声嚷着什么,有人大声回答他。美国梧桐的枝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只一瞬,风便息了。
“乔治——为什么我们不接着走,到农场去吃晚饭?农场里有晚饭。”
乔治翻了个身。“对你来说,什么也不为。可我喜欢这里。我们明天就要去干活。我看到打谷机了,就在往下的路边。这就是说,我们得去背麦包,拼了命地干活。可今天晚上,我就想躺在这里,看看天。我喜欢这个。”
莱尼翻身跪起,低头看着乔治。“那我们不是没晚饭吃了?”
“当然有,只要你能去捡一点干柳树枝回来。我的铺盖卷儿里有三个豆子罐头。你去生火。等你捡好树枝回来,我再给你火柴。然后,我们就把豆子热了,吃晚饭。”
莱尼说:“吃豆子我喜欢加番茄酱。”
“得了,我们没有番茄酱。你去捡柴火。别乱逛。天马上就黑了。”
莱尼慢吞吞地爬起来,消失在灌木丛中。乔治躺着没动,轻轻吹起了口哨。莱尼消失的方向传来水花溅开的声音,有什么下了河。乔治停下口哨,仔细听了听。“可怜的王八蛋。”他轻轻说了句,重新吹起口哨。
不一会儿,莱尼“哗啦哗啦”地穿过灌木丛,回来了,手上抓着一根小柳枝。乔治坐起来。“行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把老鼠给我!”
莱尼比出一个精心设计的无辜手势。“什么老鼠,乔治?我没有老鼠。”
乔治伸出手。“快点。给我。你骗不了我。”
莱尼犹豫着往后退,左右打量着成排的灌木,像是打算为了自由而逃跑。乔治冷声说:“是你自己把老鼠给我,还是我先揍你一顿?”
“给你什么,乔治?”
“你知道那该死的是什么。我要老鼠。”
莱尼不情不愿地把手伸进口袋,声音里透出一丝呜咽。“我不懂我为什么不能留着它。它不是谁的老鼠。我不是偷来的。它就在路边,我看到的。”
乔治的手依旧不容反抗地伸着。慢慢地,就像一只舍不得把球交给主人的小狗,莱尼上前,退后,又上前。乔治猛地掰开他的手指,莱尼应声把老鼠放在了他的手里。
“我没对它干坏事,乔治。就是摸摸它。”
乔治站起来,用尽全力把老鼠扔进越发模糊的灌木丛中,然后,走到池塘边洗手。“你这大蠢蛋。你以为我看不到你的脚湿了?不知道你蹚水过河去捡它了?”听到莱尼抽噎着哭了,他转回身。“哭哭闹闹,像个婴儿一样!耶稣基督啊!就你这么个大块头。”莱尼嘴唇颤抖,泪珠在眼里聚集。“噢,莱尼!”乔治伸手按住莱尼的肩头,“我拿走它不是没道理的。那只老鼠不新鲜了,莱尼。再说你也已经把它的皮都摸破了。等下次,你再找到只新鲜的老鼠,我会让你留一阵子。”
莱尼坐在地上,沮丧地垂着头。“我不知道哪里还有老鼠。我记得以前有位女士一直给我老鼠——只要她找到,就会给我。可那位女士不在这里。”
乔治嗤笑一声。“女士,哈?连那位女士是谁都不记得了是吧。那是你亲姨妈克拉拉。而且她也不给你老鼠了。你老把它们弄死。”
莱尼哀伤地抬头看着他。“它们太小了。”他分辩道,“我就是摸一摸,可它们老是转过头来想咬我的手指,我就只轻轻捏一下它们的脑袋,结果,它们就死了——都是因为它们太小了。”
“我希望我们能早点有些兔子,乔治。它们不那么小。”
“去他的见鬼的兔子吧。就因为不敢给你活老鼠了,你姨妈克拉拉还特意给了你一只橡皮老鼠,可你根本不理它。”
“那个摸着不舒服。”莱尼说。
落日的余晖从山顶消失了,暮色降临山谷,柳树和美国梧桐间变得半明半晦。一条大鲤鱼蹿上池塘表面换气,又神秘地沉入幽深的水里,只留下水面上荡开的涟漪。头顶上,树叶重新发出沙沙的声响,一朵朵小柳絮飘下来,落在池塘水面上。
“你去捡柴火吧?”乔治提出要求,“那棵美国梧桐背后就有很多。洪水冲下来的木头。现在就去,捡一点回来。”
莱尼走到树后,捡来一点干树叶和细树枝,放在老灰堆上,堆成一小堆,又回去,再拿一些,再一些。天差不多完全黑了。一只鸽子扑扇着翅膀掠过水面。乔治走到火堆边,点燃干树叶。伴着噼啪声,火焰从小树枝间蹿起,燃了起来。乔治解开他的铺盖卷儿,拿出三个豆子罐头。一个一个立在火边,尽量靠近火堆,却并不真的碰到火苗。
“这些豆子够四个人吃的了。”乔治说。
莱尼隔着火焰望着他,不厌其烦地说:“我喜欢加番茄酱。”
“行了,我们没有番茄酱。”乔治爆发了,“我们没什么你就要什么。全能的上帝啊,要是我是一个人,该过得多自在啊。我能找份工作,只管干活就行,没有麻烦。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没有。等到月底,我就拿着我的五十块钱到城里去,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嗨,我可以在妓院里过上一整夜。我想到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只要我想,饭店,随便哪里,点他妈随便什么东西,只要我想得到。他妈的每个月我都可以这么干。喝一加仑威士忌,待在台球房里,打牌,打台球。”莱尼跪起身子,隔着火光,望着发怒的乔治,脸上写满了惊恐。“可我得到了什么,”乔治继续发火,“我得到了你!你什么工作都保不住,还连我的工作也统统搞没了。害得我只能到处跑来跑去,没完没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你还惹麻烦。你干了坏事,我就得带着你逃跑。”他几乎是在吼了。“你这笨蛋狗娘养的。你害我一直过得水深火热。”他做出小姑娘们彼此模仿时做作的模样,“就是想摸一摸那个女孩子的裙子——就是想摸一下,像摸个老鼠——得了吧,见鬼的她怎么知道你只不过想摸摸她的裙子?她一回头,你就一把捏住她,好像那是只老鼠一样。她尖叫起来,我们就不得不在灌渠里蹲上一整天,躲外面那些找我们的家伙,等天黑了再溜出来,跑出那个地方。真希望我能把你关在笼子里,里面放上一百万只老鼠,让你玩个够。”他的愤怒突然消失了。看见火堆对面莱尼痛苦的脸,他羞愧地掉转视线,盯着火焰。
天很黑了,可火光照亮了树干和头顶弯曲的树枝。莱尼一点一点蹭着,小心翼翼地绕过火堆,直到抵达乔治身边。他在自己脚跟上跪坐下来。乔治把豆子罐头转了个向,换一面烤。假装不知道莱尼就在他身边,离他这么近。
“乔治。”非常轻的声音。没反应。“乔治!”
“干吗?”
“我就是开个玩笑,乔治。我不要番茄酱。就算我们有番茄酱,就在这里,我也不要。”
“有的话,你可以吃。”
“我不吃,乔治。我全部留给你。你可以用它们把豆子都盖住,我一点都不碰。”
乔治依然愁苦地盯着火焰。“一想到没有你的好日子,我就疯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安宁。”
莱尼继续跪坐着。他调转视线,望向河对岸那黑洞洞的一片。“乔治,你想要我走开,让你自己待着吗?”
“你能去什么鬼地方?”
“噢,我可以。我可以去那边的山里。我可以在什么地方找个山洞。”
“是吗?你吃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找东西吃。”
“我能找到,乔治。我不要加番茄酱的好吃的。我可以躺在地上晒太阳,没人能欺负我。要是找到老鼠,我就留下来。没人能从我手里把它拿走。”
乔治飞快地抬起眼皮,探究地看他。“我很坏,是吗?”
“要是你不想要我一起,我可以走,到那些山里去,找个山洞。我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不——你看!我只是开玩笑,莱尼。我想要你跟我在一起。老鼠的问题是,你总是会把它们弄死。”他顿了顿,“跟你说我要做什么,莱尼。只要一有机会,我就给你弄条小狗。说不定小狗不会被你弄死。那比老鼠好。你还可以摸得重一点。”
莱尼躲开这份诱饵。他察觉到了自己的优势。“要是你不想要我,只要说出来,我就走,到那边的山里去——一直走到那些山里头去,自己过活。谁都不能偷走我的老鼠。”
乔治说:“我想要你跟我一起,莱尼。耶稣啊,要是你自己过活的话,会被人当成郊狼打死的。不,你要和我一起。你姨妈克拉拉不会想要你自己跑开过活的,虽然说她已经死了。”
莱尼狡猾地说:“说给我听——像你以前说的那样。”
“说给你听什么?”
“兔子什么的。”
乔治咬牙道:“别跟我耍花样。”
莱尼恳求道:“拜托,乔治。说给我听。求你,乔治。就是你以前说的那样。”
“你就喜欢这个,是吗?好,我说给你听,说完我们就吃晚饭……”
乔治的声音变得低沉。他吟诗般再一次重复起自己的话,仿佛已经说过许多遍。“那些像我们一样,在农场里工作的人,是这世上最孤单的。没有家。不属于任何地方。到一个农场,干活,赚钱,然后进城去花个精光,你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掉头去了别的农场。他们的日子没有指望。”
莱尼高兴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现在说说,我们怎么样。”
乔治继续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未来。我们有关心的人,可以互相说话。我们不用坐在酒吧里把口袋掏空,就因为没地方可去。要是他们那些家伙进了大牢,就会烂透了,因为他们没人关心。可我们不会。”
莱尼插了进来。“可我们不会!为什么?因为……因为我有你照看我,你有我照看你,那就是为什么。”他高兴得大声笑起来,说,“接着说,乔治!”
“你都记住了。你可以自己说。”
“不,你说。有些东西我忘记了。说说然后会怎么样。”
“好。等到有一天——我们一起攒够了钱,就会有一幢小房子、几英亩地、一头牛、几头猪,还能——”
“还能靠种地过日子。”莱尼叫起来,“还有兔子。接着说,乔治!说说我们的菜地里有什么,说说笼子里的兔子,冬天下雨和炉子,还有牛奶上的奶油有多厚,像是刀都切不开一样。说说那个,乔治。”
“你干吗不自己说?你都知道了。”
“不……你来说。我说就不一样了。接着说……乔治。我要怎么照看兔子。”
“好吧。”乔治说,“我们会有一大片菜地,有个兔子棚,还养鸡。冬天下雨的时候,我们只说句‘去他的’,就不开工了,我们在壁炉里生起火,坐在炉子边,听雨落在屋顶上——该死!”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刀,“我可没工夫接着说了。”他把刀插进一个豆子罐头的顶盖,切掉罐头盖,递给莱尼。再切开第二罐。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把勺子,分给莱尼一把。
他们坐在火边,塞了满嘴的豆子,用力嚼。有几颗从莱尼嘴角滑下来。乔治挥动勺子比划了一下。“明天,要是老板问你话,你要怎么说?”
莱尼停止咀嚼,咽下嘴里的东西。整张脸皱成了一团。“我……我不……我一个字也不说。”
“好孩子!很好,莱尼!说不定你正在慢慢好起来。等我们有几英亩地以后,我就能放心让你照看兔子了。只要你能像这样好好记住事。”
莱尼骄傲极了。“我能记住。”他说。
乔治又挥了挥他的勺子。“瞧,莱尼。我想要你看看这里。你能记住这个地方,对吗?沿着上面那条路再走四分之一英里就是农场。就跟着河边走,记得住吗?”
“当然。”莱尼说,“我能记住。我不是记住了一个字都不说吗?”
“当然,你记住了。好,瞧,莱尼——万一你不小心惹了麻烦,就像你之前一直惹的那种,我要你到这里来,藏在灌木丛里。”
“藏在灌木丛里。”莱尼慢慢地说。
“藏在灌木丛里,等我来找你。你能记住吗?”
“当然能,乔治。藏在灌木丛里,等你来。”
“但你决不能再惹麻烦,因为要是又惹了的话,我就不让你养兔子。”他把空罐头扔进灌木丛里。
“我不惹麻烦,乔治。我一个字也不说。”
“好,把你的铺盖卷儿拿到火边来吧。这里睡着舒服点。可以看天,还有树叶。别再添柴火了,我们得让火慢慢熄了。”
他们在沙地上铺好床,随着火焰一点点低下去,火光照亮的范围越来越小,曲曲折折的树枝消失了,只剩下微弱的光亮映出树干的所在。黑暗中,莱尼唤道:“乔治——你睡着了吗?”
“没有。干吗?”
“我们要养好多颜色的兔子,乔治。”
“当然,我们会的。”乔治迷迷糊糊地说,“红的蓝的绿的兔子,莱尼。成千上万只兔子。”
“毛茸茸的兔子,乔治,跟我在萨克拉门托市集上看到的一样。”
“当然,毛茸茸的。”
“当然,我走也没关系,乔治,住在山洞里。”
“你下地狱也没关系。”乔治说,“闭嘴吧。”
木炭上的红色光亮渐渐黯淡。河上游的山上,一只郊狼开始嗥叫;河对岸,一只狗发出了回应。
轻柔的夜风中,美国梧桐的叶子沙沙作响。
注释
[1]为实施罗斯福新政而建立的政府职介所,持该机构工作卡务工的劳动者可视为政府派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