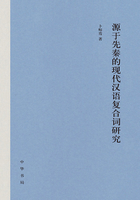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训诂学的语义观
“中国训诂学是植根于汉语的,以词汇意义为研究中心,以语义探求(考证)、贮存与解释为应用实践的传统学科。从训诂学里体现出来的语义观,是中国固有的语义观,也是符合汉语实际的语义观。” 王宁师将这种语义观概括为三个方面:语义主体论、词汇意义系统论、音义关系约定性和理据性的统一。由于本书是对复合词的研究,因此我们主要立足于前两点:
王宁师将这种语义观概括为三个方面:语义主体论、词汇意义系统论、音义关系约定性和理据性的统一。由于本书是对复合词的研究,因此我们主要立足于前两点:
1.“语义主体论。语义与语法的一致性和二者的相互作用,已经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语法与语义谁是具有主导地位的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的。传统训诂学从学术渊源上是以语义为中心的,它的语义观是语义主体论。语义是语言的内容,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普遍哲理,不但首先是语义决定语法,而且语义系统决定音系的规模。语法、语音在成熟后也对语义产生影响,但那是一种第二位的反作用。”
2.“词汇意义系统论。语义是以词音和句法为依托形式的,但它是自成系统的,它的系统首先在自身的聚合中实现,并不依靠句法。传统‘小学’从完全依靠语言环境的随文释义,发展到脱离文献的纂集专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实现了意义的类聚,使意义脱离了文献的言语,不再依赖具体环境,而成为互相依赖的一群,这就使它很容易从具体词语释读的目的,进入词汇意义系统的思考。词汇意义系统论的具体观点是:同一种语言的意义之间互有联系,或处于级层关系,或处于亲(直接)、疏(间接)的关系,词汇意义的演变牵一发而动全局,首先是自身系统决定的。”
(二)共时与跨时代的历时比较相结合
索绪尔把语言分为共时和历时两种状态,认为“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9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 “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
, “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自索绪尔提出共时、历时的分化后,共时、历时已经不仅仅是对语言状态的描写,更成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切入点和方法。
。自索绪尔提出共时、历时的分化后,共时、历时已经不仅仅是对语言状态的描写,更成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切入点和方法。
在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共时的“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这种投影不是简单的投影,在汉语词汇发展中,这种投影又表现为跨时代的要素常常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现有的语言之中,并限制、制约着共时层面上词义的组合和发展。同样,虽然“历时事件总有一种偶然的和特殊的性质”
。这种投影不是简单的投影,在汉语词汇发展中,这种投影又表现为跨时代的要素常常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现有的语言之中,并限制、制约着共时层面上词义的组合和发展。同样,虽然“历时事件总有一种偶然的和特殊的性质”![[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但我们不认为“引起系统变动的事件不仅与系统无关,而且是孤立的、彼此不构成系统”
,但我们不认为“引起系统变动的事件不仅与系统无关,而且是孤立的、彼此不构成系统”![[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6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实际上历时中每个要素的演变和演变规则都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因此,只有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才能使描写与解释共存。
。实际上历时中每个要素的演变和演变规则都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因此,只有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才能使描写与解释共存。
本书在运用历时研究法时并不是一般的具有严格时间层次的历时法,而是跨时代的比较。所谓跨时代的历时比较是指不对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作细致关注,而只从源头与现状的对比中进行分析。运用在本书中,是指直接把先秦文言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对比,不过多关注中间的历史阶段。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基于如下原因:
首先,“文言”从先秦产生到“五四”退出,内部系统是相对稳定的。张中行先生说:“所谓‘文言’,古代大致以秦汉为准,有个相当明朗的规格,后代,不管是强调仿古的唐宋八大家和明前后七子,还是强调创新的明公安派,都亦步亦趋地照着规格作。” 从这个角度说,“文言”对“白话”的影响实则等同于先秦汉语对白话的影响,而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代表的是白话文发展成熟的共时系统。而且,如前所述,“文言”对“白话”的影响并非是完全历时的传承,而常常是不同时代的横向直接进入。对于横向直接进入的词,我们很难对它从时间层次上进行分析。
从这个角度说,“文言”对“白话”的影响实则等同于先秦汉语对白话的影响,而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代表的是白话文发展成熟的共时系统。而且,如前所述,“文言”对“白话”的影响并非是完全历时的传承,而常常是不同时代的横向直接进入。对于横向直接进入的词,我们很难对它从时间层次上进行分析。
其次,对于词汇的研究,跨时代的比较往往可以对共时现象作出解释。共时是试图找到一个描写的切入点,历时是观察要素产生过程的途径,但有时对于一些语言现象跨时代的历时比较往往可以寻求一定的解释。例如:“产生”“发生”在共时中是对立的,但为什么用“产”“发”,这里面有深层的语义制约,当我们想去寻找这种语义制约时,往往不需要完全依照历时过程进行追溯,只需对构词语素的发源意义做比较分析。“产”, 《说文》:“产,生也。”指的是生物在繁殖中由已有的生物体产下新生物体的过程,因此,“产”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泛化到非生物体,也常指物体内部的东西经过开发分离出来。“产”需要一定的自然基础,强调过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可预知性。“发”, 《说文》:“发,射发也”,本义为“把箭射出去”。这使“发”在引申出“生长”“产生”这个意义时,强调新状况的出现,而不强调过程,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可预知性。因此,当它们分别和“生”结合时,就造成了词义的差异。“产生”指“由已有事物中生出新的事物”;而“发生”指“原来没有的事物出现了”。应该说,这种比较不是完全历时的,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去考虑“产”和“发”以及“产生”“发生”从源头到现代这一漫长阶段的变化过程,但却可以解释现代的词义差别。
另外,本书强调跨时代的历时比较旨在说明主要采用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在研究中对历史时间上演变的进程视而不见和完全抛弃,而只是在不同问题的处理上分清使用方法的主次。
(三)系统方法
系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诸多要素(不少于两个),相互间按照一定方式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具有目的性、整体性、有序性和等级性等特点。“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人们自觉认识到系统思想之前,就在进行着系统的思维,语言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要是正确地提出和评价现代系统论,就不能把它们看作一时时髦的产物,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人们自觉认识到系统思想之前,就在进行着系统的思维,语言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要是正确地提出和评价现代系统论,就不能把它们看作一时时髦的产物,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美]贝塔朗菲著、王兴成译《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 《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第66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在西方语言研究中,比较明确地运用系统思想研究语言的是索绪尔。他认为“一种语言就构成一个系统”![[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而且“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
。而且“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8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他在系统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要素的“价值”,认为“价值”是由差别和对立来体现的,“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相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于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 “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的”
。他在系统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要素的“价值”,认为“价值”是由差别和对立来体现的,“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相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于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 “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的”![[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1—16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
。“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3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但是,索绪尔并不就此否认语言系统作为整体存在的积极作用。他指出:“说语言中的一切都是消极的,那只有把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才是对的:如果我们从符号的整体去考察,就会看到在它的秩序里有某种积极的东西。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虽然都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和消极的,但它们的结合却是积极的事实;这甚至是语言惟一可能有的一类事实,因为语言制度的特性正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
但是,索绪尔并不就此否认语言系统作为整体存在的积极作用。他指出:“说语言中的一切都是消极的,那只有把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才是对的:如果我们从符号的整体去考察,就会看到在它的秩序里有某种积极的东西。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虽然都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和消极的,但它们的结合却是积极的事实;这甚至是语言惟一可能有的一类事实,因为语言制度的特性正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F4532A/1371750360511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3824128-3xcp5TPy9nHCdWtieE92mZ2GaNptf0bm-0-e566a4c98fc3aa659bc0483b4aff7fa5)
索绪尔之后,布拉格学派运用索绪尔的“系统”概念,创立了音位学理论,使“系统”理论充分显示出在语言学领域的深远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中,虽没有明确地提出“系统”,但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却是存在的,在传统训诂学的词义训释中,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在解释词义时,“并不孤立地看待一个一个的词,而是把每个词语,放在与它相关的其他词中间,前后沟通、左右联系,去探讨它的意义” 。从对比和辨析中来看待它在语言中的价值。例如:《尔雅》:“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其次,他们注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类聚研究。《方言》《尔雅》《释名》中均体现了词义类聚的观念和方法。《尔雅》根据词义的相近、相关的编纂,这就是早期的粗略的语义系统观念,因为“字、词、义一经分类,就显示出内部的系统性”
。从对比和辨析中来看待它在语言中的价值。例如:《尔雅》:“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其次,他们注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类聚研究。《方言》《尔雅》《释名》中均体现了词义类聚的观念和方法。《尔雅》根据词义的相近、相关的编纂,这就是早期的粗略的语义系统观念,因为“字、词、义一经分类,就显示出内部的系统性” 。
。
由于中国传统训诂学是以意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它所采用的系统研究和结构主义的有所不同:1.系联和辨析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共时领域,而是常常把超地域和超时代的语言要素在平面上系联比较,从而探讨它意义的真正内涵。2.把意义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形式,强调形式的差别对立是有其意义的内在动因在起作用。索绪尔的“价值”是指一个词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与其他词构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包括语义关系,也包括语用和语法。因此,所谓“价值”即一个词在其所处的系统中的分布情况,是它与其他词的差异所在。应该说,索绪尔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注意到了单个词具有表达概念的“意义”,而且还注意到了词在语言共时系统中还具有与其他词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即“价值”。但是,“价值”不可能是先验的结果,它是可以寻求解释的,而这种解释是无法在共时领域中完成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语言中词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个词为何能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价值”。在汉语词义的研究中,“价值”的动因往往可以从大量的训诂成果中寻找答案。因为训诂学关注的是意义,而且是古今沟通的意义,意义的探源是训诂学的首要任务。这种探源不仅包括词源意义的探求,也包括词义引申脉络的探求。这些积聚下来的材料和方法都可以在探索词共时“价值”背后的语义动因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关于词汇以及词义系统的探讨,已取得了很大成果。周祖谟(1955)提出并探讨了词汇系统性的表现。此后,高名凯(1962)、陆宗达和王宁(1983)、蒋绍愚(1989ɑ)、刘叔新(1990)、张志毅和张庆云(1994;2001)、符淮青(1996)、宋永培(2000)、葛本仪(2001)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词汇词义系统进行了研究,这些前修时贤的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