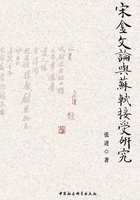
第一节 梅尧臣首倡“平淡”诗美
北宋首倡平淡诗风的是梅尧臣,经欧阳修之倡导,至苏轼的大力推崇而影响始巨。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侍读学士梅询之侄,世称宛陵先生。《宋史》本传说他“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荫为河南主簿”[7],历任德兴县令等地方小官。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参与编撰《唐书》,“成,未奏而卒”[8]。注《孙子十三篇》,有《宛陵先生集》60卷。
一 处穷而“以深远古淡为意”
在宋初诗人普遍学唐诗的风气中,梅公是被认作学唐人平淡诗风的。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9]
所谓“唐人平淡处”,大约是指唐代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格。《宛陵先生集》卷三有《拟王维偶然作》,卷四有《咏王右丞所画阮步兵醉图》,卷十二有《拟王维观猎》《拟韦应物残灯》等作。南宋初年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有“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的说法。但梅公真正推崇仿效的对象是陶渊明(下详)。从梅公的论述及创作实践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处穷而超然淡泊。他说:
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
……
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10]
《宋史》本传说“尧臣家贫”,其悼念亡妻的《怀悲》诗云:“自尔归我家,未尝厌贫窭。夜缝每至子,朝饭辄过午。十日九食齑,一日倘有脯。东西十八年,相与同甘苦。”[11]欧阳修亦有诗曰:“念子京师苦憔悴,经年陋巷听朝鸡。儿啼妻噤午未饭,得米宁择秕与稊。”[12]其生存状态之贫困由此可见。其仕途亦不顺达,欧阳修说:“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13]梅公年届五十,乃征召为文书,虽有诗名,屈处于下僚,使他不免自比于孟郊,如云“窃比于老郊”(卷三十三《别后寄永叔》),“已为贫孟郊”(同上《因目痛有作》)。但他不同于孟郊的是,孟郊的诗多为“不平之鸣”,慨叹仕途失意,抨击浇薄世风,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反映了世途艰险,也表现了作者愤激的情绪。梅公虽然也是以诗抒发不得其志的感慨,却心怀坦荡、澹然处之。如云:
不忧贫且老,自有伯鸾心。[14]
我今才薄都无用,六十栖栖未叹穷。[15]
识尽穷通理,超然乐有余。[16]
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17]
梅公以伯鸾自比,谓自己不忧贫不叹老。伯鸾乃东汉梁鸿的字,梁鸿家贫好学不求仕进,与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夫妇相敬有礼。(见《后汉书·逸民传·梁鸿》)梅公自谓才薄,年已六十而不为重用,仍未曾嗟老叹穷,因为自觉能识穷通之理,所以能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之,且自得其乐,乐而有余。有这样的超然澹泊之心,他说自己不学唐季诗人之雕琢苦吟,借“区区物象”以消磨时光。在他心目中,林逋的诗是值得肯定和推许的。他称:
(林逋)其顺物玩情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18]
指出林逋诗的平淡而又深邃之美,在于不计较世事、不抒发怨刺的超然之心、静正之态。这与梅公的心思和追求一致。梅公不独于诗追求平淡,其字也同样潇洒。张与材《跋题干越亭送君石秘校二诗后》说:“今观其笔意潇散,有髙人逸士风度,此岂汲汲于声利者心画正尔,岂特坐诗穷耶?”[19]
二 梅公的超然来自儒家与佛老
梅公的超然澹泊主要来自儒家之道义。欧公谓其:“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合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20]梅诗亦云:
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
平生少壮日,百事牵于情。
今年辄五十,所向唯直诚。
既不慕富贵,亦不防巧倾。
宁为目前利,宁爱身后名。
文史玩朝夕,操行蹈贤英。
下不以傲接,上不以意迎。
众人欣立异,此心常自平。
……我迹固有贱,我道未尝轻。
力遵仁义途,曷畏万里程。
安能苟荣禄,扰扰复营营。[21]
……
平生守仁义,齿发忽衰暮。
世事不我拘,自有浩然趣。
未由逢故人,坐石语平素。[22]
穷不忘道,穷不改操守,力遵仁义之途,自有浩然之趣,这是梅公安身立命的根本。苏轼当年受梅、欧之拔擢,对梅公深为敬佩,作《上梅直讲书》云: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23]
指出梅公才高位下而不怨天尤人,文章宽厚敦朴,正是有“道”作为支撑,故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道。
其次,梅公还有取于老庄,如云:
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24]
且梦庄周化蝴蝶,焉顾仲尼讥朽木。人事几不如梦中,休用区区老荣禄。[25]
他自谓将以老子为师,以其“淡泊”的思想来保全自己的精神,又以庄周梦蝶的故事,表现一种精神的自由放松。他说自己白天想睡就睡,不在乎像宰予那样被圣人讥为朽木。人生恍若一梦,他要打破外物(荣禄)对心的束缚。在《长歌行》一诗中,他阐发了庄周“一死生”的道理,说“释子外形骸,道士完髓精”“庄周谓之息,漏泄理甚明”[26],表现出对生死的淡泊超然的态度。
佛家思想也给他一定的浸润。在当日佛教流行的文化背景中,梅公不像欧阳修、范镇等人那样排佛,他也与僧人交往[27],也去游佛寺。其《和绮翁游齐山寺次其韵》:
扪萝但识康乐径,饮酒安问远公禅。
清猿不到俗士耳,香草已入骚人篇。
水鸟念佛次浄界,野鹿衔花来象筵。
在昔探赏犹可数,深景秀句今得传。
辞韵险绝兹所骇,何特杜牧专当年。
重以平澹若古乐,听之疏越如朱弦。
……[28]
完全是一副平澹、怡然的心态。他在《题三教圆通堂》中,表明了三教圆通的思想:
处中最灵智,人与天地参。其间有佛老,曷又推为三。
共以圆通出,诚明自包含。……[29]
由上述可见,以儒家的仁义操行、温厚平和为其主导,参以佛老的超然淡泊,构成梅公尚平淡的思想基础;处穷而不怨,是其平淡诗美观的精神实质。苏轼后来主张三教融通,成为蜀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可能有来自梅公的影响。
三 梅公的平淡以陶渊明为典范
梅公在仕途蹭蹬之际,极怀慕陶渊明,诗中多次咏及,称颂其人:
深希陶渊明,澹然意已真。[30]
每读陶潜诗,令人忘世虑。
潜本太尉孙,心远迹亦去。
不希五斗粟,自种五株树。
旷然箕山情,复起濠上趣。
今时有若此,我岂不怀慕?[31]
予心每澹泊,世路多变诈。
……
我趋仁义急,不解如陶谢。[32]
他仰慕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超然品格,认为自己愧不如陶、谢。在“爱陶”方面,他与欧公的心思是相通的。有诗云:“夜坐弹玉琴,琴韵与指随。不辞再三弹,但恨世少知。知公爱陶潜,全身衰弊时。有琴不安弦,与俗异所为。寂然得真趣,乃至无言期。”[33]陶渊明蓄“无弦琴”,人多不解,而欧、梅二公则深知其“与俗异所为”的意趣所在,不愧是知音。
梅公亦向往渊明描写的世外之乐,作《桃花源诗并序》,他是宋代第一位作桃花源诗的诗人。梅公又有《依韵和丁元珍》诗云:
实惭寡时用,又顾无奇行。
……
稍思桃源人,翩尔乘鱼艇。
寻花逐水往,岂念衰与盛。
歌讴非俗情,山响自答应。
……[34]
诗言“实惭寡时用”,正见其不为时用;“稍思桃源人”,则表现出与渊明的理想颇为一致。正是相同的现实境遇,相同的理想追求,让他推赏渊明诗的平淡:
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35]
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36]
宁从陶令野(公曰“彭泽多野逸田舍之语”),不取孟郊新(公曰“郊诗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琢砾难希宝,嘘枯强费春。[37]
梅公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情性,不须大放厥声。诗之理出之于平淡,诗家之典范即是陶渊明。“宁从陶令野”云云,强调宁从陶公的野逸,不取孟郊的尖新。从诗题和诗注看,这里含有一段故事。梅公曾将自己的近诗作为见面礼赠予宰相晏殊,并一起谈论诗。其间,晏公谈到陶渊明的诗“多野逸田舍之语”,孟郊的诗“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梅公后来忽然收到晏公的酬赠之诗,十分欣喜,作诗以和,表达了他推崇陶诗平淡自然之美的诗学观点。在他看来,沙中取宝,枯树探春,都是勉为其难、强行费力的事情,不如自然为好。不少论者认为梅诗学孟郊诗,如明宋濂说:“梅之覃思精微,学孟东野。”[38]这是徒见其表,不见其里。梅公虽以家贫自比孟郊,作诗未必取法孟郊。他是兼取儒家中和之美与道家朴素之美的美学思想,以陶诗为圭臬,从而构成了平淡诗美的基本特征。
梅公以为,平淡乃诗歌之难造之境,他的论诗名言是: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39]
可知梅公把“平淡”看作诗之至难之境。何以谓之“难”?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似透露此中天机。他说: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40]
梅公的回答是,声律、文语的讲求和锻炼是可言告的,而“心之得者”则“不可以言而告”。这说明“平淡”之美,不仅是语言的锤炼,更在于“心之得”,即把一腔穷愁不平之气磨揉化解为平和之音、淡泊之意。正是有这种“磨揉”与“化解”,使得平淡之美包含着情感的内在冲突与张力,具有了独特的美感。欧公又说:
圣俞常语予: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同上)
是知梅公的“唯造平淡难”,不独立意难——心有所得;而造语亦难——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还要将写景与表意融合,含言外之意,斯为至善至高之境。所以,欧公说梅公:“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41]可以说梅公的“平淡”论,是对宋以前关于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论述的极好概括,开启了宋人重“韵味”的风尚。
综上所述,梅公倡“平淡”,是建立在处穷而能保持淡泊的心态并孜孜追求艺术高境的基础上的。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也说,梅尧臣的诗“确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方才到达平淡之境的”[42]。这需要有坚毅而超脱的精神,梅公说的“文字出肝胆”,指的恐怕就是这种精神。因平淡之美包含着情感的内在冲突与张力,又有文字的反复锤炼,可谓是“平淡而山高水深”。张舜民(字芸叟)说:“梅圣俞之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见之,不觉屈膝。”[43]梅公倡导的“平淡”,其意义不仅在于革除西昆体浮华雕琢之文风,更在于开启一种美学风尚,崇尚一种人生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