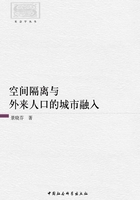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
本书主要关注外来人口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对不同城市空间位置的占据对他们的城市融入存在什么样的影响。从空间角度对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进行研究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城市空间表征变化
1978年开始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序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的是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社会阶层、职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变化。此后,中国一直处于“转型”话语之下,这一转型涉及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城市和乡村。城市空间作为人类活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场所,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于其中,不同时期因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同,城市空间都呈现出与之相关的布局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和国内外的严峻环境,我国实行了全盘的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组织生产过程以及分配消费品。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并出于人口管理的需要,单位制成为一个合理选择,因为单位是一个“既能最大效益地安排生产与生活,又能把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空间组织”(顾朝林,2004),几乎所有的城市劳动居民都被分配于不同的单位,这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体现在城市空间格局上就是:城市以一个个单位为界被分隔成几乎同质的社会空间,各个单位在生产生活方面都自成一体,构成一种单位社区。单位社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或半封闭空间,人们的工作、生活、居住空间高度重叠。最能体现空间格局的住房主要是通过福利的方式分配给单位职工,分配的原则主要是根据级别、工龄、婚姻状况、家庭情况等,在单位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住房差异,形成住房资源上的低水平短缺。在单位外部,因为不存在住房市场,所以收入对个人或家庭的住房情况并不构成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城市虽然实行的是街居制管理体制,但实际上对社会的控制权却是分散于各个单位之中,街居只能管理少数的城市无业人员。这种由单位社区而形成的空间分隔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空间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城市空间的隔离主要体现为单位间的隔离,空间差异也主要体现为单位差异。单位是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功能为一体的空间,城市的功能分区不明显,整个城市空间处于一种工业、商业、生活混杂的状态,缺少主题鲜明的公共空间。官僚组织和经济组织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合二为一,从而使得经济组织也具有了国家行政功能(李路路、李汉林,2000),这是当时政府社会运行在空间上的表征。在这里经济力量显然是被政治力量(政府的计划)覆盖了。这种由单位制形成的社区空间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在空间上的一种体现,在一个强调集体高于个人的年代,社会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遭到政治空间的挤压,处于一种微不足道的境况。在当时的先生产、后生活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政府统管一切的政治空间过多地挤占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这一时期在社会结构上也比较简单,城市阶层构成以工人、干部以及少数的无业人员为主,但这种社会阶层上的分化并未形成独特的空间形态,在职业空间、居住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上不同阶层都呈现很大的重合。虽然社会职业分化明显,但在强调“职业只不过是不同的劳动分工”的大背景下,职业并没有成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城市空间上也未形成围绕职业等级的分异或隔离。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开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中从全面干预转向逐渐退出,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逐渐减弱,整个社会开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原来单一的经济主体变得多元化,一系列的民营、私营、外资、合资企业纷纷兴起,经济形态的多样化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和单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新兴的经济形态与单位制下企业不同的是,它们只承担经济功能,员工与企业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员工除了在工作上与企业发生联系以外,其余的居住、生活、社会交往等都在单位以外完成。另外,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退出,原来国家统领一切的无处不在的政治空间也开始退缩。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兴经济形态的冲击和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原来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传统单位制企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许多国企陷入困境,纷纷改制或破产,改制或破产后的国有企业中原来单位包办的居民社会生活部分交由市场或社会去管理,传统的单位社区就此瓦解,体现于城市空间的便是原来的单位大院的消失。再加上同时期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许多城市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都提出了“退二进三”的产业调整目标,原来的许多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向城外搬迁,而原来的生活区则继续留在城中,这就导致了融生产、生活、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单位制发生分裂,单位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经济空间,原来职住一体的格局也不复存在。
伴随着经济形态转变而来的是城市政府对于城市发展的规划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这两方面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发展目标指导下,各地的城市政府都主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如旧城中心改造,修建用于居民休闲交往的广场、绿地、公园;整修道路,建造供居民购物娱乐游憩的中心场所等,这些都大大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同时,我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由原来的福利住房制度向市场化方向转变。1988年,国务院发布《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是房改的开始,到了1994年,国务院再次颁发《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开始并向深入迈进。与住房制度改革相随的是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从90年代起,全国房地产开发热潮涌起,并一直持续至今。住房制度改革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原来住房只依赖单位供给的单一途径被打破,住房不再由单位统一解决,而是自行到市场上寻求,对住房空间的选择更多地体现出个人的主观意愿、经济能力、文化偏好等。
这一时期,城市空间表征变得多样化起来:
(1)因为财政制度的改革和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标准,激发了城市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强大动力,政府直接介入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中,造就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空间,如商业中心、道路、休闲广场、公园、绿地等。
(2)延续至今的单位制在城市中还有部分存在,如部分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依然保留了单位制下的空间格局,只不过将一些原来由单位承担的服务性的业务分离出去,但在空间上基本上还是保留了职住一体的格局,在住房分配上还存在着统一建房或统一购买的方式,其居住方式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3)从房地产市场自行购买住房的,对这部分人来讲,收入是决定其居住区位、房屋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内部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经济实力较强的,居住于环境优美的城市空间,而一些较为下层的,只能购买政府提供的位置较为偏远的经济适用房以及从城市中心置换的郊区住房。
(4)在城中村这样的“城市飞地”中还存在着身份依旧为农民的城市居民,他们的住房主要是宅基地上的自建房,为了追求房租带来的利益,他们通常将自建房加高、分割,形成一种高密度的居住空间。
(5)进入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员,一般居住于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自己租住在城中村和城郊村,居住地不稳定且环境较差。
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空间分配过程中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当强势阶层凭借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占据了空间分配过程中的有利地位时,弱势阶层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遭到了剥夺,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社会矛盾。同时,城市景观的反差也越来越明显:高档的门禁社区、奢华的购物休闲娱乐场所、城市优质地理空间的私人化与矮小脏乱的棚户区、拥挤不堪的城中村、廉价商品充斥的地摊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城市空间更新和城市空间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如何使城市空间的分配更为合理,在分配过程中保障各个阶层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是本书写作的主要动机。
(二)城市化进程使得原来分处城乡两个空间的矛盾压缩进了城市这一空间,城乡差距的对比更为明显和直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乡关系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即1949年到1953年。在这个时段,中国社会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农业,城市工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一时期并无明显发展。在社会结构上虽然表现为城市和乡村两种形态,但并未形成城乡对立格局,各种资源要素和人口都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从1957年开始,国家开始重点发展城市工业,为了获取工业启动的原始资本,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后来扩大到几乎所有产品。同时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无序涌入城市而带来的城市压力,开始实行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从此以后,通过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将城乡置于相互隔离的两个环境之中。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都是处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之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连接是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来实现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并不直接发生联系。城市和乡村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之中,城市人和农村人也成了身份地位不同的两个群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城乡之间存在着贫富和身份地位差距,但因为国家对整个社会的严格管控和城乡之间的绝对封闭,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讲只是一个遥远的羡慕目标,除了感叹城市人命好之外,大多数农村人包括整个社会并未对这种城乡间的不公平做太多深入的思考,因而在人们感知上并未形成自觉的、强烈的城乡不公意识。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经过几年发展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如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到1.86∶1(见图1—1)。但建立在农户积极性基础上的动力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很快,农村发展进入瓶颈期,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增收困难。而从1985年开始,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城市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阵地,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差距再次拉大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农业收益的下降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将目光投向城市,同时,户籍制度的松动也使得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可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全国范围内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农民工进城带来的城乡关系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便是将原来的处于两个隔离空间的城乡矛盾集中到了城市这一空间,在城市地域内部,农民工与城市其他阶层之间的相依和共存、对立和冲突全方位上演。城乡关系不仅全部体现于城市地域和乡村地域之间,而且也体现在城市内部各个不同的空间上。为此,将城市空间作为社会流动背景下城乡关系的一个研究场域是城乡关系变迁现实的必然选择,从空间的角度对外来人口进行研究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

图1—1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1957—200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三)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以及城市外来人口构成情况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城市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从20世纪80年代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以来,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从1985年的约250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5863万人(见图1—2)。除了绝对数量的增长外,经过近30年的时间变迁,农民工的构成情况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表现在:
(1)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一个独特的引人关注的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8487万人,占所有农民工的58.4%;2010年为6502.04万人,占所有农民工的42.4%。[1]通常人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是他们年轻、文化程度较老一代农民工要高、缺乏务农经历、吃苦耐劳特征较弱、外出动机兼具经济与发展两种考虑、生活方式上与城市人更为接近、有更强烈的留居城市的意愿,但对来自城市的歧视和社会排斥更为敏感等(王春光,2001;刘传江、程建林,2007;姚俊,2010等)。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处于未婚状态,他们大部分的重要人生事件将都要于城市务工期间完成,如恋爱、结婚、生育、子女上学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2010年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做的调查也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时已婚的占60.20%,他们大都是在婚后外出的,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已婚的仅有5.23%(景晓芬、马凤鸣,2011),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要在城市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伴侣,返乡对于他们变得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不可能。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这些特征使得他们不愿意将城市作为自己生命历程某个阶段的暂时场所,他们将自己的未来更多地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

图1—2 1985—2011年农民工数量变化(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1985—2007年数据来源于杨聪敏计算,他用来估算外出农民工(即本乡镇以外务农农民工)数量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次《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调查中都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进行数据收集,因而在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异,农民工的数据也只是大概的估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在缺乏农民工数据的情况下,这样的估算不失为测算农民工数据的一种尝试。2008—2011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在农民工监测数据中,外出农民工被界定为: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2)农民工迁移模式从个体外出向家庭迁移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民工进城呈现出与流动初期不同的特征,其中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从一开始的单个外出向举家迁移转变。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数据显示,从2008—2011年,农民工家庭外出人数依次为2859万人、2966万人、3071万人、3279万人。《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也显示:“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家庭外出与个体外出对于农民工本人和他们所进入的城市空间意义是不同的,一般来讲,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尤其是当有子女一同外出时,他们所面临的城市生活内容比个体外出的农民工要丰富得多,城市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消费空间。以住房空间需求为例,个体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为15.5%;而夫妻一起外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32.7%(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远远高于前者。另外,还有对更多的日常用品的需求以及可能面临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公共空间需求等。
(3)虽然也有大量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有着强烈的返乡意愿,但多是老一代农民工,而且他们返乡多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力在城市继续工作的无奈选择或出于叶落归根的想法,当然也有部分是回乡创业,但毕竟是农民工中的少数,大多数的农民工,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都还是在城市中接受他人雇佣。所以,无论是决定留城还是具有强烈返乡意愿的农民工,他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城市中度过,如果将一个生命中二三十年都在城市中度过的人还视为农村人,将与他生活相关的所有安排还放在农村的话,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个人不便和社会麻烦,在城市政府周到地为那些短暂居留城市的旅行者或商务人士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设施和良好的服务时,没有理由将在城市中生活半辈子的农民工排除在外。
农民工构成的这些变化和他们在城市中的长期生活对城市空间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与这种强烈需求相对应的现实情形是他们在空间分配过程中的极端不利位置。从居住情况来看,农民工住在单位宿舍和工地工棚的比例为42.6%,租住私房的为34.6%,仅有0.7%在城市中拥有自购住房(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无论是住在单位宿舍、工棚还是租住私房,其居住环境都不容乐观而且流动性很大。从居住空间区位来讲,大多是在与城市其他阶层居民相对隔离的地域,无论是单位宿舍、工棚还是租住城中村的私人住房,都是一个与城市中其他群体相对独立与隔离的空间。空间上的这种隔离可能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着非常负面的制约作用。对比农民工参与空间分配的意愿和农民工在城市空间分配中的现实状况,将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放在公平参与城市空间分配和空间调整的大背景下显得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