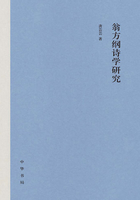
第一节 “肌理”的被定义与“一衷诸理”
这个流行颇广的解释,源于翁方纲的两句话:“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原文出自《志言集序》:
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
因为后文直接提出著名的“为诗必以肌理为主”的观点,所以,此处的“肌理”正是我们要讨论的诗学概念。但翁方纲想说的是,此一“理”,大而统摄万民万物,这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大环境;近而系诸平常事境,而事境又是诗人创作的基础 ;细而关联声音律度,此是诗作的基本要素。人间万事万物,统而归于一“理”,而“文理”、“条理”、“通理”,都是“理”于不同场合呈现的各种状态。这段话意在说明“一衷诸理”,无论是自然生物,还是人文活动,无一例外。“义理”之理,与“文理”之理,与“肌理”之理,都归于一处。这里并不是解释“肌理”的含义,否则为何不将“肌理”置于“义理”和“文理”之前?可见,仅从这则材料推出“肌理”包含“义理”和“文理”,是不确切的。
;细而关联声音律度,此是诗作的基本要素。人间万事万物,统而归于一“理”,而“文理”、“条理”、“通理”,都是“理”于不同场合呈现的各种状态。这段话意在说明“一衷诸理”,无论是自然生物,还是人文活动,无一例外。“义理”之理,与“文理”之理,与“肌理”之理,都归于一处。这里并不是解释“肌理”的含义,否则为何不将“肌理”置于“义理”和“文理”之前?可见,仅从这则材料推出“肌理”包含“义理”和“文理”,是不确切的。
而在翁方纲《理说驳戴震作》一文中,亦有相似的表述:
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义理之理,即文理、肌理、腠理之理,无二义也。
戴震认为“理”是密察条析之谓,而非性道统挈之谓,反对朱子“性即理”的观点,他由对“理”的理解,向朱子发起挑战。翁方纲在此处即强调“理无二义”,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所有的“理”都可以归一,所谓“文理”、“义理”、“肌理”,都无一例外。此处也并非解释“肌理”的含义,否则“腠理”一词又将如何安置?
“理”,即程朱理学,是翁方纲一生奉为圭臬的学说,他将一切都归之于一个“理”字,对相畔者视如仇敌。这样的一个彻上彻下的概念,只能说是诗学的指导原则,而不是他的学说内涵。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就能清楚“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的真正意义,就能避开对“肌理”内涵解释上的误区。
研究者都注意到“理”在翁方纲诗学中的崇高地位。这个地位的无上性,是任何概念也无法比肩的。“理”不但是其诗学,更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的交叉现象,导致了一些论述的混乱。那么,要彻底认清这个问题,解开“理学诗”的误会,必须从翁方纲学术思想的“理”谈起。
一、“考订以义理为主”
研究者都关注翁方纲诗学与乾嘉学术的关系,或认为他是考据学家,或认为他是理学家。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身份做过评定。他既用汉学考证的方法,从事金石研究,同时又有笃守程朱的一面,坚信“考订以义理为主”。他是一个历任地方学政的文人,对于官方学说的权威性有尊崇的义务。实际上,他也相信自己的坚持。
从康熙开始的“融理学于经学”的思想,在乾隆朝得到了实践。乾隆十年(1745)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蒋元益等三百一十三人于太和殿,指出:“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 之所以最高权威提出这一点,原因之一就是对鄂尔泰、张廷玉等理学名臣言行不一的失望。于是,以究经义为目的的“汉学”,便开始风靡。
之所以最高权威提出这一点,原因之一就是对鄂尔泰、张廷玉等理学名臣言行不一的失望。于是,以究经义为目的的“汉学”,便开始风靡。
当然也有人反对考证的方法,故而争议在所难免。乾隆四十年(1775),钱载、戴震论学不和,翁方纲致信程晋芳,对此作评:
萚石谓东原破碎大道,萚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况宋儒每有执后世文字习用之义,辄定为训诂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辨,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然二君皆为时所称,我辈当出一言持其平,使学者无歧惑焉。
他由宋儒的空疏,指出明义理必须先细究考订诂训,从而对曾与之深交的钱载作出批评。在乾嘉学人中,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派,所求在“会诸经,而求其通”,虽出入汉儒门户但不守藩篱,讲求综贯会通,不偏至一家,他们的目的在于究诂训而明经义: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孔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训故、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故训明则古经明”,在这场争论中,翁方纲站在戴震一方。但他反对戴震“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的观点:
东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可矣。若综诸经之义,试问《周易》卦、爻、彖、象,乘承比应之义,谓必由典制名物以见之,可乎?《春秋》比事属辞之旨,谓必由典制名物见之,可乎?即《尚书》具四代政典,有谟训诰誓之法戒存焉,而必处处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即《诗》具征鸟兽草木,而有忠孝之大义,劝惩之大防,必尽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圣门垂教,《论语》其正经也,《论语》、《孟子》必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孝经》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戴君所说者,特专指“三礼”与《尔雅》耳。“三礼”云者,经部统签之称也。究当分别言之。……学者正宜先知《礼运》首段之并非歧入异说也,又宜知《学记》之并非泛事空说也,又宜知《玉藻》郑氏所明脱烂处之不宜径皆接合也,又宜知《乐记》十一篇之宜各审其篇次也。此又岂概以典制名物得之者乎!《周官》、“六典”何以不略见于诸经,《礼记》“六太”何以不同于《周官》?古籍邈远,不能详征,必欲一一具若目见而详陈之乎?况《礼》所具者,周典耳。夫子于夏殷礼皆能言之,以其无征,故民弗从,而不言也。今虽周之典制,尚有存其略者,而其于善之无征,民之弗从,则一也。是以方纲愚昧之见,今日学者,但当纂言,而不当纂礼。纂言者,前人解诂之同异,音训之同异,师承源委之实际,则详审择之而已矣。
他这里反驳戴震的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很多义理本身由于形而上的本质,无法通过考证获得;二是古籍邈远,很多义理之真伪正误无法验证。他举出《周易》卦象、《春秋》大义、《尚书》政典的法戒作用、《诗》中鸟兽草木的比兴,还有《论语》、《孟子》、《孝经》等圣人立言之作,其中体现的义理都无法由典制名物考证。那么,戴震或者是专指“三礼”和《尔雅》吧。研究“礼”,确实需要对大量的名物制度有深厚的考证功夫,但是,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必须先对“礼”本身的基本知识进行了解。比如“《礼运》首段之并非歧入异说”,即相信文中孔子对大同、小康社会的描述不是异说,这是对下文关于礼的发展和运用的描述,及通过礼治达到大顺境界的理解基础,也是典制名物考证的基础。而这个信仰本身是无法通过典制名物考证来证实的。即使可以通过考证证实义理的地方,很多由于古籍邈远,若要一一从典制名物证实,也是不可行的。
于是,翁方纲提出:“今日学者,但当纂言,而不当纂礼。”他对于学《礼》的观点是“学《礼》者,师其意而已矣。知其意则其礼至今可行也” 。《礼》的合法与否,已经无需证明,今人需要做的,只是对前人的解诂、音训、师承原委,进行审核别择的工作,这就是纂言。其实,这是他对阎若璩辩难《古文尚书》的反驳。他认为惠栋、戴震等人“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但并不欲子弟朋友效之。他虽“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但“考订必以义理为主”。
。《礼》的合法与否,已经无需证明,今人需要做的,只是对前人的解诂、音训、师承原委,进行审核别择的工作,这就是纂言。其实,这是他对阎若璩辩难《古文尚书》的反驳。他认为惠栋、戴震等人“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但并不欲子弟朋友效之。他虽“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但“考订必以义理为主”。
然而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未如翁方纲想象般,在考订与义理间找到平衡点,而是弊端百出:
凡嗜学多闻之士,知考订者,辄多厌薄宋儒以自憙,今日学者之通患也。
也有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凌廷堪:或者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
宋儒空疏,导致空谈,这已经毋庸置疑。但是现实的状态是,汉学家往往矫枉过正。这种平衡的想法被现实打破了,翁方纲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变化。因为他有与汉学家相区别的基本态度。
乾隆五十七年(1792),发生了一件事,在翁方纲的仕宦生涯中,可谓一劫:
六月二十六日,乾隆颁谕,指斥山东学政翁方纲姑息坊贾删节经书陋习:
谕曰:翁方纲奏科试情形一折,内称考试士子经解默经时,却于坊间所删经题内出题,其有未读全经者,概不录取等语。《五经》为圣贤垂教之书,士子有志进取,竟有未读全经者,可见士习之荒疏卑靡。翁方纲身任学政,自应认真董率,俾承学之士全读经义,身体而力行之,方不负训迪之责。如《诗》、《书》内不祥讳用语句,不便出题,乃后世过于回避之陋习,朕所不取。兹公然竟有删去者,岂不可鄙!是亦学术式微之一大证也。经籍俱经孔子删定,岂容后人更复妄有删节!今该学政明知坊间删经之不可,而不能去,不过调停其间,且相沿陋习形之奏章,若为定例然。殊属非是,著传旨申饬。……此事于士风大有关系,不可不明为查禁。著通谕各督抚及学政等,务须实心查察,严行禁止,俾士各通经,文风振作。
在数十年官宦生涯中,翁方纲作为一介儒臣,虽无多大建树,但始终谨慎存身。这次乾隆的指斥对他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打击。这件事并没有随着他的请罪而结束。乾隆随即颁布全国查禁删本经书、解京销毁的谕旨。翌年三月十三日,又颁谕,重申查禁删本经书,以“整饬士风,崇尚实学” 。四月二十三日,又“因各省查禁删本经书,惟山西、广东两省所办较为认真,其余各省收缴无多”,再次强调“著该督抚等,将各属每年收缴若干之处,于五年汇奏一次,以副朕整饬士风,崇尚实学之意”
。四月二十三日,又“因各省查禁删本经书,惟山西、广东两省所办较为认真,其余各省收缴无多”,再次强调“著该督抚等,将各属每年收缴若干之处,于五年汇奏一次,以副朕整饬士风,崇尚实学之意” 。七月二十七日,再次颁谕重申查禁坊间“删节陋本”
。七月二十七日,再次颁谕重申查禁坊间“删节陋本” 。
。
其实,翁方纲的思想,与乾隆关于“实学”的强调,正相契合。他认为“古文诸篇,皆圣贤之言,有裨于人、国家,有资于学者” 。他所强调的实用,不是说汉学家都脱离实际,而是说“义理”本来就有益于治国治家,不必要在这上面下功夫考证得失。只要有实用性就行,何暇顾忌其真伪?翁方纲结合“整饬士风,崇尚实学”的上谕,对当下的学术实际进行了剖析:
。他所强调的实用,不是说汉学家都脱离实际,而是说“义理”本来就有益于治国治家,不必要在这上面下功夫考证得失。只要有实用性就行,何暇顾忌其真伪?翁方纲结合“整饬士风,崇尚实学”的上谕,对当下的学术实际进行了剖析:
迩者大江南北之士,颇皆知俗儒兔园册子之陋,知从事于注疏矣,知研习于《说文》矣,而徽国文公(按:指朱熹)之正学,迩之在日用行习之地。虑或有转事高谈汉学而卑视宋儒者,其渐不可不防也。往时学者专肄举子业,于训诂考证置之弗讲,其弊固已久矣。今则稍有识力者,辄喜网罗旧闻,博陈名物、象数之同异,以充实为务,以稽古为长,是风会之变而日上也。而此时最要之药,则在于扶树宋儒程朱传说,以衷汉、唐诸家精义。是所关于士习人心者甚钜。
同样是对学术现状的分析,翁方纲的态度与之前评钱戴之争时,已经大不相同了。这里集中批判的,是时人滥用汉学名义,网罗旧闻,以稽古为务,却忘了乾隆强调的“通今”。他提出的针砭之药,便是扶树宋儒程朱传说。这是程朱传说在学风中被束之高阁的情况下发出的号召。他对程朱传说的强调,在于纠正学风。这其中包含学官的责任心,或许比学者本身的担当更为重要。所以他后来在各地为学政,都强调这一点,希望即将出任安徽学政的吴廷选也这么做,以纠正士习人心。
那么,对程朱义理的尊崇,就成了翁方纲治学思想的核心。他在《理说驳戴震作》中,强烈地表达了对戴震涉猎理学的不满:
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就其大要,则言理力诋宋儒。以谓理者,是密察条析之谓,非性道统挈之谓。反目朱子“性即理也”之训,谓入于释老真宰真空之说,竟敢刊入文集,说“理”字至一卷之多。其大要则如此,其反覆驳诘、牵绕诸语,不必与剖说也。
戴震等人其实也是持考据为究明经义的观点。为何当戴震涉足经义时,翁方纲会如此激动?原因很简单,就是戴震所讨论的经义,不是程朱“义理”,违背了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最基本定义。这是对整个程朱理学的震撼,在翁方纲看来,自然是“侈言” 。
。
于是,翁方纲提出“为学不可自外于程朱” ,开始全面强调以程朱义理为上。虽然他赞同在义理范围内的考订是合法的,但是也指出疑古的害处,并对考订做出限定:
,开始全面强调以程朱义理为上。虽然他赞同在义理范围内的考订是合法的,但是也指出疑古的害处,并对考订做出限定:
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异、不嗜博嗜琐而专力于考订,斯可以言考订矣。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
他认为,之所以有如阎若璩、戴震之类从考订动摇程朱理学的人,也就是考订不以义理为主的人,是因为他们嗜异、嗜博或嗜琐,斤斤于断章片语,便质疑整个义理之学。考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阙疑才可考证,而不是经义必须从考证处得之。一如《古文尚书》十六字真言,和对“理”的阐释,朱子已经说得很明白,完全不必存疑,更无需考订。在翁方纲看来,这些不是考订当用力之处。
二、作诗“一衷诸理”
针对严羽以禅喻诗得出的“不涉理路”,王渔洋宗之,进而认为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字不必深究,翁方纲深不以为然。他恰恰着重分析了这个“理”字:
杜之言理也,盖根极于六经矣。曰“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 《易》之理也;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书》之理也;曰“春官验讨论”, 《礼》之理也;曰“天王狩太白”, 《春秋》之理也。其他推阐事变,究极物则者,盖不可以指屈。则夫大辂椎轮之旨,沿波而讨原者,非杜莫能证明也。然则何以别夫《击壤》之开陈、庄者欤?曰:理之中通也,而理不外露,故俟读者而后知之云尔。若白沙、定山之为“击壤派”也,则直言理耳,非诗之言理也。故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此善言文理者也。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且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沉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而或仅以藻缋目之,不亦诬乎!
翁方纲是极力反对陈白沙之言理诗的。他认为“白沙定山之为‘击壤派’也,则直言理耳,非诗之言理也”。若如陈白沙“直以理路为诗”,则“不足以发明六义之奥而徒事于纷争疑惑”。所以,“诗之言理”有其独特的方式,应当如杜诗一般,“理之中通,而理不外露,故俟读者而后知之”。
翁方纲用训诂的方式对“理”字进行剖析:“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他并引《易》中“言有物”作为理之本,“言有序”作为理之经,从而阐明“理”与“言”的关系 ,得出“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提出“不涉理路”的反命题。那么,所谓“熟精《文选》理”,具体指的是什么?“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沉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杜诗中表现出来的,本乎《文选》的“孝敬”、“人伦”的“理”,可为示范。这个“理”“贯彻上下,无所不该”,又必须在行文时不偏一隅,既非“不涉理路”,又非“直以理路为诗”,才算得上真正根极于六经,阐发其旨意。
,得出“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提出“不涉理路”的反命题。那么,所谓“熟精《文选》理”,具体指的是什么?“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沉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杜诗中表现出来的,本乎《文选》的“孝敬”、“人伦”的“理”,可为示范。这个“理”“贯彻上下,无所不该”,又必须在行文时不偏一隅,既非“不涉理路”,又非“直以理路为诗”,才算得上真正根极于六经,阐发其旨意。
在《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中,翁方纲所举的杜诗例子,其实并非如其所言体现了六经之理 。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理论叙述而断章取义,目的是以此强调“理”的重要性,及其与诗的关系。在晚年编选《志言集》时,他提出了作诗“一衷诸理”的观点:
。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理论叙述而断章取义,目的是以此强调“理”的重要性,及其与诗的关系。在晚年编选《志言集》时,他提出了作诗“一衷诸理”的观点:
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
翁方纲将“理”与“诗”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化。在心为志,言者,心之声也;发言为诗,诗者,言之精,谐之声律者。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和实践,都必须衷于“理”。而“理”又有各种存在方式,“文理”、“条理”、“通理”、“义理”、“肌理”等等。他在《神韵说》中又说“理亦即神韵也”,即“理”可体现于“神韵”。“理”的地位得到无限强化。“理”指的是程朱义理。
对于诗而言,“理”的根本,体现于六经。只要后世诗文体现六经的精神,便是遵循“理”的要求。“理”既然涵盖一切,学问当然也是“理”的一种存在形态,所以“考订以义理为主”。我们要注意的是,既然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形式,那么“学问”就并不等同于“理”。所以有的研究者将翁方纲充斥学问的诗,称为言理之诗,是不对的。前文讨论过,至于形式,他反对陈白沙《击壤篇》的写作方式,强调“理之中通”,而“理不外露”。“理”是作诗的最高标准,是诗思的终极体现,但并不是诗的具体内容。诗的具体内容,是承载“理”的各种题材,如忠孝,如友悌,如节义,如学问,并一切在六经中已含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