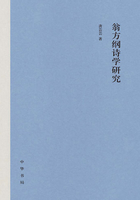
第二节 研究契机和研究构思
郭英德先生在《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中,总结了明清文学研究的难点:材料太多,成见太多,问题太多,研究者太多 。笔者认为,成见太多,是难中之难,却也是突破口。一旦确立了“成见”的存在,就预示着我们工作的意义,至少可以纠正一个文学史的误会。
。笔者认为,成见太多,是难中之难,却也是突破口。一旦确立了“成见”的存在,就预示着我们工作的意义,至少可以纠正一个文学史的误会。
郭绍虞等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讨论,基本上确定翁方纲的核心诗学思想为“肌理”说,内涵就是“义理与文理”。“肌理”说与王士禛“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并立为清中期“四大学说”。这些定论一直被沿用在各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中,并且理所当然成为翁方纲研究或清代中后期诗学研究的立论基础。这样的基础似乎不可动摇。以“义理和文理”为“肌理”说的核心,并将其他诗学概念整合进来,是一种求统系而极易忽视细节的研究思路。因为以“肌理”评诗,在翁方纲前期的资料中,这一概念并不通行,且含义并不固定。而又以“肌理”与其他三大学说并立,似乎是四足鼎立划分天下的观点,事实上忽视了清代中期诗学观念的演变实际。
注重纪实题材,倾向写实的艺术手法,以及在诗中表现渊博学问的清诗的主流风格,在乾嘉道时期逐渐成型。一种稳定的诗风的形成,必然包括理论的倡导、传播,及其指导下的创作实践。这个过程中,翁方纲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和过程的清理是认知的重要环节”,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是蒋寅先生提出的清代诗学研究方法 。
。
所以,本书的关注重点,可以归结为三个:
第一,翁方纲诗学(不仅仅是被称之为“肌理”的部分)的形成过程;
第二,将翁方纲诗学置于清代诗学的环境中,考察与之有关的诗学演变过程;
第三,翁方纲诗学理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影响和演变。
第二个问题事实上可以包含第一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联系紧密,所以本书的思考立足于整个清代诗学史来进行,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为翁方纲“肌理”说辨析。这部分从郭绍虞先生对“肌理”的误会开始讨论,重新考察引起误会的材料。并以翁方纲的学术思想为背景,对“理”的内涵与价值进行深度辨析。然后结合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手稿本《石洲诗话》卷十,以及《杜诗附记》的例子,对“肌理”说的内涵进行讨论辨析。无论是“理”,还是“肌理”的讨论,都注重展现思路的形成过程。最后纵观翁方纲“肌理”说的建构过程,讨论其特点、价值及缺失。
第二章和第三章便是观照翁方纲诗学在整个清代诗学中的价值。作为王渔洋的再传弟子,其诗学建构过程,就是走出“神韵”的过程。第二章从探讨翁编《七言诗三昧举隅》的动机入手,并结合他对渔洋七律学古实质的发现进行分析,进而解析“神韵即格调”的断语。为与渔洋尊奉的“妙悟”立异,他拈出了“正面铺写”作为诗歌的最高理想,并因此强调“切实”,要求诗歌达到切实能“化”的境界。本章最后对“正面铺写”与“肌理”、“事境”的关系进行辨析。
清代唐宋诗之争到了乾嘉时期,症结在于对宋诗价值的判断。翁方纲为宋诗特征的定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并不是从寻求与唐诗的异质角度定义宋诗特征,而是将宋诗放在整个文学史中,通过与唐诗进行类比,展现作为一个时代的宋诗特征。这些都是他从批评《宋诗钞》开始的。他首先反对以某种风格论宋诗;更重要的是,他将杜甫置于整个文学史进行思考,认为杜甫不但代表唐代,而且代表整个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通过“节制”、“逆笔”等将杜甫与宋诗代表苏轼、黄庭坚联系起来,于是,关联唐诗和宋诗的,就不再是某一种风格,而是“肌理”、“正面铺写”等内化的诗学理念。与之相关的,翁方纲用“事境”理论将学界争论不休的学问与性情合一,从而“以学入诗”得以合法化,唐诗与宋诗具备了风格之外的共同特征。
第四章观照翁方纲的诗学实践及其影响。面对清代中期的诗歌创作环境——学问的细化和试帖诗的盛行,翁方纲都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取舍分明。他的诗歌创作被袁枚、洪亮吉等人批评为“以考据入诗”。本章深入分析“以考据入诗”评语的具体内涵,并一一进行辨析,认为“句句加注”、抄书、缺乏性情等,都不构成“以考据入诗”的断语。翁诗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缺点,正体现了其诗学理论的特征和缺陷。而追究到袁枚等人反对的实质,其实是诗歌题材,所以翁方纲的诗歌应该称之为“以金石入诗”。他用诗学理论和诗歌实践构建并发扬“以金石入诗”,后来冯敏昌、梁章钜、阮元、潘祖荫继承并做出修正,达到真正救“神韵”之虚的目的,成就了徐世昌总结的“清诗第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