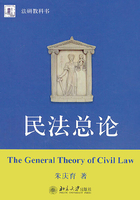
第三节 民法的法源
一、法源的含义
法源系法律渊源(Rechtsquelle)之简称,有广狭两义。狭义法源称规范法源(präskriptive Rechtsquellen)或法学法源(juristische Rechtsquellen),对法官具有法律拘束力,法院裁判应当予以援引;广义法源则进一步包括所有能够对法律产生影响的事实,举凡法学著述(“法学家法”)、行政活动、法院实践以及大众观念(一般法意识)等,均在其列,它们虽然未必能拘束法官,却有助于形成法律认知,往往构成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应的,此类法源可称“社会学法源”(soziologische Rechtsquellen)。 规范法源与社会学法源的区别主要有二:前者具有规范性特点,后者则是一种社会事实;前者应得到法官的援引,后者则对法官无拘束力。不过,此等界限其实颇为模糊。例如,学界“通说”对于法官并无拘束力,乃是一种事实存在,属于社会学法源;但“通说”常为法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具有应然的规范结构,法官可直接援引判案,在此意义上,又不失为规范法源。
规范法源与社会学法源的区别主要有二:前者具有规范性特点,后者则是一种社会事实;前者应得到法官的援引,后者则对法官无拘束力。不过,此等界限其实颇为模糊。例如,学界“通说”对于法官并无拘束力,乃是一种事实存在,属于社会学法源;但“通说”常为法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具有应然的规范结构,法官可直接援引判案,在此意义上,又不失为规范法源。
法源论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法官应援引何种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以及如何依规定之不同来源进行体系化整理。 可见,法源论在实证法学中占据基础地位,唯有首先了解法律如何构成,才有可能进一步谈及法律规范的效力、解释、适用等实证法学的各种问题。另外,在法律理论上,法源论亦是法学流派得以形成的基础,所谓自然法学派、法律实证主义、历史法学派,之所以并峙而立,在某种程度上说,无非是因其各自所持法源论不同而已。
可见,法源论在实证法学中占据基础地位,唯有首先了解法律如何构成,才有可能进一步谈及法律规范的效力、解释、适用等实证法学的各种问题。另外,在法律理论上,法源论亦是法学流派得以形成的基础,所谓自然法学派、法律实证主义、历史法学派,之所以并峙而立,在某种程度上说,无非是因其各自所持法源论不同而已。
二、民法法源的基本框架
(一)规范法源
民法法源的类型较为繁复,广至国际公约、窄至村规民约,上至中央立法机关的制定法、下至地方各级政府的具体政令,均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民法裁判。为简化问题,本书主要以最高法院2009年发布的《裁判规范规定》为据,对我国法院应予援引的民法规范法源框架略作分析。在此司法解释中,民法法源被分为两档,一是作为裁判依据的法源,即规范法源,包括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第4条),二是作为裁判理由的法源,指的是前述列举之外,“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的规范性文件(第6条),主要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政府规定等。第二档法源介于规范法源与社会学法源之间,可称“准规范法源”:具有规范性,但对于法院无拘束力,法官可经自由裁量选择适用;同时,此类规则不得直接充当裁判主文的依据,只能用作裁判理由。
下文主要讨论第一档的规范法源。
(二)法律
在成文法国家,制定法(法律)是首先被考虑的法源。问题是,哪些规则可称作“法律”?
《立法法》第2条规定:“(第1款)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第2款)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此条,并结合其他相应规定,“法律”一词可在三个层次上使用:最严格的用法,仅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第7条第1款);其次,亦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第56条),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的市(省会或首府城市、经济特区城市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第63条),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第66条第1款,《民法通则》第151条);最广义用法,则再加上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第71条第1款)、省级与较大的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第73条第1款)。《裁判规范规定》第4条所称“法律”,显然是在最狭义上使用。当然,依据该条,第二层次上的法律,亦是法院裁判的依据,只不过效力等级低于狭义法律(《立法法》第79条第1款)。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一般意义上,狭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均具有民法法源的地位,但亦不排除某些领域有其特别的法源构成,例如,《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此处“法律”,依通说,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狭义“法律”,既不包括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亦不包括司法解释与司法判例。 至于是否包括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则不甚明确,但《立法法》第66条第2款既然授权它们“变通”法律之规定,即意味着,民族自治地方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特点特设物权类型。
至于是否包括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则不甚明确,但《立法法》第66条第2款既然授权它们“变通”法律之规定,即意味着,民族自治地方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特点特设物权类型。
宪法比较特殊。《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由此表明,处于效力等级顶端的宪法并非前文所称“法律”。但我国现行宪法与法律一样,亦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修正。就宪法能否直接作为裁判依据问题,学界存有争议,司法实践亦有反复。 2001年“齐玉苓案”中,被告冒原告之名为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所录取,而使原告失去录取机会,并影响其后的择业,原告就此请求民事赔偿。最高法院应山东高院请示,作出法释(2001)25号批复,称:“……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高院据此批复,直接在裁判主文援引《宪法》第46条作为裁判依据,判令冒名入学的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01年“齐玉苓案”中,被告冒原告之名为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所录取,而使原告失去录取机会,并影响其后的择业,原告就此请求民事赔偿。最高法院应山东高院请示,作出法释(2001)25号批复,称:“……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高院据此批复,直接在裁判主文援引《宪法》第46条作为裁判依据,判令冒名入学的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该案被称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许多学者认为,宪法规范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大门从此开启。
该案被称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许多学者认为,宪法规范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大门从此开启。 然而,七年之后,法释(2001)25号批复被法释(2008)15号《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以“已停止适用”为由废止,至于何以“停止适用”,则未见说明。“宪法司法化”的实践由此停住脚步。
然而,七年之后,法释(2001)25号批复被法释(2008)15号《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以“已停止适用”为由废止,至于何以“停止适用”,则未见说明。“宪法司法化”的实践由此停住脚步。
(三)法律解释
《裁判规范规定》列举的第二项民法法源是“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系在《立法法》的意义上使用,指的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定程序对法律作出的解释(《立法法》第42条1款),即所谓“立法解释”。《立法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在两种情况下需要作出法律解释:第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第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此等“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第47条),其实亦是立法行为。
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未对民事法律做过专门的法律解释,为数不多的法律解释案,集中于刑法领域,而且,各解释案基本上都陆续被纳入修正后的刑法正式文本。
(四)司法解释
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授权最高法院解释“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之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除重申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权外,更将此项权力加授于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所作的法律解释称“司法解释”,构成第三类民法法源。不过,民事案件需要检察院作出解释的情形甚是罕见,作为民法法源的“司法解释”,基本上指的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依最高法院2007年发布的《司法解释规定》第6条,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分“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形式。其中,解释是“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如《合同法解释二》,这类解释亦可能以“意见”、“解答”之名发布,前者如《民通意见》,后者如《名誉权解答》;规定是“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如《诉讼时效规定》;批复是“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如“齐玉苓案”批复;决定则用以“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如《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除批复外,其他三种司法解释均以抽象条款的方式作出,同时,无论何种形式的司法解释,一经发布,即具有反复适用的一般效力,就此而言,司法解释可谓是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的立法权。虽然司法解释有其法律依据——“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但对这一界限模糊的授权,最高法院显然作了扩张解释,不仅具体裁判中的个案解释成为题中之义——以至于有权以“批复”的形式指示下级法院判案,以发布抽象条款的方式进行一般解释亦被理所当然地纳入其中,甚至,法院裁判应如何援引法律规范,也被当作“行业自律”的内容,由最高法院以“规定”的形式发布。这种明显带有自我授权性质的扩张解释,在制定法总是过于粗糙的背景下,直至今日,依然得到我国法律现实的默许。![不仅如此,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经验还向下蔓延,得到各省级高院的纷纷效颦。如,京高法发[2003]38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9]43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此类“意见”当然不是规范法源,但现实中,在我国高度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各高院通常会指令“辖区”内的下级法院遵循,而后者一般都会服从。](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4B284/13173372005581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1940263-YdySvP4kqv2Ui9OSx6QEEcp7gTNxpjwf-0-703f26c20a9cad22ef9ce1144e28af9f)
2010年11月26日,最高法院发布《案例指导规定》,对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第7条),这似乎表明,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法院网站及《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形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6条第2款),将获得相当于英美法上应予遵循的先例的效力。果如此,通过自我授权,最高法院又创造新的司法解释形式。
奉行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国家,司法机关不能拥有立法权力,既无权主张个案裁判得到当然的反复适用,更无权以抽象条款的方式发布一般规范。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此,“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大陆法系国家,甚至一般不以司法判例为规范法源。法官仅对法律负责,任务则在就个案独立作出裁判,因而,任何法院都没有义务以与之前案件相同的方式解释法律,亦没有义务与上级法院作相同裁判,相应地,上级法院无权指示下级法院判案。不过,法院一般会考虑、甚至遵从先前裁判或上级法院类似裁判,但此等遵从只是说明,先前裁判与上级裁判构成社会学法源,与英美法系之遵循先例制度相去甚远。
大陆法系国家,甚至一般不以司法判例为规范法源。法官仅对法律负责,任务则在就个案独立作出裁判,因而,任何法院都没有义务以与之前案件相同的方式解释法律,亦没有义务与上级法院作相同裁判,相应地,上级法院无权指示下级法院判案。不过,法院一般会考虑、甚至遵从先前裁判或上级法院类似裁判,但此等遵从只是说明,先前裁判与上级裁判构成社会学法源,与英美法系之遵循先例制度相去甚远。
三、习惯的法源地位
无论制定法有多完备,都无法给出所有纠纷的解决方案。只不过,这一现象的意义,因法域而有不同。刑法领域奉行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刑法》第3条),制定法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规范法源存在的空间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制定法之“疏漏”,应作有利于刑事被告处理。宪政理念下,公权行为的正当性以法律明文授权为基础,法无明文授权即为无权,由此确立的行政纠纷解决原则是,若制定法存在授权“疏漏”,作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处理,相应的,除了制定法,其他规则在行政法法源上的意义不大。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制定法之“疏漏”,应作有利于刑事被告处理。宪政理念下,公权行为的正当性以法律明文授权为基础,法无明文授权即为无权,由此确立的行政纠纷解决原则是,若制定法存在授权“疏漏”,作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处理,相应的,除了制定法,其他规则在行政法法源上的意义不大。 民法与刑法、行政法不同。当民事被告损害他人时,法官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作有利于被告的判决,亦不得以法无明文授权为由,否认当事人所实施的私法行为的正当性。这意味着,为解决民事纠纷,在制定法之外,尚需其他规范法源作为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习惯法。德国通说在列举民法法源时,即以制定法与习惯法并举
民法与刑法、行政法不同。当民事被告损害他人时,法官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作有利于被告的判决,亦不得以法无明文授权为由,否认当事人所实施的私法行为的正当性。这意味着,为解决民事纠纷,在制定法之外,尚需其他规范法源作为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习惯法。德国通说在列举民法法源时,即以制定法与习惯法并举 ;瑞士更是通过《民法典》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习惯法是制定法的补充法源。
;瑞士更是通过《民法典》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习惯法是制定法的补充法源。
所谓习惯法,是指非由立法者制定,而是通过法律共同体成员的长期实践,并且对其已形成法律效力之信念的法律。 根据罗马法传统,习惯而成为法,须具备三项要件:第一,长期稳定的习惯(longa consuetudo);第二,普遍的确信(consensus omnium);第三,观念上以其为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规范(opinio necessitatis)。
根据罗马法传统,习惯而成为法,须具备三项要件:第一,长期稳定的习惯(longa consuetudo);第二,普遍的确信(consensus omnium);第三,观念上以其为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规范(opinio necessitatis)。 当代德国,习惯法之形成,一般需要借助法官的法律续造活动,如2002年债法现代化法之前的缔约过失与积极侵害债权等制度。
当代德国,习惯法之形成,一般需要借助法官的法律续造活动,如2002年债法现代化法之前的缔约过失与积极侵害债权等制度。 民国有关习惯法的法律实践与立法,明显带有德瑞痕迹。民国《民法典》第1条前段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1928年最高法院一项判例要旨则称:“习惯法之成立,须以多年惯行之事实,及普通一般人之确信心为其基础。”
民国有关习惯法的法律实践与立法,明显带有德瑞痕迹。民国《民法典》第1条前段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1928年最高法院一项判例要旨则称:“习惯法之成立,须以多年惯行之事实,及普通一般人之确信心为其基础。” 这一认识,迄至今日,仍为台湾地区所延续,甚至有所扩张。例如,民国《民法典》第757条原本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习惯法被排除在“物权法定”的法源之外,2009年1月23日,台湾地区颁布“民法”物权编的部分修正案,第757条被修正为:“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习惯由此取得法源地位,修正理由称:“本条所称‘习惯’系指具备惯行之事实及法的确信,即具有法律上效力之习惯法而言”。
这一认识,迄至今日,仍为台湾地区所延续,甚至有所扩张。例如,民国《民法典》第757条原本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习惯法被排除在“物权法定”的法源之外,2009年1月23日,台湾地区颁布“民法”物权编的部分修正案,第757条被修正为:“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习惯由此取得法源地位,修正理由称:“本条所称‘习惯’系指具备惯行之事实及法的确信,即具有法律上效力之习惯法而言”。
在强调制定法的环境下,习惯法的功能往往被定位为填补制定法的漏洞。此亦《瑞士民法典》第1条前段之观念基础。 不过,管见以为,这并不表示,制定法的效力等级必定高于习惯法。民法规范,虽然可能以制定法的形式表现,但不宜视之为立法者专断意志的产物,毋宁说,它只是立法者对于民众交往习惯的概括,因而是被“发现”而非被“创造”的。照此推论,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为立法机关以文字的方式所明确表述,而制定法之所以在法律适用时先于习惯法得到考虑,并非因为前者效力高于后者,而是因为前者的确定性高于后者,更符合法律安全的需求。换言之,若对法律安全无所妨碍,习惯法亦可能优先得到适用。对此,《合同法》第22、26、293与368条等可为佐证。更早的法律实践则可见之于民国时期,1937年最高法院一项判例要旨指出:“依民法第一条前段之规定,习惯固仅就法律所未规定之事项有补充之效力,惟法律于其有规定之事项明定另有习惯时,不适用其规定者,此项习惯即因法律之特别规定,而有优先之效力。”
不过,管见以为,这并不表示,制定法的效力等级必定高于习惯法。民法规范,虽然可能以制定法的形式表现,但不宜视之为立法者专断意志的产物,毋宁说,它只是立法者对于民众交往习惯的概括,因而是被“发现”而非被“创造”的。照此推论,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为立法机关以文字的方式所明确表述,而制定法之所以在法律适用时先于习惯法得到考虑,并非因为前者效力高于后者,而是因为前者的确定性高于后者,更符合法律安全的需求。换言之,若对法律安全无所妨碍,习惯法亦可能优先得到适用。对此,《合同法》第22、26、293与368条等可为佐证。更早的法律实践则可见之于民国时期,1937年最高法院一项判例要旨指出:“依民法第一条前段之规定,习惯固仅就法律所未规定之事项有补充之效力,惟法律于其有规定之事项明定另有习惯时,不适用其规定者,此项习惯即因法律之特别规定,而有优先之效力。”
《民法通则》与最高法院《裁判规范规定》均未将习惯当做法源,而选择“国家政策”作为制定法的补充(《民法通则》第6条)。所谓“政策”, 《辞海》(1999年版)给出的解释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新政府成立之初,国民政府的旧法被断然废止,新法却未及制定,国家政策与党的政策长时期起着替代法律的作用。然而,二者差别不容忽视:内容上,国家政策有强烈的目标指向性,服务于特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体现的完全是“路线”和“任务”规划者的意志,以管制为基本取向;程序上,政策之制定,不受立法法制约,无法定的制定程序,无相应的救济措施,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关于政策的法源地位问题,洛克早在三百余年前即已指出:“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 此亦表明,政策作为法源的程度,与法制的健全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此亦表明,政策作为法源的程度,与法制的健全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不过,习惯法在我国实证法律体系中并非毫无意义。鉴于《合同法》多次提及“交易习惯”, 《合同法解释二》第7条第1款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交易习惯”由此获得相当于习惯法的地位,前者对应一般规范意义上的习惯法,后者则为个别规范之习惯法。
四、法律行为(契约)的法源性
法律行为对于当事人有拘束力,若由此发生纠纷诉诸法院,法官应尊重当事人意志,以之为据作出裁判。这意味着,法律行为亦拘束法官。不仅如此,由于民事制定法中的任意规范得为当事人意志排除,因而,对于法官来说,法律行为的效力等级犹在任意规范之上,《合同法》中大量诸如“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可为之提供佐证。由此推论,法律行为当属民法法源无疑。 然而,德国通说认为,法律行为(契约、社团章程等)不构成民法法源,原因在于,法律行为并不是法律规范(Rechtsnorm):规范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特点,而契约只拘束双方当事人,在特定个案中有效,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性质;社团章程虽然可适用于多数人,但惟有成为社团成员,才受制于章程,而入社与退社原则上均取决于成员自由意志,国家法则对所有人一体适用,当事人无自由进退之余地。
然而,德国通说认为,法律行为(契约、社团章程等)不构成民法法源,原因在于,法律行为并不是法律规范(Rechtsnorm):规范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特点,而契约只拘束双方当事人,在特定个案中有效,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性质;社团章程虽然可适用于多数人,但惟有成为社团成员,才受制于章程,而入社与退社原则上均取决于成员自由意志,国家法则对所有人一体适用,当事人无自由进退之余地。 显然,当中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法律规范。
显然,当中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法律规范。
传统法律理论以一般性与抽象性为法律规范的特点,凯尔森认为,此等一般规范(generelle Rechtsnormen)确然以制定法与习惯法为法源,但并非法律规范的全部,在此之外,尚存在只对个案有效的个别规范(individuelle Rechtsnormen) ,民法上,法律行为即具有规范创制能力,属于个别规范。
,民法上,法律行为即具有规范创制能力,属于个别规范。 若能接受凯尔森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的划分,不将法律规范局限于一般规范,则法律行为之法源地位亦可得到认可。
若能接受凯尔森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的划分,不将法律规范局限于一般规范,则法律行为之法源地位亦可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