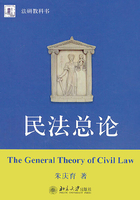
第一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民法基础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
一、“民法”的语源
了解语词构形演化与意义流变,能够为理解概念提供有益的历史视角。
(一)西文
“民法”源于罗马法上的 ius civile。罗马私法曾被三分为 ius naturale(自然法)、ius gentium(万民法)与 ius civile(市民法),其中,自然法适用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万民法系人类一体适用的法律,市民法则是专属罗马市民适用的法律。 不过,这一分类未被罗马法贯彻始终。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大帝(Caracalla)一项法律规定,全部帝国臣民均得适用市民法。自此,万民法与市民法的界限逐渐烟消。
不过,这一分类未被罗马法贯彻始终。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大帝(Caracalla)一项法律规定,全部帝国臣民均得适用市民法。自此,万民法与市民法的界限逐渐烟消。
中世纪时,基督教会在与世俗王室的权力争斗中提出,不仅精神之剑,世俗之剑亦应执掌于教会之手。 教会法因而近乎全面控制了世人生活。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古罗马 corpus iuris civilis(市民法大全)重见天日,世俗法学家以之抗衡教会法,从而形成二元的法律结构。此时,ius civile所偏重的,乃是与 ius canonicum(寺院法)相对的“世俗法”之含义。
教会法因而近乎全面控制了世人生活。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古罗马 corpus iuris civilis(市民法大全)重见天日,世俗法学家以之抗衡教会法,从而形成二元的法律结构。此时,ius civile所偏重的,乃是与 ius canonicum(寺院法)相对的“世俗法”之含义。
随着教会法逐渐退出世俗领域以及市民阶级、个人主义观念的兴起,罗马法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再次占据主导地位,ius civile 之称谓为许多国家所继受,如法语 droit civil、意大利语 diritto civile、德语 Zivilrecht(日耳曼词根的同义表达是 bürgerliches Re-cht)等。同时,《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瑞士民法典》(Schweizerisches Zivilgesetzbuch)
、《瑞士民法典》(Schweizerisches Zivilgesetzbuch) 、《意大利民法典》(Codice Civile Italiano)
、《意大利民法典》(Codice Civile Italiano) 等莫不以此为名。唯须注意者,各立法例下,虽同以语词 civil(Zivil)指称民法典,但用法略有不同:在民商分立的法德,民法典一般不包括商法规则;奉民商合一的瑞意,则将商法规则一并纳入其中。
等莫不以此为名。唯须注意者,各立法例下,虽同以语词 civil(Zivil)指称民法典,但用法略有不同:在民商分立的法德,民法典一般不包括商法规则;奉民商合一的瑞意,则将商法规则一并纳入其中。
(二)中文
清季变法,曾出现“国律”、“文律”、“民律”等不同语词 ,最终选定“民法”,通说认为,典籍无所本,系因袭日本的结果。
,最终选定“民法”,通说认为,典籍无所本,系因袭日本的结果。 唯清光绪33年民政部奏请厘定民律称:“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
唯清光绪33年民政部奏请厘定民律称:“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 查《尚书孔传》释“咎单作明居”云:“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又《史记·殷本纪》:“咎单作明居。”马融注曰:“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另查《荀子·王制》:“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显然,所谓“明居民法”,系明晓民众筑土安居之法之谓,典籍中的“民”、“法”二字,甚至未尝构为一词,与今日所称“民法”,相去自是不可以道里计。
查《尚书孔传》释“咎单作明居”云:“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又《史记·殷本纪》:“咎单作明居。”马融注曰:“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另查《荀子·王制》:“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显然,所谓“明居民法”,系明晓民众筑土安居之法之谓,典籍中的“民”、“法”二字,甚至未尝构为一词,与今日所称“民法”,相去自是不可以道里计。
西法东渐中,日本率先接纳西方法律体系,并以汉字组合“民法”二字作为 ius civile的对译语词。 对此译名,张俊浩教授颇不以为然,讥之为“貌似神失,移桔变枳”的误译,理由是,ius civile意为“市民法”,而“市民法”注入了“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一字之差的“民法”则将这些信息“差不多全给丢掉了”。
对此译名,张俊浩教授颇不以为然,讥之为“貌似神失,移桔变枳”的误译,理由是,ius civile意为“市民法”,而“市民法”注入了“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一字之差的“民法”则将这些信息“差不多全给丢掉了”。 管见以为,日本这一“依字义直译”
管见以为,日本这一“依字义直译” 的译名虽然未必如何高明,似乎也不至于误译。civis(Bürger)从古罗马开始,基本含义即是作为特定人群的“市民(城市居民)”,相应的,civitas(Bürgerrecht)特指“市民身份”或“市民权”,因而,罗马时期的 ius civile 实际上是典型的身份立法的产物。这一传统,直到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R,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依然得以延续。邦法将国民区分为农民身份(Bauerstand)、市民身份(Bürgerstand)与贵族身份(Adelstand)三种类型,分别予以不同的权利。
的译名虽然未必如何高明,似乎也不至于误译。civis(Bürger)从古罗马开始,基本含义即是作为特定人群的“市民(城市居民)”,相应的,civitas(Bürgerrecht)特指“市民身份”或“市民权”,因而,罗马时期的 ius civile 实际上是典型的身份立法的产物。这一传统,直到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R,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依然得以延续。邦法将国民区分为农民身份(Bauerstand)、市民身份(Bürgerstand)与贵族身份(Adelstand)三种类型,分别予以不同的权利。 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recht)以bürgerliches Recht指称ius civile,同时将后者身份立法的含义去除,伯默尔(Gustav Boehmer)指出:“bürgerliches Recht并不是专门适用于依出生或职业身份而确定的‘市民’或其社会阶层的法律,它不过是如同其他众多流传至今的法律术语,系罗马法术语的借用,自拉丁语词 jus civile翻译而来。在古罗马的演进中,这一概念早已失去与特定‘身份’的关联。”
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recht)以bürgerliches Recht指称ius civile,同时将后者身份立法的含义去除,伯默尔(Gustav Boehmer)指出:“bürgerliches Recht并不是专门适用于依出生或职业身份而确定的‘市民’或其社会阶层的法律,它不过是如同其他众多流传至今的法律术语,系罗马法术语的借用,自拉丁语词 jus civile翻译而来。在古罗马的演进中,这一概念早已失去与特定‘身份’的关联。” 就此而言,以“市民法”作为对译语词固然贴近 ius civile的原意,但原意中的身份立法含义亦可能被一并带入。
就此而言,以“市民法”作为对译语词固然贴近 ius civile的原意,但原意中的身份立法含义亦可能被一并带入。
无论“民法”之表述源自何处、与本义的差距有多大,既已约定俗成,自不必推倒重来,况且,起源于罗马的 ius civile 在社会变迁中,含义本非一成不变。对于理解概念,比语词选择更重要的,是概念如何实际使用。不过,张教授的批评虽稍严苛,其间所表现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野的观念,以及在此背景下对于私权神圣的尊崇,却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二、调整对象学说
对于多数新中国法学家而言,欲要了解民法概念如何实际使用,必先明确其调整对象。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说法是:“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研究将关系到我国民法科学的建立、民法典的编纂以及司法实践中对民法规范的正确运用。因此,民法对象是民法科学中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民法通则》第2条正是这一观念的结果。
《民法通则》第2条正是这一观念的结果。
(一)学说史略
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讨论为苏联法学所引发。调整对象问题,被认为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民法典的制定、法律的正确适用以及法律教育的开展诸环节的根本问题,为此,1938—1940年与1954—1955年,苏联曾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讨论。 讨论之后,民法教科书的标准表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与此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其中,财产关系包括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社会主义组织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非财产关系则与人身不可分离而无财产内容,如荣誉权、名誉权、姓名权、著作权等。至于婚姻家庭关系,因其“如此特殊”,以至于不能如资产阶级般划归民法之列。
讨论之后,民法教科书的标准表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与此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其中,财产关系包括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社会主义组织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非财产关系则与人身不可分离而无财产内容,如荣誉权、名誉权、姓名权、著作权等。至于婚姻家庭关系,因其“如此特殊”,以至于不能如资产阶级般划归民法之列。
苏联关于调整对象的讨论曾全面影响新中国民法学。“两个一定”(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与一定范围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表述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各民法教科书的固定表达。 对此成说,佟柔先生表示,所谓“一定范围”,过于笼统,不足为训,综观法律史,民法均是为调整商品关系而设,只不过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调整的分别是简单商品关系、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或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自然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
对此成说,佟柔先生表示,所谓“一定范围”,过于笼统,不足为训,综观法律史,民法均是为调整商品关系而设,只不过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调整的分别是简单商品关系、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或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自然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
佟柔先生对于苏联范本的修正,意义在于:第一,佟先生基于商品经济的特性,力证当事人地位平等与等价有偿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苏联法学虽亦称“公民享有平等权利”,但主要是在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方面强调平等 ,至于民事交往中的地位平等问题,则存而不论。佟先生认为,奉行按劳取酬原则的,与其说是属于民法范畴,不如归诸劳动法调整更为恰当。
,至于民事交往中的地位平等问题,则存而不论。佟先生认为,奉行按劳取酬原则的,与其说是属于民法范畴,不如归诸劳动法调整更为恰当。 地位平等与等价有偿原则,后被写入《民法通则》第3条与第4条。第二,依佟先生之见,苏联的“两个一定”说之所以含糊,还在于它其实未为民法确定一个统一的调整对象,“商品关系”说则既为民法确立统一的调整对象,更由此划出民法与其他法律尤其是经济法的界限。佟先生指出,经济法是把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过程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不具有统一性,调整时,需要借助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财政法甚至刑法等多种调整手段,因此不成其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地位平等与等价有偿原则,后被写入《民法通则》第3条与第4条。第二,依佟先生之见,苏联的“两个一定”说之所以含糊,还在于它其实未为民法确定一个统一的调整对象,“商品关系”说则既为民法确立统一的调整对象,更由此划出民法与其他法律尤其是经济法的界限。佟先生指出,经济法是把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过程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不具有统一性,调整时,需要借助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财政法甚至刑法等多种调整手段,因此不成其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当是时也,依托于计划经济的经济法观念颇有否弃民法并取而代之之势,佟柔先生的“商品关系”说,为风雨飘摇的民法确立了生存根基,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当是时也,依托于计划经济的经济法观念颇有否弃民法并取而代之之势,佟柔先生的“商品关系”说,为风雨飘摇的民法确立了生存根基,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民法通则》第2条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2条是关于调整对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调整对象的表述中直接突出“平等主体”,这一界定方式于当时的法学界略显陌生,就笔者所见,《民法通则》之前的教科书,唯杨振山先生关于民法的定义与之相似:“民法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的,用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不过,在佟柔先生眼里,所谓“平等主体”,也许不过是“商品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必然取决于商品经济关系,并以商品经济关系为核心”。
不过,在佟柔先生眼里,所谓“平等主体”,也许不过是“商品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必然取决于商品经济关系,并以商品经济关系为核心”。
除“平等主体”这一中国元素外,《民法通则》第2条的表述其实还是打上了鲜明的苏联烙印,不仅“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这等繁琐的表述明显自苏联财产关系的三分法改造而来,“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之并列,亦是舶来苏联法学之物。尤具说明价值的是,苏联民法所称人身关系,只是荣誉权、名誉权、姓名权、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等如今被归入人格权的关系,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则被排除在外,与之相应,《民法通则》颁行之初,教科书在解释第2条之“人身关系”时,亦大多表示:指的是平等主体之间因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著作权、发明权等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解释不是唯一的。关于“人身关系”的理解,虽然几乎是众口一词,却仍偶有异声。《民法新论》一书即反对将婚姻家庭法独立于民法之外,认为《民法通则》第2条所称人身关系,亦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等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身份权。 这部由未参与立法的年轻学者编撰的教科书,在解释法律条文时,显然未太多受制于“立法原意”。20世纪90年代以后,“立法原意”越来越远离大众视线。伴随着婚姻、继承法对于民法体系的回归,第2条中的“人身关系”逐渐被拆解为“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的合称。
这部由未参与立法的年轻学者编撰的教科书,在解释法律条文时,显然未太多受制于“立法原意”。20世纪90年代以后,“立法原意”越来越远离大众视线。伴随着婚姻、继承法对于民法体系的回归,第2条中的“人身关系”逐渐被拆解为“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的合称。 时至今日,《民法通则》颁行未满三十年,第2条之“立法原意”已几乎为人所淡忘,法律解释中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消长,于此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民法通则》颁行未满三十年,第2条之“立法原意”已几乎为人所淡忘,法律解释中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消长,于此可见一斑。
《民法通则》之后,学界关于调整对象的争论逐渐偃旗息鼓,普遍转而依制定法框架进行阐述。
三、公法与私法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理解民法概念,这只是众多可能的路径之一。欧陆民法传统中,更通行的路径是公法与私法之分野。在此分野格局中,民法被划归私法之列,或径被当作私法的同义表达。然则公法与私法如何界定?
(一)各种学说
区分公法与私法的传统在欧陆可谓源远流长,期间形成的理论学说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利益、隶属与主体三说。
1.利益说
罗马法时期,由乌尔比安(Ulpianus)提出并被优士丁尼大帝(Flavius Iustinianus)编入钦定教科书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公法事关罗马国家秩序,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 此即所谓“利益说”(Interessentheorie)。然而,私法中未必没有公共利益的因素,例如,公共利益通常是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而亲属法等事关伦理的法律规范,更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法等公法其实亦是直接关乎个人利益。上述定义显然有欠周延。不仅如此,哈耶克(F.A.von Hayek)甚至认为,公法对应公共利益、私法只保护私人利益的观点,实属是非颠倒之论,从根本上说,私人目的在自由秩序中顺利实现才是真正的维护公共利益之道,通过政府组织实现公共福祉,反倒是拾遗补缺之举。
此即所谓“利益说”(Interessentheorie)。然而,私法中未必没有公共利益的因素,例如,公共利益通常是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而亲属法等事关伦理的法律规范,更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法等公法其实亦是直接关乎个人利益。上述定义显然有欠周延。不仅如此,哈耶克(F.A.von Hayek)甚至认为,公法对应公共利益、私法只保护私人利益的观点,实属是非颠倒之论,从根本上说,私人目的在自由秩序中顺利实现才是真正的维护公共利益之道,通过政府组织实现公共福祉,反倒是拾遗补缺之举。
另外,“利益说”的缺陷还在于,以“利益”属性为判断标准,可能为“一切法律皆公法”的主张提供支持。德国纳粹法律理论即宣称,所有法律均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工具,因此,私法亦是关乎公共利益之法,与公法别无二致。 如今,“利益说”在法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如今,“利益说”在法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德国则几乎无人再予支持。
,在德国则几乎无人再予支持。
2.隶属说
“隶属说”(Subordinationstheorie)或称“主体地位说”(Subjektionstheorie)曾长时间在德国占主导地位。 该说主张:第一,在法律关系的内容方面,公法关系中主体地位具有隶属关系,下位意志受制于上位意志;私法则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任何一方意志不得强加于对方。第二,在法律关系的发生方面,公法关系一般是依国家意志而产生,相对人处于他治地位,无自由选择之余地;私法关系则因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产生。这一学说在面对警察法、税法等行政法以及民法中的大多数法律关系时,解释力较强,但仍有缺陷:
该说主张:第一,在法律关系的内容方面,公法关系中主体地位具有隶属关系,下位意志受制于上位意志;私法则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任何一方意志不得强加于对方。第二,在法律关系的发生方面,公法关系一般是依国家意志而产生,相对人处于他治地位,无自由选择之余地;私法关系则因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产生。这一学说在面对警察法、税法等行政法以及民法中的大多数法律关系时,解释力较强,但仍有缺陷:
其一,一方面,等级相同的国家机关地位平等,但彼此权力划分与行使关系由公法调整;国家之间的地位平等,但国际法被划归公法之列;而立法权这一最高层次的公权力,依现代民主理论,系基于权利平等的民众授予,因此,立法权之行使,究其根本,乃是民众自治而非他治的表现,再者,民众在面对国家权力时,并不总处于服从地位,其基本权利亦须得到后者尊重。另一方面,私法社团内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均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却属于私法,属于私法契约的雇佣契约与培训契约,受雇人与受教育人亦须受制于对方意志。
其二,一方面,私法关系未必依自由意志产生,如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亲属之间的抚养义务以及法定继承关系等。另一方面,公法关系亦可能由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引发,除国家之间的国际法关系外,国内公法关系如入籍申请、公法契约之订立等均是如此。
3.主体说
“主体说”(Subjekttheorie)分新旧两说。“旧主体说”认为,一方当事人为公权力者,即形成公法关系。此说可解释平等地位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具隶属关系的私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化解“隶属说”的一些困境。但新的缺陷随之而来:公权力者亦可能参与私法关系,如国家机关缔结的普通买卖契约。
现今德国通说,是融合了“隶属说”与“旧主体说”的所谓“新主体说”(“修正的主体说”)。其说略谓:当公权力者以公权力担当人的面目出现时,形成公法关系,否则即为私法关系。 如果公权力与私人领域能够被划分得比较清楚,新主体说的解释力大致可得以维持,但在中国,难免面临诸多难题,例如,在私人无法拥有土地所有权、铁路邮政等行业为国家所垄断等现实背景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承包经营合同、铁路运送以及邮政合同等各种法律关系,具有多大程度的私法性质,在解释上并非没有疑问。就此而言,新主体说虽然未必适合于中国,却为观察中国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介入程度提供了一块试金石。
如果公权力与私人领域能够被划分得比较清楚,新主体说的解释力大致可得以维持,但在中国,难免面临诸多难题,例如,在私人无法拥有土地所有权、铁路邮政等行业为国家所垄断等现实背景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承包经营合同、铁路运送以及邮政合同等各种法律关系,具有多大程度的私法性质,在解释上并非没有疑问。就此而言,新主体说虽然未必适合于中国,却为观察中国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介入程度提供了一块试金石。
(二)区分的相对性
“国家—社会—个人”之关系当然不可能泾渭分明,正如梅迪库斯(Dieter Medicus)所指出的,想要单纯用某种固定公式为公法与私法划出楚河汉界,必将无功而返。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的交错日渐突出,不仅民法这一典型的私法越来越面临公法规范的入侵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的交错日渐突出,不仅民法这一典型的私法越来越面临公法规范的入侵 ,更引人注目的是,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经济法以及劳动法的兴起,使得任何区分标准均为之徒叹奈何。在此背景下,“第三法域”之主张顺势出现。德国法学家帕夫洛夫斯基(Hans-Martin Pawlowski)将此“第三法域”以“社会法”(Sozialrecht)相称,归入其列者,包括劳动法、经济法(如卡特尔法)、婚姻法、承租人保护法、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团法(das Recht der wirtschaftlich bedeutsamen Vereine)以及一般交易条件法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当事人对于法律关系的建立受到约束,但自由度较之公法领域为大。
,更引人注目的是,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经济法以及劳动法的兴起,使得任何区分标准均为之徒叹奈何。在此背景下,“第三法域”之主张顺势出现。德国法学家帕夫洛夫斯基(Hans-Martin Pawlowski)将此“第三法域”以“社会法”(Sozialrecht)相称,归入其列者,包括劳动法、经济法(如卡特尔法)、婚姻法、承租人保护法、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团法(das Recht der wirtschaftlich bedeutsamen Vereine)以及一般交易条件法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当事人对于法律关系的建立受到约束,但自由度较之公法领域为大。
(三)区分的价值
欧陆传统对于区分公私法之思维并非全无异见。其中最著名的反对者当属凯尔森(Hans Kelsen)。凯尔森主张公私法一元论,其说略谓:公法与私法之别,只在于法律的创制方式不同,公权命令是行政法的个别规范,私人法律行为则是民法典的个别规范,而无论是行政法还是民法典,它们作为一般规范,均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国家公法行为与私人法律行为融汇于统一的国家意志,公法与私法具有一元性,纵然有着某种对立,亦不过存在于体系内部。
凯尔森统合公私法的见解,遭到哈耶克的强烈批评,后者指出:“就正当的法律行为规则尤其是私法而言,法律实证主义所谓法律的内容始终是立法者意志之表示的断言,根本就是谬误的。” 在哈耶克看来,奉行组织规则(rules of organization)的公法与奉行正当行为规则(rules of just conduct)的私法,其间差别是根本性的:组织规则是立法机构刻意制定、用以规范公共权力机构的规则,规范对象必须遵照相应的命令作出行为;正当行为规则则是在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志,亦不指令当事人作出积极行为,只是通过禁止性规则划定行为界限,实际如何行为,取决于行为人的自由意志。
在哈耶克看来,奉行组织规则(rules of organization)的公法与奉行正当行为规则(rules of just conduct)的私法,其间差别是根本性的:组织规则是立法机构刻意制定、用以规范公共权力机构的规则,规范对象必须遵照相应的命令作出行为;正当行为规则则是在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志,亦不指令当事人作出积极行为,只是通过禁止性规则划定行为界限,实际如何行为,取决于行为人的自由意志。 就此问题,梅迪库斯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私法一般奉行决定自由,不必说明理由,与之相反,公法中的决定则受到约束。”
就此问题,梅迪库斯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私法一般奉行决定自由,不必说明理由,与之相反,公法中的决定则受到约束。” 这意味着,如果将公法与私法统归一元,结果将是,或者导致本应受约束的公法行为如私法行为般自由任性,或者使得本应自由作出的私法行为如公法行为般受到管制。
这意味着,如果将公法与私法统归一元,结果将是,或者导致本应受约束的公法行为如私法行为般自由任性,或者使得本应自由作出的私法行为如公法行为般受到管制。
哈耶克所论,非杞人之忧。法西斯时期,国家社会主义者即声称,私法应全部融入公法,当时一位“负有盛名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法学者”甚至断言:私法是毫无价值的废物。 在此意义上,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之论断,仍不失为睿见卓识:“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私法乃是一切法律的核心,公法则不过是一个单薄的保护性框架,它为私权尤其是私人所有权提供保障。”
在此意义上,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之论断,仍不失为睿见卓识:“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私法乃是一切法律的核心,公法则不过是一个单薄的保护性框架,它为私权尤其是私人所有权提供保障。”
(四)调整对象学说与公私法之区分
由于意识形态的钳制,加之苏联范本的影响 ,我国法学长期无法正面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调整对象学说与公私法区分学说之间毫无关联。从内容上看,《民法通则》第2条之以“平等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调整对象,与“主体地位说”可谓遥相呼应、殊途同归。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于调整对象的讨论,其实不过是明修栈道之举,所暗渡者,正是公私法之区分。
,我国法学长期无法正面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调整对象学说与公私法区分学说之间毫无关联。从内容上看,《民法通则》第2条之以“平等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调整对象,与“主体地位说”可谓遥相呼应、殊途同归。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于调整对象的讨论,其实不过是明修栈道之举,所暗渡者,正是公私法之区分。
不过,如拉德布鲁赫所指出的,“私法”和“公法”不是实证法的概念,在逻辑上先于法律经验而存在,具有先验性。 《民法通则》以实证法定夺私法与公法的区分标准,实属立法的僭越。
《民法通则》以实证法定夺私法与公法的区分标准,实属立法的僭越。
四、民法与其他法域
(一)宪法
在区分公法与私法的格局下,宪法与民法对峙而立:宪法的主要功能是分配与限制国家权力,是政府组织规则(公法)的基本法;民法则为私人自由行为提供支持,是私法的普通法。政治体制不同,权力结构亦不同,宪法内容也就不同;私人交往则受政治变迁的影响较小,以至于罗马法时代确立的规则能够沿用至今。 正是因为革命虽然能够修改宪法,却很难改变私人之间的正当行为规则,法国人将其民法典视为“真正的宪法”。
正是因为革命虽然能够修改宪法,却很难改变私人之间的正当行为规则,法国人将其民法典视为“真正的宪法”。 《德国民法典》同样独立于政制变迁,自1900年生效之后,法典迄今经历了五种宪法体制:帝国时期、魏玛宪法时期、纳粹时期、联邦共和国时期以及1975年之前亦适用于民主德国。
《德国民法典》同样独立于政制变迁,自1900年生效之后,法典迄今经历了五种宪法体制:帝国时期、魏玛宪法时期、纳粹时期、联邦共和国时期以及1975年之前亦适用于民主德国。 “公法易逝,而私法长存”
“公法易逝,而私法长存” ,此之谓也。
,此之谓也。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说法是:“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法通则》第1条亦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问题在于,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根本大法”?私法的制定为何需要“根据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根据宪法”?
我国宪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政治与经济制度、国家机构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前两部分内容涉及国家政体与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划分,若说其“根本”,也只是体现在规范公权力的公法领域,与民法内容并无太大关联;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宪政国家宪法的功能只是对公民提供基本权利之保障,同时对政府施以尊重基本权利之义务,而一般不将宪法义务加诸普通公民,我国宪法关于公民义务之规定,系属例外 ,并不具有说明价值。问题的关键因而在于,民法权利是否来自于宪法基本权利?
,并不具有说明价值。问题的关键因而在于,民法权利是否来自于宪法基本权利?
我国法学家习惯于认为,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民法则赋予民事权利,既然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法位列其下,民事权利自然以宪法基本权利为依据。这是典型的权利法定观念,其实质,乃是主张私人权利来自于公权力的赋予。对此,美国人权法案的争议可提供另外一个观察视角。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当人权法案被提议入宪时,却遭到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联邦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举措,“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因为,“人民不交出任何权利;既然人民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任何个别权利”。并且,“人权法案条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与政府的权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权力的借口。既然此事政府无权处理,则何必宣布不得如此处理?……笔者并非谓这类规定将形成处理权的授予;但它将为擅权者提供争夺此项权利的借口则甚为明显。彼等可能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声称:宪法何能如此荒谬,竟然限制对未曾授予权力的专擅?” 显然,联邦党人坚持的是人权天赋、公权法定的观念。如果这一观念可以得到认可,那么,即使要在宪法中规定基本权利,亦是在彰示政府:公权力者有义务尊重公民基本权利,而非通过宪法赋予公民权利,如此,民事权利自不必以宪法基本权利为据。权利法定之主张,正当性值得三思。
显然,联邦党人坚持的是人权天赋、公权法定的观念。如果这一观念可以得到认可,那么,即使要在宪法中规定基本权利,亦是在彰示政府:公权力者有义务尊重公民基本权利,而非通过宪法赋予公民权利,如此,民事权利自不必以宪法基本权利为据。权利法定之主张,正当性值得三思。
当然,《民法通则》所称“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并非没有意义。立法权的配置,由宪法所规定,任何立法活动,都必须“根据宪法”。这意味着,所谓“根据宪法”,要表明的,不过是立法权的正当性问题。
(二)商法
立法例上,有所谓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别。若采后者,则民法为私法普通法,商法为私法特别法,特别适用于商人之间的商行为。法德为民商分立典范,民法典之外并立商法典,瑞士则首开民商合一之先河,将商法内容纳入民法典债编。民国民法典采民商合一体例,并在“民商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书”中,从历史沿革、社会进步、世界交通、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订标准、编订体例及民商关系诸方面详列八项理由予以论证,我学者对此多有援引,以为定论。 通说认为,现有立法格局奉民商合一,未来的民法典仍应如此,以呼应“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商法化’”。
通说认为,现有立法格局奉民商合一,未来的民法典仍应如此,以呼应“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商法化’”。
民商合一的制度环境与规范配置
新近法典如意大利、俄罗斯、荷兰等均采民商合一体制,即使是在传统民商分立国家如德国,商法(典)独立存在的价值亦频遭质疑 ,就此而论,称民商合一乃是立法趋势,当不为过。只不过,世界趋势未必适于本土。
,就此而论,称民商合一乃是立法趋势,当不为过。只不过,世界趋势未必适于本土。
民商合一,以商人不具有特殊地位为前提。随着欧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历史形成的商人阶层越来越与普通市民身份重合,民商法呈合一趋势,自有其社会经济背景。然而,在我国现实法律环境下,民法人并非理所当然可依意愿成为商人。例如,欲要设立公司,以商法人的面目参与交易,至少需要满足诸如普通有限公司3万元(《公司法》第26条第2款)、一人公司10万元(《公司法》第59条第1款)、股份公司则高达500万元(《公司法》第81条第3款)的注册资本等条件,即便是只想成为商事合伙、商自然人,亦有义务向行政机关提交申请,以便获准登记(《合伙企业法》第9条,《独资企业法》第9条),至于各种行业壁垒、行政垄断以及以城市卫生与环境管理为名的“摊贩”管理,更是渗透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如此苛刻的市场准入条件未先作改变,即奢谈商人地位已不再特殊,似乎是错将理想当成了现实。民商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将民法人与商人等量齐观,从而提高民法人的注意义务。如果一方面,成为商人需要克服层层法律与行政障碍,另一方面又以商人的行为标准加诸民法人,此民商合一,余未见其可也。
如此苛刻的市场准入条件未先作改变,即奢谈商人地位已不再特殊,似乎是错将理想当成了现实。民商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将民法人与商人等量齐观,从而提高民法人的注意义务。如果一方面,成为商人需要克服层层法律与行政障碍,另一方面又以商人的行为标准加诸民法人,此民商合一,余未见其可也。
另外,民商分立抑或合一,将影响规范的具体设置,稍有不慎,易生讹误。例如,在分立体例下,对于金钱之债,除非有约定或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民法当事人不会一般性地负担付息义务。 但《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211条第1款则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前者确立借款合同的一般规则,以付息为原则,显然是将商行为作为规范对象;后者属于例外条款,所谓“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当解为民事借款合同——只不过立法似乎忽略了“商自然人”的概念。将商事契约与民事契约区别规范,这本是民商分立的模式,在此格局下,民法规则当属一般法,商法则为特别法,但号称民商合一的《合同法》却反其道行之,将商法规则(第196条)作为一般法,民法规则(第211条第1款)反倒变成特别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被颠倒了。
但《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211条第1款则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前者确立借款合同的一般规则,以付息为原则,显然是将商行为作为规范对象;后者属于例外条款,所谓“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当解为民事借款合同——只不过立法似乎忽略了“商自然人”的概念。将商事契约与民事契约区别规范,这本是民商分立的模式,在此格局下,民法规则当属一般法,商法则为特别法,但号称民商合一的《合同法》却反其道行之,将商法规则(第196条)作为一般法,民法规则(第211条第1款)反倒变成特别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被颠倒了。
管见以为,商法是否足以独立到自成法典之程度,固然值得怀疑,在中国既有制度格局下,民商合一之立法是否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似乎更是需要三思。
(三)经济法
经济法(Wirtschaftsrecht)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方面,战争导致资源匮乏,从而带来管制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观念的兴起,对之前普遍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构成极大挑战。在此双重背景之下,强调国家管制的经济法迅速兴起,矛头直指崇尚自由的传统民法,德国则在纳粹执政时期臻于全盛。 如今,以竞争法为典型的德国经济法被视为私法与公法的结合体,前者称经济私法(Wirtschaftsprivatrecht),是专对工商经济适用的特别私法,后者则称经济行政法(Wirtschaftsverwaltungsrecht)。
如今,以竞争法为典型的德国经济法被视为私法与公法的结合体,前者称经济私法(Wirtschaftsprivatrecht),是专对工商经济适用的特别私法,后者则称经济行政法(Wirtschaftsverwaltungsrecht)。
新中国重建法制,学步苏俄,对其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经济法观念自然亦是照章收纳,甚至犹有过之——苏联尚且存在民法典,经济法却成为我们取消民法的理由。 如今,随着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经济法已不至于危及民法的生存,但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举足轻重。关于我国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旁观者苏永钦教授的描述可谓是一针见血:“经济法在台湾原是民法的例外,是‘偏房’,在大陆却是正室,民法很长一段时间连个名分都没有。”
如今,随着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经济法已不至于危及民法的生存,但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举足轻重。关于我国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旁观者苏永钦教授的描述可谓是一针见血:“经济法在台湾原是民法的例外,是‘偏房’,在大陆却是正室,民法很长一段时间连个名分都没有。” “在西方,经济法往往被视为‘对私法的批判’,在中国内地,则是后来的民法反而多少意味着对既存管制的批评。”
“在西方,经济法往往被视为‘对私法的批判’,在中国内地,则是后来的民法反而多少意味着对既存管制的批评。”
(四)民事诉讼法
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在于,法律纠纷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法即为此而设。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唇齿相依。如果诉讼程序无法为纠纷的和平解决提供渠道,民事纠纷演化为暴力报复也就仅剩一步之遥。
在公私法分立的框架下,民事诉讼法如何归类,颇有争议。法国通说以之为私法,主要是因为它旨在处理私人之间的利益纠纷 ;德国学者则多视之为公法,因为它规范的是国家司法权力的活动。
;德国学者则多视之为公法,因为它规范的是国家司法权力的活动。 德国另有见解指出,民事诉讼法涉及三方当事人关系,争议双方地位平等,诉讼中奉处分原则,具有私法的性质,涉及法院者,则属公法性质,因而,难以简单将其非此即彼地归入私法或公法,解决之道是,将公私法之区分限定于实体法,对于诉讼法,不必强作区分。
德国另有见解指出,民事诉讼法涉及三方当事人关系,争议双方地位平等,诉讼中奉处分原则,具有私法的性质,涉及法院者,则属公法性质,因而,难以简单将其非此即彼地归入私法或公法,解决之道是,将公私法之区分限定于实体法,对于诉讼法,不必强作区分。 是说可采。
是说可采。
(五)刑法
刑法规范的是最严重的侵权行为与背信行为,在此意义上,它与民法具有承继关系。只不过,民法以损害赔偿为救济方式,旨在回复受到侵害的权利,刑法则以国家的名义施以惩罚,意在维护公共秩序,二者目标大异其趣。 正因为如此,同一行为,受到刑法评价而承担刑责,并不影响兼负民事赔偿之责,两种责任不相冲突。
正因为如此,同一行为,受到刑法评价而承担刑责,并不影响兼负民事赔偿之责,两种责任不相冲突。
有如民事诉讼法,关于刑法的公私法属性问题亦歧见纷呈。法国传统将其归入私法,因为刑法所保护者,常常是私人权利 ;哈耶克亦持私法说,理由是刑法事关正当行为规则。
;哈耶克亦持私法说,理由是刑法事关正当行为规则。 德国学者则有以之为公法者
德国学者则有以之为公法者 ,亦有将其与公法、私法并列者。
,亦有将其与公法、私法并列者。 笔者以为,私法说似乎过于强调私人权利受侵犯(正当行为规则被违反)的情形,实际上,刑法亦规制诸如渎职之类直接侵害公共秩序(违反政府组织规则)的行为,此类规范对于维护私人权利(正当行为规则)可能并无直接关联,公法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将刑法单列,也许较为妥适。
笔者以为,私法说似乎过于强调私人权利受侵犯(正当行为规则被违反)的情形,实际上,刑法亦规制诸如渎职之类直接侵害公共秩序(违反政府组织规则)的行为,此类规范对于维护私人权利(正当行为规则)可能并无直接关联,公法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将刑法单列,也许较为妥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