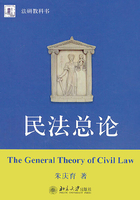
第二编 法律行为
第三章 法律行为的本质
第七节 法律行为的概念
一、法律行为的功能
当代德国民法体系乃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弗卢梅指出,“潘德克顿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前置总则之体例,总则之核心则在法律行为理论。”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法律行为理论是“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的绝对主题,而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所获得的世界性声誉,正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法律行为理论是“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的绝对主题,而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所获得的世界性声誉,正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 就此而言,无论如何强调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概念在德国法系中的地位,皆不为过。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形式上,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使得民法典各编能够提取一般性的公因式,从而促成总则编的出现。其二,实质上,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令民法各种自治行为在体系上得到整合,实现了私法自治理念的技术化。
就此而言,无论如何强调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概念在德国法系中的地位,皆不为过。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形式上,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使得民法典各编能够提取一般性的公因式,从而促成总则编的出现。其二,实质上,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令民法各种自治行为在体系上得到整合,实现了私法自治理念的技术化。
所谓私法自治,依弗卢梅经典定义,指的是“各人依其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 而法律行为之要旨正在于根据行为人意志发生相应法律效果,因而,它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这一认识,至少早在德恩堡(Heinrich Dernburg)的著作中,就已经得到明白无误的表述。德恩堡明确指出:“法律行为是私法自决(privatrechtliche Selbstbestimmung)的一般工具。”它“服务于私法自决,此等性质划定了这一概念之边界。为此,并非只有话语性的意思表示才是法律行为,毋宁说,其他行为,只要是指向法律关系之设立或废止,即在其列”。
而法律行为之要旨正在于根据行为人意志发生相应法律效果,因而,它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这一认识,至少早在德恩堡(Heinrich Dernburg)的著作中,就已经得到明白无误的表述。德恩堡明确指出:“法律行为是私法自决(privatrechtliche Selbstbestimmung)的一般工具。”它“服务于私法自决,此等性质划定了这一概念之边界。为此,并非只有话语性的意思表示才是法律行为,毋宁说,其他行为,只要是指向法律关系之设立或废止,即在其列”。 实际上,德国法律行为概念之形成,所贯穿的中心线索,正是私法自治之维护。
实际上,德国法律行为概念之形成,所贯穿的中心线索,正是私法自治之维护。
法律行为概念史略
Rechtsgeschäft语词之出现
“法律行为”成为一般性法律概念,系18世纪潘德克顿法学的成就。 18世纪末,Rechtsgeschäft一词作为术语开始出现于一些法学家的作品中,如,韦伯(A.D.Weber)1784年首版的《自然之债理论的体系发展》(Systematisch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den natürlichen Verbindlichkeiten),以及胡果1789年首版的《当代罗马法学阶梯》。
18世纪末,Rechtsgeschäft一词作为术语开始出现于一些法学家的作品中,如,韦伯(A.D.Weber)1784年首版的《自然之债理论的体系发展》(Systematisch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den natürlichen Verbindlichkeiten),以及胡果1789年首版的《当代罗马法学阶梯》。 不过,大体而言,18世纪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术语。法学家不仅混用拉丁文与德文表述
不过,大体而言,18世纪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术语。法学家不仅混用拉丁文与德文表述 ,且拉丁文许多语词均可对应于日后的 Rechtsgeschäft,如 negotium, actus, actum, contractum, gestum以及 factum等等
,且拉丁文许多语词均可对应于日后的 Rechtsgeschäft,如 negotium, actus, actum, contractum, gestum以及 factum等等 ,即便是德文,用以指称“法律行为”概念的语词亦各不相同。直到1807年海泽出版《供学说汇纂讲授之用的普通民法体系纲要》,所采用的 Rechtsgeschäft才逐渐成为德国法学的共同选择。
,即便是德文,用以指称“法律行为”概念的语词亦各不相同。直到1807年海泽出版《供学说汇纂讲授之用的普通民法体系纲要》,所采用的 Rechtsgeschäft才逐渐成为德国法学的共同选择。 《纲要》将“行为论”章置于“总论”编,并以法律行为与不法行为为其基本类型。体例如下
《纲要》将“行为论”章置于“总论”编,并以法律行为与不法行为为其基本类型。体例如下 :
:
第一编总论(Allgemeine Lehren)
……
第六章行为论(Von den Handlungen)
I.行为总论(Von den Handlungen im Allgemeinen)
A.概念及主要类型(Begriff und Haupt-Arten)
B.意思决定论(Von der Willens-Bestimmung)
C.意思表示论(Von der Willens-Erklärung)
II.法律行为论(Von den Rechtsgeschäften)
A.法律行为总论(Allgem.Lehre v.d.Rechtsgeschäften)
B.具体类型(Einige einzelne Arten)
III.不法行为论(Von unerlaubten Handlungen)
A.概念(Begriff derselben)
B.归责论(Von deren Imputation)
C.效力(Wirkungen derselben)
Rechtsgeschäft的含义
Rechtsgeschäft的早期表述是 rechtliche Geschäfte。 它至少可追溯至内特尔布拉特(Daniel Nettelbladt)。内特尔布拉特在首版于1748年的《一般实证法学基础体系》(Systema elementare universae iurisprudentiae positivae)一书中,将拉丁语词 actus juridicus与 negotium juridicum引入法学文献,并在1772年的《日耳曼普通实证法学新论》(Nova Introductio in Jurisprudentiam Positivam Germanorum Communem)一书将其译成德文ein rechtliches Geschäft。
它至少可追溯至内特尔布拉特(Daniel Nettelbladt)。内特尔布拉特在首版于1748年的《一般实证法学基础体系》(Systema elementare universae iurisprudentiae positivae)一书中,将拉丁语词 actus juridicus与 negotium juridicum引入法学文献,并在1772年的《日耳曼普通实证法学新论》(Nova Introductio in Jurisprudentiam Positivam Germanorum Communem)一书将其译成德文ein rechtliches Geschäft。 他特别指出,actus juridicus是指“人的合法行为”。不过,这一新概念其实并未得到严格使用。在内特尔布拉特的其他著作中,不法行为(facta illicita)亦曾被归入 actus juridicus之列。
他特别指出,actus juridicus是指“人的合法行为”。不过,这一新概念其实并未得到严格使用。在内特尔布拉特的其他著作中,不法行为(facta illicita)亦曾被归入 actus juridicus之列。 其后,海泽接续胡果传统,以 Rechtsgeschäft作为行为(Handlung)之特别表现形式,并明确将其视作不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gen)之对立概念。
其后,海泽接续胡果传统,以 Rechtsgeschäft作为行为(Handlung)之特别表现形式,并明确将其视作不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gen)之对立概念。 不过,总体而言,“直到19世纪初,‘法律行为’仍然没有被普遍使用,该艺术性语词之为法学专业术语尚未获得一般性的认可,而契约这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类型亦未体系化地直接与行为概念相联结。”
不过,总体而言,“直到19世纪初,‘法律行为’仍然没有被普遍使用,该艺术性语词之为法学专业术语尚未获得一般性的认可,而契约这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类型亦未体系化地直接与行为概念相联结。”
曾经担任普鲁士王国枢密院法律顾问的阿福尔特(A.Affolter)指出,首先对“法律行为”概念作出深入论述的是萨维尼及其后继者普赫塔,他们的学说几乎未加修正即迅速成为通说。
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3卷中,对于通过“法律行为”获得“个人意思的独立支配领域”之观念作有系统阐述,使得法律行为成为当事人设立与变更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萨维尼指出,法律事实(juristische Thatsachen)包括权利人的自由行为与偶然事件,前者是指“任何人据以取得与丧失权利的言语行动” ,以行为人意志是否直接指向法律效果为标准,又可分为两类,其中,“尽管一项行为也许不过是其他非法律目的的手段,只要它直接指向法律关系的产生或解除,此等法律事实就称为意思表示(Willenserklärungen)或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e)”。
,以行为人意志是否直接指向法律效果为标准,又可分为两类,其中,“尽管一项行为也许不过是其他非法律目的的手段,只要它直接指向法律关系的产生或解除,此等法律事实就称为意思表示(Willenserklärungen)或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e)”。 换言之,“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这种法律事实应作如下理解:它不仅是自由行为,而且其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指向法律关系之产生或解除”。
换言之,“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这种法律事实应作如下理解:它不仅是自由行为,而且其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指向法律关系之产生或解除”。 这一概念界定的关键之点在于,通过“直接指向”(auf...unmittelbar gerichtet)之表述,法律行为中行为人意志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得以建立,而这显然也是萨维尼所要强调之点。
这一概念界定的关键之点在于,通过“直接指向”(auf...unmittelbar gerichtet)之表述,法律行为中行为人意志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得以建立,而这显然也是萨维尼所要强调之点。
萨维尼的教席继任者普赫塔继受了萨维尼关于法律行为的基本见解 ,并有所发展。表现之一是,普赫塔以更具技术性的“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概念来表述萨维尼所称“自由行为”(freye Handlungen),将其定义为“引发法律效果之行为”。
,并有所发展。表现之一是,普赫塔以更具技术性的“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概念来表述萨维尼所称“自由行为”(freye Handlungen),将其定义为“引发法律效果之行为”。 依普赫塔之见,行为效果与行为、尤其是与行为人意旨之间存在着两重关系,如果法律效果存在于行为人意旨,换言之,法律效果系基于行为人意旨而发生,则称“法律行为”。
依普赫塔之见,行为效果与行为、尤其是与行为人意旨之间存在着两重关系,如果法律效果存在于行为人意旨,换言之,法律效果系基于行为人意旨而发生,则称“法律行为”。
自此,法律行为系根据行为人意旨而发生法律效果之行为,这一观念成为德国法学的共识。典型者如:温德沙伊德(Bernhard Windscheid)认为,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类,是指向权利设立、消灭与变更的私人意思表示 ;德恩堡亦将法律行为定义为“据以设立、变更或废止法律关系之人的意思表示”
;德恩堡亦将法律行为定义为“据以设立、变更或废止法律关系之人的意思表示” ,并明确指出,“法律行为的特征在于法律效果对于意志的依附性”。
,并明确指出,“法律行为的特征在于法律效果对于意志的依附性”。
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到19世纪晚期,主流学说已牢固地将 Rechtsgeschäft 确立为法律教义学与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
法典中的 Rechtsgeschäft
法律行为理论首次实证化于法典,应属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不过,邦法所采纳的术语并非“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而是“意思表示”(Willenserklärung)。 此后,两部大型的法典,即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与1811年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均未接纳法律行为理论。
此后,两部大型的法典,即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与1811年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均未接纳法律行为理论。
“法律行为”概念作为术语进入法典,始见于1863年的《萨克森王国民法典》。该法第88条为之作有定义:“行为意志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若产生法律关系之设立、废止或变更之效果,该行为即为法律行为。” 101896年8月24日公布、19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亦采纳了“法律行为”概念,并以之为第一编第三章的章名,但未作定义。对其基本含义,负责《德国民法典》总则部分起草工作的格布哈特在其预案(Vorentwurf)理由中表示:“草案将其理解为私人意思表示,它借助私法所赋予的创造性效力,以人的意志活动而指向法律世界之改变,尤其是权利之产生、消灭或变更。法律行为的特性在于,该法律要件是一项意志行为,其中包括旨在引发法律效果之意志活动,以及使得法律要件中所欲表示的法律结构在法律世界中实现之法制话语。”
101896年8月24日公布、19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亦采纳了“法律行为”概念,并以之为第一编第三章的章名,但未作定义。对其基本含义,负责《德国民法典》总则部分起草工作的格布哈特在其预案(Vorentwurf)理由中表示:“草案将其理解为私人意思表示,它借助私法所赋予的创造性效力,以人的意志活动而指向法律世界之改变,尤其是权利之产生、消灭或变更。法律行为的特性在于,该法律要件是一项意志行为,其中包括旨在引发法律效果之意志活动,以及使得法律要件中所欲表示的法律结构在法律世界中实现之法制话语。” 第一草案“立法理由”基本采纳了上述见解:“草案中的法律行为是旨在引发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示,法律效果之所以根据法律制度而产生,是因为行为人有此欲求。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旨在引发法律效果之意志活动,以及通过承认此等意思而令欲求的法律结构在法律世界中实现之法制话语。”
第一草案“立法理由”基本采纳了上述见解:“草案中的法律行为是旨在引发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示,法律效果之所以根据法律制度而产生,是因为行为人有此欲求。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旨在引发法律效果之意志活动,以及通过承认此等意思而令欲求的法律结构在法律世界中实现之法制话语。”
后法典时期的 Rechtsgeschäft
《德国民法典》颁行之后,出现了大量以民法典为阐述对象的教科书。其中,总论教科书尤以恩内克策鲁斯(Ludwig Enneccerus)的《民法总则教科书》(从第13版开始由尼佩代[Hans Carl Nipperdey]修订出版)与冯·图尔(Andreas von Tuhr)的《德国民法总则》最具代表性。二者均上承潘德克顿法学传统,下启法律教义知识格局,卓然蔚为大家。从这两部经典教科书中可以清楚看到,法律行为概念所传达的私人意志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质,得到后法典学者的信守。
恩内克策鲁斯与尼佩代指出:“在现行私法制度与宪法之下,人们被授予广泛的权力根据自己(表达出来的)意志形成法律关系,并由此协调各自的需求与偏好。为之服务的手段,乃是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系于其上的私人意思表达——之作出。单方意思表示或与他方意思表示的结合,加之经由意志附设的其他构成要件,被承认为意欲法律效果之基础,所有这些意志行为或者另加经由意志附设的其他法律要件,我们称之为法律行为。” 在此,法律行为系私法自治手段之观念,得到清楚的表述。
在此,法律行为系私法自治手段之观念,得到清楚的表述。
冯·图尔持相似见解。他表示,“私法领域内的自由自决不妨称之为私法自治”。 而法律行为则为实现自治的手段:“个人的法律关系由各自调整乃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并因此许可当事人在广泛的范围内为自己的法律关系作出决策,这一观念构成民法的出发点。为该目的服务的,是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中最重要的类型:法律行为。因此,指向私法效果(法律关系或权利的创设、废止或变更)之私人意思表达实为法律行为构成中的本质因素。”
而法律行为则为实现自治的手段:“个人的法律关系由各自调整乃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并因此许可当事人在广泛的范围内为自己的法律关系作出决策,这一观念构成民法的出发点。为该目的服务的,是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中最重要的类型:法律行为。因此,指向私法效果(法律关系或权利的创设、废止或变更)之私人意思表达实为法律行为构成中的本质因素。”
当代德国,法律行为乃是私法自治工具之观念,依然是民法学者的普遍共识。
二、法律行为及其相邻概念
(一)概念体系
法律行为可一般性地定义为当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萨维尼以来,法律行为通常被置于法律事实(Rechtstatsachen)范畴。法律事实可三分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曰法律上的行为(Handlungen im Rechtssinne, rechtlich relevante Handlungen, juristische Handlungen)、状态(Zustände)和事件(Ereignisse)。 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可作以下进一步分类
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可作以下进一步分类 :
:

德国刑法学家与法哲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n)的这个分类舍略了公法上的合法行为与程序法上的行为,因而并不完整,仅具示例意义,但它可以清楚显示法律行为在整个行为概念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同时,较之民法学者自身的分类,它也许更能说明,法律行为概念的用法并不仅仅为民法学者所接受。
法律行为概念可在与相邻概念的比较中得到理解。上表显示,与法律行为概念相邻的,主要是事实行为与准法律行为。另外,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如散步、远眺等与法律行为判然有别,本不必多言,但其中有一类与法律行为在外观上相似、亦可能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称情谊行为。情谊行为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如何,需要专作讨论。
(二)法律行为与情谊行为
法律行为属于具有法律意义或者说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首先应与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相区分。日常生活中,不具备法律效果的交往行为有所谓的情谊行为(Gefälligkeitshandlungen),基于情谊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则可称情谊关系(Gefälligkeitsverhältnisse)。 情谊行为虽常以契约的形式出现,但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德国通说认为,因其缺乏可探知的受法律拘束之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
情谊行为虽常以契约的形式出现,但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德国通说认为,因其缺乏可探知的受法律拘束之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 情谊行为如邀请参加聚会或商定约会地点等,所谓的“君子协定”亦多属其列。
情谊行为如邀请参加聚会或商定约会地点等,所谓的“君子协定”亦多属其列。
德国法上临界情谊行为的判断
单纯的情谊行为不会进入法律评价领域。问题是当中存在一些临界行为,它们才是区分法律行为与情谊行为的真正难点。例如,相互之间结成博彩共同体,而其中一人忘记交出彩票,是否需要赔偿其他博彩人所错过的收益?行人免费指引驾车人将车倒出,却发生事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同居生活的一方未遵守服用避孕药之约定,当中是否存在违反契约义务的行为?另一方若因此对所生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是否须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此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判断情谊行为?第二,何种情况下存在情谊关系与法律关系的混合,因而可能引发法律义务?第三,情谊关系的责任如何承担?
首先,关于判断情谊行为的标准。德国通说认为,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存在受法律拘束之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这通过解释确定。原则上,判断受法律拘束的意思之有无,采客观方法,不以无法把握的行为人内心意思为断,而以交易中诚实信用的理性人之理解为标准。同时,为最大限度尊重行为人意志,在考虑客观标准时,应尽可能探知行为人的内心真意。
考察是否存在受法律拘束意思的主要依据有:第一,有偿或者无偿。有偿行为原则上可以肯定存在受法律拘束之意思。若是无偿,则有可能是情谊关系。当然,无偿亦可能形成法律关系,如赠与、借用、委任、保管等。因而,这只是考虑的因素之一。第二,进一步的考虑因素是,是否产生值得信赖的法益风险(Risiko für wertvolle anvertraute Rechtsgüter)。比如,替邻人照看小孩者,即负有对该小孩生命与健康危险的注意义务。同时,无偿行为人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这尤其表现在经济领域。因此,博彩案中,博彩人不负有法律义务。另外,若承诺受领人的自己责任明显可知,受法律拘束之意思亦欠缺,此适用于自愿为司机指引行车的情况。第三,某件事的法律或经济重要性亦具关键影响。诸如清理地窖之承诺,因其一般而言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过于微小,而只是单纯的情谊行为。相反,投资建议涉及价值重大的经济决定,若属于职业性建议,而非《德国民法典》第675条第2款(“对他人提出建议或作出推荐之人,尽管需要负担契约关系、侵权行为或其他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责任,却不负有赔偿因遵循建议或推荐而产生的损害之义务”)之情形,则须遵守具有法律拘束力之注意义务,这尤其适用于银行等投资、金融机构。第四,在某些领域,法律制度可能涉及自由决定之保障问题,尤其是宗教或伦理问题,或者原则上自由不得以法律行为进行限制的情形。此时,即便存在受法律拘束之意思,法律制度亦将对之作出限制。服用避孕药之约定为其适例。
其次,关于混合关系。存在限制性的受法律拘束之意思,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无初始给付义务之契约(Vertrag ohne primäre Leistungspflichten)。当事人无给付义务,却基于自愿而作出给付。此时,该当事人即负有特定的保护与注意义务。如,为邻居或熟人照看小孩,医生的免费治疗,或与资本投资有关的自愿咨询与建议。其二,附单方对待给付义务的契约(Vertrag mit einseitiger Gegenleistungspflicht)。若无义务之一方自愿作出给付,则另一方因此应当承担一项可诉请履行的对待给付义务。如,自愿为抛锚的汽车以燃料提供帮助者,对方有义务给付汽油花费之赔偿。与诸如赠与、借用或委任等无偿契约只存在一项主给付不同,附单方对待给付义务的契约存在两项主给付,只不过仅有一项附有义务并且可诉请履行。
最后,关于情谊关系的责任承担。若情谊关系因缺乏受法律拘束之意思而未产生契约义务(单纯的情谊行为),则可能基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发生损害赔偿。如自愿为他人指引行车方向之人,可能涉及对第823条第1款所谓法益的一般法定义务。混合关系的责任问题则复杂一些。存在限制性法律拘束意思的情谊行为能够产生准契约谨慎义务。《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尤其是第311第2款第3项(法律行为式的接触)所确立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对之有适用余地。问题在于:责任标准(Haftungsmaßstab)或更明确地说是过错标准(Verschuldensmaßstab)如何确定?一些学者认为,应类推适用民法典关于无偿契约(第521条赠与、第599条借用、第690条无偿保管,但不包括委任)仅就故意(Vorsatz)或重大过失(grobe Fahrlässigkeit)负责的规定。德国司法判例既拒绝借助类推实现责任优待之主张,又否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默示的责任排除合意(stillschweigender vereinbartener Haftungsausschluss)之假定。其中,后一举措值得赞同,因为无论如何不能径直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着排除责任的法律上的合意,但前一举措值得商榷。存在法律上契约约束的无偿法律关系(赠与、借用与无偿保管)尚且仅需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负责,情谊行为的当事人似乎没有理由承担更重的责任。因此,如果出现义务违反情形(第280条、241条第2款、311条第2款),理应享有责任优待。当然,如果某种情谊行为与委任的性质相近(如分担交通费用的情谊搭乘关系),则与委任同其对待。另外,混合的情谊关系亦可能有第823条第1款的适用余地。
(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
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Realakt, Tathandlung)均可产生法律效果,区别在于,各自法律效果如何产生。法律行为的效果根据行为人意思表示发生,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与行为人意志无关,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事实行为如无因管理(《民法通则》第93条),建造、拆除房屋(《物权法》第30条),拾得遗失物(《物权法》第109条),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物权法》第114条),创作行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第1款)等等。
既然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与行为人意志无关,行为人就不必将其意志表示于外——即便表示于外,亦不影响行为的法律效果。进而,既然事实行为非属表意行为,有关意思表示的法律规则(如行为能力、效力瑕疵等)自无适用余地。申言之,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不会因为行为人无行为能力而受影响,亦不存在无效、可撤销等问题。行为一旦实施,无论行为人意志如何,法律为之设定的效果便随之发生。
德国与台湾地区通说均以事实行为为合法行为(适法行为)的亚分类。 我国大陆许多学者则认为,事实行为未必合法,不法的侵权行为亦在其列。
我国大陆许多学者则认为,事实行为未必合法,不法的侵权行为亦在其列。 后一见解在德国亦偶有支持者,著名者如梅迪库斯(Dieter Medicus)。
后一见解在德国亦偶有支持者,著名者如梅迪库斯(Dieter Medicus)。 在法律效果直接由法律规定而不受行为人意志影响以及非属表意行为方面,建造等事实行为与侵权行为确无二致,并且,二者均不适用行为能力(Geschäftsfähigkeit)制度。就此而言,将侵权行为归入事实行为之列,似无不可。只不过,在逻辑上,不适用行为能力制度,唯表明非属法律行为而已。更进一步观察,侵权行为虽不适用行为能力制度,法律效果却受制于不法行为能力或称侵权行为能力(Deliktsfähigkeit),后者属于广义的“行为能力”(Handlungsfähigkeit);其他事实行为则与任何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均无关联。这意味着,若以侵权行为为事实行为,为将其与其他事实行为相区隔以便适用法律,就需要再作划分:与任何“行为能力”均无关的事实行为及受制于不法行为能力的事实行为。结果,合法的事实行为与不法的侵权行为仍然被区别对待。这种概念架构方式,除了能够在事实行为与侵权行为之间建立上下位阶关系,其他方面不仅未见实益,反倒使得概念体系变得杂乱。其实,虽然表面上看,事实行为的概念未包含合法性特征,但既然不适用行为能力的规则,不法行为就已经被排除在外。因为,几乎所有不法行为,均以行为人的过错能力(Verschuldensfähigkeit)为前提,而过错能力之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以行为能力为基础,例如,无行为能力亦不具有过错能力。
在法律效果直接由法律规定而不受行为人意志影响以及非属表意行为方面,建造等事实行为与侵权行为确无二致,并且,二者均不适用行为能力(Geschäftsfähigkeit)制度。就此而言,将侵权行为归入事实行为之列,似无不可。只不过,在逻辑上,不适用行为能力制度,唯表明非属法律行为而已。更进一步观察,侵权行为虽不适用行为能力制度,法律效果却受制于不法行为能力或称侵权行为能力(Deliktsfähigkeit),后者属于广义的“行为能力”(Handlungsfähigkeit);其他事实行为则与任何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均无关联。这意味着,若以侵权行为为事实行为,为将其与其他事实行为相区隔以便适用法律,就需要再作划分:与任何“行为能力”均无关的事实行为及受制于不法行为能力的事实行为。结果,合法的事实行为与不法的侵权行为仍然被区别对待。这种概念架构方式,除了能够在事实行为与侵权行为之间建立上下位阶关系,其他方面不仅未见实益,反倒使得概念体系变得杂乱。其实,虽然表面上看,事实行为的概念未包含合法性特征,但既然不适用行为能力的规则,不法行为就已经被排除在外。因为,几乎所有不法行为,均以行为人的过错能力(Verschuldensfähigkeit)为前提,而过错能力之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以行为能力为基础,例如,无行为能力亦不具有过错能力。
(四)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
准法律行为(geschäftsähnliche Handlung)可分两类:一是意思通知(Willensmitteilungen)或称意思表达(Willensäußerungen),行为人将含有特定目的之意思向相对人表达;二为事实通知(Wissensmitteilungen)或称观念通知(Vorstellungsmitteilungen)、观念表达(Vorstellungsäußerungen),行为人把附有某种法定效果的事实通知对方。
宥恕行为的法律性质
汉语通说认为,准法律行为可作三分,宥恕(Verzeihung)之感情表示(Gefühläußerungen)亦属其列。 此三分法可见诸早期德国法学著作。
此三分法可见诸早期德国法学著作。 不过,当代德国法一般已将宥恕单列于准法律行为之外。理由主要是:其一,宥恕通知并不具有决定性,关键在于是否作出可认定为宥恕之行为。此与准法律行为重在通知不同。其二,行为能力对于宥恕没有意义。一方面,宥恕行为具有高度人身性,不可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另一方面,宥恕行为之效力与行为能力无关。宥恕人不必有能力理解行为的法律效果,在事实上对于判断是否原谅对方具有足够的精神成熟程度,即为已足。不过,有关表意瑕疵(如受欺诈、胁迫等)的规定仍得准用,故宥恕亦非事实行为。
不过,当代德国法一般已将宥恕单列于准法律行为之外。理由主要是:其一,宥恕通知并不具有决定性,关键在于是否作出可认定为宥恕之行为。此与准法律行为重在通知不同。其二,行为能力对于宥恕没有意义。一方面,宥恕行为具有高度人身性,不可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另一方面,宥恕行为之效力与行为能力无关。宥恕人不必有能力理解行为的法律效果,在事实上对于判断是否原谅对方具有足够的精神成熟程度,即为已足。不过,有关表意瑕疵(如受欺诈、胁迫等)的规定仍得准用,故宥恕亦非事实行为。
有关宥恕之规定,大致存在于三种场合:其一,夫妻之间的宥恕(德国旧《婚姻法》第49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053条);其二,被继承人对继承人的宥恕(《德国民法典》第2337、2343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145条第2项);其三,赠与人对受赠人的宥恕(《德国民法典》第532条,台湾地区“民法”第416条第2项)。具体情形如下:
首先,夫妻之间的宥恕,产生离婚请求权消灭之效果。此项规定,系以离婚的过错原则(Verschuldensprinzip)为前提。 在过错原则之下,配偶一方若存在法律所列举的过错情形,另一方即取得离婚请求权。法院可依诉请直接判决离婚,不论过错方同意与否(德国旧《婚姻法》第42—48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052条第1项)。但如果请求权人对配偶表示宥恕,离婚请求权即消灭。德国1976年6月14日通过《婚姻与亲属法改革第1号法律》(Erstes Gesetz zur Reform des Ehe-und Familienrechts),离婚制度舍过错原则(Verschuldensprinzip)而改采破裂原则(Zerrüttungsprinzip)。
在过错原则之下,配偶一方若存在法律所列举的过错情形,另一方即取得离婚请求权。法院可依诉请直接判决离婚,不论过错方同意与否(德国旧《婚姻法》第42—48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052条第1项)。但如果请求权人对配偶表示宥恕,离婚请求权即消灭。德国1976年6月14日通过《婚姻与亲属法改革第1号法律》(Erstes Gesetz zur Reform des Ehe-und Familienrechts),离婚制度舍过错原则(Verschuldensprinzip)而改采破裂原则(Zerrüttungsprinzip)。 旧《婚姻法》第49条同时被废除。如今,德国法已无夫妻宥恕之规定。其次,对于实施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等行为之人,被继承人有权剥夺其继承资格或特留份(《德国民法典》第2333、2339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145条第1项)。但若被继承人表示宥恕,则权利消灭。再次,对于侵害赠与人或有重大忘恩负义行为的受赠人,赠与人有权撤回(撤销)(《德国民法典》第530条,台湾地区“民法”第416条第1项),但若赠与人表示宥恕,则撤回权(撤销权)消灭。
旧《婚姻法》第49条同时被废除。如今,德国法已无夫妻宥恕之规定。其次,对于实施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等行为之人,被继承人有权剥夺其继承资格或特留份(《德国民法典》第2333、2339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145条第1项)。但若被继承人表示宥恕,则权利消灭。再次,对于侵害赠与人或有重大忘恩负义行为的受赠人,赠与人有权撤回(撤销)(《德国民法典》第530条,台湾地区“民法”第416条第1项),但若赠与人表示宥恕,则撤回权(撤销权)消灭。
我国《婚姻法》采感情破裂的离婚原则(第32条),无宥恕之规定,并且,《婚姻法解释一》第3条规定,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据提起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若已受理,则裁定驳回起诉。忠实义务既未提供请求权基础,宥恕自然亦无意义。此外,《继承法》第7条规定继承权丧失制度,《合同法》第192与193条规定赠与人及其继承人的撤销权,但均无宥恕之规定。这表示,讨论宥恕行为之法律性质,于我国而言,仅具比较法意义。
意思通知虽含有特定目的,但法律效果并非来自于行为人的目的意思。原因在于,意思通知的目的不指向规范层面的法律效果,缺乏意思表示中的法效意思(Rechtsfolgewille),在性质上属于自然目的意思。例如,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权代理人)未征得允许而订立契约时,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合同法》第47条第2款与第48条第2款)。催告的目的是让法定代理人(或本人)对契约进行追认(自然目的意思),法律效果则是开始起算1个月的追认期。至于催告人是否意识到催告行为具有此等效果,在所不论。再如,债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催告(《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催告的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自然目的意思),法律效果则是起算法定“合理期限”,期限经过,债权人有权解除契约。
事实通知与意思通知不同。行为人所表达的,非其行为目的,而是某种事实。事实通知甚至自然目的意思尚付阙如,法效意思更是无从谈起,因而,法律效果不可能为行为人意志所确定,只能来自于法律规定。例如,要约人依《合同法》第29条所作承诺迟到之通知,所通知者,系承诺迟到之事实,法律效果则是使得迟到承诺不生承诺效力。再如,《合同法》第80条第1款之债权让与通知,所通知者,系债权已作让与之事实,法律效果则是使得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可见,准法律行为系无法效意思之表示行为,与法律行为同属表示行为,却与之不同,因为其法律效果之实现不取决于行为人意思,而为法律所直接规定。另一方面,准法律行为亦非事实行为,前者需要具备意思表达或宣告要件,后者则无此要求。
针对准法律行为的规则极少,法律适用时,需要类推与之最接近的规范。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虽为法律所直接规定,但毕竟属于表示行为,更接近法律行为,故称准“法律行为”而非准“事实行为”。因此,原则上,准法律行为类推适用的是法律行为的规范。不过,并非所有法律行为的规范均有适用余地。类推时,须作甄别:首先,准法律行为系表示行为,对其表示内容的理解能力属题中之义,所以,有关行为能力之规范,准法律行为亦须遵守。此亦准法律行为区别于事实行为的关键之点。其次,准法律行为一般针对相对人作出,因而,有关需受领意思表示的规则,如意思表示的发出与到达、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等应予准用。复次,表达内容须真实,表达行为须自由,为此,影响法律行为效力之瑕疵,如错误、欺诈、胁迫等,原则上可予类推。惟准法律行为之法律效果与行为人意志无关,故所谓的法律效果错误,不生影响。又复次,有关代理之规则,准法律行为因其属于表达行为,得予准用。最后,表达自然目的意思或通知某项事实,一般不受公序良俗评价。
准法律行为概念之检讨
王伯琦先生虽然正确地指出,法效意思之有无,系区分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之关键,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准法律行为概念有其存在之必要。其理由略谓:第一,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固然是源于法律直接规定,但法律行为其实亦是如此,“绝非由于行为人之意思”。第二,准法律行为适用关于意思表示及法律行为之规定,“作此分别,亦少实益可言”。第三,“至于在行为人心理作用上有所不同,是属心理学之研究范围,在法律科学上既无实益可言,亦无详予分析之必要也。”
管见以为,在法律适用上,由于大部分法律行为规范均得准用于准法律行为,故分立二者的实益确实不大,但若因此否认准法律行为概念之必要,则又未免走得太远。首先,法律行为效果究否为制定法所赋予,这涉及法律行为效力来源之重大法律哲学问题,此处姑且搁置不论。即便果如王先生所言,亦不表示,法效意思对于准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具有同等的意义。在准法律行为中,行为人将其意思指向法律效果既非必要、亦不具有决定地位,此与意思表示截然不同。 因而,可能影响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错误,对于准法律行为无足轻重。这一区别,虽然意义未必如何深远,但总不至于可予完全忽略。其次,准法律行为虽可类推适用法律行为规范,但在何种情况下具有可类推性,并非无需甄别。此已为上文所述。最后,法学研究行为人心理,与心理学不同。前者关注规范效力,后者则属事实观察。正因为如此,属于事实层面的自然目的意思对于法律效果之确定才不生影响。唯有指向法律效果的法效意思,始得进入规范视域。因而,法学与心理学未必相互排斥。
因而,可能影响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错误,对于准法律行为无足轻重。这一区别,虽然意义未必如何深远,但总不至于可予完全忽略。其次,准法律行为虽可类推适用法律行为规范,但在何种情况下具有可类推性,并非无需甄别。此已为上文所述。最后,法学研究行为人心理,与心理学不同。前者关注规范效力,后者则属事实观察。正因为如此,属于事实层面的自然目的意思对于法律效果之确定才不生影响。唯有指向法律效果的法效意思,始得进入规范视域。因而,法学与心理学未必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