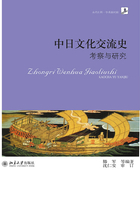
第三节 金印的证言——汉光武帝册封倭奴国
两汉时期是中国的农耕文明向日本大量传播并在日本获得大面积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与日本新兴的诸多部落、小国开始通交并向其册封的起始时期,还是中国正史正式记载日本历史的起始时期。
在两汉的这大约400年中,日本经历了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时代在中国大陆先进文明的影响下,由采集狩猎经济较快地转型为以稻米耕作为主的农耕经济,农业生产物资得到了积累,开始出现简单的物资交易。
弥生时代的日本,原始社会逐渐瓦解,陆续出现的一些部落、小国开始积极地向中国朝廷贡献,以期在部落小国间的争斗倾轧过程中取得正名的强势,并从中国学得更多的先进文明。在此情势下,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早期的册封关系就形成了。
而本节将主要论述的“金印”就是记录两汉时期中日往来的最强史证。但在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金印以前,中国通过朝鲜半岛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日本的过程。
《汉书》(写于1世纪)中留下了记述日本的十九个字: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十九个字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出现的。在《汉书·地理志》里,对秦王朝所设的103郡分别进行了记述,在其之后,又按“分野” 进行了综述。在叙述玄菟、乐浪之后,在其最后才勉强添写了上述的十九个字。从这十九个字的记载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三个问题:(1)倭人的百余个国家,当时没被划入汉的势力范围;(2)有了乐浪(公元前108)以后,中国人才对倭有了初步的认识;(3)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尚浅,班固写不出十九个字以外的有关日本的情况。但是比起徐福时,即秦时人们对日本的那种神仙三岛式的渺茫的想象来说要具体得多。
进行了综述。在叙述玄菟、乐浪之后,在其最后才勉强添写了上述的十九个字。从这十九个字的记载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三个问题:(1)倭人的百余个国家,当时没被划入汉的势力范围;(2)有了乐浪(公元前108)以后,中国人才对倭有了初步的认识;(3)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尚浅,班固写不出十九个字以外的有关日本的情况。但是比起徐福时,即秦时人们对日本的那种神仙三岛式的渺茫的想象来说要具体得多。
《汉书》十九个字中的“乐浪”处于朝鲜半岛的北部,为当时中日往来的中继站。显然,对于乐浪以及当时朝鲜半岛局势的解读是搞清《汉书》十九个字之历史背景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秦以前,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属燕的势力范畴。燕国派卫满在此经营。因其驻地较偏僻,自由度较大。秦灭燕,建立辽东郡,但辽东郡的势力范围不大,只划到了丹东。卫满盘踞在辽东郡的外侧而皮毛未伤,不仅如此,卫满还在平壤修建了王险城,大有稳坐泰山之势。其间,不少内地流民移居至卫满的领地。卫满收留难民,扩充势力。进入西汉很久了,王险城的势力犹存,如果卫满的孙子卫右渠能对汉武帝顺柔一些的话,很有可能长期保持政权,但他迟迟不给汉武帝上贡,并阻碍朝鲜半岛上的东南地区的小国上贡给汉武帝,这当然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终于下令征伐卫右渠。汉军分水陆进攻朝鲜半岛,很快获胜。

图17 汉朝时的朝鲜半岛地图
同年,汉在半岛设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其后,三郡统归乐浪。直至公元313年乐浪为高句丽所灭为止,乐浪郡共存在了421年。在这一时期,许多汉人、汉官便来到乐浪。乐浪成为了朝鲜半岛上中国大陆文化的大本营,同时也是离日本最近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宣传窗口。在当时的乐浪有许多日本人,他们把乐浪的文化传到日本。中国大陆的朝廷也通过乐浪逐渐认识了日本。
1935年,日本考古工作者对乐浪郡遗址进行过发掘。其址位于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的台地上,东西约长700米,南北约长600米。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历年采集所得的有砖瓦、封泥、陶器和铜铁器等。还发现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字样的瓦当。乐浪郡遗址的南面有一乐浪墓群,有墓葬2000座以上,已发掘50余座。各墓出土的带铭文的漆器达57件,多数的有纪年,其代表性发掘成果是从乐浪郡太守掾王光之墓中出土的“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的木章、画有30个汉人物的漆匣子、写有“蜀郡西工官”字样的漆器耳杯等。这些出土遗物都证明了乐浪郡属当时汉中央政府的管辖地并与中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乐浪郡存在的422年中,乐浪汉政权为日本弥生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量的中国大陆信息。它在向日本展示中国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承担着向汉朝廷提供日本列岛信息的任务。《汉书》中记载的“以岁时来献见云”之事,据考也是由乐浪郡来代收一些日本小国的贡物,然后再转送给汉中央政权的。
西汉灭亡后,王莽建立新政。王莽信奉五行说,当他向周围各国炫耀新政权时也不例外,由他派往东方的使节身着绿色服装,马匹也用绿色装扮。其使节到过乐浪、玄菟、高句丽、夫余。使节们的任务是收回西汉王朝的封印,而重发王莽新朝的封印,但王莽对周围国家比较苛刻,把许多“王”降成了“侯”,把“玺”降成了“章”,由此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又加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的蜂拥而起,像乐浪郡这样的偏僻势力便获得了相对的独立状态。公元25年,刘秀建东汉,公元41年派祭彤为辽东郡太守。辽东郡离中央政府较近,自古易于控制,所以,汉光武帝便指示祭彤来镇守半岛。祭彤做太守30年,成绩斐然,他不仅有行政能力,而且在军事上也很能干,文武双全。《后汉书·东夷传》说他“辽东太守祭彤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其中便有倭的朝献。以下是光武帝时的辽东及半岛的周边国家对东汉归属的确切情况和先后顺序。

图18 乐浪墓群出土的画有30个汉人物的漆匣子
公元32年,高句丽朝贡,刘秀恢复了其王号。
公元44年,韩人来乐浪,申请内属。
公元49年,乌桓要求内属。
公元49年,夫余国朝献。
公元54年,鲜卑人朝献。
公元57年1月,倭奴国王奉献。
公元57年2月,光武帝驾崩。
由以上来看,公元57年日本九州的奴国到洛阳朝贡,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的。位于现福冈地区的奴国之所以率先向中国朝贡,是因为它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佐贺地区离半岛最近,能最先捕捉到半岛的政治气氛。其实,光武帝让祭彤来治理半岛,并未期待相隔以海的日本如何如何,奴国的朝贡尽管出于他本身的政治需要,但对临近迟暮之年的光武帝来说毕竟是额外的惊喜,这对他的对外成果而言可谓是锦上添花。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奴国使者在洛阳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并被授以金印紫绶。就此,《后汉书·东夷传》中有如下的记载: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那么奴国出使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据《后汉书》记载,当时日本仍有三十多个小国相互征伐,而谁能更多地持有从中国传来的青铜器、武器、农具乃至生产技术的话,谁就能形成更大的势力,如果能直接受到中国的册封的话,其政治上的地位就更高了。于是,奴国便走出了这一步棋。步奴国其后,有许多日本小国前来中国朝贡。据《后汉书》记载还有面土国等。但为什么只给了奴国金印,这是与奴国最先来朝并且和光武帝当时处于临终前的时机有关。在这以前,日本的朝贡均是交到乐浪为止,再由乐浪统一送到中央。而奴国的直接朝贡使中日文化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开始了持续到隋以前的册封受封,开始了日本与中国的直接的交流(当然大部分还是通过朝鲜半岛)。
1784年,在古地名为佐贺、现地名为福冈的志贺岛村,两位为甚兵卫打工的农民在一个靠近海边的水田里修整自家的水渠,他挖到一块两人才能合抱的大石头。因石头挡住了他家的水渠,他把石头搬了起来,在石头下面,发现了一块金光闪闪的东西。甚兵卫把它洗净,交给了在福冈米店里打工的哥哥喜兵卫。又通过米店老板请当地著名汉学家龟井南冥鉴定。由龟井南冥初步断定为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金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目,自1784年发现之时起,有关这方金印的真伪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首先是关于金印的外形及质地的讨论。据日本通产省计量研究所在1966年6月所做的实测结果:印面是“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分成三行排列,汉隶白文。印面正方形,每边长约2.347厘米,由于埋在地下时间过长,可能发生磨损等变化,所以每边长度并不一致,稍有参差。印钮蛇形(或称为虺形),体盘屈;头有双目,反顾向后;尾左旋,下有横通小孔,供挂绶之用;钮高1.312厘米,长2.142厘米,宽1.274厘米。印体连钮,即金印总高2.236厘米,重108.729克,比重17.94。虽不是纯金,但含金量极高,约在95%。

图19 志贺岛出土的金印
根据汉制,赐诸侯王的印,大不逾寸。此金印每边长2.34厘米,正符合东汉初铜尺的一寸。就尺寸来说,此印应是真品,但就金印的蛇形钮一直存有异议,龟井南冥早在受到黑田藩主委托他作鉴定的时候就指出:蛇钮稍异于汉制。因依汉制,皇帝赐给列侯的印是金印龟钮,赐给蛮夷的印是铜印蛇、虺、驼、兔钮。金印配蛇钮是违背汉制的。
1956年,在中国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汉墓群的6号古墓中出土了一方刻有“滇王之印”的西汉的蛇钮金印,因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南,所以赐了蛇钮印。尽管蛇的形态和日本出土金印的蛇钮不同,但其为蛇则是同样的。由此可以证明,汉时规定赐给蛮夷的印用铜,但也有用金的,是随情况而异的,这也许表示了汉光武帝对倭的重视,或表现了其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一些学者还对金印上的“王”字的写法提出了异议。此金印上的“王”字的三横为等间距。在古代,等间距的“王”字是“玉”字。1981年,扬州市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二号墓发掘出了一方刻有“廣陵王璽”的龟钮金印。据考,此金印是公元58年赐给广陵王的,其下赐年份比“漢委奴国王”印仅晚一年,并且两印同出一个位于洛阳的制印作坊。两印的外形,特别是尺寸、印座、字型极为相似,宛如一对兄弟印。其“廣陵王”的“王”字的三横也取相同等间距排列。此印的出土,打消了人们对“王”字的疑惑,同时,有关“漢委奴国王”这方金印的真伪讨论也落下了帷幕。1987年”,漢委奴国王”印与“廣陵王璽”印在福冈市博物馆同柜展出。
竹内实 还发现“漢委奴国王”印上铭刻的“漢”字右下角是个独立的“火”字,而一般所见“漢”字的右半是连写的。在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中,没有发现相同的写法,而上海博物馆藏的“漢匈奴破虏长”“漢归义氐陌长”印上的“漢”字右半部的中间也是隔断的,使得“火”字独立出现在印章上。竹内实分析道:这是因为汉代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代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元素组成,即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说是水德,有时说是火德。但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汉光武帝占领洛阳后,曾讨厌“洛”字的三点水,令改为“雒”。“雒”字的右半通雉鸟,具有火性。
还发现“漢委奴国王”印上铭刻的“漢”字右下角是个独立的“火”字,而一般所见“漢”字的右半是连写的。在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中,没有发现相同的写法,而上海博物馆藏的“漢匈奴破虏长”“漢归义氐陌长”印上的“漢”字右半部的中间也是隔断的,使得“火”字独立出现在印章上。竹内实分析道:这是因为汉代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代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元素组成,即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说是水德,有时说是火德。但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汉光武帝占领洛阳后,曾讨厌“洛”字的三点水,令改为“雒”。“雒”字的右半通雉鸟,具有火性。

图20 “漢委奴国王”印与“廣陵王璽”印的比较
其次是关于印文内容的讨论。金印上的五个字,应如何解释呢?印文第一个字的“汉”字是没有问题的,表示接受这个印章的国家是臣属于汉的。第二个字的“委”字,在中国的古文中与“倭”相通,从字形上很快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第三个字的“奴”字是单指一个国即“倭”属下的“奴国”呢,还是与上面的“倭”字连起来作“倭奴”,指一个国家呢,于是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
龟井南冥主张倭奴国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称谓。汪向荣赞同这一观点并就此有详尽的论述:“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来称臣纳贡的‘国家’,必然就是这一地区有代表性的,所以有赐印之举,以示政权上加以支持。……金印上的‘汉委奴国’,绝难解释为臣属于汉帝国的倭国治下的奴国。如是的话,汉王朝为什么不把更高的印赐给其王国的倭国呢?……或者说,当时汉帝国的中央政府和日本列岛相距较远,往来也不多,可能因此不了解而误授,可是作为其派出在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不可能不了解。汉王朝为了表示对周围民族国家的德化,在事前不会不郑重考虑的。很难相信会把一个相当于诸侯王玺的金印,赐给一个臣属于本身就不大的倭国所统治的小国。只有当倭奴国和邪马台国一样,是日本列岛某一地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时,才符合事实。……实际上,从范晔的叙述来看,倭奴国和倭国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词。倭奴国是个政治学的名词,而倭国却是地理上的名词,倭国是代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日本列岛,倭奴国的地理位置在日本的极南面。”
而以三宅米吉 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把金印的印文内容读成“汉之倭之奴国王”,认为奴国之上还有一个“倭国”的存在。其主要理由在于:
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把金印的印文内容读成“汉之倭之奴国王”,认为奴国之上还有一个“倭国”的存在。其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在《三国志·魏志》中有关于奴国的记载。其中言:“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据研究表明,奴国就在现福冈的附近,即离金印出土地点东南22公里处的春日市的须玖冈本遗迹、比惠遗迹、那珂遗迹一带。据对以上三个遗迹的调查表明:奴国是一个自绳纹时代晚期至弥生时代前期的大国,是在日本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区内有超过20个的聚落遗迹及数百个瓮棺遗迹、生产铜器、铁器、玻璃质地勾玉的作坊遗址、青铜器范100个以上。区内还发现有250多个水井及木棺土坑墓多个,还发现了一个具有完整石室的王墓。据当时奴国拥有的生产力来看,奴国是有能力向汉朝进贡并与周边势力进行抗衡的。虽然如此,奴国只有2万余人口,比起有7万户人口的邪马台国来说,仍然是小国,所以,奴国是作为以邪马台国为盟主的联合国家——“倭国”中的一个小国而存在的。而奴国的使者在公元1世纪经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往返4000公里,步行至东汉的首都洛阳朝贡,谒见了汉光武帝。对于其率先朝贡的突出贡献,汉光武帝慷慨地赐予了上述金印。

图21 奴国位置图
其二,《后汉书》中指出:倭奴国在倭国的极南界。虽然可能是由于古代的中国人把地理位置搞错了,但中国人认为奴国在一个地域的“极南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这对于以中原为重的古代中国人来说,是不会把其当作一个代表性大国的。
其三,金印的授予与奴国出使贡献的时机有关。奴国出使贡献是在公元57年的1月,正值东汉的开朝皇帝刘秀(前6—后57)临终的前一个月。刘秀自31岁称帝建东汉以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减免赋税、徭役,多次下诏释放及禁止残害奴婢,发展农业生产。在刘秀的统治期间,社会生产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史称“光武中兴”。而四周小国纷纷来朝贡献。一些可从陆路来往的小国早就来朝贡献了,而唯有史称“蓬莱仙国”的日本列岛一直没有来朝贡者,这对于临终前的汉光武帝来说,恐怕有些遗憾。而奴国使者的突然出现使汉光武帝感到分外之喜。虽然客观上说,“金印”对于奴国来说规格过高,但是这可能是汉光武帝出于装扮自己的内外政绩之完美无缺的主观需要。目前,三宅米吉的论点在中日史学界占主流位置。
再次,是关于埋藏方式和地点的讨论。被称为中日史上最大的文化遗产的金印,其被保存的方式却过于简陋,当甚兵卫把它拾起时,金印的周围没有任何陪葬品(比如,一些管玉、铜剑、铜镜等),似乎也没有任何包装,其四周只有一个小型石室的构件,中间塞满了淤泥。而被埋藏的地点也是人烟稀少的荒岛的陡坡上。
1973年,九州大学对金印出土地的周围进行了发掘,没能发掘出任何可能与金印相关联的史迹和遗物。1985年,福冈教育局又对金印出土的附近进行了发掘,结果发现在离地表1.2米的地层有水田遗址的痕迹,就此仅可证明甚兵卫的水田确实存在过而已,而没有出土其他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一方宝贵的金印会被埋藏在志贺岛呢?其主要的见解如下:
其一,亡国埋藏说。中山平次郎认为,2世纪以后,日本列岛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列岛生产力的中心由九州地区移至本州岛的近畿地区,出现了由卑弥呼女王统治的强大的邪马台国,奴国在争斗中被彻底兼并,奴国王被逐出奴国,流落至志贺岛,其国王只得把象征权力和汉帝国支持的金印临时地、隐蔽地埋藏起来。
其二,祭器保存说。森贞次郎认为,在北九州一带,弥生时代有将祭器埋藏在山坡上的习俗。即在有祭礼时从山坡上取出来用,用完后埋在村落附近的山坡上。至今九州一带已发现有祭祀用铜剑、铜铎的上述埋藏遗迹。金印虽小,但可用于祭礼的功能是不变的,甚至更大。但当上述祭器保存的习俗改变之后,金印就被人们忘记在了志贺岛的山坡上。
其三,设施破坏说。西谷正认为,在金印的周围,本来有相应的埋藏设施,如牢固的石室、石棺等,只是由于被海水侵蚀洗劫,或由于16世纪日本为抗击外来侵略者挖炮台所致,埋藏设施遭到彻底破坏而已。
除上述三种见解外,还有人认为金印埋在志贺岛上是为了祈祷航海安全;金印是同奴国王埋葬在一起的;金印是和志贺岛上的海人集团的首领埋葬在一起的等等。总之,关于金印的埋藏方式和地点的讨论至今没有定论。疑点重重,更增加了金印的文物价值。
1981年,金印正式被认定为日本国宝,保存于福冈市博物馆,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之源的象征。
实地考察金印公园
志贺岛位于博多湾的出口处,明治维新以前是一个孤岛,其后因砂石淤积,与陆地之间有了一个陆桥。从福冈市中心乘公交车行驶1小时,或从博多湾坐市营的联运船只需45分钟即可到达志贺岛。志贺岛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3.5公里,面积约6平方公里,环岛一周约9.5公里,岛上最高处海拔约167米,常住人口约3000余人。因于1784年2月23日发掘出汉光武帝赐给奴国的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而成为中日友好的溯源之地。
岛上有金印公园。其前立有一个高5米左右的石碑。此碑为1922年立,上写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地”11个阴刻大字。不用“发掘”而用“发光”二字,可见人们对出土金印的敬仰之情。石碑旁有“金印公园”的木牌,牌文强调此地为金印出土之地。沿石阶攀上半山腰就是金印公园了。金印公园是于1973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由福冈市观光局建造而成的。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金印外形的石雕,只见在一个方形的斜面的石台上刻有金印的印文:“汉委奴国王”五个字。游人在观赏此石雕时,须面向西方,即面向洛阳的方向,以示对约两千年前汉光武帝赐印的感激之情。

图22 2009年北京大学日本历史文化考察团考察金印公园
再向上攀一组石阶便到了“方位广场”,广场的地面是一幅东亚地图,标志着奴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地面上写有“离洛阳1600公里,离广州2020公里”等。再向北走,见一块草坪,立有两块石碑,一为杨尚昆1980年所书:“带水横陈两市相望友谊永恒”,是为广州市与福冈市缔结城市友好条约而作。另一为郭沫若诗碑,上面刻有郭沫若1956年访日时所作诗一首:
战后频传友谊歌,
北京声浪倒银河。
海山云雾崇朝集,
市井霓虹入夜多。
怀旧幸坚交似石,
逢人但见笑生窝。
此来收获将何似,
永不重操室内戈。

图23 金印石雕
郭沫若先生早年曾留学于九州大学医学系,在福冈度过了他的青春时代。1975年,福冈的有识之士们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周年,将郭沫若的这首和平之诗镌刻于金印公园,以激励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来到志贺岛,在与专家、村民们的实际采访中才知道一些有关金印的真情。其实,现场发现金印的不是甚兵卫,而是给甚兵卫打工的秀治、喜平二位农民。但将此事上报时用的是甚兵卫的名义,其后便误传成是甚兵卫发现的。关于金印的第一个鉴定人龟井南冥也有几番故事。就在金印被发掘的1784年2月福冈藩同时开办了两个藩立学馆,一个叫修猷馆,由世袭官儒的传人竹田定良担任馆长;一个叫做甘棠馆,由民间的儒学者龟井南冥担任馆长。龟井南冥上任后的第四天,金印就出土了,其后不久便领命参加鉴定工作。龟井发挥了渊博的汉学知识,撰写了《金印辩》的论文,一开始就指出了金印为汉光武帝所赐之物;而同时领命参与鉴定的修猷馆竹田定良馆长等五位教授所提交的《金印议》论文,竟把金印说成是1185年平氏一族西逃时所携带的宝物之一。金印在平氏一族于澶之浦自尽后随海流飘散至数百里之外的志贺岛,后被村民埋藏在山冈。这种缺少中日交流史常识的主观推测成为了后世的笑柄。在金印被发掘的18世纪后半叶,日本已感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国家意识开始膨胀。当金印出土后,一些国粹主义者不愿看到自己的皇朝祖先曾为汉的属国之历史事实,强烈指责金印是惑众乱世的妖物,主张用火熔掉,铸成刀鞘上的金属饰件。在紧急关头,龟井南冥挺身而出,写信给甚兵卫愿以十两黄金买进,但甚兵卫没有回信。于是,龟井南冥再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甚兵卫看到金印有如此高的价值,便放弃了熔掉的念头。最后金印被当地藩主黑田出百金若干获得。正是在龟井南冥的英勇的保护之下,金印才得以保存至今。

图24 龟井南冥像
如今,这方金印被保存在福冈市博物馆二层最显著的位置。在一位专任警卫24小时的看护下,金印静静地睡在精致的透明柜子里,它闪闪发光,仍不失两千年前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