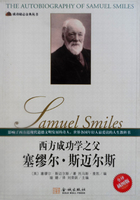
第7章 行医哈丁顿
1833年——哈丁顿的医生们
“我们应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父母为我做的一件事就是给予我良好的教育。这胜过给我一笔财富。然而,我该怎样利用它呢?这就是我,一个不满二十岁,已经结业的外科医生所面临的问题。我太年轻了,还无法开创自己的事业。如果我开创了这个事业,谁又来照顾我的生意呢?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呢。
不幸的是,那时的外科医生对民众来说是供过于求。欧洲正处于和平时期。军队并没有招募医生,而是解雇了许多医生;在哈丁顿,情况也是这样,经验丰富的军医跟当地的从业者争抢着折半的薪资。海军人数也在减少;由于改良的需要,似乎还会大幅裁员。欧洲不再会有战争了。有的医生去了印度,但我却无法在那里找到立足之地,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此外,我是母亲最可靠的助手,她希望我能在家里呆上一些年头,最后我答应了她。
1833年,我去格雷谢尔斯拜访了亲戚,并寻找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我找到一个老同学,他的生意刚刚开张。他说,“如果你来了,我就只好走人啦!”由于他还是首次找到立足之地,我也就踏上了归途。途中,我经过了阿伯特斯福德,我还是第一次去那儿。这一年是瓦尔特爵士去世的第二年,人们看上去很悲伤、很沉默。我还去考登·诺斯农场拜访了亲戚叶娄利斯一家,他们盛情地接待了我。接着,我经过劳德回了家,几年前那里曾发生了一场暴乱。
可我不能无所事事呀。布朗市长(市政改革法案下的第一任市长)、文法学校的书记戴维先生请我为学员们上化学课。这是一种愉快的职业。我把夏季的大量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我写了十二篇演讲稿——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稿子。我享有使用学校精密仪器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使听众有了进步,我只知道,自己倒是在化学、热学、电学和流电学的实际知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从前的老师约翰斯通先生,隔一天会来上数学和自然地理学课,而阿基巴尔德先生则上矿物学和地质学课。他们也在教区学校上这些课,来听课的人也非常多。白天,教区学校是孩子们的教室,晚上便成了成年人的教室——利用公共建筑造福于各阶层人民,这种方法颇为正确。
我最终决定在哈丁顿安顿下来,在这里实践医术——至少暂时如此。我并没有对出人头地抱有多大希望,因为镇上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口不多,流动性不大,而且我是八个从业者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些从业者包括一父一子两个豪登斯大夫,他们已出道很久了;罗里默大夫和克鲁伊克夏克大夫,我曾受雇于前者;布莱克大夫,一位退休军医;伯顿大夫;安德森大夫;最后是我自己,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不过,我还是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主要是为穷人治病。
1833年——天生的绅士
乡村医生的生活,尽管变化多端,却又单调乏味。约翰·布朗大夫曾在他的散文里,巧妙地把这一职业称为“我们的风尘仆仆的犹太勇士。”在讲这句话之前,他先引用了曾当过乡村医生的马高·帕克的话“我宁愿回非洲,也不愿再留在皮布尔斯郡当医生了”。医生必须对每一个人有求必应,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无论是远还是近,无论有偿无偿都得出诊。就我来说,无偿服务占了多数——跟所有年轻的乡村医生一样。不过,我遇到了许多善良的人,有农场工人,也有农民。当我为农民们看病的时候,他们总是很愿意款待我,还为我倒上一杯威士忌。这些耗费我大量精力的下层阶级人民,是很值得钦佩的。一位游历过多处的女士对我说,“东洛锡安的农民没有什么特点,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那些农民一样。”不,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是没什么特点,可他们在教区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还有敏锐的判断力——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智慧,比任何特点都更实用。苏格兰低地人民勇敢、节俭、勤奋,有点儿沉默寡言,却也顽固、好争辩——有点儿一意孤行、毫不妥协意味。
我就认识这样一些睿智明达的人,这是宝贵经验累积的结果——尽管他们每周的收入不超过10先令,他们也会从微薄的收入里挤出一部分供孩子上学。但是,当他们遭受病痛的折磨时,留给医生的治病钱也就所剩无几了。他们颇为知足,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也相当满足,并设法充分利用它们。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人,才是富有的人:因为聪明人都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得上皇帝。好在“善”并不专属于某个特殊阶级,因此,我曾在被称之为“穷人”的人们中间,发现了一些最善良、最有礼貌的人。
穷人们明白,尽管他不能做一位英雄,但总可以做一个“人”——“人”毕竟才是最真实的。这不在于穿的衣服好不好,而在于衣服里跳动的那颗心好不好。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绅士,拥有着人类的优良品质,还把它们表现了出来,而这种人随处可见。我曾看见他们在家庭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时,陷入了悲伤和痛苦,却从没看见他们做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乞求别人的怜悯。
我就不必把乡村医生的生活悉数道来了。我工作的作息时间十分不规则,有时两三个晚上不能睡觉,有时却没多少事情做。如何运用我的业余时间呢?我开始学法语,买来法语书自学。埃米·马丁和德热兰多的著作都是我最喜欢的。前者在妇女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方面为我灌输了新观点,后来我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观点。我有许多娱乐方式:学音乐、练小提琴、加入了四重奏乐团,甚至还能进行慈善义演了。我还继续学习绘画,开始画油画和水彩画了。此外,我还着手准备生理学和健康状况的一系列讲座,为它们画上插图,就象我的老导师——爱丁堡的弗莱彻那样。这些准备工作不仅充实了我的时间,还带给我许多乐趣。我在郡法院大厅做了大约十五次演讲,每次都有很多人来听。
1833年——塞缪尔·布朗
我有许多好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汤姆·托德里克[25],他是一位十分亲切、诚挚、理智的小伙子。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块儿。我们一起读伦敦的《调查者》,当时正值这份刊物的黄金期,编辑是阿尔巴尼·冯布兰克;我们还读了《每月记事》,其主要撰稿人有福克斯、萨拉·弗劳尔·亚当斯、索斯伍德·史密斯大夫和勒曼·格里姆斯通太太。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诗歌,特别是雪莱和济慈[26]的作品。后来我又迷上了柯尔雷基[27]和沃兹沃斯[28]的作品,因为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它特别的吸引力。我想,境界最高的,当属莎士比亚的作品。由此可见,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时间。
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塞缪尔·布朗。尽管他是个冲动任性的年轻人,却也十分能干、健谈,后来成为一名令人佩服演讲者。人们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可不知为什么他却误入了“歧途”。在研究自己所精通的化学之时,他产生了有关原子和身体组成元素的新观点,为了研究这个课题,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象他自己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
第一步,就是英雄的一步。我不得不在黑暗中,孤独地迈出这一步;只有能够承担过去一切的人,才能迈出这一步;那些循规蹈矩、不堪一击的人,是不可能迈出这一步的。
这封信能让大家对此人的本质有所了解。当他还在爱丁堡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以下这封信:
人们在某一天总结出来的理论,只能表明他们在那一天了解了什么,而随着认知的发展,理论只是流淌的泉水。理论就象帝国一样,会消亡,会被人们遗忘。而昨天被人们嘲讽的谬论,在今天和明天也会受到嘲讽!难道我们还要带着这种可悲的疑惑,继续摸索下去吗?难道我们不该总结出最终的原则和真理吗?难道不该找到能让时间停止的花岗岩吗?难道没有任何办法能探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要找的宝藏吗?在那时,我们才能因为得到了永恒的真理而欢欣鼓舞,而不用担心某个更“权威”的怪物说:“你们在做什么?”不!有一个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数学求证法。只有符合数学绝对逻辑性的科学,才是完善的科学。天文学、静力学、水力学和声学等科学都是完善的,因为它们是数学化的。举例来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确知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有关大自然奇妙炼金术的最终无误的法则,除非我们能够数学化地求证化学问题。我们有成功的希望吗?有!你和我都将看到粒子科学得到完善的那一天!各种物质都是从一个基本原子里释放出来的——目前经过确认的55种元素都是同质异构化合物,都属于这个基本原子,它们按一个等差级数递增;每个元素的吸引力是由它们的体积比率决定的,我们以后就会知道这个比率,而且——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吗?不!这会让你痛心,也会让我痛心。如果我能如愿完成这项研究,那将会为人类科学的各个领域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啊!这将涉及到多么重要玄学问题啊!……我坚信,只有当粒子科学得到完善的时候,玄学才能得到大规模的普及。
我把这段冗长的文字从塞缪尔·布朗的信中摘录下来,是因为它能表明他的人生梦想,而这个梦想把他的一生都给毁了。不过,他的梦想也许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科学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管怎样,如果他是对的,他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后来,在哈丁顿的化学实验室里,塞缪尔·布朗竭力地跟我解释他的观点,当时他已能使用技术学校的设备了——我曾对它们十分熟悉;但我始终对他的理论不感兴趣。据他所说,他发现了一种能增加碘的体积的办法,即把淀粉转化成碘,这可以通过对反应结果的称量来证明。但我始终也没有看到事实的证据所在。不久后,满怀着对“发现”的憧憬,他把这个课题带进了法拉第[29]这位权威人士的视野,而法拉第始终没有对此涉足太深。尽管那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异想天开式的课题,但他对此的所持的态度却是谦逊的。他本来可以对这个提问者毫不在意或者不屑一顾的,不过,他还是回了如下这封善意的信给他:
我毫不犹豫地建议你为支持你的观点做实验,因为,不管你是证实了它们,还是驳倒了它们,你的实验结果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对于这些观点的本身,除了说它们有利于激发探究真理的精神以外,我也就无可奉告了。对实验科学的进步稍稍思考一下,你就会明白,你的观点对预见性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障碍。长期以来,我对有关吸引力和物质的粒子和原子的理论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在实验辅助下,我越思考,就越觉得物质的粒子和原子没有什么区别。
从法拉第那里再也得不到什么了。但塞缪尔·布朗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他和爱德华·福布斯携手,在爱丁堡哲学协会会员面前,就“科学哲理”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讲。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因为大家都敬佩他。当时,爱丁堡大学化学系正好缺一位教授,于是这位年轻的演讲家就成为了一名候选人。毫无疑问,他本该当选的,因为他的宗教政治支持者在学校董事会里占了多数席位。但他那些关于原子和物质可变性的荒唐的、不科学的观点(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却遭到了嘲笑。然而,他太正直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这样,他烧了自己的船,炸了自己的桥,断了自己的后路。他打算带着这些观点去找李比希[30]——当时人们公认的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想让它们得到他的关注。于是,他去了吉森[31],见到了李比希,而他们的谈话内容就不为人所知了。不过,结果是不圆满的,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最后,选举在爱丁堡大学举行,由于塞缪尔·布朗的引退,另一个人被任命为教授。
他仍然决心要揭开自然的秘密。后来,一位跟布朗合作的年轻化学家告诉我,他俩一起在伦敦附近的布莱克黑兹找到了房子,并在那儿展开了一系列精密的研究。为了一心一意、坚忍不拔地投入工作,他们达成了协议:把一半的头发剃掉,以戒除俗念。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征服自然。
下一次我发现他的踪迹,是他发表在《顺势疗法医学》上的妙文“微剂量”,看来这种新疗法引起了他的兴趣。后来,他在《北方评论》上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他暂时离开了科学的老路,至少他没有继续走下去。对于塞缪尔·布朗,他的堂兄约翰·布朗大夫如是说:
对他来说,他的翅膀太沉重了。他永远都在攀登科学上的西奈山[32]和毗斯迦山[33],他要跟上帝对话——他始终在黑暗中、在危险中孤独地攀登,如果他运气好的话,他或许能破解时间之谜,发现“希望之乡”……他的命运悲哀而另类,但他明白这一点,在完全知道结局的情况下,他对命运发起了挑战。
在塞缪尔·布朗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几乎没有痊愈的希望。他前往德贝郡(在那里尝试催眠术),然后去了伦敦,最后回到了爱丁堡。在他去世前,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我曾在《伦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父亲这位流动图书馆创始人的文章,而他希望得到一份这一期的杂志。他说他病了,是致命的病,但他希望在临死前为父亲尽点儿孝道。于是,我后来发表了一篇他父亲的传记。可怜的布朗死在了39岁上。无论是在他小时候,还是长大成人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但是,他太过聪明绝顶了——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冲动——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他的许多定论下得太过草率了。然而,他的堂兄约翰·布朗大夫却对他和他的理论做了如下评价:
我们当中有人也许能活着看到早逝的塞缪尔·布朗坟墓边刻满了“我将再起”的誓言,看到人们对这位在黑暗中沉睡的人表示感激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