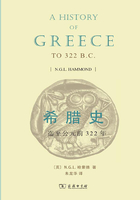
中译本序
对于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民说来,西方的希腊文明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参照对象。希腊开创了西方文明的传统,虽然它在两千年前就已衰亡,可是它树立的古典楷模却延续至今,所以西方有识之士仍然总是“言必称希腊”。如果说在从古到今的东方文明中我们中国不愧为擎天巨柱,那么古典希腊在西方文明中可被公认为一条辉煌夺目的红线。正因为如此,当国人初次接触西方之时,古希腊始终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热点”,无怪乎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便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于1604—1608年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为中文,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徐光启对这部古希腊著作中包含的科学性光彩很是佩服。他一方面肯定“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一方面又展望未来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 可以说,他在明末之际已模糊地预感到希腊开创的西方文明中的某些科学性的精华(我国“五四”时代热烈欢迎的“赛先生”),正是中国未来之所必需。这个第一例也形象地表明,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希腊文明最杰出之处,就是它在那么遥远的古代便为未来的近代西方孕育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这也可说是最为吸引我们的“希腊文明之谜”吧!
可以说,他在明末之际已模糊地预感到希腊开创的西方文明中的某些科学性的精华(我国“五四”时代热烈欢迎的“赛先生”),正是中国未来之所必需。这个第一例也形象地表明,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希腊文明最杰出之处,就是它在那么遥远的古代便为未来的近代西方孕育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这也可说是最为吸引我们的“希腊文明之谜”吧!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看,这个“希腊文明之谜”却不难解开,因为它无论如何神奇,终归是人类文明发展总过程的一部分。随着历史科学(包括考古学)的进展,我们逐渐对希腊历史的远古部分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而这一部分正是过去人们了解得很不够,从而加深了希腊之谜的浓雾的部分;另一方面,同样也是通过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我们逐渐对包括希腊在内的古代世界和古代社会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也了解了希腊和走在它之前的各个古代东方文明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异同;与此同时,本来比较丰富(当然只是相比于其他古国而言,若用现代要求看则仍很不够)的希腊古代文献,于今也可用新的科学和史学眼光加以诠释、比较、订正和分析。总而言之,对希腊历史与文明的比较全面、比较科学的新的了解和综合,现在已有可能了。如果说20世纪初的口号主要是“重新改写希腊史”,那么到20世纪中叶这一改写已落实到一些杰出的著述中,本书——哈蒙德的《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便可被以为是其中之一。
N.G.L.哈蒙德(Hammond)是英国著名的希腊史研究家,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相继担任两部英国最重要的古典史学巨著——《牛津古典辞书》和新版《剑桥古代史》的主编,就充分说明了他在希腊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他还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请,写了这部长达70多万言的《希腊史》。本书初版于1959年、1967年出了第二版,以后多次重印,受到广泛欢迎,被公认为20世纪希腊通史著述的重要成果之一。哈蒙德此书所以成功,除了文笔精练清丽,不失古典风范而外,更重要的是他能综合融汇上述各方面史学考古研究的进展于一炉,既立足于希腊又放眼于整个地中海文明,既充分重视考古研究又全面利用了古代文献,考据精确而又眼界开阔,从而能把希腊历史从远古到公元前322年的长期发展较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史学界出现的新趋势是走向新的综合。各种对立的学派和观点取长补短、互为促进固是一种综合,考古新证与传统史料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也是一种综合,史实校订和规律探索并行不悖、异曲同工更是一种综合……但归根结底,这种新的综合的大势无非是历史科学本身的进展已达到万流归宗的地步,即归结于对历史事实本身的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理解。若说哈蒙德此书反映了较新的史学研究的水平,也是指其具备了这种综合与理解而言。因此他这部书受到各国和各方面史学界的欢迎,也受到东西方学术界的欢迎。由于对希腊古史的实际有较全面的理解,书中不少论点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希腊历史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有些见解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发展必然是由无阶级、无国家的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国家的文明社会,而第一个文明社会,受当时尚属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必然是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无论东西方皆无例外,也为一切古代文明的历史所证实。希腊文明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这是希腊人自己所承认、也为一切研究希腊史的学者首肯的。问题在于,希腊文明如何能在奴隶制这种最落后、也最野蛮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精华的古典传统。奴隶社会居然还有民主!对这个似乎荒谬的现象如果细加剖析,不难看出它也有其合乎规律性的一面,其中最具关键意义的是以下两个因素:希腊文明在地中海各古代文明,亦即通常所谓的古代东方文明中最为晚出,因而东方给它准备了较丰厚的文化遗产:铁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字母拼音文字、东部地中海的国际贸易市场等,希腊人甫从原始社会而出,便有这些现成的东西供其拿来使用,自不难创出后起之秀的业绩;另一方面,希腊在作为古代东方三千年文明发展的继承者的同时,它又有直接从原始社会蜕变而来的特殊背景,原始社会最后阶段的军事民主制和氏族部落组织仍有相当影响。当然,我们不能说希腊的民主是从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发展而来,因为希腊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在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之时总是军事首领变成国王,希腊各邦最初都有国王统治,然后又历经贵族统治,只是在平民群众(公民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之后,才逐渐废除贵族特权而建立了奴隶制的民主政治。就这一点说,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只能是为希腊走向民主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如各邦皆存在公民大会,选举风习亦未断绝等),而民主政治本身则是希腊社会内部斗争的产物;同时还要看到斗争之激烈也无非是希腊在接受东方遗产条件下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的一个反映。由此可见,包括民主在内的希腊文明的优异之点,只能看作是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是东方文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直接的军事民主制背景,两者交叉纠结、酝酿升华,从而促成希腊之腾飞。一部好的希腊史,应该对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复杂、辩证关系有所交待,哈蒙德此书可算一个佳例。虽然作者恪守叙事为主的古典史学传统,但他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他已充分掌握的古史文献,对希腊文明形成之际的情况做了较全面的介绍。本书第一卷介绍的“远古诸文明”(主要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是19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为希腊古史增添的新篇章,但这些远古的或早期的文明虽在希腊土地上出现,犹未能遭逢上述复杂而辩证的历史机遇:它们是青铜时代的文明而犹未进入铁器时代,发展比较有限(在希腊全境只能说是在几个点上有所发展),缓慢的从新石器到文明的历程产生了和东方类似的较强大的王权(王宫是这些早期文明遗址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便说明这一点,日后的希腊则无王宫),如此等等,可见由考古发现而为我们所知的这些早期文明不仅使希腊古史提前一两千年,也反衬出我们所说的希腊文明产生的条件有其具体的历史机遇,因而较早出现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都走上了类似东方文明的道路,未反映出希腊本色。此后,在迈锡尼文明衰微之际侵入希腊并导致这一文明覆亡的新的一批移民,以及由这些移民引起的本地居民的大迁移,才彻底改变了希腊历史的布局。这些移民的主体——多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才是未来创造希腊文明的真正的希腊人。在这个移民大浪潮席卷而至时,希腊各地一度进入了黑暗时代,国家覆亡、城市毁灭、文字消失、商旅断绝,可是在这一片“黑暗”中却孕育着新的希腊文明的胚胎。这些移民犹未建立国家,仍生活于军事民主制之下,却使用着得自东方的炼铁术制造的武器与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大移民浪潮及它所促成的黑暗时代却为我们上面所说的希腊文明产生的历史机遇开辟了道路,其作用不可小视。哈蒙德在本书第一卷中以专章论述大移民,可谓慧眼独具。他着重指出了移民使用铁器和过着部落生活的特点,从而为此后出现的新的希腊城邦勾画出一幅确切而具体的历史背景。本书第二卷“希腊的复兴”便是详述新的希腊城邦如何在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既没有忽略东方的影响和商业的发展,也充分注意到各城邦之间、多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之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巨大差异,但在共同的历史机遇之下,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都或多或少地具备我们所说的希腊城邦的四大历史特点 :小国寡民而始终保持独立、奴隶制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民主政治或公民政治的建立、古典文化的繁荣。本书第三卷“希腊的凯旋”就以希腊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为主题,进一步描述了希腊如何凭靠其独具一格的城邦体制而走向光辉的顶点:伴随着反抗波斯的军事胜利,是雅典奴隶制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希腊文明多方面的前无古人的成就,以至于恩格斯说:“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
:小国寡民而始终保持独立、奴隶制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民主政治或公民政治的建立、古典文化的繁荣。本书第三卷“希腊的凯旋”就以希腊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为主题,进一步描述了希腊如何凭靠其独具一格的城邦体制而走向光辉的顶点:伴随着反抗波斯的军事胜利,是雅典奴隶制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希腊文明多方面的前无古人的成就,以至于恩格斯说:“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
了解希腊尤以取得优异成就的历史条件,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希腊特殊化”的结论,恰好相反,作为古代奴隶社会的一员,希腊仍始终受制于奴隶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如果说希腊城邦体制的形成得力于其特殊的历史机遇,那么城邦的衰落却正是奴隶制发展的共同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为什么庆祝希腊凯旋的欢呼声犹未消失,两个最大的兄弟之邦雅典与斯巴达便展开了“自我毁灭”的大战,接着便是连绵近百年的城邦危机?这另一个希腊文明之谜同样也应从奴隶社会的规律性发展求其解答。我们认为,古代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小国、大国及至帝国。 其始必然是小国,因为奴隶社会是由无国家的原始社会发展而来;而奴隶制经济的成长则要求其国家规模必然由小到大,最后建立广土众民的帝国,到帝国阶段,奴隶社会也就达其繁荣的高峰。这一规律不仅显而易见,并具必然与普遍意义,东西方奴隶社会虽各有其特点,无不在此共同规律作用下达其高峰。希腊城邦体制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它以小国寡民的规模而达到了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如果把希腊放在地中海文明发展的总格局中看,那么它便是在东方已多次出现帝国之后受东方遗产之赐而得天独厚的,并无悖于这一规律。更有甚者,奴隶制繁荣之时必有帝国这一点却反过来制约了城邦本身的发展,因此城邦盛极而衰,很快由凯旋进入危机,而希腊历史日后的总趋势是建立霸权和帝国。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看到的不是希腊人建立的帝国,而是其邻族马其顿人建立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各个希腊化王国。哈蒙德在本书中虽然不会明确提及奴隶制的规律性发展之类的话题,但他在本书后半部分(第四卷至第六卷)却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发展的内容,看到了希波战争之后百余年间的希腊史实质上是城邦体制已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堕入危机的历史。然而,城邦的危机又是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以,这时期政治上虽然动荡,经济和文化仍然高涨。哈蒙德也充分认识到这种辩证发展关系,断言称这时为衰落完全不符实际,“希腊文明像过去一样浩荡奔流。这是一个在政治、哲学、文学和艺术上大胆试验的时期。”(第五卷第一章第一节)其实,通常所谓的希腊文明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此时完成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斯提尼都生活于其间,更烘托出城邦危机与奴隶制经济繁荣之间的反差与对照。由于实际上已意识到我们所说的这种规律性发展所起的核心作用,哈蒙德对这后半部分的希腊史的描述也是相当出色的,尽管头绪纷繁,细节充盈,却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动乱之中有创新、迷惑之中有解放的五彩缤纷的画面,同前半部的昂扬上进共同组成希腊古史动人心弦的篇章。与之相伴的是,他对亚历山大建立帝国的成就也能从历史必然的角度给予正确的评价,虽然难免多少带有从西方看世界的偏见。
其始必然是小国,因为奴隶社会是由无国家的原始社会发展而来;而奴隶制经济的成长则要求其国家规模必然由小到大,最后建立广土众民的帝国,到帝国阶段,奴隶社会也就达其繁荣的高峰。这一规律不仅显而易见,并具必然与普遍意义,东西方奴隶社会虽各有其特点,无不在此共同规律作用下达其高峰。希腊城邦体制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它以小国寡民的规模而达到了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如果把希腊放在地中海文明发展的总格局中看,那么它便是在东方已多次出现帝国之后受东方遗产之赐而得天独厚的,并无悖于这一规律。更有甚者,奴隶制繁荣之时必有帝国这一点却反过来制约了城邦本身的发展,因此城邦盛极而衰,很快由凯旋进入危机,而希腊历史日后的总趋势是建立霸权和帝国。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看到的不是希腊人建立的帝国,而是其邻族马其顿人建立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各个希腊化王国。哈蒙德在本书中虽然不会明确提及奴隶制的规律性发展之类的话题,但他在本书后半部分(第四卷至第六卷)却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发展的内容,看到了希波战争之后百余年间的希腊史实质上是城邦体制已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堕入危机的历史。然而,城邦的危机又是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以,这时期政治上虽然动荡,经济和文化仍然高涨。哈蒙德也充分认识到这种辩证发展关系,断言称这时为衰落完全不符实际,“希腊文明像过去一样浩荡奔流。这是一个在政治、哲学、文学和艺术上大胆试验的时期。”(第五卷第一章第一节)其实,通常所谓的希腊文明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此时完成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斯提尼都生活于其间,更烘托出城邦危机与奴隶制经济繁荣之间的反差与对照。由于实际上已意识到我们所说的这种规律性发展所起的核心作用,哈蒙德对这后半部分的希腊史的描述也是相当出色的,尽管头绪纷繁,细节充盈,却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动乱之中有创新、迷惑之中有解放的五彩缤纷的画面,同前半部的昂扬上进共同组成希腊古史动人心弦的篇章。与之相伴的是,他对亚历山大建立帝国的成就也能从历史必然的角度给予正确的评价,虽然难免多少带有从西方看世界的偏见。
本书的另一优点,对我们说来也是特别有用的,便是它对有关文献史料的征引相当完备。哈蒙德曾以充分考核史料为本书写作宗旨,他在这方面用功的勤苦、学力的深厚素为国际史学界推崇,而深入之后能浅出、繁博之上见简明,却又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因此,凡某一史实于古典文献有征之处,无论多寡他都详予罗列,但这些征引出处又不等于直接引文,只是提供读者做进一步探讨研究之用,因此提到的文献虽与史实有关,却不一定观点一致,多种出处彼此之间也有差异甚至矛盾之处(为了保持行文的简洁,哈蒙德对注释出处一律用简称,我们翻译时为保持原文风格也做了相应处理,这方面问题较多,下面另附专文详加说明)。哈蒙德觉得这样一来可引起读者去检索古籍、接触原始资料的兴趣,他的这个希望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说来应更富有启发性。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古籍的了解仍非常有限,哈蒙德此书比较丰富的古籍出处征引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就有“按图索骥”的功效,岂不是特别有用么?虽然对古籍旁征博引并非评价史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哈蒙德此书重视古籍的倾向却不失为新史学的综合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面,也是我国有关研究亟待加强的一面。
我国世界史学界的老前辈齐思和、周一良、吴于廑、胡钟达先生对本书的翻译工作十分关怀。译文初稿是在“文革”期间抽空完成的,当时依据的英文本是1959年的初版。后来,我们看到了1967年的再版和1977年的重印本,发现第一卷的第一、二章有较大改动,因当时我正在美国讲学,遂请郝际陶同志据新版改译了第一章第一节的前数页和第二章第一节以及附录2—8,并对大部分译稿做了初步校阅。后来,经林志纯先生协助,又请程庆昺同志对全书译稿再校一遍,最后由我定稿。由于我们都忙于其他工作,此书译、校竟拖延20余年之久,深感成事之不易。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对本书的翻译工作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译稿将难以完工,在此谨向编辑部有关同志致以深挚的感谢。尽管时间拖了很长,最后定稿仍感仓促,疏漏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朱龙华
癸酉清明于北大畅春园